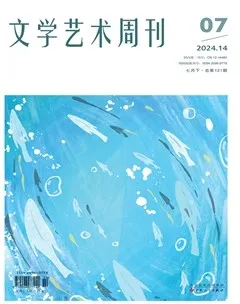浅析贾平凹小说《河山传》中的生态美学意蕴
《河山传》是贾平凹创作的城市题材小说,讲述了农民工洗河和企业家罗山四十多年里的传奇故事。作者详细描绘了两个小人物在工业化进程中展现出来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展现了对生态美学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本文结合前代美学家的生态美学思想,从自然本真的生态美景、“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和精神世界的生态问题三方面分析贾平凹小说《河山传》中的生态美学意蕴,并对其在生 态文明中的尴尬处境进行讨论,以期更深入地理解贾平凹的生态美学观和作品中蕴含的生态美学价值。
一、自然本真的生态美景
生态美学家认为,“自然在其本真存在的意义上就是原始本真的自然生态美”。贾平凹对自然美景的书写符合生态美学的这一观点,他笔下的自然风光,秉承着古朴自然的风格。《河山传》中的主人公罗山与好友兰久奎一同去秦岭打猎,进山先看见的是圭峰,“一座莲花状的山包上,草木葱郁”,圭峰上没有树,也没有路,“沿着峰下的祥峪进去,就是从西往东的河,河里不见流水,白花花的都是沙”。贾平凹在作品中描写自然美景时,只是简单地 平铺直叙,以一种白描的手法,用寥寥数笔勾勒出风景的美感。这样的描述,简洁又不失诗意,让读者仿佛同书中人一起置身于秦岭山水之间,感受到一片自然的宁静与和谐,展现出一种不经任何处理的天然形成的自然之美。
罗山一行人打猎至双鼓坳,发现此处“南面梁上有瀑布,瀑布下聚着水潭,水从潭里溢流出来,凡浸漫的地方生了蒲草。时阳光普照,水汽氤氲,有幻影就反映在鼓崖上”。双鼓坳的自然景观没有受到人为破坏,保持着原始状态,呈现出一种天然和谐的整体感。这种和谐不仅体现在土梁、瀑布与幻影的相互映衬中,也体现在自然景观与生命力的相互融合中。作者对秦岭美景的描绘,不仅是对自然景观的赞 美,更表达了内心对和谐生态的向往。
二、“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
曾繁仁认为生态美学有两个支点,一个是来自西方的现象学,“另一个是中国古代的以‘天人合一’为标志的中国传统生命论哲学与美学”。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许多文人在作品中都表达出了“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这种生态书写偏重于展示人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一面,偏重于展示人融合于大自然后的愉悦体验,可以称为生态抒情”。贾平凹也是如此,他小说中的人与自然也展现出了和谐统一的状态,传达了作家独特的美学追求。
《河山传》中,借划分土地这件事,作者为我们刻画了一幅“天人合一”的生态美景。文丑良对划分土地这件事颇有微词,他说:“就那么些土地么,收上来,分下去,再收上来再分下去。”但村里人对于分到的土地还是很重视, “所有的人家都在院门墙上修个龛,敬上了土地神”。这说明他们并不奢望有太多 的物质享受,仅仅希望能守住这方土地即可,因为有了土地,他们就有了生存的希望,他们坚信只要努力耕种,就能获得好收成。后来, “洗河家的屋里挖了地窖,仅仅是红薯,储了两千斤,不仅蒸吃煮吃,还切片晒干磨粉,摊煎饼,炸丸子,压饴饹,吊起粉条”。村民因土地而满怀希望,土地因村民而满怀生机,在这种相互作用下,人与自然达到了一种和谐的状态。
这种人与自然的互惠共生体现了贾平凹“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作者借此表达了对人与自然和谐生态关系的推崇,并鼓励读者在现实生活中追求和谐,共同构建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
三、精神世界的生态问题
作为“后工业文明”的产物,生态美理论本身就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超越)。贾平凹的作品紧紧把握了生态美学思想,在《带灯》中,他进一步深化了自己的生态观念,他指出是商业文明的快速发展激发了人内心的贪欲,滋生了利己主义,这使得现代人的精神生态发生了变异。
《河山传》继承并发展了《带灯》的生态观念,罗山在建立自己商业帝国时,通过贿赂和钱权交易获得更多利益。为了生意往来,罗山在秦岭修建的别墅,逐渐演变为阿谀奉承的法外之地。罗山还声称“啥时候都是钱走在前头,人走在后头”。他用金钱来衡量生命,他用金钱来疏通关系、发展事业,还用金钱挑战法律。这种金钱至上的心理正是工业文明进程中人类精神异化的表现。
工业文明虽然给人类带来丰美的物质享受,但无限膨胀的欲望又将人带入破坏和谐关系的悖论,使人陷入“自掘坟墓”的险境。罗山为了建一座全城最高的楼,不惜转让自己的 运输队。但在路上他发生了意外,被一位跳楼的女子砸死。如果罗山能保持清醒,节制欲望,探求和谐的生态关系,也许就不会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河山传》中,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与自然的联系,精神世界变得扭曲和变异,人的本真之美也随之丧失,贾平凹在作品中抒发了对城市文明的厌恶。面对别墅修建中意外死去的工人伯父的质问,洗河回答:“你儿子死了是毒,没给你五十万一百万是毒,人活着都是毒。”由此看出,即使是洗河这种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对城市文明也有一种厌恶和反感。贾平凹更是借助这些比喻表达出对城市文明堕落、城市居民精神变异的悲愤。
四、贾平凹对生态文明的关注和反思
刘杨认为,贾平凹的乡土小说既站在农民的立场, “较为真实地展现农民的生活细节与情感世界”,又“努力借助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反思农民无法察觉或无从表达的问题”。贾平凹在《河山传》中也结合使用了这两种意识,表达了对生态文明的深刻关注和反思。
(一)新农民的困境
在贾平凹的意识里,他只是一个居住在城市里的农民,他在《河山传》的后记中写道:“因出生于乡下,就关心着从乡下到城市的农民工,这种关心竟然几十年了,才明白自己还不是城市人,最起码不纯粹。”这种意识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
在《河山传》中,贾平凹用洗河的故事展现了新农民在城市生态文明中的尴尬处境。虽然洗河身处城市,但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身上还保留着农民习性。洗河住进高档酒店之后,“几次想抬脚要把鞋印踩在那头的贴了壁纸的墙上,开窗时猛地用力去扳把手,想让把手断裂”,洗河享受着现代城市社会的便利,却又无法完全融入其中。他只得用这种破坏行为,表达对城市文明的抗拒。
贾平凹本人也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一步步从商州走向西安。他作品中新农民在现代都市中的困境,也是自身生活经历的外 化。“说到根子上,咱还有小农经济思想。从根子上咱还是农民。虽然你到了城市,竭力想摆脱农民意识,但打下的烙印怎么也抹不去。”
这种新农民的困境更多体现在心理层面,虽然他们已经远离了农村生活,具有了一定的现代意识,但他们又难以彻底摆脱固有的农民思维。所以,这些新农民处于一个既城市又乡村,非城市又非乡村的尴尬境地,这种矛盾和冲突,实际上也反映了工业化进程中农民身份认同的复杂性。贾平凹对这种新农民形象的刻 画,不仅丰富了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也为读者理解城乡关系和农民身份的转变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知识分子的无力
作为一个文人,贾平凹借《河山传》中的知识分子文丑良之口,对农民自身没有觉察到的一些现象进行了反思。身为崖底村少有的知识分子,文丑良的写作事业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文丑良直言已经对农村题材的作品感到迷茫, “新兴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惨烈地争斗、对抗、厮杀,人性之恶全都出来,生活是了一堆垃圾”。
身处于这种怪诞的生态环境中,文丑良也开始向现实妥协。在洗河的帮助下,文丑良被调到了西安市近郊的一所小学里工作。后来,文丑良写的一篇关于农民工的文章被呈红发表在了公众号上,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呈红他们还在网上推波助澜,爆出文丑良的各种照片,编写文丑良的“黑历史”。面对被破 坏的生态环境,文丑良由最初的批判一步步走向妥协,再到最后深陷舆论之中,饱受非议。文丑良的经历深刻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工业化浪潮中的尴尬处境,这种处境也是贾平凹自身经历的真实写照,“《河山传》的角色如此,我也如此”。
面对城市的生态文明,新农民和知识分子都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贾平凹不仅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反思,还在书中传达出一种对未来发展的忧虑和期待。“这样写行吗?这是我早晨醒来最多的自问。如果五十年,甚至 百年后还有人读,他们会怎么读,读得懂还是读不懂,能理解能会心还是看作笑话,视为废 物呢?”贾平凹的这种担忧,实际上是对社会、文化、道德等多个层面的深刻思考。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引导读者进行反思,思考如何在 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和维护好社会生态环境。这种思考不仅仅是对生态环境的关注,更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刻思考。
五、结语
生态美学思想主张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关系。在《河山传》中,贾平凹批判了工业文明下爆发的各种生态问题,表达了对“天人合一”生态观念的追寻,对自然生态的深切呼唤,启示我们面对浮躁的社会环境时,应该努力营造和谐有序的生态关系。同时,作品也流露出了贾平凹作为文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关怀,这也是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可以在当代文坛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谢富康,男,汉族,陕西汉中人,景德镇陶瓷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