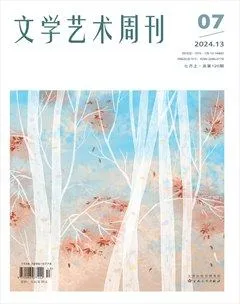浅析嵇康《声无哀乐论》中的音乐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持续动荡与不安定 的时期,社会政治环境则如同翻涌的潮水,复 杂多变,随着儒家权威地位的松动,文化艺术 领域及其审美观念在思想解放的氛围中迎来了 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
这样一种思想解放的浓郁氛围,为嵇康、 阮籍等文人提供了独特的思考空间,艺术不再 是政治和宗教的附属,他们深入探索音乐韵 律、艺术真谛乃至人生哲理。他们得以挣脱束 缚,畅所欲言,畅谈各自对音乐、艺术及人生 的独到见解。他们不仅以非凡的才情和特立独 行的生活态度,成为后世文人追求独立精神与 高尚情操的典范,更在深层次上,对中国的思 想文化、艺术创造乃至民族心灵的塑造,产生 了深远且不可磨灭的影响。
嵇康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竹林七 贤”的精神领袖。
嵇康的音乐见解有着明显的反礼教色彩, 他否认儒家音乐理论,不认可音乐的政治伦理 性质,他把音乐看作是天地间的自然自在之 物,认为它有善恶之分,却不含有爱憎哀乐等 情感。嵇康在这一时期写下《声无哀乐论》, 是其针对当时音乐理论界普遍存在的将音乐 简单等同于政治教化工具的观点,提出的一种 全新的音乐美学思想。《声无哀乐论》是一部 具有深远影响的音乐美学著作,在《声无哀乐 论》中,嵇康主要涉及三个大的方面:音乐本 体论、音乐审美、音乐功能。
一、音乐的本质探索
在《声无哀乐论》中,嵇康将音乐的本质 置于核心地位,致力于揭示音乐的属性和内涵。 《声无哀乐论》开篇即借秦客之口——秦客即 与嵇康观点不同的俗儒化身——表明儒家关于 音乐本质的思想: “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 音哀以思。夫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故哀思 之情,表于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也。” 在传统儒家音乐观中,人们认为通过音乐这种 独特语言,统治者能洞悉民情,因为不同的情 感和社会景象,会通过不同的乐器(如打击乐 传达哀伤,弦乐、管乐传达和平景象)和不同 的音乐风格来展现,因此音乐被视为治国理政 的重要辅助工具。
嵇康反对儒家将音乐视为政教工具的观 点,批判儒家音乐观,认为音乐不应该承受过 多的政治和道德功能。“夫天地合德,万物贵 生。”这是嵇康对音乐本质的见解, “天地合 德”强调天地之间的和谐共生与协同运作,为 万物的起源与繁衍提供了基础条件,和谐状态 是万物生存的根本。这种宇宙观深深影响嵇康 的音乐思想,他认为音乐如同天地自然现象一 样,音乐的本质为“自然之和”。
嵇康认为音乐是“自然之和”的产物,音 乐的本质在于其内部的和谐统一。他认为形而 上的音乐属于“和域”,这种和谐不仅仅体现在音乐的基本要素上,即旋律、音色、节奏 等,更体现在音乐与宇宙、自然、人心的共鸣 上。
“和域”在音乐中表示一种直入人心的升 华的和谐境界,人的喜怒哀乐,无论什么样的 情绪都能被“和乐”激发出来,并且得到释放, 这种表现是自然的,是和谐的。听众在听音乐 时能感受到这种和之美,与音乐产生共鸣。
二、音乐审美的新视角
嵇康认为没有哀乐之分,虽然音乐种类 繁多,但离不开音乐的基本要素,如音调、旋 律、节奏、音响等,正因为有这些音乐要素的 组织排列,音乐才会美,这种美是客观的,是 自然的,与人的情感和意志无关。但“声无哀 乐”的观点,并非否认音乐能引发人的情感反 应,而是强调音乐本质无固有哀乐或其他属 性。嵇康主张,音乐为独立于主观意识之外的 客观音响现象,音乐之所以能够触动人心,引 起人们心中哀乐的情绪,是因为人们心中本来 就有哀乐,只是被音乐引发出来,也就是说音 乐能够激发人的情感,但这种激发并非音乐本 身所固有,而是人们根据自身的经历和心境, 对音乐进行的主观解读和感受,音乐只是发挥 媒介作用。这种区分音乐与情感的观点,主张 将音乐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来欣赏和体 验,这体现了嵇康对音乐审美独立性的重视。
嵇康还强调音乐的形式美。对于具体可感 的音乐,嵇康强调“和”, “和声之感人心, 亦犹酒醴之发人情也”,这句话展现了音乐形 式中所蕴含的美学魅力和嵇康对音乐形式美的 体会。和声是音乐中各种要素(音高、音色、 节奏等)相互协调、相互融合的结果,它创造 出一种和谐、统一的美感。他认同音乐有多种 变化元素,但也脱不开其根本——音乐的和谐 之美,所谓“五味虽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嵇康认为音乐的魅力在于 其内部结构的精妙协调与对外在宇宙自然法则 的呼应。在他看来,无论音乐如何千变万化, 其核心始终是一种纯粹而自然的和谐状态。他 倡导,唯有那些遵循自然规律、展现和谐之韵 的音乐,方能被视为艺术之精品。这一观点不 仅彰显了嵇康对音乐审美标准的独到见解,也 体现了其对音乐本质美的不懈追求。
三、音乐功能的多元解读
剖析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时,我们不难 发现其对音乐社会功能的独到见解,尤为强调 的是音乐在塑造社会风尚与道德秩序方面的潜 在力量。
在《声无哀乐论》中,秦客与东野主人的 第八次答难中,秦客继续坚持音乐能够引发哀 乐之情的观点,而东野主人(即嵇康本人)进 一步阐述其音乐教育思想,提出“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深入探讨了音乐与情感关系的本 质和音乐的社会功能。“古之王者,承天理 物……玄化潜通,天人交泰。”古代圣明的君 主,会顺应天理治理国家,使得教化在无形中 发挥作用,天与人和谐交融。又提到“播之以 八音,感之以太和,导其神气,养而就之”。 可用八音、太和作为引导,潜移默化影响人们 的气质精神,塑造民众的精神风貌,以此培养 民众。[1] 嵇康将音乐视为一种通过和谐音韵来 潜移默化地熏陶人心、促进个体心灵和谐与宁 静、引导人们精神气质的媒介。他认为,当个 体的内心世界趋于平和与和谐时,这种内在的 平和将逐渐外化为社会风气的改善,进而推动 社会向更加稳定与繁荣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 社会整体的和谐与太平。这一过程,实质上是音乐以其蕴含的道德与美学价值,在无形中塑 造人们的情感倾向与行为举动,从而实现对社 会风气的积极影响与引导。
[1] 出自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 上海教育出版 社 2011 年出版。
嵇康认为,音乐具有娱乐功能, “宫商集 比,声音克谐,此人心之至愿,情欲之所钟”, 当各种音调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时,能够触动人 们内心最深处的愿望和情感,使人们在欣赏音 乐的过程中得到快感和美感。[1] 音乐能够给人 带来愉悦和享受,滋养和满足个人情感。
嵇康在文中虽没有直接谈论音乐的养生功 能,但阐述了音乐能够满足人的审美需求,使 人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获得愉悦和放松。这种 娱乐与美感作用有助于缓解人的压力,调节人 的情绪,从而达到养生的效果。嵇康强调音乐 的“和”,而音乐对情感有调节作用,音乐的 和谐性能够引发人心中的平和宁静,有独特的 养生作用。
四、音乐教育思想的革新
本文认为,上述音乐功能方面的阐述,也 算是嵇康的音乐教育思想。
嵇康认为音乐之所以具备移风易俗、教 化人心之效能,其根本驱动力是“心”,而非 对外在刺激的被动接受。这一观点相较于传统 上仅将音乐视为被动接受对象的观念,具有显 著的革新意义,它强调了受教者主体性的重要 性,强调个体对音乐的独立感知与理解,这一 理念映射到教育领域,即鼓励学习者摆脱传统 被动接受的角色,要成为知识探索与技能习得 的主动参与者。激发受教育者的内在动力,培 养其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教育才能真正 实现其培养全面发展个体的目标。
因此,嵇康的音乐思想不仅是对音乐本质的洞察诠释,更是对教育本质的一次有力呼唤, 为后世的教育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与指导。 它启示我们,在当今教育实践中教师应更加注 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我们可以创设开放性的 学习环境,采取切实有效的教学策略,引导受 教育者主动探究,深度思考,积极实践,培育 其自信心和独立思考能力,帮助其掌握有效的 学习方法,增长主体的实践能力和本领,在教 育过程中激发并最大化地利用学习者的主动性 与内在潜能,以使我们的教育目的获得更大程 度的实现,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1] 出自石天然《嵇康音乐思想之研究》, 中国艺术研 究院 2016 年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五、结语
通过对嵇康《声无哀乐论》的剖析,我们 深刻地感受到其音乐思想所蕴含的革新力量与 深远影响。其音乐思想不仅是对魏晋时期音乐 美学理论的一次重大革新,更是对中国古代音 乐哲学思想的深刻反思与显著超越。嵇康以其 独到且深邃的见解,为我们揭示了音乐艺术的 本质核心及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嵇康提出的“声 无哀乐”论断,强调了音乐作为一种独立艺术 形式的客观性与自主性。他认为音乐的魅力源 自其内在的和谐与节奏之美,而非其所能引发 的特定情感或道德教化作用。这一观点不仅为 音乐艺术赢得了独立的地位,更为我们探索和 理解音乐的本质内涵开辟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 间。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以其独特的魅力, 深深影响了中国音乐学术发展,为后世的音乐 研究提供启示与借鉴。嵇康的音乐思想内涵与 价值值得我们挖掘,进而为推动中国音乐艺术、 艺术教育的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与力量。
[ 作者简介 ] 赵珮宏,女,汉族,湖南永州人, 就职于桂林信息科技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 艺术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