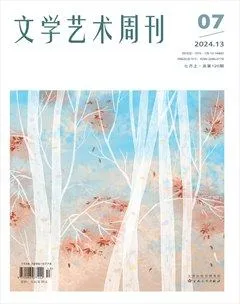一诗舞成
袁行霈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泰斗 级人物,将最初的研究方向定在中国诗歌艺术 的研究上,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古代文学批评 与文学史拆分研究现状的驱动。袁行霈的《中 国诗歌艺术研究》在对中国古代诗词进行深入 分析的同时,也为当代诗歌的创作提供了有益 的借鉴。《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分为上、下两 编,上编着眼于中国诗歌艺术理论,着重论述 了言、意、象、境等中国传统美学概念。《中 国诗歌艺术研究》在总结中国诗歌艺术经验的 基础上,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广泛的采撷, 力求在对中国诗词艺术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对 体系性的理解进行系统的架构。下编的内容属 于中国诗歌艺术史的范围,论述了屈原、陶渊 明、谢灵运等十三位诗人的艺术特点、风格、 成就等方面的内容,并将他们的创作置于当时 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观察,着眼于他们的艺术个 性,并对他们的创作进行深入的探讨。
“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1] ,该书开篇 就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多义性进行了论述。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到,能指(符号 本身)与所指(符号指称对象)本身并不具有 逻辑性、必然性的关联,而仅仅是约定俗成的 产物,因此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这种观点仿 佛为以语言符号为基础组建起的诗歌的多义性 提供可能,因为某个词语与我们熟知的词语指 称并不固定,因此诗人可以在诗词的世界中建 构出属于自己的语言模式。
[1] 出自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八,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出版。
但是正如袁行霈所认为的那样,诗能借多 义之词,以成多义之效,但诗人既要借词本身 的种种意义抒情状物,又要带动文字,用艺术 的方式构成意象和意境。这便进入罗兰 · 巴特 的“二级符号系统”当中去了。在《神话学》 中,罗兰 · 巴特认为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的对 应关系只是一级符号系统,文化尚未进入这个 符号系统。一级符号系统也可以作为一个能指, 指的是特定的社会文化意义。当前代诗人将某种符号纳入“二级符号系统”冠以特定的文化 内涵之后,便成为“典故”,为后代诗人表 达相同意蕴时使用。这被袁行霈称作中国古典 诗歌的“情韵义”“象征义”。如“今夜偏知 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中的“绿窗”,不 仅指称绿色的窗纱,更多的是指温暖的家庭气 氛、闺阁气氛; “凭栏”既指倚杆而望,又可 表示怀远、吊古、悲愤等情绪; “菊花”更是 在众多诗词中衍生出丰富的意蕴,有屈原“夕 餐秋菊之落英”的高尚,有陶渊明“悠然见南 山”的归隐,孟浩然“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 花”使菊花成为秋天的象征,杜甫“丛菊两开 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使菊花有了悠悠岁 月之感,晚唐黄巢一句“满城尽带黄金甲”菊 花又有了冲天的杀气,明代“梅兰竹菊”以君 子形象出现,菊花又有了更多的含义……正如 袁行霈所言“语言是意象的外壳”,诗人的意 象借助辞藻固定下来,读者则需要运用联想和 想象把这些辞藻还原为生动的意象,进而体会 诗人的情感。
诗歌与乐舞是两种仿佛毫不相关的艺术 门类,但中国古代的“乐”既有歌唱,又有 乐器,既有咏叹,又有舞蹈。汉赋作家傅毅的 《舞赋》中写有“臣闻歌以咏言、舞以尽意, 是以论起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 形”[1],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传统可见一斑。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诗歌与乐舞大概有两种对 应关系:一是诗歌作为舞蹈的唱词,如《诗 经》 中“颂” 部、屈原《 九歌》及即兴舞辞 等;二是记录舞蹈场景、描绘舞蹈意蕴及观舞 感受,如《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等。
屈原将自己的一生活成了一部永远鲜活的 诗篇,他的故乡楚国,成为许多人心中的首善 之地。袁行霈认为屈原既有“独立不迁”“上 下求索”的人格之美,又有“瑰奇雄伟”“绚 丽回旋”的诗歌之美。屈原的一生坚定又迷 茫,他坚定着自己的追求,天地却对他的求索视而不见,苦苦追寻的他,却是天地之殇。楚 国延续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传统,“信 巫鬼,重淫祀”。屈原的《九歌》记录了楚国 大型祭祀活动,从作为唱词的《九歌》中推断 出,楚地的祭祀是载歌载舞、群体参与的。每 一个祭祀的对象都有特定的舞蹈,也有模拟鸟 兽鱼虫之舞。诗歌唱词的变化也对舞蹈的风格 形态有极大的影响,对此,王宁宁在《“长袖 善舞”的历史流变》中有详细论述,唱词、舞 蹈、乐曲互为表里,相互影响,三者特点的流 变见证了中国古代审美情趣的变化。[2]
除了作为唱词的诗歌之外,还有大量描写 舞蹈观感的佳作,如《霓裳羽衣舞》中: “飘 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 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虽然没有真实的影 像图片,但是这句“小垂手后柳无力”便是一 幅灵动的临摹画。舞女摇曳多姿, 如弱柳扶风。 尽管不知具体的舞姿动作,但对这种美的刻画 已然超越了刻板的描摹,也让我们瞬间抓住这 个舞姿的精妙。从这简单的例子中便可以看出, 诗歌语言对舞蹈的重要性,在无法看到真实舞 姿的背景下,好的舞诗确实在我们研究古代舞 姿中起到极大的作用。这背后的缘由与逻辑, 在茅慧的《从诗歌中的舞蹈成像到舞蹈符号的 多重对位》一文中得到了阐释。诗人必然在脑 海中有“弱柳扶风”的形象,那种娇柔的意境 和感受必然在诗人心中挥之不去,舞姿“小垂 手”表面上看与柳树没有任何关联,但是它传 达出的轻缓柔美的感觉却可以与弱柳随风摆动 相对应。“正如人们有了‘柳无力’的记忆, 才会有‘柳无力’的诗句。而这里的构型,在 于它不仅是静止的图式,更是运动和生成的过程。它最后必须是成像的、完整的,能够传达 一种意义,产生一种效应。”[1] 这便是前述的 一级语言符号能指(小垂手)和所指(小垂手 具体舞姿)与另外一对一级语言符号能指(柳 树)和所指对应后产生的艺术魅力,这两者表 达的柔媚具有同一个文化内涵,即茅慧所说的 “表层对位”与“潜层对位”的关系。由此可 见,诗歌完全有能力运用自己的方式传达舞蹈 的内涵,研究舞蹈诗确是研究古代舞蹈的一种 可行性方法。
[1] 出自费振刚、仇仲谦等《全汉赋校注》, 广东教育 出版社 2005 年出版。
[2] 出自王宁宁《“长袖善舞”的历史流变》, 《北京 舞蹈学院学报》2013 年第 3 期。
研究中国古典艺术,意境和意象是无论 如何也绕不开的话题。古往今来,对于意境的 论述滔滔不绝,尤以王国维的“境界说”集大 成。袁行霈梳理并阐释了其中的主要观点,从 不同的维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意象是 形成意境的材料,意境是意象组合后的升华。 虽然中国古典艺术强调意境,但是“有无意境 不是衡量艺术高低的唯一标尺”[2] 而且意境本 身也有高下之别。体裁、诗人的思想境界等都 是影响诗人作诗意境的重要因素。意境也不仅 仅是作诗的要求,诗歌、读者也需要有意境, 读者的意境可以不同于诗人、诗歌的意境,但 不能界定和改变这二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 以有不同的感受和解读,但是诗歌的意境无须 依赖读者而存在。而如何将物象变为意象,意 象在诗歌中如何组合形成诗句,便是应继续探 讨的问题了。
意象与意境不仅存在于古代诗歌创作追 求中,中国古代舞蹈对意境的营造更是精妙 绝伦。汉代傅毅的《舞赋》以盘鼓舞为描写对 象,其对舞蹈场面的描写“独驰思乎杳冥”“游 心无垠,远思长想”是指舞蹈表演一旦进入状态,就要根据舞蹈中的意境让思想自由驰骋, 不受时间空间的约束,此时便“雍容惆怅,不 可为象”,此“不可为象”并非没有舞蹈表演 具体的物象,而是指象外之象。舞袖翻飞中超 越时空的限制,进入只有美的境界,观者陶醉 于舞姿带来的飘忽之感……而当“回身还入, 迫于急节。浮腾累跪,跗蹋摩跌”之时,仿佛 将观者的思绪从遥远的天际拉回,感受当下热 烈似火的昂扬。节奏的快与慢, 舞姿的静与动, 合着贯穿全身的呼吸动律,就着上下翻飞的长 袖,一幅绝美的人生图景就这样展现在观者的 面前。袁行霈在其著作中论述诗歌的音乐美, 特别关注节奏、音调、声情,依托于这些元素 的诗歌的抑扬顿挫,起承转合同样存在于舞蹈 艺术之中。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袁行霈倡导 “横通与纵通”以及“博采、精鉴、深味、妙 悟”,要把研究对象从一个狭小的范围里解放 出来,学会对资料进行鉴别和考证。舞蹈艺术 的研究也应如此。在舞蹈戏剧性减弱,纯舞急 速发展之时,更离不开舞曲与舞蹈的配合。舞 蹈不仅是运动着的物质,更是运动着的精神, 这个精神便是中国古代舞蹈的艺术追求、艺术 特质,要了解这个精神,就不可将其与诗歌剥 离。《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论述并梳理了中国 古代诗歌理论和史论,体大虑周,为中国舞蹈 艺术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武器。
[ 作者简介 ] 杨田雨,女,汉族,山东临沂人, 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方向为中 国舞蹈史。
[1] 出自茅慧《从诗歌中的舞蹈成像到舞蹈符号的多重 对位》,《民族艺术研究》2015 年第 5 期。
[2] 出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02 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