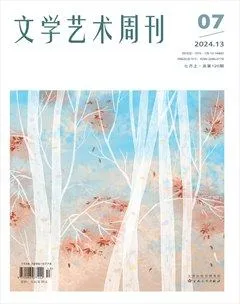语言权力观视域下《巴别塔》中的身份与叙事关系评析
少有著作将翻译作为主题进行深入探究, 这是因为很长时间以来翻译被广泛认为是语言 之间的简单转换。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学者 匡灵秀所著的《巴别塔》就格外引人注目。不 仅仅因为匡灵秀曾就读于剑桥大学与牛津大 学,学养深厚,更因为《巴别塔》中随处可见 其华裔作家身份对于主人公罗宾个体叙事建构 与价值观取向塑造的影响。作者匡灵秀凭借此 书一举斩获 2023 年第 58 届科幻星云奖最佳长 篇小说奖,足见这本书在西方主流学界与出版 界的影响力。她的作品聚焦于翻译的学习成长 历程,对种族、民族身份等西方语境中的尖锐 话题毫不避讳,既改变了社会大众对于翻译的 固有认知,将翻译活动描画成了一种媲美魔 法、对现实世界起改造形塑作用的社会实践活 动,又给广大读者提供了西方主流出版界边缘 作者的独特视角。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匡灵秀 就读于西方殿堂级学府,并获得了西方主流学 术界的认可,但主人公罗宾在故土与异乡、孕 育自己的母亲与后天教育自己的父亲、遥远的亲缘纽带与优渥的学习生活环境之间的摇摆不 定,仍是匡灵秀自己割裂的身份认同的投射。
一、身份、权力与叙事话语
根据福柯的权力理论,语言即权力,话语 是社会实践主体相互角力的结果。在福柯看来, 权力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力量关系,在任意两点 的关系中都会产生权力。他进一步提出,哪里 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构成一种制约和反抗 的辩证关系。在权力视域下,考察权力关系在 知识话语当中的运作机理,有助于消解知识和 话语的绝对性和权威性,进而揭示主流社会叙 事背后的权力运作。同时,既然权力与抵抗之 间是互为因果、互相依赖、此消彼长的关系, 那么强势权力扶植的主流宏大叙事和元叙事与 弱势权力所代表的旨在消解宏大叙事的细小叙 事也处在一个互动甚至是共生的关系中。社会 权力关系建构叙事,叙事也会反作用于社会, 叙事建构本身就是改造世界的一种积极的实践活动。
身份与叙事是密不可分的。人类主体并 不是一个与生俱来、固定不变的先在客体, 国籍、种族、性别、语言、亲缘等单一或多重 身份都会对个体与社会叙事建构产生影响。 书 中 反 复 出 现“ 翻 译 即 背 叛”(Traduttore, traditore.)这种说法的意思是译者囿于自己身 份与价值观取向无法完全做到对原文和源语文 化的忠诚。从德里达到斯皮瓦克,后殖民主义 和女性主义通过操控文本消解殖民主义与男权 至上主义的翻译策略已成为广泛共识。被殖民 者、庶民与女性的身份只是致使翻译“背叛” 的其中几重身份,游走其间、闪烁乍现,发挥 着亘古不变的操纵作用的依旧是权力关系。在 翻译语境中,这种权力关系具体体现为源语与 译语、源文本和译文、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 作者与译者之间的拉扯与角力,也体现在主流 叙事与微观叙事之间的博弈,本文聚焦于探讨 主体身份在叙事建构当中发挥的作用,以期管 窥并揭示“翻译即背叛”背后译者身份的影响 作用。翻译在语义层面关涉字词的语际转换, 看似不需要发挥主体性,但放大到文本和篇章 层面,译者是否要将原文中的异质元素原封不 动地迁移进译文,让读者主动地去靠近原文; 还是让译文主动地去靠近读者,需要主观能动 性。前者会增大读者的阅读理解难度,后者会 主动消除这种障碍,故而后者通常被戏称为 “一种背叛”。翻译选择背叛与否,与翻译的 身份认同密不可分。
二、《巴别塔》中以翻译施法的奇幻架空世界
“忠诚”是个有着丰富含义的相对概念。 从翻译的身份出发,所产出的翻译成果靠近源 语和源语文化即为直译,即为忠诚;靠近译语 和译语文化即为意译,即为背叛。假如翻译是 译语母语者,从民族身份的角度出发,靠近源语和源语文化为背叛,靠近译语和译语文化则 为忠诚。但在本国文学外译的过程中,归化是 背叛,是对异族、异域文化、他国语言的皈依, 异化是忠诚,是对母族、母国文化、本国语言 的坚守。回归到《巴别塔》,书中的故事发生 在鸦片战争前夕一个奇幻架空世界中。大英帝 国内部充斥着不同语言、不同民族身份之间的 交锋与冲突,逐渐走向分歧与分裂;而延伸到 大英帝国本土疆域外的殖民地亦是如此,中心 对于边缘的控制力与统治力疲态尽显、急剧转 弱。背后的原因是英国赖以运行的魔法银条逐 渐失效。魔法来源于翻译时不同语言间丢失的 语义,从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再到各种 民族语言,只要语言的转换过程中出现了语义 的丢失,比如纯字面上的转换造成了隐喻含义 的丢失,魔法就会在刻字银条上生效,将丢失 的语义以具象的形式呈现。语言在这个架空时 空中就有了积极改造世界的力量。银条的翻译 魔法产生自语言及种族之间的距离、差距、差 异甚至是对立,而维系统治的手段是开展跨国 贸易,让他国依赖英国的工业制造品。悖论就 此形成——贸易的畅通会使语言间的距离逐渐 缩小,使银条逐渐失效,而闭关锁国又不符合 大英帝国的经济利益。
无论是在书中的架空世界,还是在真实世 界中,历史上每一次跨文化的商贸往来与人文 交流都伴随着语言间的相遇与碰撞以及词汇的 相互借用。书中对于魔法生效的机制描述在真 实世界中存在映照。语言间距离越远,譬如印 欧语系印度语族的梵语与印欧语系意大利语族 的拉丁语,汉藏语系中的汉语与藏语,配对形 成的刻字银条的效力就越大;语言间的距离越 近,例如同属于印欧语系的法语和英语,字词 的含义就越接近,配对形成的刻字银条的效力 就越有限。在那个以银条与翻译魔法为硬通货 的时空里,为了生产更多的银条,巩固大英帝 国的殖民统治,需要在全世界各地,尤其是印度、中国和南太平洋地区网罗外语人才并加以 培养,向他们灌输殖民主义思想,待他们学成 之后为帝国所用,转而以代理人的身份协助帝 国开展殖民统治。主人公罗宾就是被素昧平生 的洛弗尔教授从广东瘟疫肆虐的废墟中带到了 英国牛津接受高等教育。洛弗尔教授在学业上 待罗宾极为严苛,却从未承认他为自己亲生骨 肉的事实,言语间对广东、对罗宾的生母、对 英属殖民地也充满不屑。罗宾与其父亲的关 系,凝结了罗宾对英国、对英语、对英国社会 主流叙事(即英国理所当然应该奴役、掠夺、 搜刮其他国家,将其他国家置于政治、经济与 舆论边缘地带的态度)。直到罗宾踏上广东故 土、遥远的记忆被唤醒前,罗宾对父亲的态度 一直都是既归顺又排斥,既依赖又反抗,而父 亲一而再再而三对被殖民者生存真相的漠视造 成了父子间矛盾的大爆发。
三、身份认同与“背叛”
除了罗宾,娇俏可爱,生在海军上将家 庭却不受重视的英伦玫瑰莱蒂;生于海地,国 破之后寄住在法国家庭,被告知不能说海地克 里奥尔语,只能说法语的维克图瓦;生于加尔 各答,全家在白人精英家庭做工的拉米,他们 都是本书的主人公。他们在共同经历了罗宾与 父亲的决裂、罗宾父亲意外殒命的事故后,也 因身份的不同产生了裂隙。随后,每个人的命 运如分叉的铁路一样导向了不同的方向。但这 次转折之前各人的际遇早有端倪,结局仿佛写 在了相遇的开端,如草蛇灰线般伏脉千里。由 语言、民族身份、肤色族裔交织而成的复杂个 体,在各种机缘巧合与命中注定的碰撞中,分 别诠释了“翻译即背叛”的含义。莱蒂因其女 性的身份处于边缘,也因此与其他三位主人公 在求学期间产生共鸣,始终保持紧密关系,但 莱蒂在其他层面无法与这几位同窗感同身受。
其他三位饱受种族歧视的伤害,任何对少数族 裔的扶持与优待在他们看来都是渐进式的,唯 有民族独立、流血牺牲才是根治痼疾的良方。 莱蒂无法理解有色族裔不惜牺牲眼下的安逸富 足也要争取独立的想法。在她看来,作为女性 的她都能通过勤奋、隐忍与持久的等待为自己 在牛津学府争得一席之地,拥有这么优越的学 习条件,理应感恩戴德,他们都战胜了各自既 定的命运,走上了一条能够尽情发挥个人潜质 的康庄大道,何苦将这一切拱手相让。她没有 想过性别的不同对个人发展的阻力要小于肤色 不同。最终,莱蒂为了自保背叛了他们。罗宾 是最早被招募进反叛组织赫尔墨斯社的,却向 志同道合的维克图瓦和拉米隐瞒了这个秘密, 直到数年之后撞见后两位为赫尔墨斯社效力时 才和盘托出,这与他是教授之子、不愿与学术 建制彻底切割不无关系,而为了道义与良心, 他与赫尔墨斯社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
个人身份的建构是在特定的社会秩序中实 现的。语言作为叙事的载体,可以作为一种社 会实践活动以独立主体的形态呈现。但是叙事 的生成无法脱离特定的社会语境与秩序,并会 受到主流社会叙事与权力结构的影响。在英国 时期,罗宾在亲缘的羁绊下对巴别塔的做法抱 有一定的质疑——同父异母的兄弟格里芬将其 招募进赫尔墨斯社并向他揭示世界运行的真相, 与母亲在广东相依为命的遥远记忆以及母亲的 溘然长逝令他心生疑窦——他无法说服自己相 信牛津大学与巴别塔皇家翻译学院搜罗世界各 地语言人才,控制银条供应,宣扬巩固白人至 上与大英帝国中心主义的合理性与正义性。他 对自己在巴别塔无忧无虑的学习生活与优渥的 环境怀有歉疚之心,但此时的罗宾尚且无意颠 覆巴别塔所象征的威权。直到他再次踏上故土, 在一次任务中发现英国为扭转对华贸易逆差, 强行打开中国大门,不惜出口鸦片;在英国甚 至酝酿着一股侵华势力,意图借清廷有识之士抵抗鸦片之由对华发起战争,进一步劫掠中国 的财富,践踏中国的主权,罗宾的态度才开始 急剧转变。罗宾随后质问洛弗尔教授,为什么 没能在霍乱中救下母亲,洛弗尔教授对昔日爱 侣丝毫不加掩饰的居高临下与嗤之以鼻代表了 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真实态度——被殖民者态 度上的绥靖、顺从、尊崇与行为上将本国的财 富、语言、文化、人才拱手相让,并不会换来 殖民者的尊重与平视。直到这一刻,罗宾才看 到自己血缘及事实上的“父亲”以及自己称为 “祖国”并发誓要为之效劳的国家的真实面 目,至此全书迎来了推动情节发展的最大冲突 点,东方以情感、关系和家族作为纽带的“和 合”理念与西方强调开疆拓土、征服劫掠,以 契约作为纽带的个人主义形成了强烈的碰撞与 冲击。在外界的刺激下,罗宾完成了自己的身 份构建。他对殖民者懵懵懂懂的认知开始变得 清晰,过去犹疑不决、摇摆不定的认知开始坚 固。罗宾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意味着他将永远抛 弃过去安逸富足的生活,走上一条前途未卜、 颠沛流离的路,但这也是一条不愿为奴、直面 真相的独立之路。
回到作者的写作上,作者作为西方文学出 版界的少数族裔作家,一方面不想让讨论的焦 点被身份遮蔽,希望评论界对其作品的品评聚 焦于写作水准、构思与世界建构上;另一方面 边缘作者(Marginalized Writer)与少数族裔俨 然是出版界用以介绍作者的标签,这种标签本 身尽管有简单化的嫌疑,但确实为意欲了解其 他族群生存状况的读者提供了快速检索的一扇 窗。作者也毫不避讳地将自己作为少数族裔在 西方社会的真实生活感受与体会借主人公之口 尽数讲出——尝试融入,但无法改变黄皮肤与东方面孔,无法摆脱边缘位置。作者在播客上 也说过,《巴别塔》是她写给牛津大学的情书, 也是诀别信,她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发现牛津 大学与剑桥大学等高等学府自建校之初便服务 于帝国的扩张与殖民统治,这与她希冀的学术 氛围浓厚、远离是非的象牙塔相差甚远。西方 的第二代“ 流离者”(Diaspora)即移 民后代 (Descendant)都经历过如浮萍般在两种文化与 两种身份之间流离失所的感觉。这种移民身份 不是他们自主选择的,而是父辈强加于身的, 然而从孩提起,他们便需要面对、消化同龄人 的排斥与奚落。匡灵秀就坦言母亲到学校给自 己送小笼包时,身边同学纷纷作鸟兽散,说是 味道太重。“母国”“故土”“家园”的概念 于他们而言是流动且混乱的,久而久之,他们 总会回到东方“家园”寻根问祖,寻求传统的 文化认同与不竭的灵感来源,这何尝不是一种 “回归”呢?书中除了叙事主线以外,还穿插 着以第三人称视角描述的四位主人公的成长经 历与心路历程,以叙事的手段再现了四位主人 公身份构建的全过程,读者每每读到此处便有 恍然大悟之感,使主线情节的每一次递进都不 会显得突兀。本文认为,宏大叙事既然由社会 权力结构建构起来,必然有其存在的依凭与理 由,细小叙事与宏大叙事应构成众星拱月、相 互映衬的共生关系,这样书中所描述的离心力 与割裂分歧将会不攻自破。
[ 作者简介 ] 齐晓彤,女,汉族,北京人,就职 于北京国译翻译有限公司,国家二级同声传译, 毕业于外交学院翻译专业,硕士,研究方向为 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