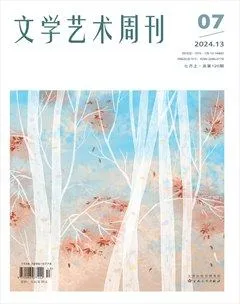日本近代对中国、西方文论中“情”的转换
日本从古代到近代,都经受了不同的外 来文化冲击,其文论便是在一次次外来与本土 文论交融中逐渐形成并发展的。纵观日本文论 史,关键性的问题是如何吸收和内化外来文 学。本文从“情”的概念出发,探讨日本文论 是如何将中国、西方“情”的概念进行融合, 并形成自己独有的文论观念的。
日本近代文学的形成离不开日本古典文 学以及近世文学的理论与创作,而日本古代文 论是在与中国文论的深度交融中逐渐形成的。 因此,要考察日本近代的文学理论,就离不开 对日本古代文论以及其所关联的中国文论的分 析。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提出“小说的 眼目,是写人情”的观念,广泛而深刻地影响 着日本近代文学,而“人情”这一概念同日本 及中国的古代文论都有深刻的承接关系。
一、中国古代文论与日本古代文论中的“情”
中国自古以来就讲求对感情的节制,儒家 思想讲求温柔敦厚、中正平和。孔子评价《诗 经》亦用“思无邪”三字,讲求的是对情感的 节制。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和文 学作品较之以前都有了很大的不同。魏晋时 期,儒学衰落,受到时代动乱的影响,掌权者
更倾向于任用懂得治国之术、用兵之道的谋臣, 而非只会吟诗作对的文臣。儒学既衰落,必然 会导致思想束缚的松弛。观其魏晋时期,刘勰 在《文心雕龙 · 时序》中论及建安文学时曾言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概括了整个魏晋时 期的作品风貌。“雅好慷慨”一词缘于曹植《前 录》的序, “慷慨”一词之意即为:直抒胸臆, 意气激荡,强调的是对于自身情感的抒发。陆 机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也 强调了人的情感对于创作的重要性。钟嵘在《诗 品》中亦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 情,形诸舞咏”,也将人的自然感情作为文学 的本源,并强调环境和社会生活对诗人诗情的 抒发作用。
然而发展到了齐梁时期,宫体诗盛行,其 绮丽淫靡的诗风一直延续到唐代早期。陈子昂 曾评价齐梁诗风为“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 二是“汉魏风骨,晋宋莫传”。前者批判了齐 梁诗风华丽而无深刻的内涵,后者则是批判晋 宋后的诗歌丧失了汉魏时期诗歌的内涵与艺术 性。可见, 这类写宫廷生活和男女恋情的诗歌,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情,但这种世俗情 感表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高。
明代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 观念也有所松动,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是对“情”的重视。李贽的“童 心说”认为“童心”也是“真心”的表现,主 张文学创作要表现真情。汤显祖在《牡丹亭记 题词》中说道: “世总为情,情生诗歌。”其 将文学产生的根源归结为“情”。冯梦龙也在 《情史序》中提出:“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 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 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没,唯情不虚假。有情 疏者亲,无情亲者疏。”可见冯梦龙将“情” 看成世间极为重要的事物。因此,“情”既是 文学创作的核心与动力,也是评价文学作品的 重要标准之一。
总的来说,在中国古代文论中, “情” 不仅指代人的情感体验,同时也是文学创作的 原则,是文学批评的标准,它贯穿于文学的创 作、批评与接受的全过程。
在日本文论中,“情”有两种形式,一种 是写作汉字的“情”,在早期的日本古代文论 中,汉字的“情”讲的都是人的感情,而且是 审美性的感情。[1] 而在汉字的“情”传入之前, 日本人用“なさけ”来表示“情”的含义,用 汉字标记为“情け”。不过用“なさけ”(情 け) 表示的含义同用汉字“情”表示的含义略 有不同。“情け”既指人的感情,同时还有 “同情心”“懂风雅”“知情趣”“恋情”的 含义。而这些含义相较于中国文论中的“情”, 虽然从含义上看更为狭窄一些,但是更具有 “人情主义”的倾向。
二、从写“人情”到坪内逍遥“小说的主脑是 人情”
明治维新后,随着西方小说和文学理论的 大量传入,日本亟需解决的便是如何基于传统 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学理论。近代日本文学史, 是在西方与日本、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对立中寻 找微妙平衡的历史。
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揭开了近代日本 文学史的序幕。他在书的第二章“小说的眼目” 的开篇就写道: “小说的眼目,是写人情,其 次是写事态风俗。人情又指的是什么呢?回答 说,所谓人情即人的情欲,就是指所谓的一百 零八种烦恼。人既然是情欲的动物,那么不管 是什么样的贤人,善人,很少没有情欲的。”[2] 在坪内逍遥看来,小说是用来展现人的内心情 感的。这就将日本文论对于“情”的重视提到 了相当重要的高度。然而,人的内心情感是极 其隐蔽的,因而, “揭示人情的机微,不但揭 示那些贤人君子的人情,而且巨细无遗地刻画 出男女老幼的善恶邪正的内心世界,做到周密 精细,使人情卓然可见,这正是我们小说家的 职责”。
较以往的日本古代文论不同的是,坪内逍 遥虽然也强调小说要写人的情感,但是他结合 西方文论进一步提出了要结合心理学的相关理 论来塑造人物。“即使写人情,如果只写了他 的皮毛,那还不能说它是真正的小说,必须写 得入木三分,才能认为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 所谓稗官之徒,应该像心理学者那样,根据心 理学的规律,来塑造他的人物。”
坪内逍遥以曲亭马琴的《八犬传》为例, 批判曲亭马琴所写的八犬士只是八个傀儡,而 非有血有肉的人物。曲亭马琴将这八个人物的 行为写得完美无缺,是为当时统治者需要的“劝 善惩恶”风气服务的。然而,这样只根据自己 的设想,虚构出的有悖于心理学规律的人物, 只能是作者的傀儡。
在作为对《小说神髓》理论的实际应用而创作出来的小说《当代书生气质》中,坪内逍 遥虽然展现了几个从事自由民权运动的书生的 不同性格,但是他以旁观者的态度做写生式的 摹写,并未做到他在《小说神髓》中提出的要 结合心理学理论分析人物内心的方法。
[1] 出自王向远《中日古代文论中的“情”“人情”范 畴关联考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 年第4期。 出自坪内逍遥《小说神髓》, 刘振瀛译, 人民文学
[2] 出版社 1991 年出版。本文所引坪内逍遥文字皆出 自此书,后文不再重复注释。
即便如此,我们也能看到日本近代文论在 对西方文论的吸收与融合中所做的努力。
三、从“人情本”到尾崎红叶
日本文坛从明治初期广泛引进和学习西方 文学,到明治二十年人们追逐西方的热潮逐渐 冷却,崇尚古典文学的砚友社成为这一时期文 坛的主流文学。在文学史上,这个时代一般被 称为“混沌时代”。在砚友社的核心人物尾崎 红叶的身上,最能体现这种“旧的事物尚未退 却,新的事物正在酝酿”的新旧交织的特征。
尾崎红叶早期的作品受到净琉璃、伽草子 和井原西鹤的影响,有日本江户文学的痕迹。 同时,他在作品中积极描绘明治时期日本受到 西方浪潮的冲击而发生的改变,这一时期的作 品很好地展现了欧化风潮与元禄文学复兴这两 种倾向。尾崎红叶以“近世人情本”的模式接 近现代小说,比如在表现样式上,一是重视一 节一场面的生动描述,而不追求故事情节;二 是重视场面与场面之间的连续来实现创作的构 思;三是描写人情世态等。[1] 虽然尾崎红叶的 作品是通过古典文学范式来接近近代文学的, 因此被国木田独步评价为“穿着西装的元禄文 学”,但是无法否认他对于日本近代文学的巨大贡献。
[1] 出自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近代卷》, 经济 日报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2] 出自高须芳次郎《日本近代文学史》, 黎跃进、杜 武媛、李建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年出版。
[3] 出自中村新太郎《日本近代文学史话》, 卞立强、 俊子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0 年出版。
他于 1891 年后不断钻研“言文一致体”, 在《多情多恨》这部小说中成功地使用了“で ある”调。他说:“山田美妙的也没意思,用 “だ”调的话,太生硬,用“ありません”调 太正式,都不能令人满意。”[2] 自此,日本近 代文学中非常重要的“言文一致体”,通过尾 崎红叶的实践达到成熟。
尾崎红叶的代表作《金色夜叉》更是拓展 了坪内逍遥未能实现的心理学描写手法。《金 色夜叉》主要讲述的是失去双亲的青年贯一寄 住在曾受到父亲恩惠的鸣泽家中。鸣泽将女儿 阿宫许配给贯一,女儿阿宫却倾慕于富有的少 爷富山。最后,阿宫不顾贯一的劝说,嫁给了 富山。贯一彻底变了,他当上了高利贷的代理 人,企图用金钱来复仇。而阿宫逐渐被丈夫厌 弃,多次写信给贯一,请求他的宽恕,而贯一 根本不予理睬。突然有一天,贯一梦见阿宫自 杀,猛然醒悟自己走错了路,而阿宫此时也处 于悲惨境地。故事就在这里中断了。在这部作 品中,尾崎红叶已然采用了心理学的方法剖析 人物的内心活动,刻画人物的能力有了很大的 提高。[3]
尾崎红叶从江户的戏作文学出发,寻找近 世与近代的交汇点,虽然他创作的文学仍然不 是彻底的现实主义,然而像红叶这样,在传统 与近代中积极寻找桥梁的做法,仍是日本近代 文学发展的必经之路。
分析日本近代文学理论与实践,有助于我 们梳理日本近代面对西方文学的巨大冲击,是 如何做到吸收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实现自身的 转化,并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学体系。而这一点 对于中国文论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作者简介 ] 王艺洁,女,汉族, 江苏连云港 人,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 向为汉语言教育、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