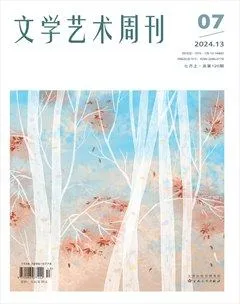《静静的顿河》与《日瓦戈医生》主人公悲剧之比较
在灿若繁星的俄罗斯文学史上,曾经有这 么两部作品都描写了十月革命前后一系列的重 大社会事件,在文学史上获得了不朽的声名。 它们就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帕斯捷 尔帕克的《日瓦戈医生》。
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塑造了一个 复杂、摇摆的哥萨克勇士形象——格里高利。 他是“顿河哥萨克中农的一种独特的象征”, 既有着哥萨克广大农民的优秀品质:天性纯 朴、骁勇善战、诚实正直、勤劳热情,同时也 受到哥萨克落后传统观念和道德偏见的影响, 徘徊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最终酿成了自己的悲 剧。而《日瓦戈医生》中的主人公则是二十世 纪初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受到良好的 学校教育和舅父韦杰尼亚平宗教文化的熏陶, 擅长思考、医术精湛、关注人性,却又常常表 现得懦弱、无能、渺小,面对生活的苦难时往 往深陷迷惘不安。这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典型 角色,在时代洪流中却拥有极为相似的人生经历及个人结局。两位主人公亲身经历了第一次 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等 一系列重大社会历史事件,有过徘徊动摇,也 有过痛苦迷茫,在那疾风暴雨的历史舞台上如 浮萍般身不由己地被时代所裹挟。
一、格里高利的悲剧
格里高利追求哥萨克的名誉,以军人为职 业,骁勇善战,在寻找正道的路上不停探索, 却又一次次地陷入迷茫,一生都徘徊在革命和 反革命之间。他时而支持布尔什维克,认为人 民政权的建立是理所应当的;时而觉得哥萨克 应当争取自治权。两次加入红军、三次加入白 军,最后却成了散兵游勇,穷途末路。
他追求爱情与家庭的和美,却又在妻子娜 塔莉亚和情人阿克西尼亚之间动摇,因为自己 的犹豫踌躇导致了两个女人的悲惨命运:深爱 着格里高利的娜塔莉亚没有得到丈夫的爱,在遭遇丈夫的不忠后选择自杀,落下终身残疾。 当格里高利终于明白娜塔莉亚深沉细腻的爱而 回心转意后,他们一起度过了六年的快乐时 光,还有了一双儿女。可格里高利与阿克西尼 亚的再次相聚,让娜塔莉亚陷入了绝望,她下 定决心打胎,却不幸因堕胎而身亡。不同于温 柔含蓄的娜塔莉亚,情人阿克西尼亚热情洋 溢、性格泼辣,有着火一般的生命力。在意识 到自己的真心之后,她不顾哥萨克宗法制的束 缚和众人的责骂,大胆地表达对格里高利的 爱。阿克西尼亚和心上人在一起受尽了磨难, 最终在陪伴格里高利逃亡的途中被征粮队哨兵 打死。
二、日瓦戈医生的悲剧
日瓦戈医生清楚地意识到了俄国沙皇制度 的腐朽,在革命刚刚爆发之时,他由衷地赞美 革命: “多么出色的手术啊!拿过来就巧妙地 一下子把发臭的多年的溃疡切掉了!既简单又 开门见山,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 来的非正义做了判决。”但革命的残酷性又使 他转向隐居来逃避现实,苟且保全“小家”的 安宁。在被抓到红军游击队做队医的日子里, 他目睹身边不断发生的惨剧,革命武装力量和 反革命武装力量之间激烈斗争,“穷人变得更 穷,富人变成穷人”的社会现实使他对革命产 生了抗拒。他开始把充溢着暴力革命的国家比 作《圣经》中的世界末日。在这样一个暴力革 命的时代, 日瓦戈医生对个体生命价值、人的 理性的追求难免呈现出矛盾的结果,使自己陷 入迷茫痛苦之中。
日瓦戈医生对爱情的追求也呈现出悲剧色 彩。日瓦戈医生与妻子冬妮娅本是青梅竹马, 但是两个人的婚姻并非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 而是出于一种伦理和责任。冬妮娅给予日瓦戈 亲情的温暖,但两人在革命战争的洪流下一次次地被迫分离,最终分隔异国,家庭破裂。而 拉拉给予日瓦戈的则是知己般的理解,他们之 间的爱情是精神上的互通。可这份爱就像暴风 骤雨中的火苗,最终还是湮没在时代的风雨中: 日瓦戈拱手将拉拉推到自己痛恨的仇敌科马罗 夫斯基身边,最后思念着拉拉的日瓦戈在莫斯 科街头因心脏病猝死。拉拉冒着生命危险参加 日瓦戈的葬礼,最终下落不明,只化作一串无 姓名的号码。
三、二人悲剧成因的共同因素
格里高利和日瓦戈这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 人物却呈现出相似的人生轨迹:都象征着各自 的文化结构和历史传统,被卷入革命的浪潮成 为时代洪流的一部分,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徘徊 犹豫,眷恋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又在对现实感 到绝望之际自甘堕落,最后都泯灭在时代剧变 中。对于格里高利来说,精神家园是哥萨克人 民世世代代深恋着的土地和草原;对于日瓦戈 来说,精神家园则是和拉拉在战争夹缝中构建 起来的爱巢。看似大相径庭的道路却把他们引 向了同一个终点,可见二人的悲剧成因有共通 之处。
( 一 )固有文化心理结构的潜在影响
文化心理结构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深 层逻辑,是其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特有生存方 式的体现。格里高利是一个典型的哥萨克勇士 形象,其文化心理结构是哥萨克式的。“哥萨 克”一词源于突厥语,其含义是“自由自在的 人”,哥萨克男子自幼习武,勇猛剽悍,是草 原上天生的骑兵。自十八世纪起,哥萨克勇士 经常充当俄国沙皇的雇佣兵,到了十九世纪至 二十世纪初,又被当成镇压人民革命的武器。 同时,哥萨克人遵循军民合一的部落自治传统, 但其自身社会历史、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决定了其既要依附于外部政权的扶持,又必须保持一 定的独立性。农耕和游牧、独立和依附,这便 是哥萨克人分化成不同性格的底层逻辑。格里 高利的主要性格正是由这两个维度组成:他在 顿河畔的农民家庭长大,有着哥萨克农民最朴 素的美德:勤劳善良、纯朴热情、眷恋故土, 又有着哥萨克勇士尚武善战、重视战功、追求 自由的特点。既有着哥萨克族群鲜明的群体归 属意识,主张依附,又追求自由,渴望争取哥 萨克的独立,这些典型的哥萨克文化心理结构 绘就了格里高利灵魂的底色:当他第一次进入 战争,在战场上用长矛刺进了一个奥地利人的 身体时,他内心的善良使自己背负上了沉重的 心理包袱;但是当他获得了乔治十字勋章返回 家乡时,民族英雄的身份、众人的谄媚与敬重 又使他忘却了内心的不安。于是,他又以“一 个出色的哥萨克的身份重新回到前线”。可以 说,格里高利是哥萨克传统影响下形成的在思 考和行动中间徘徊的矛盾统一体。
日瓦戈医生的形象则更广泛地反映了那个 时代俄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生存和精神困境。他 们博学多才、追求精神独立,具有独立的人格 和深邃的思想,在疾风骤雨的革命年月里,他 们既探索国家前进的道路,又力图寻找个人精 神的家园。拉季舍夫作为“俄国第一个知识分 子”,在其著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中,以一次假想的旅行描绘了沿途底层人民遭 遇的非人压迫和剥削,批判了沙皇专制制度的 罪恶,揭开了俄国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的序 幕。俄国社会的动荡,使知识分子承受了命运 赋予的诸多苦难,却又以时代为己任,彰显出 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东正教和多神教的 交织融合、几经变革的动荡历史,致使俄罗斯 民族精神呈现出复杂而独特的面貌,反映在知 识分子群体上则呈现出救世情怀、忏悔意识、 极端性等特征。而这种民族精神难免会掺杂时代复杂的政治因素从而变得面目全非,使人陷 入矛盾迷茫的泥沼。这种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 在日瓦戈医生这一形象上可见一斑。日瓦戈出 生在一个富商家庭,却在年幼时成为孤儿。他 在舅父韦杰尼亚平的庇护下长大,受到舅父宗 教文化的熏陶和学校的良好教育,成了一名杰 出的诗人和医生。他目睹了专制制度的种种黑 暗、腐败,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使他渴望救国 济世,热情盼望着革命的到来。然而在被抓到 红军游击队做队医后,知识分子的本性让他本 能地抗拒暴力革命所带来的种种流血、杀戮、 家庭悲剧,当他走出象牙塔,真正身处革命风 暴之中时,暴力革命黑暗的一面才赤裸裸地全 盘展现在他的面前,打破了一个知识分子美好 的信念。日瓦戈医生对革命的态度由赞美到困 惑,最后再到疏远,是一代知识分子在革命岁 月陷入迷茫的共同缩影。
日瓦戈医生身上,还体现出了俄国知识 分子传统的人道主义情怀。日瓦戈从小便耳濡 目染地受舅父韦杰尼亚平基督教仁爱思想和托 尔斯泰主义的影响,力图从精神上探索人类的 生命价值。他曾认为革命能消除人民疾苦、解 救危难中的俄罗斯民族,所以对革命表现出了 极大的热情;当他真实地看到祖国大地因革命 而千疮百孔、人们因战争而流离失所时,他内 心的爱国主义被仁慈之心所战胜,人道主义精 神使他坚守着维持人的生命和尊严的本性,于 是他投身于爱情乌托邦之中,企图远离目睹的 残酷与血腥。他把爱情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 他与拉拉情投意合、心灵相通,缔造起爱情的 “伊甸园”。他们是真挚爱情的典范,也是家 庭伦理的叛徒。在享受甜蜜爱情的同时,两人 也背负着沉重的道德伦理负担:他们都眷恋着 自己的家庭,对自己亲人的责任感一次次地使 他们陷入痛苦。日瓦戈医生身上所代表的当时 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事实上是一种超越 时空的、具有永恒意义的精神困境,即理想倾向和现实处境相背离、道德判断和情感意志相 背离。
(二)认知层次的影响
格里高利和日瓦戈医生的出身不同,其所 导致的固有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不同又制约着各 自的认知水平,二人各自的认知层次是导致命 运悲剧的关键因素。
不同于日瓦戈医生受过良好的教育,格里 高利更偏向于一个原始愚昧的自然人。他有着 传统哥萨克式的道德观念、认知方式。对于事 物的发展,他更多的是从一种原始的、主观的 角度看待,带有强烈爱憎的感情色彩和基于直 觉的善恶判定,导致了格里高利在复杂的历史 迷雾中难以形成正确的判断,找到符合历史发 展规律的道路,即他的认知层次落后于时代的 要求。他对于哥萨克的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 但在不同道路的选择中迷失了方向,从而背离 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铸成了个人的悲剧。
这也是时代悲剧的一个缩影,虽然二十世 纪初的俄国处在革命激流中,但是哥萨克人民 生活的顿河地区远离革命中心,生产力落后、 社会保守、消息闭塞,仍处于小农经济阶段。 并且,顿河地区有着比俄国国内其他地方更为 复杂的斗争形势:哥萨克人民有着传统的哥萨 克自治论的思想、苏维埃推行“非哥萨克化” 的政策打击哥萨克武装力量,这里的白军势力 比其他地方更为强大……哥萨克人民运用过时 的历史观面对新政权的建立,难免产生出无法 避免、难以解决的疑惑,在纷繁复杂的革命形 势中迷失了方向。格里高利作为一个典型的哥 萨克勇士,他在历史迷雾中探索的道路必然呈 现出曲折、反复的特点,这种命运的必然更加 增强了格里高利的悲剧色彩。
如果说格里高利的悲剧源于自身认知落后 于时代,那么日瓦戈医生的情况则恰恰相反, 他的悲剧的源头是其超越时代的认知层次。日瓦戈医生的悲剧体现的是俄国一代知识分子因 囿于时代所发出的悲鸣。知识分子深厚的学识 使其具有常人所不及的思想深度,在瞬息万变 的革命年代能更为敏锐地洞悉到蕴藏其中的规 律。然而,这种脱离实际、虚无缥缈的感触使 得他们既不能全心全意地投身于革命事业,又 在摧枯拉朽的岁月里迷失了精神家园。俄国哲 学家别尔嘉耶夫对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境遇有 一个恰当的评价: “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普遍都 体验过内心的流亡,孤独和无根性是俄罗斯知 识分子的特征之一。”正是身为知识分子的超 越时代的认知层次,导致了他们在摧枯拉朽的 革命岁月中饱受精神的煎熬,在迷茫和彷徨中 耗尽了青春。以日瓦戈为代表的一代俄国知识 分子,身上有着哈姆雷特般的延宕。哈姆雷特 “生存还是毁灭”的痛苦思索源于他的人文主 义思想与冷酷现实之间的冲突,他那超越时代 的认知层次恰恰是导致他“时代的忧郁症”的 罪魁祸首。日瓦戈医生也同哈姆雷特一样,感 受到了个人的主体意识与宏观社会的矛盾,他 既不愿顺应时代而变得麻木不仁,又没有能力 在时代洪流中改变社会,只能孤军奋战,成了 一个“单枪匹马的哈姆雷特”。
总之,格里高利和日瓦戈医生人生悲剧的 根本成因是二者固有的文化心理结构无法与时 代发展相协调,从而形成了二者性格矛盾犹豫 的特点。这种个人意识与社会发展相背离所导 致的悲剧,是具有普遍性的。肖洛霍夫和帕斯 捷尔纳克两位伟大的作家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 时代的悲剧并诉诸笔端,凭借其伟大的人道主 义思想及冷峻的思考,把这两部作品带入世界 文学的神圣殿堂,为人类留下了永久的精神财 富。
[ 作者简介 ] 彭雨菲,女,汉族,河南郑州人,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 为俄罗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