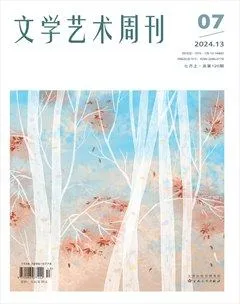《繁花》落尽:逃出“不响”的上海叙事
一
电视剧《繁花》一经播出就引起了现象级 讨论热潮,至播放结束,豆瓣评分高达 8.5 分。 可整部电视剧王家卫式的美学风格还是遭到了 不少人的诟病,大面积的光晕、浓郁的色彩渲 染、胶质的色调,以及单机位运镜下的灯红酒 绿,让人一时分不清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 上海还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原著书 迷批评最多的就是,电视剧的剧情完全脱离了 原著的故事情节,演成了“宝式”盖茨比的商 战之路。不难看出,电视剧和小说给观众和读 者展示的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两副面孔,一如波 德莱尔笔下繁华与破败并存的法国巴黎。
关于王家卫导演,大多数人的印象还停留 在《春光乍泄》《重庆森林》《花样年华》等 影片中,无论是《重庆森林》里暧昧但总归圆 满的少男少女,还是《花样年华》里摇曳生姿 的苏丽珍,都带有导演对于文艺青年们出离忧 郁生活的艺术想象。在电视剧《繁花》里,同 样是商业市场上的女性,夜东京的玲子市侩, 面面俱到而不失上海女人的“嗲作”,至真园 的老板娘李李狠辣却又多情,外贸公司的白领汪小姐看似天真直率实则隐忍,她们身上或多 或少都染上了上海这座城市的世俗气息。编剧 秦雯笔下的女性群体,构成了电视剧最出彩的 部分,这正验证了王安忆说的,写上海,最好 的代表是女人,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 勃勃。作家金宇澄在 2012 年发表了长篇小说 《繁花》。2013 年,王家卫导演买下了该书的 版权,2013 年到 2023 年,十年之约, 不负等 待。上海是一座桥,它在跨时空的维度上连接 了沪港两地相隔千里的作家和导演,同时因两 地文化因子的趋同性而有了文化深入交流的可 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香港经济最为繁 荣的时期,王家卫作为在港生活的导演,在构 思拍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时,不免掺杂 了他所熟知的中国香港生活的影子,这就导致 有人说“黄河路不是尖沙咀”。从另一个角度看, 创作不是机械的映射,被艺术化的生活场景和 生活方式,通通构成了导演独特的视听美学。
二
对于初读作品的人来说,整部小说留给读 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重复出现的“不响”,有 人统计过,全书共出现了 1000 多个“不响”。
人物间的对话看似接不下去的时候,有意制造 间离的叙事节奏时,总是以“不响”两字结 束。不响,在上海话里是不作声的意思。不 响,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以沉默的力量对抗生 活的庸常。我们看到,作家尝试化身说书人, 用类似古代话本的写法,务求通俗,而在进行 语言表达的时候,段落间又夹杂着文言和鸳鸯 蝴蝶派的古典语言文本,且借鉴了传统文人小 说简约凝练的写作方式。这并不意味着小说语 言失去其先锋和实验意味,尽管作家金宇澄自 己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先锋已经走向衰落, 取而代之的是“新写实小说”“新市民小说” 和“后先锋”。
相较于池莉描写婚姻家庭的一地鸡毛, 《繁花》虽也是取材于市民生活,但语言的疏 离和节制,带来的是惯常思维的断裂和阅读接 受的困难,读者很容易落入叙事圈套之中。这 种写法显然受到了现代派和后现代小说,尤其 是法国新小说的影响。小说中蓓蒂和她的外婆 在寻找钢琴的路上离奇失踪,姝华坚称看到她 们变成鲫鱼和金鱼游走了,她们像极了马尔克 斯笔下的蕾梅黛丝。作者本人也曾表示,最喜 欢的法国新小说是米歇尔 · 布托尔的《变》, 该小说通篇使用第二人称“你”,多角度的重 复叙述使得小说不受时空的限制,突破了传统 小说的时间线性规律。在某些长篇小说中,重 复往往是一种强大的叙事力量,就像《百年孤 独》里不断循环往复的布恩迪亚家族的姓名, 在反复的语言迷宫里创造永恒的时间之流。
形式主义者说,除了语言,什么也不存 在。语言不仅仅是一副好皮相,它似毛细血 管般渗入文学作品的肌理。导演也深谙语言之 道,因此,电视剧推出了普通话和上海话两个 版本。上海话乍听是吴侬软语,对应到这篇小 说中是口语化的单刀直入,琐碎、急促的语音 单位,夹杂着平坦绵长的音调,小说中出现的 “事体”“ 小囡”“十三点”“孃孃”“ 汰浴”等上海话方言词,如同电视剧里的“阿宝 泡饭”和“排骨年糕”一样,成了上海最具标 志性的事物,正如谁去过上海,要是学不会说 一句“阿拉是上海人”,倒显得自己不那么地 道了。记者问金宇澄,《繁花》对他意味着什 么,他回答说,使用改良方言,使用实验的元 素,用母语思维写小说,并且使用话本形式写 小说。在《南方周末》的采访中, 他则说,《繁 花》的样式上不分行,里面出现繁体字,尽量 省略标点符号,这些都和影视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要建立一个所谓的语言特征。事实证明, 他做到了,小说建立了一个陌生化的与日常话 语相悖却意味深长的语言体系。
三
上海是中国近代较早开放的港口之一,在 这里,海派文化的形成有着深厚的生长土壤, 这座城市是冒险者的天堂,它以海纳百川的胸 怀接受四方来客,各种新思想、新思潮也不断 冲击着本土文化,而那些看似故步自封的老上 海人有着深深的文化依恋。以吃来论,上海人 极讲究,小说中阿宝家被抄,一家人被迁往曹 杨新村,落魄大伯来家里做客,借他的口细数 了上海的高级西餐,中餐名堂更是多,金粉滑 金条、西湖莼菜羹、荷叶粉蒸肉、扁口八宝……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不管是小市民还是资产 阶级阶层,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例如,阿 宝和蓓蒂爱集邮,蓓蒂收集了哥伦比亚美女票 和法国皇后丝网印刷票;思南路的社会青年们 时常聚会跳舞、听唱片, “男的模仿劳伦斯 ·奥 利佛”“女的烫赫本头,修赫本一样眉毛,浅 色七分裤,九分鞋,船鞋”[1]。褪去了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外衣,追求时髦和时尚成了刻 在他们骨子里的记忆。尽管曾历经战乱和沧 桑,不远处的地方依然有贫穷和饥饿,作为远 东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始终保持着最新潮的 前沿姿态和文化品格。
[1] 出自金宇澄《繁花》,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 年出 版。本文所引金宇澄文字皆出自此书,后文不再 重复注释。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海派作家。根据 钱理群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中的说 法,海派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东 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畸形繁荣的产 物。初期的新海派接续着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商 业性传统,从白话小说的先锋时期向通俗层面 回落,第二代海派是以施蛰存、刘呐鸥等人为 代表的新感觉派。依据鲁迅对于海派文学的评 价: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足以看出海派文 学的形成与商业发展之关系。无论是哪个时代 的海派作家,总要用现代上海人的语气说上海 故事,创造自己的海派文学。
创作的发生是有意识的,但想要人物鲜 活起来,必然是沉潜到时代的激流之下有感而 发,主题先行的作品难有召唤人心的力量。因 此,评论家唐诗人说:“让每个城市的作家、 艺术家、导演等按照某些既有的城市文化去创 作,这是本末倒置,金宇澄写《繁花》如果按 照张爱玲那一套去写,就不可能是我们看到的 《繁花》。” [1] 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带着时代的 创伤印记,上海是一座城,困住了随波逐流的 饮食男女;而王安忆塑造的上海弄堂虽有温 度,却仅仅是上海小姐的青春避难所,她们最 终在时代的洪流中走向堕落或死亡。海派作家 大都注重都市中人的感觉和欲望表达,写都市 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的生命体验。金宇澄的上海 叙事显然继承了海派文学以方言写市井小人物 的传统,但不再延续海派文学写现代都市文明 “城市病”的老路,即使是写欲望,也不是人 生理想幻灭后的迷茫和沉沦自戕,而是清醒地 表达:欲望是生活的一部分,又很快被生活的 常态吞没;欲望与爱情交织,甚至超越了简单的肉体之爱。
四
小说在叙事结构上分双线叙事,分章节穿 插讲述主角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 的故事,小说中的三个男性主角阿宝、小毛和 沪生,分别是资产阶级家庭、工人阶级家庭和 军人家庭出身,他们是少年时期的好朋友。小 说通过人物行动着重描绘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到八十年代上海弄堂、街道的旧时生活风貌, 穿插了主角们的家庭变故、情感经历等一系列 人生大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 到来,物质迅速膨胀,以夜东京和至真园为活 动中心,酒局、包厢内各色人物粉墨登场,聊 八卦、聊生意经,在觥筹交错中上演了商场上 的明争暗斗和人性较量。电视剧里的爷叔说, 和平饭店是面子,苏州河是里子。和平饭店是 成年人外在身份的象征,而苏州河是可退可守 的精神领地,贯穿全文的苏州河意象成了大时 代的风向标。书中的爱情叙事也很多,主角们 的爱情关系错综复杂,作者写爱情有意肤浅化, 他无意拉低情感带给人的愉悦,他也在寻找如 何在现实层面将爱情合理化,寻找爱的归途。 也许,爱情于现代人而言不是必需品,而是消 费品,麻木的爱情带给他们的欢愉短暂且虚无。
小说的叙事内容倾向于日常生活,描写 饮食男女就是要从贴近生存最底层的地方写, 小说开头就是陶陶和芳妹的夫妻床事,接着便 写陶陶拉着沪生喋喋不休,在沪生看来,陶陶 的分享显得有点好笑, “陶陶讲的轰动,就是 某某人搞腐化,女老师欢喜男家长,4 号里的 十三点”。鸡零狗碎的小道消息和绯闻成了两 人格格不入的谈资。家长里短构成了人们最熟悉的生活场景,也是在最平常琐碎处道出了时 代变迁。就像王家卫所说,《繁花》里没有连 贯的叙事,表面是饮食男女,里面是山河岁 月。书中还写了小毛与邻居少妇银凤偷欢,银 凤出于勾引设计了一场洗浴戏码,洗浴的场景 极具肉欲色彩,随着朦胧的性意识的觉醒,小 毛跌入了银凤的“棉花仓库”中。李李和阿宝 的露水情缘虽有些香艳,他们共度的一夜,引 出了李李曾经沦落风尘、被解救继而被包养的 不堪往事,命运坎坷的她拥有一颗不屈的灵 魂。李李这个人物身上有太多的闪光点,尽管 编剧对原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但塑造的 李李依然比较贴近原著人物性格的角色。金宇 澄说自己小说中的女人都是花一样绽放,她们 释放的语言能量很美,可这些女性大都依附于 男性。电视剧改编的女性形象更为饱满生动, 编剧给女性人物注入了独立的思想,也为女性 的生存困境找到了现实出路。
小说的叙事框架依托于城市的发展,城市 不仅仅创造了更高级的文明,它的进化也带来 了不同阶层、不同阶级之间明显的政治分野, 对此作家的感受尤为深刻。阿宝一家人被迫从 皋兰路搬到“两万户”,可餐桌上还保留着从 前吃饭的基本礼仪,大伯来蹭饭吃得狼吞虎咽 虽然粗鲁,也使得一个落魄的资本家形象更加 真实。
[1] 出自米荆玉《〈繁花〉:时代琳琅,阿宝“不响”》, 《青岛日报》2024 年 1 月 8 日。
作家在小说的开篇即以王家卫《阿飞正传》里的句子开头, “独上阁楼,最好是夜 里”。在电视剧第一集中,导演让金宇澄自己 化身演员与胡歌饰演的阿宝对话,说出这句经 典话语。人生无常,行至迟暮之年,方能体会 几许人生况味,西风凋碧树,望尽天涯路,不 免生出独上高楼的悲凉感。悲凉感贯彻了整部 小说,作家不止一次在小说中提到“荒凉”, 人生不过是一场荒凉的修行。小说中的人物没 有一个人的结局是圆满的,小毛的妻子春香难 产而亡,小毛在病痛中去世;陶陶为爱离婚, 到头来是一场骗局;李李出家;沪生和阿宝都 与有过感情纠葛的女人们分道扬镳。电视剧中 也没有设置大团圆结局,围绕在阿宝身边的汪 小姐、李李、玲子是知己般的存在,却始终不 曾获得过他的真心,曾经于市井发迹、驰骋商 场的宝总在股票大战中看透名利,从宝总一夜 变回阿宝,他的退出股市也正预示着人物个人 奋斗史诗的落幕。
一切繁花落尽,终成绝响!
[ 作者简介 ] 张学晶,女,汉族,安徽含山人, 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 向为文艺学。江飞,男,汉族,安徽桐城人, 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美学与文艺评论 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 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