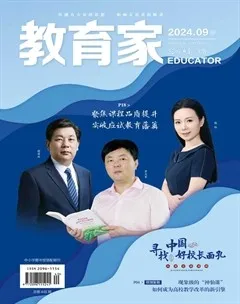改到深处是课程,关键难点在学科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改到深处是课程。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高校亟须构建一套灵活的自我调整机制,以课程改革促进“学习革命”,用“学习革命”推动高等教育“质量革命”。
近二十年来,南京大学逐步明晰了“办中国最好的本科教育”的办学思想,强调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的重要标识,优质课程是一流本科教育的核心要素。从2014年起,学校把本科教育改革的重心放到课程改革领域,集聚全校资源,实施“十百千”优质课程建设计划。计划实施以来,南京大学累计建设了优课1600余门,覆盖全校近一半课程,其中51门课程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2门课程入选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3门课程入选国际慕课平台Coursera“最受中国学习者欢迎的课程”。在课程建设实施进程中,学校更加突出“以学生成长与发展为本”的理念,强调以德为先,全面发展。课程建设的内容则注重反映学科前沿动态与社会发展需求,努力体现多学科思维融合、产业技术与学科理论融合、跨专业能力融合等。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人才培养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因而教学改革、课程建设永远在路上。从长远看,我们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以及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同时,高等教育自身也处于历史发展的重大节点:一方面,我们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每年入学新生都超过1000万人;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关注的重心从idea 嬗变为uses,大学的价值钟摆从“理想”转向“功用”,充分显示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需求以及高等教育人才观、质量观出现的根本性变化。大学所要培育和造就的,不再是像“学问大师”亚里士多德或培根那样的“以所有知识为自己研究学问领域的人”,也不再是潇洒的骑士、高雅的绅士或“修齐治平”的能吏,而是越来越多的医生、护理师、路桥工程师、建筑设计师、数据科学家、芯片设计师或程序录入员……这既牵涉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的解读与落实,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对高等院校教学变革与课程改革目标的反思与重构。我想强调的观点是:既要坚持“改到深处是课程”,又要承认“关键难点在学科”。
学科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知识分野和认知通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学科的成形与嬗变催生了现代大学。欧洲中世纪大学突破了古希腊以七艺(或者说“三艺”加“四科”)为主的课程范畴,逐步形成并完善了以学科为依托、为准绳的人才培养范式。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经、法……大学的学科组织破茧成蝶、泾渭分明,课程分门别类、按部就班,特别是学科知识的系统化、学科理论的自洽性,以及学科方法的完整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得高层次人才培养有法可依,知识传授和专业训练有章可循。规矩已定,方圆可成。这是近千年来学科、专业发展对大学人才培养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新的科技革命方兴未艾、迭代加速,学科既不断分化又相互渗透、交叉融合,社会对高等院校造就的人才则突出了多样化和适切性要求。这就使得不断强化、固化甚至有些僵化的学科培养范式,难以适应变化了的客观需要,其与生俱来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对世界及科学整体性的切割与局限,影响了人才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和整体把握现实世界的能力。诚如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所说:学科专业这盏“聚光灯”,既有聚光、投射并使某些局部“纤毫毕现”的优点,又可能会隐去背景,甚至造成部分的扭曲变形。伯顿·克拉克倡导“打开多盏聚光灯”,即形成多学科的视野,取长补短,尽可能避免单一学科在某种程度上的“井蛙之见”和辨别力的缺乏。
现代大学人才培养面临着历史性的嬗变节点,就是从单一的,以学科为依托、为导向的人才培养,转向既依托学科,又不囿于学科,通过多学科交叉造就新型人才,在继续造就高素质学术人才的同时,探索以适应社会需求、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新型人才培养范式。
“关键难点在学科”的原因之一在于,首先要让学生进入学科,接受程序化、符号化、概念化的学科(专业)训练与教育,同时又要帮助他们在“入乎其里”之后能够“出乎其外”,能够“跳出学科”,避免单一学科藩篱带来的局限与束缚,学会运用其他一个甚至多个学科的视野观照客观事物,认识现实世界。欧美一些著名学者如美国的亨利·埃兹科维茨和英国的迈克尔·吉本斯等,已经揭示了知识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嬗变。如知识生产模式1(以学科导向、学科共同体为主体,以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为目标、为宗旨的知识创新模式)仍然存在并继续发展;而知识生产模式2(问题导向,跨界行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以解决问题、提供新技术、新对策,形成新业态、新经济为目的的知识创新模式)已经出现。可以预见,大学的知识传递范式也将产生类似的历史性变革,即在以传统学科为导向、为依托、为基准的人才培养范式之外,出现以问题(社会需求)和应用为导向、以多学科、跨学科为特征的新的知识传授与人才培养范式。对此,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更需要起而行之,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与持久的实践探索。
“关键难点在学科”的原因之二在于,我们现有的高校教师,几乎清一色是在以学科为导向的人才培养范式中成长起来的,不引进新的变量,汇聚新的资源,不采取非常举措,恐怕很难开出多学科、跨学科取向和问题导向的课程,难以完成历史性的跨越。可喜的是,一些高校已经多管齐下,大胆尝试。如南京大学发挥学科综合优势,汇聚顶尖专家学者和课程资源,集全校之力建设1+X+Y三层次“人工智能通识核心课程体系”(即1门必修的人工智能通识核心课+X门人工智能素养课+Y门各学科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前沿拓展课),从知识、能力、价值观与伦理三个维度,探索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结合不同专业方向学生的认知特点与学科特色,采取集中授课、小班研讨、实践参访等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重在培养学生的数据思维、计算思维、智能思维等能力素养。更有价值的尝试在于迈出大学之门,深度推进科教融合、产学协作,与重点实验室等科研机构,以及阿里云、百度、华为等人工智能产业领域头部企业合作,开发支撑人工智能教学和考核的智能化工具,强化对课程教学各环节的有效供给。
“关键难点在于学科”的原因还在于,需要打破思维定式,激活学生,使其从被动受教的角色转化为主动寻觅、积极探索、应变成才的主人。美国学者亨利·埃兹科维茨在分析MIT副校长凡尼佛·布什当年带领学生去企业开展咨询服务时强调:“凡尼佛·布什说他的许多研究想法来自他的咨询实践。他也因此指导他在MIT的学生探索这些实践问题的学术价值。”“大学里的发明一般来自学生而非直接来自教授。作为教师,教授们提供指导和资源,但实际的想法和工作通常来自学生。”此类激活学生、“反客为主”的范例完全可以移植到知识传授方式的变革进程。例如,完全可以开发一类新的课程,它不从学科着手,而是从那种多面性问题开始。这里的焦点集中在问题上,各门学科则通过在解决问题中发挥它们各自的作用,进而加强之间的联系。此类课程(如贫穷问题研究、全球气候转暖、东西部差距之消弭等)可以由各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来修读。他们将从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的学科理论和方法,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这样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往往能够产生学科交叉与互补,使思维相互碰撞,达到集思广益的效果。学生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被动的“受体”,而具有了新的活力和新的面貌。
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改到深处是课程。所以,我们一直在路上。而真正的关键和难点在学科,我们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