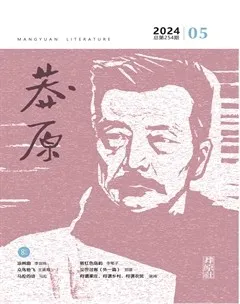何谓梁庄,何谓乡村,何谓农民
下午好,首先感谢铃木将久教授的邀请,感谢各位来到这里。东京大学非常美。我在银杏树下走了一圈儿,感受到了一种金黄色的美丽。但是今天下午我们讲的梁庄,可能比那些金黄色的美丽更加驳杂一些,也更加复杂一些。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耐心地来听。
我来这里的契机是《中国在梁庄》在日本翻译出版,这本书已经出版八年,可在这里还是新的。我原定的题目是《废墟与新生交织下的中国乡村》,其实这是一个大致的主题,根据我自己准备的讲稿看,用三个问题来当标题更为恰当:即“何谓梁庄,何谓乡村,何谓农民”。其实,就是探讨一个写作者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一种生活场景,进入一个所谓的历史的空间,在这样的视野和角度下,来观察梁庄、乡村、农民是什么样子的。
下面我想用这三个问题,来串起我想讲的内容。
第一个问题:何谓梁庄。
就像我刚才讲的,什么是梁庄?“梁庄”是我给大家写出来的,是一种新的风景的建构。这里我用了柄谷行人的观点,“从前人们没有看到过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没有勇气去看的风景”。在这里我想稍微引申一下,就是说被我们的观念、知识和情感遮蔽了的风景。
我可以举一个小的例子,曾经有一位县长给我写信,他在基层和中国乡村直接打交道,他说他看了我的书后,他不认识他所看到的中国乡村了。他每天都要去访问乡村,访问农民,但他说他不认识他们,不认识我书中所写的人物。我想,他所说的“不认识”,其实是指当他看了我的书后,他意识到他没有“发现”我所写的那种形态。
回到我自己的专业上,我自己研究中国的乡土文学,从鲁迅开始,一直到当代莫言他们这一代,你会发现中国当代文学史所描写的乡村,并没有超出鲁迅他们那一代的内部逻辑。作家们仍然会不自觉地按照闰土、祥林嫂、阿Q的形象去理解并塑造乡村生命的精神形态。它已经成为一种知识,而不是情感,也不是现实,而是进入作家的常识之中。我此处所谓的“知识”是一种固定的成见,它会忽略现实中的一种变化。
当我有这种意识之后,我在面对我自己的家乡,面对梁庄的时候,我怎么样来建构风景?这是我的课题。首先我觉得一个作家,或者说一个思考者,必须要承认,当你要书写你的对象时,你一定会受到自己的知识与偏见的影响,所以与先验的知识博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2008年回到我的家乡做考察,前后住了五个月时间,我当时写作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我想呈现出一个村庄的内部场景,内部的生命状况。我不把它作为文化的原型来描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中国作家写的乡村,我们是把它作为一种代表性的东西来读的。这个乡村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是所有乡村和所有农民的集合体。我想展示的就是“梁庄”自身,梁庄里面的一个个人怎么生活,梁庄是什么样子,是非常实在的、具体的村庄的场域。根据这样一种愿望,我就非常强调现场和现场感,强调农民自己的声音。
在反复的琢磨过程中,我最后选取了一种结构,这个结构在之前的文学史里面好像很少,是一种新的文体。以“我”作为一个梁庄的女儿,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回到家乡为基本线索,以梁庄农民的自述为中心,其中有人类学的口述历史和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这样的写作其实非常艰难和冒险,因为它需要社会学式的田野调查,也需要对人的一种明晰的理解。我当时之所以花那么多的时间来进入梁庄,是因为我想写的梁庄就是一个真的梁庄,实实在在的梁庄。尽可能接近它内部的逻辑,尽可能接近人的内部的情感。所以,虽然读者读《中国在梁庄》得到的可能是故事,但是对写作者而言,它是有建构的痕迹在里面的。
建构并不意味着虚假。书写(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接近、深入生活的内部。所以梁庄被称作非虚构写作,也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真实里面是有“我”的。这个“我”虽然是被非议的,但是我把这种个人性呈现了出来。就是我让大家看到这个故事是“我”所写的,是“我”所看到的梁庄。
在《中国在梁庄》里,建构和真实,并不是一对相互对立的概念,而是在意识到自己的限度的前提下的,一种谨慎的写作。我把我自己的立场亮出来,让读者看到听到,跟着我一起,进入梁庄,进入每一个人的房间里去听他们说话。那这个时候,你所看到的听到的,也是梁庄和这个人,非常具体的个人,而不是某一种事物的代表。
我所说的“建构梁庄”,指的是在对梁庄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再去书写梁庄,书写里面的人。在书中,我写了一个在村庄后面居住很久的流浪汉,当我要和他说话时,他拿唾液梳理了自己的头发,一个非常无意识但却极有尊严的动作。他作为一个人,他内部的这一点点儿小的要求,是非常细微的,是极容易被人忽略的。在中国的文化序列里,这种人是离群者,自己把自己抛掷在生活的序列之外。为此,我采访了镇上民政局的人,采访了我们的村主任,采访了同学,也采访了周边的村民。所有人都是看不起他的,都觉得这个人是个坏蛋,是个酒鬼。但我想做的就是突破这重重的障碍,来焕发出一个人真正的形象。
包括我书中一个患精神病症的小伙子也是。当我说想给他照相时,他把自己的衣服整理了一下,还要摆各种姿势,并问我哪一个姿势好看,其实他还是希望能够被作为一个人来对待。对我而言,因为我在梁庄住了一定的时间,我才能够慢慢地发现,这样一些人背后的东西。我才能够对我对梁庄的书写,有一定的信心。
并且,对我而言,“梁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包含了历史时间和回忆的过去,它也包含了现在,还包含着一个更远的未来。我所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有机的中国基层组织,乡村是如何被改变的。那些生命,以何种方式,何种姿态,沦落为历史的废墟。所以你可以说梁庄的故事是客观的,但你也可以说它带有主观的成分。但对我而言,它恰恰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让知识的经验和情感的经验能够融为一体,变成一个活的经验。它能够使你对看到的场景有一个更复杂的理解。这也是我所谓的梁庄。
第二个问题,何谓乡村。
“乡村”这个词在当代中国非常复杂。中国近代史以来,“乡村”这个词里面所包含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要远远大于“城市”这个词语。可以说整个中国是一个扩大了的乡村。中国农民的战线非常长,从乡村来到城市,但在城市没有户口。他们在城市里面组成一个个“小梁庄”,在那里生活,不断建构。在精神方面,“乡村”可能越来越成为民众精神危机的源头或者象征,承载了人们因社会飞速变化而产生的不安全感和一种无根感。
《中国在梁庄》写的是梁庄人在梁庄的故事,《出梁庄记》写的是梁庄人在外面,城市的故事。
以我在西安的乡亲们的生活为例。我的堂哥们当时居住在一个城中村。城中村外面是一个大垃圾场,垃圾场外面是一个大围墙,围墙外面是一个巨大的现代都市,西安。城中村完全是被废墟包围起来的,里边没水没电,因为已经被废弃掉了,只是暂居。梁庄的乡亲们在西安大部分以蹬三轮车为生。在这个城中村里聚集了约二十个梁庄人,其他相邻村庄的老乡可能有一百个左右。从更广泛意义来说,这也是梁庄。
我在那里接触到的一个最年轻的三轮车夫,他只有十八岁。他看到我的时候似乎感到非常羞耻,脸一下就转了过去,我当时正拿着相机,无意间和他发生了对视,我的脸也唰地一下红了。我被我们双方的脸红给镇住了,我想考察的是,是谁让他这么羞耻?你蹬三轮车,依靠体力挣钱,你应该是非常尊严的。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尊严之感。我想他肯定看到过他的父辈们骑车被抓,胳膊被扭下去,不断地被驱逐。包括我们这些城市市民给予他的一种歧视。所以这个小孩给我的震动非常大,我在书中花了很大的篇幅来写他。
我突然感觉到自己是有罪的。因为我也在“观看”他,他看到我时他脸红了,说明我是代表某种阶层的。我在书中也写了“我”的羞耻。我把自己的羞耻也亮出来,希望读者也能够感受到这种相互观望的,某种对立的存在。
所以梁庄既是梁庄,也是你在与梁庄对视,相互的对视。你们俩在互相审视,互相观察。这是我特别坚持的一个写法。
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是一个互相嵌生,互为存在的关系。不是完全隔离的关系,但又被隔离起来。城市中的农民,仿佛沦为现代社会的废墟。不单单是生活场景的废墟,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废墟状态。
如果一定要做一个阐释的话,中国所谓的原生态的乡村,它的伦理道德和地理,正在成为一个废墟。新生可能与中国现在的发展一致。新的道路、房屋不断增加,农民也不断离开家乡去城市,去寻找新的生活。但我觉得这两个概念都不能够从表面、从字面来看。你甚至可以反过来使用。所谓道德的废墟,正在成为新道德的土壤,而新生活新房子,可能它包含着人类生活的最大的废墟。就像我的堂哥们在西安的生活,实际上被视作现代生活的废墟,虽然他自己是非常奋斗的。我们从中可以做很多思辨,同时如果你有这e15369bf28be11b8a95fcbcfd1ed9a36b6fcf129ef0c1ee6d5d4fe1bca5640be样的思考,你可以对生活的内部有更多的了解。
第三个问题,何谓农民。
我们从“何谓梁庄”,一个具体的梁庄,到“何谓乡村”,一个暧昧不清的乡村,然后再谈到什么是农民。
我想做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农民是一个个人。这句话说起来好像就是这样子的,但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观念包含在里面。因为在中国的观念里面,农民从来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一个遭受了很多不一样待遇的群体。
下面我展示一些图片带大家看一下梁庄的一个个人。
这个小孩儿在内蒙古修车胎,书中那一章叫“白牙”。我们看这张图,只有他的牙齿最亮,在阳光照射下,特别有灵性,非常美。
这是我在采访另一个打工的人,他挣了很多钱。
这是我在广东的一个工厂里遇到的一个小孩儿,他非常勤劳,在帮着做拆线的工作。这是小孩儿在跟我玩,他非常地调皮。他的生活场地就是工厂、车间。
这是我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梁庄”,也是梁庄人聚集的地方。穿白衬衫的老人是我的父亲。
这是在青岛他们租住的房子,是青岛最老的土房子,非常的潮湿。里面有巨大的发霉的味道,我一进去就想逃跑。这是被当地居民废弃了的房子,但我的堂叔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十年。
这是两家人合租的一套房子。这是我的堂叔和堂婶,他们的脸已经有些僵硬了,是轻微中毒的迹象,因为在电动厂工作。
这是他的小儿子。如果你读了《中国在梁庄》,里面有他大儿子的故事,大儿子已经被淹死了。我在《中国在梁庄》里,采访了这孩子的奶奶,她讲了孩子被淹死的故事。所以2012年我采访的是这被淹死的孩子的父母。所以这故事非常让人悲伤,我说了好多次,它包含了人类的一种非常大的痛苦。我的婶婶在夜深人静时给我讲她儿子去世时她内心的巨大悲痛。她历尽了艰难,又生了现在这个孩子。但这个小孩子非常孤独,非常悲伤。因为他没有朋友,那个厂区有两千对夫妻,只有这一个孩子在这里生活。
这涉及另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在这里稍微说一下。在中国的农民打工者,大部分是不能带孩子的。这个小孩子之所以能够在这儿,是我的叔叔和婶婶去求情,才让他留在这儿的。为什么小孩子待在这里需要向工厂的老板求情呢?因为他们都需要加班,加班是要占时间的,小孩子一放学没有地方待,只能待在车间,工厂的老板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而这个小孩子的幼儿园同学,他们都搬到另一个新社区里面,是非常好的楼房,所以这个社区里面没有老居民,只有打工者了。我在那儿待的十来天时间里,每天去接他放学。他特别孤独,喜欢李小龙。
这个故事比较复杂,就不再讲了。从《中国在梁庄》里面他奶奶讲到她大孙子的死,到《出梁庄记》里讲他父母怎么在青岛打工生活,这里面是整个中国生活的链条,可以从中发现中国内部多个方向的复杂性。
这是在青岛,夜里下班后唱赞美诗的梁庄妇女。她们用河南的豫剧唱的,我觉得非常感动。即使这样沉默寡言的农民,他们仍然希望找到内心的慰藉。
所以什么是农民?就是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一个个生活形态,他们的表情,他们的眼睛都是什么样子。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农民被作为一个群体来对待?“农民”作为一个群体的符号完全遮蔽了它作为一个个体存在的形象,并且也成为中国普通民众的社会意识。不管在普通民众的话语里,还是在政治话语结构里,农民都是一个群体。这恰恰就是问题所在。越把农民作为一个群体来对待,越容易忽略他们作为个体的价值。从中国当代文学来看,很多作家说:“我想塑造一个农民。”这样说也是把农民单摘出来,成为一个需要特别对待的群体。我自己越来越反对这种说法。因为我在梁庄的五年,跟梁庄的人亲密地接触,跟很多打工的人亲密地接触,他们是作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活在我心里面的,他们的样貌,他们的悲伤,都是非常非常鲜活的。他们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农民。这两者的顺序是不能颠倒的。这也是我后来写短篇小说集《神圣家族》和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的最根本的一个冲动。
这是中国版的《神圣家族》,很有意思,每个人头上长一根树枝。就是内心的狂想。我写了十二个人,十二个故事。其中有一篇叫做《圣徒德泉》。我写了一个患精神疾病的流浪汉,他白天捡垃圾,晚上的任务是拿着圣经去救人。虽然他总是救错人,因为他精神有问题嘛。另一个故事叫《美人彩虹》,写一个足不出户的美丽女孩子。她开了一个大的百货店,她通过百货店来完成对世界的想象。她的百货店非常整洁漂亮,是全镇人的梦想。像这样的人在生活中是无声无息、没有人去关注的,但他们身上恰恰有自己的梦想和渴望。我特别想赋予他们一点儿光亮,想他们内部的某一点精神被认知。他们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渴望,有自己想要倾诉的东西。其中有一篇叫《到第二条河里去游泳》。这一篇是我特别喜欢的。写一个农村妇女,她自杀后躺在河里漂流,所看到的和想到的。这十二个故事,代表了我所想要写的这十二个人。
我去年出版了《梁光正的光》,刚才铃木老师也介绍了,这是一个长篇小说,以我的父亲为原型。如果你读了《中国在梁庄》,里面有一章叫“梁光正”,讲他跟政治的关系,就是从那儿延伸来的。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三年了。我从日本回去马上要回老家,因为在中国,一个人去世三周年是非常重要的。这本书就写了一个爱穿白衬衫的农民。我最大的想法是,当你读完这本书后,不觉得这是个农民,而是觉得“这个梁光正怎么这么有意思”,我觉得我就成功了。他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农民。一个一生都在战斗,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人。我从家庭内部来进入,以他的子女的眼光来看这个人。我之所以这样写,是想把梁光正作为一个人的矛盾展现出来,想把他的社会身份破碎掉。同时我也有一个大的企图,想把一个宏观的历史破碎掉。为什么我们总是把农民作为一个群体来对待,是因为在我们的头脑里,我们是把大历史作为一个固定的历史来看待的。其实所谓的历史是每一个人的历史。在一个大的历史时间下,每一个人的历史是有多个方向的。这样的历史才具有一个更加本质的存在。我特别反对一句话——“通过一个人来反映壮阔的历史”。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是把历史作为一个死的历史来看待。
回到梁庄上,我认为梁庄不是一个死的、固定的梁庄。梁庄是每一个人的梁庄。每个人的生命轨迹,每个人的奋斗方向,创造了不同的生活倾向性。在这个意义上,梁庄才具有所谓的文学价值。因为梁庄是活的,是有弹性的。对我而言,写作《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也是我自己的新的重要观念的产生过程。
最重要一点在于,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写作者,非常需要你跟生活之间有血肉的关联。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写出一个具有自我创造特征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对读者有一些启发。谢谢。
(2018年12月7日在日本东京大学的演讲)
责任编辑 刘钰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