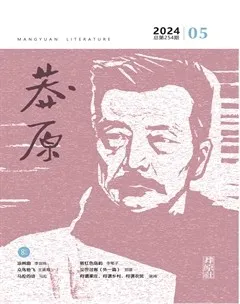砖红色岛屿
王大卫对姚旺说他昨天遇见小曹了。小曹穿着条花裙子和她姐姐逛超市。“小曹打扮起来不难看,就是头发有点儿稀,大概是营养不良吧。”王大卫说。姚旺问他哪个小曹。王大卫翻了翻眼皮说,万常青的小姨子小曹。姚旺“哦”了一声:“原来是那个二傻子呀,她叫小曹吗?”王大卫说他不知道她叫什么,只知道她姐姐姓曹,所以就称呼她小曹。姚旺笑起来说王大卫够肉麻的:“小曹小曹小曹,不知道的还以为小曹是你老婆呢。叫得这么亲。”王大卫也笑了,笑着笑着突然一脸严肃地说,小曹的确是他老婆,他跟小曹睡过觉。
姚旺经常去王大卫家看碟,那是一台老古董影碟机。现在镇上早就没有卖碟片的了,他们看的全是看过很多遍的老片子。有些碟片磨损严重,几乎放不出影像来了,王大卫还是不舍得扔。“扔一张就少一张了。”王大卫对姚旺说。
姚旺来王大卫家看碟也不全是因为碟,还因为他喜欢和王大卫聊天,准确地说是听王大卫聊天。王大卫这家伙话痨,别说对面坐着个大活人,就算对着他家的猫,也能唠叨大半天。由于他们对那些碟片内容太熟悉了,很多时候,开着影碟机只是当作两人聊天的背景音,就像你去照相馆拍照时,幕布上的那些假山假水。
一直藏在角落里的黑猫突然叫了一声,那是王大卫捡回来的流浪猫,已经养了大半年了。姚旺吓了一跳,黑猫的叫声既尖厉又脆响,就像撕一条纯棉床单,“刺啦”一下,姚旺担心猫的声带被这声叫喊给撕毁了,谁的声带受得了这种叫呢?
姚旺朝那只黑猫瞧去,见它趴在地板上,两条后腿用力朝后蹬得直直的,这让它的身体呈一个坡度很缓的直角三角形,脑袋那边高,屁股这边低,吓人的是,腰部以下的肢体正在剧烈颤抖,就像高烧的病人打摆子。
“你家的猫咋回事呀?”姚旺问王大卫。
王大卫呵呵一笑,不吱声。
“到底咋回事呀?”
“没事没事。”王大卫掩着嘴巴“呵呵呵呵”地笑。
“是不是生病了呀?”
“没事没事。”王大卫还在笑。
“不会是狂犬病吧?”姚旺说着就朝沙发里侧躲了躲,下意识地用手捂住嘴巴,似乎狂犬病病毒能通过空气传播。
“不是的。”
“可真吓死人了。”
“马上就好了,呵呵呵呵……”
两三分钟后,那猫果然恢复了正常,它从地板跳到椅子上待了一会儿,又从椅子跳到桌上,桌上放着王大卫喝水的碗,里面还有半碗水,猫用鼻子嗅了嗅,伸出粉色小舌头开始喝水。它的舌头卷起来,像用镰刀割草那样朝前一送再往回一拉,就这么一送一拉一送一拉地喝水。姚旺皱起眉头说:“大卫大卫,这也太脏了,猫怎么能跟你共用一只碗呢?”
王大卫又呵呵一笑,说姚旺对猫有偏见。“你这人哪儿都好,就是缺点儿爱心。”王大卫说,“女人都喜欢有爱心的男人,怎么体现爱心呢?当然是饲养小动物啦,呵呵呵。”
姚旺倒不讨厌小动物——他养了一条土狗——唯独不喜欢猫,他曾亲眼看见过一只花狸猫抓老鼠的情景,那场面可真是有点儿残忍呢。那只狸猫像一只小型老虎,身手敏捷嗜血成性,假如它的体型再大些,估计就该吃人了。姚旺一直不敢亲近猫,哪怕它们看似温顺,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也挺温顺,却并不妨碍它们吃人。姚旺听说王大卫每天晚上都和猫一起睡,他睡床头猫睡床尾,有时两个都睡床头,人睡左边猫睡右边。“这实在太吓人了。”姚旺心说。这猫会不会趁王大卫睡着后,一口咬断他的脖子呢?他甚至担心,下次再来找王大卫时,床上躺着一具无头尸。姚旺一直劝王大卫把猫扔了,像他一样养条狗。狗是忠臣。要是觉得住在楼上养狗麻烦,那就养点儿别的,哪怕养只老母鸡,母鸡还能下蛋呢。王大卫指指自己的家问姚旺,他倒是想养老母鸡,让他去哪儿养呢?
王大卫这套房子在五楼,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套内面积不到七十平方米,简单装修,陈设也极少,只有一组带贵妃榻的沙发,一张玻璃茶几(兼餐桌),一个电视柜,一台大屁股电视机上放着一台破影碟机,电视机旁边有一只塑料花瓶,里面插着一束仿真玫瑰,碧绿的叶,大红的花。后面墙上挂着一幅十字绣,画面不是常见的“福禄寿喜”,也不是“花开富贵”,是蓝天白云下连绵起伏的茵茵草原上有一栋挺温馨的砖红色房子,房前树荫下支着一辆自行车。姚旺看影碟时,常常有意无意瞥一眼那幅画。“住在房子里的是什么人呢?”他想,“大概是一家三口,丈夫妻子孩子,可能还有一条狗。”
姚旺指指阳台说,那绝对是养鸡的好地方,朝阳,通风,足够养五六只鸡了。
“养五六只鸡,保证你一整年不用买鸡蛋。”
“要养也是养野鸡。”王大卫说。
姚旺说养野鸡也比养猫好,猫太可怕了。直到王大卫又呵呵笑起来,姚旺才知道他说的“野鸡”不是自己以为的野鸡。
“别看她是个傻子,身材是真不赖。”王大卫又开始说小曹了。王大卫把自己跟小曹睡觉的事详细讲给姚旺听,他总能绘声绘色地讲这些事。姚旺听得极认真,这比那种影碟刺激得多,而且,他还能全都记到脑子里去,常常是,王大卫都忘记那些事情了,姚旺还记着。
王大卫说,上个月某天他发了工资,打算去超市买点儿牛肉犒劳一下自己,结果在超市门口遇见了小曹。小曹主动跟他说话——小曹会主动跟任何人说话——她问王大卫干吗去。王大卫说买肉。小曹哭丧着脸说她想吃鱼皮花生,她姐姐不给她买,还骂她是懒骨头,成天就知道吃吃吃。“我姐比地主婆还狠。”小曹说。王大卫买完牛肉,见小曹还在超市门口杵着,可怜兮兮的样子,就顺便买了袋鱼皮花生送给她。可把小曹乐坏了,癞皮狗一样边吃花生边跟在王大卫屁股后,最后竟然来到他家。
“白送上门的我能不要?”王大卫翻了翻眼珠子说。
“小曹的皮肤可白了,就跟河里的白条鱼似的。”王大卫说。
“我们就是在这张沙发上睡的。”他又指指姚旺屁股下的那张棕色皮质沙发说。
姚旺只觉得屁股像被什么东西猛咬了一口,吓得他差点儿从沙发上弹起来。王大卫又呵呵一笑:“小曹的身材是真好,前凸后翘的。”
姚旺和王大卫都是光棍,姚旺因为家穷人丑,身高还不足一米六,没有女人愿嫁给他。王大卫可不丑,个头儿虽不高,但长得好,大眼睛高鼻梁,据说他以前谈过一个女朋友,眼瞅都要结婚了又黄了。姚旺一直对这事挺好奇,却不敢问王大卫,这种事,当事人不说外人怎么好问呢?以前,姚旺和王大卫并不熟,两人名义上是一个村的,但姚旺家住在距村子三里半远的“姚家岭”。当年,姚旺他爷爷因和邻家闹不和,去“姚家岭”盖了三间草房搬了家,那时“姚家岭”还叫“茅草岭”,因遍地齐腰深的茅草得名,姚家人搬到此处后村人便管那里叫“姚家岭”了。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几年前村子拆迁,姚旺家的老房子才能逃过一劫。
姚旺是独生子,“姚家岭”上没有别的小朋友,因此,他小时候特孤单,每天都牵着一头老山羊在坡上放,直到去村里上学后才交了几个朋友。王大卫比姚旺小两三岁,姚旺对他的印象一直不太好,觉得他有点儿瞧不起人,每次在街上遇见,两人最多点点头,有时连头也不点。后来,几个朋友带姚旺去王大卫家看过几次那种片儿——王大卫收藏了很多那种片儿,有香港的也有美国的,数量最多的是日本的。王大卫喜欢和人分享那些片儿。来过几次后两人渐渐熟了,姚旺才知道王大卫是个特别有幽默感的人,爱讲荤段子,那些段子其实也没那么荤,其实都挺搞笑,姚旺总是笑得肚子疼,边笑边流泪边求饶——
“大卫,快闭嘴吧,这是要笑死人不偿命吗大卫?”
朋友们陆陆续续结婚后便不来王大卫家看片儿了,只有姚旺还来。
黑猫又在死命叫,“喵——喵——”杀猪一样。它在王大卫腿上蹭了一会儿,又跑到桌子旁用力夹住一条桌腿翻来覆去地蹭啊蹭。姚旺这才恍然大悟——闹了半天,原来是在发情。春天都过完了还发情,可真稀奇。看它那饥渴难耐的样子,姚旺既感到可怜又想放声大笑。
“该给它做绝育手术。”姚旺对王大卫说。他听说宠物都得做绝育手术,否则到了发情期它们会疯。姚旺家的大黄狗也没做过绝育手术,因为那条狗从来不拴,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它并不缺异性狗。
“你咋不带它去绝育呢?”姚旺问王大卫。
“听说那手术便宜得很,兽医站就能做。”姚旺说。
“宠物都得做绝育手术。”姚旺又说。
“不做绝育手术它们就太可怜了。瞅瞅你家的猫,真是疯了。”
不管姚旺怎么说,王大卫始终不吱声,表情还一点点儿变得凝重起来。每当他表情凝重的时候姚旺便有那么一点儿怕他,觉得这样的王大卫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几天后,姚旺再来找王大卫的时候黑猫竟然不见了,蜷缩在王大卫怀里的是只很小的橘猫。姚旺问他黑猫去哪儿了。王大卫说死了。姚旺吃了一惊,问怎么死的,不会是憋死的吧。王大卫说摔死的。
“你摔的?”姚旺的眼睛睁圆了。
“它自己从楼上跳下去摔的。”
姚旺感到不可思议:“怎么,猫还会跳楼吗?”
王大卫说那天早上他出门时忘了关阳台窗户,中午回来就看到黑猫写成一个“太”字铺在楼下水泥路上,脑袋周围全是干涸的血。
“问题是,它为什么要跳楼呢?”
“也许是楼下的母猫引诱的。”
“难道它不知道这是五楼吗?”
“它是猫,不是人。”
“猫没有高度概念吗?”
“我怎么知道?”王大卫有点儿不耐烦了,说,“快别提那只死猫了。”他抚摸着怀里的小橘猫又说:“小区的流浪猫多得很,想要啥样的就有啥样的。”说完,突然像扔一只毛线团那样将自己怀里的橘猫扔进姚旺怀里。小橘猫虚弱地叫了一声,伸出细小的爪子紧紧抓住了姚旺的衣襟。姚旺吓得全身一缩,盯着怀里的小橘猫,觉得它的眼神跟死去的黑猫一模一样,怀疑是黑猫的鬼魂附着在橘猫身上了。他不相信王大卫关于黑猫跳楼自杀的说法,猫怎么会自杀呢?求生是动物本能啊。没准儿是王大卫对那只黑猫做了什么可怕的事。
王大卫站起身去电视柜前开影碟机,两人开始看一部看过无数遍的日本片,光盘磨损相当严重,有时屏幕会突然变成一片雪白,刺得两人眼睛疼。他们边看碟边聊镇上的女人,哪个女人跟哪个男人有故事,哪个女人在城里做非法营生,哪个女人跟王大卫睡过觉。王大卫还会趁机调侃一下姚旺,管他叫“万年童男子”。最近这段时间王大卫最爱聊的是小曹。王大卫不只是跟姚旺聊,还跟厂里那些工友聊。有个年长的工友告诫他,二傻子还有个难缠的姐夫,小心祸从口出啊。王大卫便说,要是小曹她姐夫找过来,他大不了跟小曹一块儿喊他一声姐夫。
“你可真傻,”王大卫对姚旺说,“守着那么好的资源不利用。”
姚旺实在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好资源,要有好资源也不会打光棍了。
“你家院子里那个宝贝啊。”王大卫提醒他说。
“什么宝贝啊?”
“地窖。”
“地窖也算宝贝吗?”
“我要是你,就把小曹关进地窖里。”王大卫呵呵一笑,用左右手联合起来做了个下流的动作,“你明白了吧?”
姚旺家院子里有口地窖,不是用来窖白菜也不是用来窖地瓜,是预备着躲炮弹的。姚旺父亲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知道炮弹的厉害,地上建筑容易成为轰击目标,唯有地窖最安全。“深挖洞广积粮,”父亲这样告诫姚旺,“做人要居安思危,别看现在是和平年代,保不准未来会打仗。”父亲花了半个月,悄悄在自己家院子东南角掘出一口地窖,深度大约四五米,除了自己家人,谁也不知道地窖的事。因为和王大卫关系好,姚旺才告诉他的,还让他务必保密。
王大卫呵呵笑起来。笑了一会儿才说,用地窖躲炮弹那是扯淡,倒是可以藏女人。王大卫还给姚旺讲了个故事,那是他从报纸上看到的,某地有个种苹果的老头儿在自己家果园下掘了个地宫,将拐骗来的女人囚禁在里面供自己长期泄欲。这才叫物尽其用。王大卫说。
二傻子小曹连自己的十根手指都数不清,谁都能轻易将她骗走,骗一个傻子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可是,要说把她囚禁在地窖里,那就太伤天害理了,简直是畜生所为,姚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不过,他确实想跟她睡一觉,是王大卫把他心里这团欲火撩起来的,王大卫那张破嘴简直就是个吹火筒。尽管小曹是个傻子,但,就像王大卫说的,“把灯一关,傻子跟嫦娥没啥区别”。
小曹家住隔壁镇,几年前,她姐嫁给了本镇的农民万常青。小曹便常常来姐家走亲戚。十几公里的路,小曹都是走着来再走着去。小曹她姐也是个傻子,但比小曹精点儿。小曹还有个更傻的弟弟,傻到连他的两个姐姐都认不出来。姐弟三人的智商有种逐级递减的意思。每次小曹来她姐家,她姐也绝不拿她当客人,不是指使她干这个,就是指使她干那个。小曹总噘着嘴,气哄哄的,一边干活儿一边嘟哝:“成天拿我当丫鬟。”小曹会跟遇见的每个人抱怨,说她姐是地主婆,总让她干活儿,还不给她吃饱。别人就说,既然姐姐这么可恶,干脆别认那个姐了。小曹没接茬儿,只说以后再也不来了,结果,还是每隔一段时间来一次,干两天活儿,生两天气,饭也吃不饱。有时她干着干着,突然把活儿一撂就跑了。去街上的商店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去超市的货架上摸摸这个,摸摸那个,有时还会偷点儿东西吃。有一次她在超市出口被两个营业员拦住了,她们从她身上搜出来一袋开了封的QQ软糖,一袋小米锅巴,两支铅笔——小曹要送给她外甥的——还有一颗吃了半边的红富士苹果。小米锅巴和铅笔倒好说,那袋开了封的软糖和吃了半边的苹果必须得赔。小曹怎么可能有钱?超市工作人员就把她姐夫万常青找了来。万常青二话没说,一巴掌抽在小曹脸上,把她抽了个趔趄。
“傻×玩意儿,我让你偷!我让你偷!我让你偷!”
小曹刚站稳,姐夫又狠狠踹来一脚,小曹扑通一声摔在地上,咧开嘴巴哭了。
“还有脸哭,”姐夫的鼻子都气歪了,“再哭老子就踹死你。”
围观的人都劝万常青消消气,她是个傻子啊,好人不能跟傻子一般见识。再说也就两三块钱的事,赶紧赔了钱带上她走吧。
万常青不讲理了,对着劝解的人群吆喝道:“说得轻巧,两三块钱不是钱吗?谁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有本事你们掏啊?”
姚旺是从镇子回“姚家岭”的路上遇见小曹的。
小曹穿着件肥硕的长款棉衣,挽着只竹篮站在一块辣椒地头,那辣椒都已经枯黄了,尚有几个干瘪的朝天椒顶在枝头,映在蓝天下倒有几分俏皮。
姚旺本不想搭理她,不料小曹主动开口了——
“我姐让我出来割草喂兔子。”
“都这个季节了还割草呢?”姚旺心说,“不愧是大傻二傻。”
“我姐家阳台上养了两只兔子。”小曹说。
姚旺点点头,没吱声。心说,这都霜降了,草都枯了,哪儿还有什么鲜草。她姐是傻子,她姐夫又不傻。都说万常青不是个东西,看来真不是个东西。这么一想,姚旺便对小曹产生了一点儿同情,又见她身上裹着那么厚的一件大棉衣,虽说最近早晚有些凉,毕竟还没到穿棉服的时候。想到这里,姚旺的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
“我姐成天让我干活儿,还不让我吃饱。”小曹说。
姚旺只想赶紧走开,生怕自己控制不住,做出啥伤天害理的事。这时,他突然看到小曹从辣椒枝上摘下一个红辣椒丢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咀嚼着。姚旺感到很吃惊——哪有这么吃辣椒的,这东西多辣啊。
“你不怕辣吗?”
“不辣。”
“这可是朝天椒。”
“一点儿也不辣。”
“怎么可能不辣呢?”
似乎为了证明自己没撒谎,小曹又摘下一个丢进嘴巴吃起来。这可奇了怪了,姚旺心说,难道被霜打过的辣椒就像被霜打过的茄子一样没味儿了?他忍不住好奇,走过去摘下一个试探着嚼了一小口,就觉得一股火苗在他舌尖上燃烧起来。他连忙把辣椒吐出去,皱着眉,刚要责骂小曹,却见小曹像个没事人似的,已经在吃第三个朝天椒了。
“难道这二傻子有啥特异功能?”姚旺心说。
姚旺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一眼小曹,小曹也在看他,还冲他笑。姚旺招招手,让她跟自己回家吃好吃的。“我给你煮鸡蛋。”姚旺说完这话也不等小曹靠近就继续朝前走,他感到忐忑不安,路都走不稳了,就觉得脚底下的泥巴路坑坑洼洼,不小心就能狠狠摔一跤,啃一嘴泥。
姚旺给小曹蒸了碗鸡蛋羹,浇一线麻油,又撒了一小把葱花。小曹乐坏了,端着碗边吃边冲姚旺笑,跟个三岁孩子似的。姚旺也跟着笑,心说,“这傻子也真可怜,只要有口好吃的,就觉得是过年了。”姚旺又想,人哪怕是矮一点儿、丑一点儿,找不到老婆,也比傻子强啊。倘若自己是傻子的话,连个兄弟姐妹都没有,谁会管自己呢?
小曹很快就把鸡蛋羹吃光了,她抹抹嘴,端着空碗走到水池旁麻利地把碗筷洗干净。姚旺有些吃惊,大概是在她姐家锻炼出来的吧,也许,是在挨了她姐和姐夫多次毒打后才学会的,不过,会干家务也挺好,总不能成天光吃不干活儿吧?
姚旺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小曹,想起王大卫那“白条鱼”的说法,便有些按捺不住,决定将她扒光看看到底是怎么“白条鱼”的。然而,只要一想到小曹是个可怜人,他就又于心不忍了,认为该放她走。
“可是,错过这个村,还有另一个店吗?”姚旺自问。他都快四十了,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难道他不可怜?实在是比王大卫家那只跳楼自杀的猫更可怜,又有谁来同情他呢?姚旺顺从了自己体内那股汹涌澎湃的欲望——反正都把小曹带回来了,倘若被人知道了,不管他干没干,都得背上一个罪名。既如此,为什么不干?这么一想,胆子立马大起来,浑身颤抖着开始给小曹脱衣服。那件棉衣的拉链早坏了,钉了一排按扣儿。姚旺一面一粒粒拽开按扣儿,一面问小曹,王大卫是不是和她睡过觉。姚旺激动到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停了一下,深深喘口气,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还是断断续续的。小曹说她不认识什么王大卫。姚旺说,王大卫就是跟她睡过觉的那个男人。小曹还是摇头。
“看来,她确实不记得谁跟她睡过觉。”这么一想,姚旺稍稍放心了些,身体抖得也没那么厉害了。
小曹穿得可真多,脱掉外面这层外套,里面还有一层外套,是短款的灰色褂子,并不合身,一看就知道是别人穿旧的;脱掉这件褂子,里面是件起了球的薄线衣,也是别人穿旧的;脱掉线衣,底下是件脏兮兮的T恤,连T恤都不合身,松松垮垮的。姚旺已经嗅到小曹身体的味道了,由于长期不洗澡,一点儿少女的芬芳都没有,倒有一股臭烘烘的咸鱼味儿。
“应该先烧水给她洗洗澡。”姚旺心说。
当他帮小曹脱掉最后一件T恤后,那对乳房像两只因受惊而突然飞起的鸽子,差点儿撞瞎了他的眼。姚旺刚想不管不顾地伸手去抓,就看到了小曹那微微隆起的腹部,即便没任何经验,他也意识到了不正常。他用手在那腹部上轻轻拍了拍,硬得像只篮球。姚旺马上想起了朝天椒,瞬间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与此同时,他感觉自己软成了一只熟透的红柿子。
当天晚上姚旺就去找王大卫了,想跟他说说小曹的事。“小曹怀孕了,是你的吧?你也太王八蛋了,怎么能把人家的肚子搞大呢?这要是生下来,你让那个二傻子怎么办啊?”姚旺本打算这么说的,进门看见王大卫在喝酒,茶几上摆着一盘花生米和十来串烤串儿,地板上丢着一些喝空的易拉罐。姚旺问他今天啥日子,咋突然喝酒了。王大卫指指茶几下面那箱打开的青岛啤酒,让姚旺自己拿着喝。
“我想喝就喝,喝酒还得选日子吗?真是的。”王大卫说。
姚旺看着丢在地上的空易拉罐,知道王大卫又快喝高了,马上紧张不安起来。以前他俩喝过几次酒,王大卫这人酒品差,喝醉了就要哭闹,还不是小哭小闹。有一次甚至要跳楼,半条腿都耷拉到阳台外面了,姚旺死死抱着他上半身不放,又是鼻涕又是眼泪地哀求半天,王大卫才不跳了。从那以后姚旺就不和他一块儿喝酒了,这样的酒品还喝什么酒?
姚旺劝他别喝了,够了,再喝就讨厌了,没必要伤害身体。“我陪你喝点儿茶吧,你家的铁观音呢?”姚旺说。王大卫这才告诉他今天是自己三十五岁生日。“我是在给自己过生日呢。除了我,没人记得我生日。你说我可怜不可怜?”王大卫的父亲去世多年了,母亲被妹妹接去城里带孩子,妹妹准备要二胎了。王大卫一罐接一罐地朝肚里灌啤酒,就好像他的肚子是一个没有底的大缸,怎么都灌不满。
听说是王大卫的生日,姚旺也没法劝了。王大卫说姚旺是他这辈子最好的朋友,唯一的朋友。姚旺知道两个人的友谊是怎么回事,假如他们其中一个结了婚,友谊便会灰飞烟灭,是光棍这个身份将他们捆到一起的。
王大卫的舌头开始打结,通常情况下,王大卫舌头打结的时候就代表他不行了,要耍酒疯了。他果然开始哭起来,身体一下就从沙发上出溜到地上去了。姚旺忙去扶他,刚扶起来,他又慢慢出溜下去,接着便“哇”的一声,随着一股刺鼻的酸臭味儿,杂七杂八的秽物一股脑儿地从他嘴里喷出来。他像一头赖皮猪在自己的秽物里一面哭一面滚,一面滚一面哭,一面又吐出一摊新的秽物,可把姚旺愁疯了。
等王大卫折腾完,姚旺才将近乎失去知觉的他拖进洗手间,用莲蓬头帮他冲了冲衣服上的脏东西,再将他的T恤衫和长裤脱下来丢进洗衣机——姚旺不可能帮他脱内裤,眼睛甚至还要极力避开那个位置——又继续拿莲蓬头帮他冲身体,王大卫像团泥巴似的任由姚旺摆布。姚旺给他胡乱擦了擦身体,再把他拖进卧室扔在床上,又给他盖了条毛毯。
面对一片狼藉的客厅,姚旺本想一走了之,又不忍心,便留下来仔细打扫一番,把空易拉罐踩扁装进一只塑料袋丢到厨房。等他下楼的时候都快十二点了。
这件事情之后,姚旺很久没去找王大卫。冬至前一天,姚旺去超市买肉馅时遇见了一个老朋友。两人聊了一会儿。姚旺约他改天一起去王大卫家打扑克。那朋友瞬间瞪大眼睛说:“怎么?你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啊?”
“大卫那个事啊!”
“大卫啥事?”
朋友便把姚旺拉到远处一个避风角落,又递给他一根烟才说:“大卫跑了。”
一个月前的某天下午,万常青带着他那挺着大肚子的小姨子在食品厂大门口将下班的王大卫拦住了。他指着小姨子的肚子对王大卫说,听说那里面是他的种。王大卫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就跟雪人一样。他知道自己和工友们开的玩笑被当真了,要命的是,小曹还就怀孕了,现在,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王大卫百口莫辩,真恨自己那张破嘴,成天瞎咧咧,这下好了,祸从口出了。万常青身后站着两个五大三粗的侄子,王大卫是既不敢撒泼也不敢辩解。
恰逢下班时间,三五成群的工人们走出大门便遇见这种事,怎么可能放过?于是,围观的人越聚越多,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主,有人甚至还在拨火,说王大卫不该当缩头乌龟,既然把人家肚子操大了,就该把人家娶回去。
“二傻子也是人……”有人吆喝道。
“王大卫爷们儿点儿,我们还等着吃喜糖呢……”好几个小伙子跟着起哄。
万常青指着王大卫的鼻子骂了两句,让他今天务必给个说法,要么把他小姨子娶回家,要么就赔他们十万块钱精神损失费,要么就去公安局告他强奸,反正,三条路,就看王大卫选哪条。可是不管万常青怎么说,怎么骂,怎么威胁,王大卫只是低着头,不吱声。
万常青的两个侄子再也受不了了,开始对他推推搡搡,还一边推搡一边叫嚣着问:
“你哑巴啦?哑巴啦?哑巴啦……”
耷拉着脑袋的王大卫一面举起手臂遮住脸一面朝后退去,站在他身后围观的人也迅速朝后退去,圈子突然扩大出来一倍多。
“给他点儿颜色看看。”万常青对他的两个侄子吆喝道,“把他裤子脱了,让大家伙儿都看看他那狗日的玩意儿。”
两个侄子像训练有素的猎犬一拥而上,刚要动手,王大卫突然抱住自己的裤裆蹲在地上缩成了一只球。人们听见王大卫哭了起来,王大卫的哭声很奇怪,是“啊哈哈,啊哈哈,啊哈哈……”乍听上去,还以为他是被什么好玩儿的东西给逗笑的,再听才知道那是哭,继续听便能听出这哭声中暗含的绝望,后来人们才咂摸出味儿来——那是比大海更深更宽更蓝的绝望。
王大卫的哭声把两个侄子给吓住了,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一块儿去看身后的万常青。万常青抬起胳膊做了个手起刀落的姿势,他像个落棋无悔、凛然正气的领袖站在风口浪尖指挥着一场荒唐的战争。
“脱!”
两个侄子再次扑了过去,他们一个将王大卫死死摁在地上,另一个去撕扯他的裤腰带。王大卫像一只垂死挣扎的泥鳅,但,两个侄子的力气太大了,简直就是泰山压顶。王大卫挣扎几下就放弃了。人们听到他的裤腰带“嘭”的一声被扯断了,就像爆破的啤酒瓶子。伴随着王大卫喑哑的哭声,他腿上那条军绿色工装长裤连同里面的毛线裤和内裤统统被扒拉了下来。人们看到王大卫的两条腿用力夹在一起,冬日傍晚的冷风在上面激出一层细细密密的鸡皮疙瘩。当万常青的侄子将王大卫的两条腿掰开后,在场的人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所有人都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愣在了原地。躺在场地中央的王大卫如同一头待宰的认命的猪,他既不挣扎也不哭,就那么无声地躺着。似乎过了很久很久,大家突然听到一阵“哈哈哈”的笑声,那是二傻子小曹在笑——
“哈哈哈哈……”
二傻子小曹一边拍着巴掌一边笑:“他没长小弟弟!”
小曹的笑声解开了人们身上的魔咒,冬日傍晚的风吹过来,冷飕飕的,大家都感到了深切的寒意,人群开始默默散去,就像吃饱喝足的狼群,饱腹感让他们产生出无聊的空虚感。等所有人都走掉后,躺在暮色中的王大卫才慢慢爬起来,他在地上坐了一会儿,似乎在思考什么问题。终于发现了丢在一旁的裤子,工装裤、毛线裤、内裤,他将它们一件件穿上,系腰带的时候发现腰带已经崩断了,他想了想,便解开了运动鞋的鞋带,抽出来穿进裤袢里系紧。他朝小区的方向走了大约几百米远,突然就立住了,一分钟后他转过身,沿着国道朝镇子的反方向走去。
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反正从此以后人们再也没见过他。
姚旺悔得肠子都青了,都怪自己当初没及时告诉他小曹怀孕的事,否则便……“否则便”会怎么样呢?姚旺也说不清楚。
有一天,姚旺心血来潮去镇上买了一桶油漆,将他家房子的外墙涂成了砖红色,在周围植被的掩映下,他家的房子仿佛漂浮于绿色汪洋上的一座红色小岛,触目惊心。房子是他父母结婚时盖的,本是土坯房,后来在土坯外加了一圈砖,再后来又把屋顶的麦秸换成了瓦。反正,这房子就像一件粗布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就这么一春一秋一春一秋地熬,熬到姚旺父亲去世了,房子还坚挺着,又把姚旺母亲熬死了,房子还在。姚旺躺在炕上,盯着被烟熏得漆黑的屋顶,如同盯着夜晚浩渺的天空,心说,这老房子可真抗造,没准儿自己都死了,它还屹立不倒呢。
闲来无事时,姚旺会束上父亲当年束过的军用腰带,穿上父亲穿过的军靴,背上父亲的军用水壶,带着大黄狗,抓起一根竹竿,如同一位气宇轩昂的总督在自己的小岛上巡游。
他的臣民众多,有狐狸、狗獾、黄皮子、刺猬、田鼠、野兔、野鸡、野鸭子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野鸟,以及蚂蚱、蜻蜓、蟋蟀等昆虫。他挥舞着竹竿,在葳蕤的草叶间敲打着,告诫那些爬虫(蛇、蜥蜴等),趁他的铁蹄踏过来前有多远就滚多远。
他在酸枣、荆条、金雀花等小灌木丛里发现过各种野鸟蛋和嗷嗷待哺的小狐狸、小野兔、小刺猬,但他从没捡过一枚鸟蛋,也没伤害过任何一只小动物,他会吆喝着他的狗快速离去。
“姚家岭”的夜晚本来就安静,自从村子被拆迁后,“姚家岭”的夜晚就更安静了,静到姚旺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咚,咚咚……”周而复始的单调。他和他的狗坐在院子里仰头看着漆黑的天,倒扣的铁锅似的,上面缀满闪烁的星。姚旺手里抓着只手电筒,一按开关,那雪亮的光柱便如同一根长长的竹竿直入云霄。他联想到了孙悟空的金箍棒。他用手里的“棒子”用力朝天空捅去,一下一下一下……他想把天空捅出个窟窿来,看看那后面到底有什么。
夜已经很深了,他带着他的狗回屋睡觉——现在,他已经允许黄狗睡在屋里了。梦中,他又一次来到了王大卫家,两人一块儿看影碟。偶尔,他会瞥一眼那幅十字绣,那栋房子里到底住着什么人呢?他很想知道。
“是一部国产片。”早晨醒来的时候,姚旺这么对大黄狗说。
责任编辑 刘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