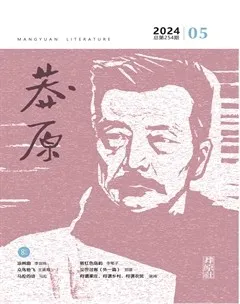生海
香房差一点儿成了燃灯街上唯一的富太太。
她长着一对注定能堆金积玉的耳朵,雪白的、宽阔的、肥嘟嘟的耳垂,露出两粒碧玉耳钉,苍翠欲滴。那耳钉刚黏上她耳朵时,她正与邻镇的高中同学夏贡谈恋爱,两人相隔一片圩海,夏贡每日坐船来找她。听说夏贡已经买好了独栋别墅,等着娶香房,燃灯街的人都觉得这是香房好日子的开头,她也打算将水果店盘出去,退出江湖,去独栋别墅里做清闲太太。
二十多年里,那对碧玉耳钉没掉落,香房的水果店还开着。今天是七月十五,据说死去之人会乘海灯船,驶入活人的梦。燃灯街飘满炸肉的香气,摆着糖果和蜡烛,成袋的金箔元宝发出粼粼的光,许多条海灯船船头挨着船尾,停在各家商铺门口,只有香房水果店的门前空着。玉竹骑车穿过街道,拨响连绵的车铃声,她长着一张娃娃脸,燃灯街上少有人说得准她的年纪。
香房奔出来,冲着玉竹飞去的背影喊道:“不来吃饭了?”玉竹在巨大的夕阳里转过头,身影被金光吞去半个,摆手说:“不去了!”
肉贩阿七拨开挂在铺檐上的猪头,伸出脖子张望,那肉铺是辆被砖头架起的绿铁皮车,常年停在香房水果店旁。阿七提着一袋卤牛肉,边走边瞧街上的海灯,不停地啐唾沫。
“算逑,谁家的灯船,扎得老大。”
燃灯街的人叫阿七“脏阿七”,说的就是他那张嘴,走南闯北后落下的毛病,讲话时“逑”“娘”的不离口,数节拍样插入,他嘴角的两撇胡子,发电报般跟着脏话抖动,终于抖到水果店门口,嚷道:“香老板,那小丫头到处窜,今天下雨?算逑了!”
“玉竹不小了,十九了。”香房闷头说。她蹲在水果店门口,往一只白瓷盘中堆血橙,因自己母亲爱吃,年年都要摆。阿七递过去卤牛肉说:“今儿生意好,不给你留就没了,知道你家那位要吃。”香房没吭声。
燃灯街上的人都知道,香房和阿七是旧相识。阿七从燃灯街上消失过几年,回来时直奔香房水果店,老板娘又叫又骂,打破了他的头,左邻右舍不知其中曲折,只知道恨与爱不过正反面,他俩的交情实在不一般。但整条街畏惧香房的脾气,不敢到她那儿多打听。
香房是女人堆里数得上的大个子,脑后束起一只高马尾,用七八只五彩发圈分截系紧,顺着脊椎一路垂下,似九节鞭在背后甩来甩去,露出一张圆盘脸,上面一对醒目的漆黑浓眉,随喜怒哀乐飞扬又垂落。若顾客在邻店排队,挡住水果店的门面,她必得出来维持秩序,货车来香房水果店送货,她也指挥司机将车停得分毫不差,绝不侵占别家一点儿地。来挑水果的居民,将有一两点儿虫眼的丢开,或伸手搓捏,香房咳一声,拖起很重的浓眉,抱臂倚着门框冷眼看,看得对方不好意思再磨蹭,匆匆称重后付钱走人,回家一量,只多不少。
有一晚,楼上旅馆的女服务员来水果店,挑了只菠萝,一对鬼火青年高坐在漆黑的摩托车上,围着女服务员打转,呜呜地喷尾气,香房掷去一只褪去半身衣服的菠萝,手边的竹签也成了武器,嗖嗖射出,后排的青年惨叫不止。两人撂下摩托,掀翻香房半个铺子,又在半夜被双双扭送至派出所。香房一战成名,被誉为“侠女香房”,还收获了一枚女粉丝——来买菠萝的女服务员维维安。
维维安是外乡人,无人知晓她真名。夏天的夜晚,香房站在楼下等维维安下班,两人在水果店门口支一张小桌,摆些炸串和毛豆,边吃边谈天,哧哧地笑,微黄的羊水样的路灯照着她们,投出两条黏在一起的影子,像一对同胞姐妹。渐入佳境时,夏贡带着从夜市买的小吃赶来,辣炒田螺或鱼丸面,都是一式两份。香房的威名,顺着小吃的香气飘到圩海那头,邻镇夜市卖田螺的老马,见到夏贡便调侃道:“你怎么敢和‘侠女’谈恋爱,不怕她砍你?”
夏贡急急地辩解道:“她那是讲义气。”
“你怎么天天傻乐呵?来买这些吃的,腿都跑细了,”老马挤着眼睛揶揄,“自己吃到没?”
“她给我留着阿七家的卤牛肉,每天都有。”夏贡咧嘴露出一板白牙,眼睛陷进脸颊肉里,融化在甜蜜中。彼时他刚提了职务,是当地商务局最年轻的副科,事业爱情两得意,想不高兴也难。
香房接过阿七手中的卤牛肉,继续埋头摆血橙。阿七被冷在那儿,不咸不淡地嘬着牙花,缩脖子朝回走,遽然转身喊道:“算逑,那傻妞又挂上她的黑船了!”阿七钻进铁皮车中,里头一阵地动山摇,他拨开铺檐上悬挂的大猪头,粉色猪头向左转了两圈,趴在阿七瘦棱棱的脖颈上,一齐担忧地望向燃灯街后的自建房。玉竹家的屋顶上,升起一只巴掌大的黑色纸船。
不止阿七,燃灯街的人都说玉竹是个傻妞,在维维安的肚子里时就被传染了。那个夏天奇热,不见一丝雨,早上七点钟,街衢就发起高热,维维安贴着屋檐下的阴影走去旅馆。她的脸很尖,一对圆溜溜的深潭样的眼,走起路寂静无声,像只白猫。她说苦夏胃口不好,晚上便不去香房那儿摆桌子了。尤其香房忙着结婚的事,夏贡提了职务,拿着一笔钱跳出体制办公司,成了老总,再无从前那些闲情逸致。他们很久不聚在一起,维维安整日套在一条宽大的衣裙里,伸出的四肢瘦了好几圈,像风中的柳枝,在热浪里蜷缩着叶子。
八月底的一个晴天,远处欻然响起闷雷,楼下的香房揭掉窗外贴的“吉店转让”,仰头望着“香房水果店”的招牌。
“你家店盘出去啦?”隔壁小超市的老板娘靠住门框,“唉,早就说你命好的嘞,你看你,耳大有福了,不像我天生受累的命,赚不到钱,也关不了店,关了店吃什么呢?就这么熬着呗……”
香房只是笑,脸庞边的碧玉耳钉眨眨眼,像在替她答话。若超市老板娘细心些,便能瞧出香房并不像喜事将近,眼神是冷冷的一泓水,两条眉毛业已枯萎,耷拉着,落在岸边。
咚咚咚,传来嘈杂的脚步,旅馆老板娘跑下楼,两只手掐着大腿,喊道:“快叫人,维维安晕过去了,说肚子疼!”
天上的雷愈近了,应声在头顶炸开,街上刮起刺鼻的腥味,玉竹与这场燃灯街阔别已久的大雨一同降生。无人知晓维维安是何时怀孕的,玉竹的父亲是谁,连香房也说不出一句话,青着脸坐在病房的床畔,看雨水汇成激流在窗上奔淌。病床上的维维安伸手去拉香房,香房扯回手,割袍断义样决绝,冰得维维安浑身一颤。
维维安出院后,整日骑着一辆自行车,到圩海滩上呆坐,玉竹就被绑在后座上,跟着母亲一起,如两颗结在一条藤蔓上一大一小的果实,形影不离。她们回来时,车座后拴着一串塑料瓶,咣啷啷穿街而过。维维安成了拾荒女,和疯子无异。
维维安经过水果店时,香房背对着街道理货,就那几筐菠萝,总也点不完,两人并不搭话,两条影子,投在夏天收尾的街道上,远远近近,沉默地对峙。
夏贡的公司倒闭,为了补亏空,小情侣商量着卖掉了新装好的独栋别墅,香房只得继续开水果店,挣钱还债,每日如走细钢丝。曾经出门坐小汽车,拎礼品回家的夏贡,一下矮了香房半个头,成了她的长随和小厮。香房忙时叫夏贡去进水果,上面盖着新鲜的,下面早已烂透,可见他念不了生意经,天生长着一张受骗的脸。夏贡脸上淡淡的,蹲在那儿捡烂果子,人们经过水果店,只听到香房的大声,结结实实压过他的低声细语,说的是吃亏是福,破财消灾这类无意义的废话。
男人事业有成时,温柔是可遇不可求的品德,锦上添花;待到落魄时,温柔便成了一种窝囊,是失败的源泉,屋漏偏逢连夜雨,散发出湿漉漉的霉味,使人生厌。夏贡就落入后一种境地了。燃灯街上的人立即觉得,拖着一屁股债的夏贡配不上香房,偏偏那对碧玉耳钉,黏在香房的耳上,展览着两人的情比金坚,大有要流芳百世的姿态。很快,香房与夏贡如约结婚,除去维维安,燃灯街上的街坊商贩都来了。维维安在街头下了车,匍匐于地,朝那热闹之处磕了个头,起身骑车离开。路人从她身边走过,并不在意。一个疯子可以做任何事,无论她做什么,都影响不了常人的世界。相当于走入亘古的时空,什么也未做。
香房新婚时,玉竹大约刚会走,六七年后,玉竹学会了骑自行车。每天早上,自行车被玉竹准时唤醒,她握紧铁钩,如骑士挥舞佩剑,冲着空院子,威风凛凛地说:“去了。”再骑车到圩海滩上去。那条藤蔓上只剩一颗孤零零的玉竹,维维安去世后,玉竹像从母亲那处继承了遗志,成了圩海的拾荒女。眼镜、项链、塑料瓶、橡皮筋……它们从各样的人身上脱落,便如水做的,云填的,飘飘悠悠,从另一个世界而来,幽咽低语,带着圩海尽头的声音。哪怕是些饼干、酸奶的包装袋,也有特殊含义,上面印着的生产日期,保不准已流浪了二十年。玉竹对这些东西,有种说不出来的痴迷,听说还有外地人专门找她买漂来的东西,当地人搞不清其中的意义,觉得不过是群怪人。
玉竹不分冬夏,赤脚板穿凉拖,一日三餐,抱着碗蹲在香房水果店门口吃,埋头专心扒饭,吃得筷子和碗交错作响,这时喊她名字,多半得不到回应。玉竹吃饭,街上的流浪猫狗也跟着开饭,她总要为它们分出几片肉,麻雀从门前经过,一样能啄走几粒米。有一次,玉竹夹起一块红烧肉,啾啾地叫着逗弄,引得一条黑白斑点狗现身,摇尾跑来,往玉竹裤腿处钻。香房丢下碗出来,一脚踹翻狗,狗打着滚发出凄厉的嚎叫,夹尾逃出燃灯街。
香房还不解恨,挥动手中饭铲,如同舞剑,与人过招,威势不减当年,骂道:“昏了头了你,从脏阿七那儿割的最好的五花,十六块九毛九一斤,菜市场买的鹌鹑蛋,我做了三个钟头,你扔给狗吃!你刚吃上几年饱饭?”玉竹缩着脖颈吃干净碗里的红烧肉,老实了好几日,不敢再随意丢弃香房的心血。
又有一日,香房水果店前蹲着一个短发青年,等青年抬起头,才发现那是长了个子的玉竹,掰指一数,顿觉汗毛倒竖,眨眼已过去十一年。“侠女香房”也香消玉减,成了老女人,水果店的招牌破了相,隔壁从超市换成运动鞋店,再换成五金店,燃灯街上的电线杆、路灯,过年时挂的灯笼,蒙了层雾一般,如潜入记忆中的老物件。可玉竹的脸也一直是娃娃模样,眉毛微蹙,嘴角下垂,颇为忧愁。等到圩海要来雨时,玉竹才如鬼上身样活泛起来,赶去屋顶上升起黑船。
今天是放海灯的日子,玉竹又升起她的黑船,注定要来雨。阿七收起门帘,锁住肉铺的门,在剧烈的风声中问:“香老板,今天不去放海灯?”香房高声笑道:“不去。”阿七钻进油腻腻的雨披中,撑起一片庇护的天地,将小巧的红色海灯珍爱地抱在怀里,那海灯他做了半年,船小而窄,十分精致,船内立着一个眉眼传神、瘦如柳枝的妇人。香房瞥了一眼,脸上的笑意被火燎了,浓眉飞扬而起,剑一般插入鬓角。她端起果盘,推门朝店里走,门在身后嘎吱乱晃。
天翻滚着浓黑,扛着海灯的路人找避雨的屋檐,街上顷刻空了。香房伫立在漆黑的屋中,走到收银台旁,掀开粉色门帘,钻进隔断间,将白瓷盘放在细桌上。香房新婚时,香房的母亲踩着缝纫机做了门帘的封边,夏贡在墙上钉了两颗钉子,将布帘挂起,夫妻俩在帘后添了张小床。冬天的晚上,两人睡在小床上,头脚错开侧躺,贴得紧紧的。门帘的粉色暗淡时,又塞进来一条细桌子,用来摆母亲的遗像。中元节时,夏贡去街尾买香,香房摆好母亲最爱吃的血橙,关了门,两人在帘后磕头跪拜。又过去两年,香房将母亲的像移到细桌的左边,将夏贡的像摆在右边。
香房轻轻一扯灯线,褪色的门帘,乌黑的细桌,油亮的血橙,没入鞘的银柄水果刀,故去之人的脸,都在眼前。那张相片拍得太好,选做遗像反倒不太好,瘦脸的男人,眯眯眼,咧着嘴,使嘴下一颗黑痣更突兀,表情抓得极妙,大笑,露出一排白牙。
好像死是一件可喜的事。
香房擦遗像,抹桌子,抚过好几遍,才一拍脑门,急急地冲出去,她来不及撑伞,头上顶着一件外套,在雨里走走跑跑。今夜别人都盼雨停,她却害怕雨一停,街上的商贩要到圩海滩上放海灯,再不快些,街尾卖香的铺子就关了。
香房跑到街尾时,雨果然停了,店主正在拉卷帘门,香房朝那儿挥挥手,深深地喘两口粗气,才喊道:“欸——等等我呀!”
月亮出来了,照得香房的圆脸晶莹发光。今夜血橙与卤牛肉的气息交织在一起,要使她在睡梦中,也闻见心碎的香气。
香房抢在街尾的铺子闭门前,买了一把香。她回到水果店,掀开滴水的外套,揣在怀里的香还是干燥的,没断一根;端起摆好的卤肉,掀开门帘,弯腰进隔断间。俄顷,从里面飘出细烟,门帘又被掀开,裂成两半,碎云似的垂在门边。
香房拂了个空,回头望,夏贡在相片里露着牙大笑,一排牙泛起光泽,再眨眨眼,才看清是细桌上摆的水果刀射出的冷光。香房也对着他笑,嘴唇把牙包得紧紧的,像在暗地里咬着牙,让人不知道她在和谁较劲。其实夏贡死前很久没笑过了,公司倒闭后,夏贡变卖了房产汽车,还余下四十万的债务。这笔钱放在过去,不难,放在目前一无所有的夏贡身上,压得他睡觉时都喘不动气。
香房想尽法子赚钱,水果店没打烊过一日,将他们的生活榨得没了水分。逢年过节时,香房还要遣夏贡去债主家送成箱的精品水果,依次还一部分钱,表明绝不赖账的忠心。街上节日气氛越浓厚,夏贡越像饮了苦酒,垂着头,抱着水果,脚步虚浮地走在附近的小区里,人仿佛落在了魂魄后头,你也不知道他的心飘去哪儿了。好在夫妻俩辛勤耕耘,多年后只剩夜市老马这最后一位债主。老马足足借给夏贡二十九万,最后还剩五千就结清,商贩们都问老马怎么敢借给夏贡那么多钱,老马笑道有侠女作证,夏贡总不会跑的。大家转而说还是老马会念生意经,别看成天卖辣炒田螺,一身的油,卖了十几年已经挣出两套房了,夏贡要是脚踏实地,和老马一样做个小买卖,不至于要将独栋别墅低价转给老马。
闲话也刮到了香房的耳朵里。圩海这一头的夜市眼见着起来了。做完亮化工程后,便被开发成景区,附近也纷纷建起小酒吧和饭馆,当地人依次吃过点评,夏贡与香房却从未踏足。燃灯街的商贩渐渐发现商机,皆派家人去海滩边摆夜市,烤鱿鱼、打冷饮、卖贝壳手链。男女老少都是摊主,大声叫卖,生意似天气火热,仿佛舀来一勺圩海的空气卖,都能赚一笔。夏贡拉着简易推车到海滩上,车里放着切好的各样水果,在一盏路灯下停脚,那位置不远不近,好似舞台为他单独打了一束光。夏贡也不吆喝叫卖,有人走近,他甚至还低下脸去,一副被香房硬逼来的模样。
夏贡没卖出几份水果捞,人群似蝗虫围上海滩,响起哭号,说孩子掉进了海里。夏贡倏然解了冻,拨开人群,两步涉进圩海。浪头一遍遍扑向岸边,送来一条黑白斑点的小狗,卷走为寻找孩子精疲力竭的男人。
他最后说:“我也是有用的。”
下半夜时,从海中出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如一尾美人鱼,将夏贡送上岸,须臾消失不见。老人抱着小狗在一旁哭,为失而复得的家庭成员喜极而泣。围观的人没看见香房掉一滴泪,她两只手捧着夏贡的脸,冷声说:“回去吧。”接着扬起手,铆足劲儿的两掌,抽得夏贡脸上的肉跟着颤动。香房松手,夏贡的头很沉地磕在沙地上。她拨开人群,歪斜着身子朝前走,长发散在风里,留下一圈被惊呆了的观众和手足无措的救护车司机。
夏贡躺在沙滩上,面含笑意,仿佛死是一件可喜的事。
清晨下着雨,两辆灵车在水雾的掩护下,匆匆穿街而过,头一辆灵车里拉着夏贡,副驾驶上坐着挺胸昂头的香房,后一辆车里拉着维维安。灵车开过灰房子,玉竹正躺在床上,抱着维维安叠给她的纸船酣睡。香房一手操办两场丧事,维维安享用豪华炉,夏贡烧普通炉,燃灯街的人称赞不愧是侠女香房。葬礼上,香房命大家统一口径,不许与玉竹谈到维维安的死,只说出远门。
没过几天,消失多年的阿七从地底下钻出来,背着一只巨大的迷彩包站在燃灯街,瘦得像个鬼。他推开香房水果店的门,倒出包里的东西,被塑料袋包了一层又一层,终于剥完外皮,露出本体:“一百二十万,一分没少,我追回来了。”阿七咽一口唾沫,蹲在地上仰头看香房,香房揪住阿七的头发,一会儿要拿刀攮进他心口,一会儿要割了他的头,阿七却嘿嘿傻笑,连跑带跳躲着香房,撞翻几箱水果,抓起前台一排串好的甜蜜蜜菠萝做防御。他发自内心的开怀,乐意承包香房的怒气,闹吧,打吧,一口气发泄出来才好。他边躲边说道:“你们都以为我跑了吧?我往北追到黑河,往西追到四川,就跟狗一样咬在他俩屁股后头,有时候想算逑了,认栽了,回来吧,可我不追回钱哪敢来见你们呢。”
阿七一脚踩中甜蜜蜜的残骸,圆竹签在脚底滚了两圈,他失去平衡,咚地倒地,头结结实实磕在收银台的尖角上,仰面朝天,捂着头叫疼,又笑嘻嘻地问:“维维安呢?我昨夜还梦见她。”
血从头上淌下,流过眼睛,眼前的燃灯街变得红了。
燃灯街的商贩们听见水果店里的吵闹声,皆从自家店铺中伸出头,如笼中的大鹅擎起脖颈,窸窣交谈。那天下午,阿七从香房水果店里冲出来,头上挂着彩,鲜血淋漓地跑到街上,嘴里喊着维维安,一句高过一句,一声惨过一声。玉竹生父之谜从此真相大白。打那之后,一有人热烈讨论起这段凄婉故事,说维维安是等待多年未果,殉情而死,香房都要纠正,说维维安是为救夏贡死的。不论何种原因,维维安已死,可香房就是这么固执。
香房认定厘清死因是很重要的事。
别人又都等着看香房,如何拿那两条枉死的命去找狗主人算账,如十几年前她为维维安出头般,演绎一段壮烈事迹。
过了头七,漏夜时分,香房果真摸到那老人的家门口。她在窗前伏下身子,见屋内灯光冷得发青,屋脊、家具都高大,那个佝偻的老人缩在其中,将斑点小狗横抱在怀里,一手端着碗,一手握住勺,舀起嫩黄的鸡蛋羹,往怀中送,小狗婴孩样搭在老人的脖颈,乖巧地张口吃饭,身后的尾巴一扫一扫,欢快地抖动。香房站在窗口,夜风从后吹来,吹得她脊背发冷。
香房回到店里,将手里攥着的东西丢在细桌上,一把银色的水果刀滑到边沿,晃晃悠悠,在半空停住了。几年后,那老人死在狗前头,狗在燃灯街流浪。
已是七月十五的深夜,垃圾桶里的野狗吠叫不止,从圩海滩回来的人,陆续经过亮着灯的香房水果店,说还债最消磨人,侠女也老啦。香房躺在隔断间里,静静听着檐前滴水的声响。
七月十五过后,玉竹好几日没在燃灯街露面,香房守在店门口,想逮住玉竹来吃饭,可一无所获。晌午,香房趴在收银台,梦见玉竹走进来,劈头盖脸地问道:“香姨,我妈死了吗?”
香房一惊,端详玉竹的脸,原本小巧的五官遽然肿大,眼珠僵在眼眶里。
“嗬呀。”香房捂住嘴。
香房面前有两个玉竹,一个是拿红烧肉喂斑点狗的傻妞,另一个则是十九岁的玉竹,她从过去那团稚气的迷雾中脱离出来,鼻梁高耸,大眼扑闪扑闪,俨然是位聪慧的女人。
“我妈给我托梦,说别人都有船坐,只有夏叔泡在海里,他求你原谅,叫你也给他放艘海灯船。”
玉竹喊夏贡夏叔。好久没听见这个称呼,这人也多年不曾入她梦来。梦中响起一阵连绵的车铃声,香房一抖,满脸潮湿地醒来。车铃仍在响,阿七骑着车从玻璃门上闪过,正是玉竹那辆早没了脚撑的自行车。香房趴在门后,射出一道冰冷冷的视线。
阿七将玉竹的车靠在电线杆旁,穿过花花绿绿的水果筐,走到玻璃门前,隔着“香房水果”“新鲜平价”的红字,回敬那道视线。香房让出路,阿七推门进来,两只鼠眼上下扫动,说:“你这店,多少年不变个样。”
香房等不及,问道:“是不是你?”
“七月十五,我们放海灯去了,玉竹终归是……”阿七咽口唾沫,好像喉咙发干,“不能当一辈子痴女。”
“你都说了?”香房的眼紧追着阿七。
“算逑,”阿七越发镇定,竖起两肩,直视着香房,“我们也有那天。”
香房听完,脖子垂到一边,如一截烧断的香。“你叫她知道了死,一个死字……她知道了,我怎么还她?”香房挣扎着奋起,猛地在阿七肩上推了一把。嘭,卷帘门阖上,阿七被隔在门外。
香房对着门,兀地骂起来,从阿七骂到出走的玉竹,从斑点小狗骂到它老死7fj68LsaVpNeBr6mpkcCTw==的主人,从老马骂到夜市管理员,骂声喷涌而出,如洪水盖过整条燃灯街,断子绝孙,寸草不生,激得脏阿七从铁皮车里拿出杀猪刀壮胆,隔着门回敬。
香房的骂声终于止住了,扶着薄薄的卷帘门,嘴无声地张合。早年夏贡在官场一路春风拂面,听多了老板们的奉承,跳出来下海创业,办了个皮包公司。那时维维安与阿七谈恋爱,有香房搭桥,夏贡才将阿七收入麾下,阿七又聘了两个业务员。前几笔还算顺利,一业务员说某地隔天急需大量花茶,托人搭上了最便宜的进货渠道,买进卖出能赚二十万,夏贡听从一试果然如此。最后一笔,货品换成了木材,价格又加了一百万,结果拉回的木材内里早被虫蛀空,品相对不上,数量也不足,联系不上供货方,更找不到要货的商家,如落水求救一遍遍打给业务员,只传来无尽忙音。隔天,阿七也消失在燃灯街。夏贡这才大梦初醒,知道命运要他摔得多狠,先要捧他到多高,从此信奉老实本分的信条,做苦工一分一毛地还债。
夏贡死去的前一夜,他还抚着香房的耳垂,喃喃道那时谈恋爱,在珠宝店说以后给你买红玉玛瑙,钻石黄金,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是只有这一对。香房毫不留情地打掉他的手,在灯下翻账本,让他与其说这些空话,不如想想怎样挤出五千块来,快些还老马,那老头子今天又来店里白拿水果,十五块钱一斤的云南大青芒,提走两大兜。她越说越生气,眼中噙着泪,埋怨老马这人贪得无厌,占着他们的婚房,若不是当初急需用钱,万万不会低价抵押给他。夏贡的脸色一下黯淡了,低声说,我做生意,总是少了一双慧眼,万幸你不抛弃我,还和我结婚,是有恩于我的,不过你到底是爱我呢,还是讲义气……
香房那时只忙着翻账本,夏贡的碎语隔了好几日才飘进她耳中。香房想,绝对是债要还清了,夏贡肩上的担子也轻了,于是当夜去奋勇救人。绝不是因她太过心急,想着侠女的信誉能做几次担保,一次次逼他褪掉最后的尊严,他才故意寻死。
这么想,又是被救的孤寡无依,救人的满腔勇气。没人做错,只将她抛到荒野,孤零零一个。钱债一笔,情债一笔,压得人不堪重负。
她不知道该怪谁。
吞下的怨是吞下猫,香房命它安静,不要使人看出端倪,却在腹中被抓出万道血痕。力竭了,瘫坐在地,老去的侠女,终于卸下铠甲,冒出泣血的哭声,耳上的碧玉耳钉,是两块被打湿的苍绿。
第二年春天,香房收到一封信,她闭了门,屏息拆开信封,抖出一张纸,信上寥寥两行字:
香姨:
我生活在内陆深处,这里万籁俱寂,可依旧会漂来东西。圩海,金碧辉煌,无处不在。托你为妈妈和夏叔放一艘海灯船,今夜入我梦来。
契女 玉竹
丁零零,从信封中跳出两枚珍珠耳钉,躺在信纸上,朝她眨眼睛。香房摸着“契女 玉竹”,又哭了一次。门外传来狗吠声,一只浑身乌黑的小狗,绕着香房水果店,呜呜地叫,香房推门出去,一人一狗转着圈相互臭骂。
香房将剩饭咣当撂在它面前,蹲下身,摘去狗身上粘的枯枝败叶,说道:“我不想管你,吃完翻脸不认人的东西。”
“嗬呀。”香房兀地叫一声。
一张皱巴巴的、褪色的纸钱,和狗毛纠缠,挂在它凸起的背上。
“傻狗,你这些日子去坟上了?”香房摸摸狗的背,手顷刻变得乌黑,狗身渐渐露出一块块黑白斑点,又说,“好狗,好狗。”
燃灯街上出了一桩奇事。天未亮透,街上的早点铺刚开张,几个早起打豆浆的人,看见水果店的香房,扛着一艘海灯船穿街而过。船上放着供果,缠满彩灯,他们从未见过粉色的海灯船,如此醒目而华丽。
这大个女扛久了水果箱,不觉得大船沉重,反而步伐轻快,闷声行至圩海边。日出未现,海滩上聚着晨泳的人,她越过白石阶,行至岸边。
海灯入水。
晨泳的人群中,有一人先脱了衣服,在头上绑紧探照灯,说:“算逑,我来打头阵。”
香房听声识人,惊讶竟是阿七。阿七一定也瞧出了她,没来搭话,不然引一堆人围观发问,她也招架不住。哗啦啦,阿七入水,灯光照亮他周身的一圈水域。紧接着,数人接连入水,他们头上绑着小灯,如一团萤火虫,漂在海面上,依次从海灯船旁游过。海灯船也渐渐远了,船上的元宝山,照出金色的光,碎在黑色的水面上,光亮越来越小,渐渐缩成几粒星子,消失在海天边际。
海滩上只留她们和一对老夫妇,静静地坐着看海。过了好一会儿,那男人站起来,说:“游一圈儿?”
身边的女人重复道:“游一圈儿。”
男人褪光身上的衣服,袒露干瘪的身躯,只裹着一条泳裤,最后,他从外套兜中拿出黑色泳帽,套在花白的头上。女人坐在岸边,看他往海边走,走过湿润的海滩,最后哗啦一沉,完全浸入海中,两臂向后摆,划水而去。
光线穿透海雾,海水轻轻摇晃,漂来一只黑色泳帽。静坐的女人,看那男人越游越远,成为海面上浮起的褐色小点,越过灰白色的海岸线,去往另一边的世界。
香房坐在海滩上,见人间的太阳又升起一次,海水变成金色。
不知他们今夜真的会入梦来吗?
“要写信问问玉竹吧。”香房喃喃道。
她耳边的珍珠熠熠发光,像在应和。
责任编辑 刘钰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