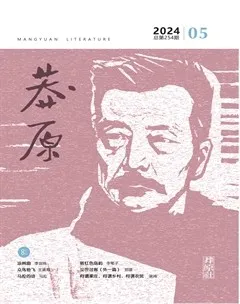租不出去的58号
已经过去一年多了,蔡婆没想到她的这间房子还没租出去。她实在想不明白,58号房子地段好啊,临近公路,对面又有海滩景区,人来人往,怎么就是租不出去。她颤颤地拿出老花眼镜,打开老人机,开始对着记录在本子上的号码一个个按下去。报数字的声音响彻客厅。
“喂,是李先生吗?”
“是,你谁啊?”
蔡婆把手机靠得离嘴巴特别近,生怕对方听不到。
“我是之前你去看那房子的房东,”她已经老了,七十多岁,驼背,平日不怎么出门,带人看房的事,她早就派给儿子和媳妇去做,“你考虑得怎么样了?”身高缩水的她坐在沙发里像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实在对不起,我已经找好房了。”
蔡婆只好假装不在意,顺便给李先生道个喜,再挂掉电话。她又接着打,但都不顺利,就算还在物色的,都不愿说再考虑考虑她的房子。
蔡婆喝口水,让嘴巴歇了会儿,又打通了一个电话,那端是女人的声音。她听到对方还没找到房,而且又不着急挂断她的电话,心里起了盼头。她说,房子靠海滩,风景好,人多,又靠公路,交通方便,无论开店做生意还是收拾出来自个儿住,都是极好的。她还拿叶秋田当例子,她是58号房子的第五任租户,在那儿开了十几年水果店,都赚够回乡下盖三层楼的钱了。
“这间房旺人的!”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
蔡婆觉得有希望,便打出最后一张王牌,降价。只要女人想签,月租少五百,不用押金,头三个月水电费也全免。
“好是好,”女人迟疑道,电话那头乱哄哄的,蔡婆听得耳腔疼,“但……但你有没有办法把房子外面的疯女人弄走?”
“疯女人?”
“对啊。只要你把她弄走,加上你刚说的条件,我们签三年都没问题。”
她问了几句,才知道有一个疯女人常常蹲在58号房子的周围。蔡婆说会想办法,等解决了,再联系她。挂断她的电话,蔡婆立马给儿子打了电话。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我们房子附近有疯女人?”
“有吗?”儿子说,“反正我带人去看房的时候,没见过。”
“你确定?”
儿子已经挂断了电话。蔡婆对儿子这么粗鲁地挂断电话的方式不是很高兴,她抓抓自己稀疏的头发,想想也不能怪他,孩子们怎么会比她还熟悉以前的老房子呢。她不如亲自去瞧一回。
隔天早上,她收拾好后出门,把手背在后背,戴了顶遮阳草帽,拎了个小袋,里面装有保温杯和毛巾。钱什么的,她不放心,就藏在裤子的暗袋里。她喜欢给自己的裤子加暗袋。太阳晒在她的后背上,久了,就烫,手心也出了汗。海风吹来,她感觉自己的皱皮肤被覆上了一层盐。偶尔有熟人跟她打招呼,但不多,跟她差不多年纪的人被土埋得差不多了。等她走过熟人的身旁,就会荡出一圈涟漪来,旁人会打听她是谁?于是解释就跟着来,像她往前走时留下的脚印。她是已经去世的高明的老婆。她男人走了二十年了,这样也好,她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在这个小镇上生活。
走得越来越近,关于疯女人的消息也越来越多。一个怪人总会给人留下更多的印象。有人说,她不是真疯,只是弱智;有人说,她不是弱智,只是不会说话;有人说她模样长得俊俏,只是长年游荡在外,晒得像条黑泥鳅;有人说她命苦,是为了逃脱男人的魔爪,才装成这样在路上走。
蔡婆停住脚,缓缓伸直腰,抬起手擦擦鬓角的汗,如果她站在那里不动,很像一尊僵硬的石雕。她喝口水,稳定了下心神。虽说目的明确,但其实她心里也没有什么主意。活了这么多年,她见过不少奇怪的人,比如把裤子拉下来吓人的老男人,拿着扫帚挑着奶罩走街的青年人,断了手臂骂骂咧咧的胖女人,但他们也不真的伤人,因而没有人去报警,也没有人去找上门。遇到他们的人只会掉回头来骂自己一句,怎么不看看皇历就出门,或者为遇到的这些人发出一点感慨,都是可怜人。他们家祖辈指不定做了什么坏事才报应到了他们头上。
蔡婆站在公路对面,穿过人行道,再往前走个几百米,就到了。她没戴眼镜,但那两个破旧的门面夹在起起伏伏的高楼里是那么的显眼。58号,长不过五米,宽不过四米,右侧留有一条小巷,可以走到后屋,有一片用围墙包围住的小土地,地的西角打了一口水井。她嫁过来之后,曾在那儿种下过白菜、辣椒、萝卜、小葱和薄荷。她也曾与男人在屋子里欢愉,生下了四个儿女,他们的嬉笑声穿过房子的土砖块,传到在地里锄草的她的耳朵里。她也曾在这儿偷偷落泪,为一些她已经忘了容貌的亲人以及她自己。她的男人原本是要推平58号,然后建两层新楼房的,但那时附近海滩还没有开发,眼前只是一片荒土,她不同意,于是他们就在离58号远一点儿,但离市场更近的地方建了房子。她还记得,关上58号的门,落好锁,举家搬往新房子的时候,有几只白鸽落在土褐色的瓦屋顶上。不知谁吹了一声口哨,这些白鸽就盘旋而上,在空中扑棱着翅膀,飞往自己的家。但愿它们没有把孩子们扔在屋顶上的乳牙带走。
住在58号附近的李嫂在家门口和她打招呼,问她怎么会过来。她点点头,声音有点儿弱,说来看看房子。李嫂家正在组牌局,人有点儿多,闹哄哄的。蔡婆躲着大家的目光,好像闯入了一块禁地。但这明明就是她的房子。她低着头想,到底有什么不对?大概是她曾经留下的气息已经被时间吹散了。
现在的58号像上了粉的姑娘。在建设新城镇的号召下,它也被请来的粉刷匠油了一层白漆。墙角还留有白点儿。但房子上了年纪,像人一样,涂多少粉,也掩盖不了皱纹。她伸手摸摸有裂纹的墙壁,不少泥块松落,留出大大小小的坑。坑洞里露出的红色砖块,像一些待人挖掘的宝石。以前58号的两扇门是木门,门上贴着面孔威严的秦叔宝和尉迟恭,后来租给叶秋田,她老公脾气大,曾经在夜里喝得大醉,一脚把门踹飞了,他们就把木门改成了铁门。两片银灰的铁门在阳光的照耀下,有种进入幻境的错觉。但蔡婆知道里面不光尘封着很多记忆,还有久不清理的蜘蛛网、老鼠屎和死蟑螂,甚至可能还有一些植物的种子。因为第一个租下58号的人,是卖草药的老中医。蔡婆见他一个人生活,才收他每个月二十块的房租。
蔡婆走到铁门前,伸手推了推,露出门缝,里面就是一片黑。死蚯蚓般的味道,涌进她的鼻子,她一连打了好几阵喷嚏,差点儿把假牙都喷出来。过往的一切已经无法再现,她的眼睛浑浊,模糊。她侧着耳朵,好像听到了一种遥远的呼吸声,忽上忽下,有点儿急促。
李嫂来到侧边,也一起瞧着门缝,和蔡婆说话:“你看得这么仔细,是不是里面还藏有什么宝贝啊。那可得小心了,别被人偷了去。”
蔡婆不答,收回脖子,轻轻晃动,放松紧绷的颈椎。她左右来回地看,没有发现什么怪异。只是她贴在墙上的招租信息褪了颜色,有必要换张新的了。
“太阳这么毒,你也走了半天的路,不如到我家歇歇脚、喝口水吧。”
蔡婆摆摆手,说自己带水了。李嫂还望着她,她想干脆回去好了,她知道李嫂这人爱嚼舌根,拉住一个人总要东问西问,她可受不了。她记得二十几年前,房子租给一个姓吴的开发廊,那人很大方,两个门面都租下来,价也不杀,给到两百。但每回来收租,李嫂都说人家干的不是正经生意,她说一到晚上,里面就有哼哼哧哧的喘息声。不到半年,发廊被举报,生意做不下去,姓吴的就退了租。蔡婆就是那时和李嫂生了气,她觉得李嫂不过是眼红她的房子能租出去赚钱。
蔡婆走到墙边,膝盖半蹲,弯腰拧开水龙头,想洗把手再回去,刚才对这房子好一顿摸,手脏了。等了好一会儿,水也没有从龙头里奔流而出。该不会是坏了?她想,这可是在房子面门上的东西,来看房的人,最容易发现。她开开关关好几回,还是没出水。不会是水井干了吧。老人常说,山主人丁,水主财,这要没水了,可不是个好意头。她想绕到后院看看。
她从暗袋掏出钥匙,插进右巷铁门的锁里。李嫂又喊了一声,让她小心,说里面久没人进去,草也不知道长多高了,小心有蛇。她假装淡定,回了一句,没事。李嫂被人喊了一声,回了自己家。她舒出一口气,为甩掉这个移动监控感到惬意。随着铁门被推开,一阵穿堂风扑面而来,把她的帽子吹掉了,她用手扒着墙,才没被吹倒。
有一股野草的味道。草从水泥地的缝隙里破土而出,长得到处都是。南方天热,什么都好长。她伸手抓了一把,仔细看叶面上的纹路,来回几遍,也没认出是什么。迎面走去,野草有高有低,像一支形象不佳的仪仗队。腿肚子忽然痒起来,她弯腰隔着薄长裤抓挠,手指头能感受到皮肤上的那片红块在蔓延。她又反手挠挠后背,一时竟感觉全身都痒起来。
她骂了一句,叶秋田你这个短命的,我只让你装水管,没想到你连后院都改了啊。从前后院是沙面的,穿着拖鞋走在上面有一种清脆的声音,不像现在是啪嗒啪嗒的。种过薄荷的田埂也不见了踪影。她看到围墙的东角建了一间小房,这肯定也是叶秋田的杰作。她心想,叶秋田还真是蹬鼻子上脸,真当这是她的家了。她忘了自己什么出身,她可是从山里来的。叶秋田很早就跟她说过,要买她的58号。不过,她才没那么傻,留着房子出租才能钱滚钱、利生利。她跟高明一直都是生意人,她做海鲜生意的时候,叶秋田都不知道有没有在山里出生。她嗤笑着想。
她用袋子扫荡着野草丛,被吓到的蚱蜢一个个蹬腿跳得老高,还有一些跳在她身上。她边走边念叨几句密语,让栖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各路妖魔神灵不要怪罪,终于走到了那间小房。她用手试探性地推了推门,“吱”一声,门开了。她还在想这是用来做厨房还是做厕所时,几块干粪便赫然刺进她的眼球。旁边还有一坨新鲜的,几只苍蝇飞在上面,一些血色的液体流淌在周围,那应该是尿。一闻到尿屎味儿,她就弯腰呕吐。这是谁干的!她抹掉嘴角的残渍,眼里生了怒意,一定是叶秋田。叶秋田在报复她,她不想让她再租出去,那样58号就只能再回到她的手上。她想买下58号。
她用手撑着膝盖,直起腰,喘了口气,又走几步,移到屋子的后壁阴凉处。她靠着墙,上气不接下气,于是用力呼吸,想尽量平复下来。她掏出水杯,拧开瓶盖,抬脖子准备喝一口水,西侧的杂物堆却突然一下子塌了。那些木片、竹段、砖头、箱子、瓶子哗哗四散开来,一条“黑泥鳅”赫然出现在杂物后。蔡婆吓坏了,水杯也掉在了地上。她下蹲,双手后抓,脚向右挪,做逃走的准备。那条“黑泥鳅”也不动,只是敞着嘴,像只温顺的猫一样看着蔡婆。“黑泥鳅”嘴里垂着项链一样长的口水。
蔡婆原本想走,但看这“黑泥鳅”的样子,心想她该不会就是别人所说的疯女人吧?她深吸几口气,决定把问题一并解决了。
蔡婆问:“你叫什么名字?”黑泥鳅不答,只是睁着灰白发空的眼球看她。蔡婆又问:
“里面的屎尿是不是你拉的?”黑泥鳅还是不答,嘴角反而有了笑。蔡婆再问:“你是怎么进来的?”黑泥鳅把一个瓶子里的水倒进嘴,然后把空瓶子放进她手上有点儿鼓的化肥袋里,又紧紧抓住化肥袋的口。
“我跟你说,别以为装傻就没事了,你这样私闯我的房子,我要是报警,警察一定会把你抓走的。”蔡婆为自己找到了支撑,便大了胆,一点点儿往前走。她走近了,才发现那黑泥鳅倒是好模样,瓜子脸,丹凤眼,细眉毛。只是头发剪得像狗啃似的,参差不齐,有几处还秃了。可惜了。
“你到底叫什么呀?”蔡婆半弯在她的面前。黑泥鳅仍然不应,只是蹲着笑,张着嘴,口水越流越多。“你真不会说话?”蔡婆伸手抬起她脏黑的脸蛋儿,“你是个哑巴?”黑泥鳅的口水流到蔡婆的手上,蔡婆原本想擦在裤子上,但想到带了毛巾,就去袋子里掏。
毛巾刚出袋口,黑泥鳅的眼睛就亮了,她喜欢上这东西了。她的化肥袋里有棕色上衣、黑色裤子、小瓶子、毛茸茸的玩具,就少这么一条毛巾。毛巾很干净,淡紫色的,正合她的心意。她伸手拿住一角,往自己的怀里拉。蔡婆没留意,来了一个屁股蹲儿。
“你干吗?这可是我的毛巾。”
蔡婆伸手把毛巾拿回来。黑泥鳅又拉。几个来回,黑泥鳅胜了。蔡婆索性大方起来:“给你好了。但你拿了我的东西,就得听我的话,以后别在这儿游荡了。行不行?”
黑泥鳅不答,起身往前走,想去拿那个掉在地上的保温杯。蔡婆骂她贪心,得了一还想二。蔡婆一扭头,看到黑泥鳅裤子屁股处有一大块儿红血印。
“你的屁股咋啦?”
黑泥鳅不应,把保温杯里的水往嘴里倒。不知道是热还是怎的,她往外喷了一点儿。终于杯子里一滴水也不剩,她把它塞进了化肥袋里。
蔡婆看着黑泥鳅走过水井盖,来到围墙下,她踩住水管,要往上爬。蔡婆叫住她,说爬墙危险,铁门开着,让她从门那儿出去。黑泥鳅不回答,继续爬着。但水管太细,塑料拖鞋踩在上面又滑,围墙也高,黑泥鳅一时爬不上去。她溜下来几次,前臂被墙面的石头刮出丝丝血痕。蔡婆这才确定,这女人真是疯了。
“你别爬啦。”蔡婆走到黑泥鳅身边,抓住她的手,往铁门的方向指了指。黑泥鳅却铁了心,非要从这里爬出去。蔡婆看到挂在墙上的她,像待卖的黑皮旗鱼。“你傻,我可没空陪你傻。太阳都把我晒蒙了。”蔡婆走近黑泥鳅,“我跟你说,从今以后你可别来我这地儿了。我们就当啥事也没有。”蔡婆伸手拍打黑泥鳅的屁股,像小孩子闯祸要给一点儿教训的样子。她收回手,发现手上有一股异味儿,不是鱼腥味儿,那味道她熟悉,是……她边挪脚,边想,是……是经血味儿。她顿了一下。
咚的一声,黑泥鳅掉在水井盖上。蔡婆扭回身子,骂道:“你真会惹事。你怎么不掉进水井里死了算了?”这话像水蛭一样,穿过溪水,悄无声息地黏附到人的腿上,慢慢吸取红色的血液。蔡婆心里一阵麻痒。要是黑泥鳅真的掉进井里,会不会更快活一些?放鱼归生,也是靠海人积德行善的事。这样她的58号房子就能租出去了,一年几万块的房租也能到手了。
黑泥鳅发出嘶哑的声音。不知道她是被摔出了什么毛病,还是痛经,只见她双腿缩着,一只手压着肚子,在井盖上剧烈打滚,另一只手在地面抓出了五条长长的痕迹。她的脸色苍白,汗珠打湿她的鬓角,又顺着脸颊滑下来。蔡婆仰脖环绕一圈,这四角的天空没有监视器。她一步步走过去,像念经一样念着,她这是在做好事,做好事,做好事……
她用手机拨通了电话,这是她第一次拨打110。她的内心像在海上,摇摇晃晃。
“救命啊,这是海滩景区对面的58号房子,有人在这儿胡打胡闹。”
她说完马上挂掉了电话。她在心里预计警车开来的时间,觉得差不多了,才拾起一块砖头。
叶秋田骑着摩托车来到58号时,附近已挤满了人。她下了车,用手紧了紧车柄上挂的塑料袋,防止它滑落下来,里面装的全是给老王女人的馒头。老王女人,就是日日夜夜游荡在这条街上的女人,她从不撑伞戴帽子,所以晒得很黑,被人叫作“黑泥鳅”。叶秋田也不记得黑泥鳅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她的水果摊边的。把化肥袋搭在肩上的黑泥鳅,用眼睛直勾勾看着摊子上的各种水果,口水直往下掉。叶秋田大声呵斥,让她快点儿走,别挡着她做生意。隔壁的李嫂,给她端了碗粥。可能就是这碗粥,让黑泥鳅对这儿留下了特别的印象。每次走到这儿,她的脚就好像被注了铅,走不动了。她用眼睛扫荡着周围,等着别人拿出一点儿东西给她。于是,她的化肥袋就越来越满,像个百宝箱似的。
两个年轻警察已经开始盘问围着的人群。叶秋田抓住一个人问发生了什么事,那人说,他在李嫂屋子里打牌,突然传来很大的声响,有人喊救命。李嫂出来看,才知道出了大事,都流血了,那么大一摊。他用手比画着。
“咋回事?”
“听说是黑泥鳅和58号的包租婆。”
“谁……”叶秋田原本想说“杀”这个字,但又被这个字所带有的威力震慑。她虽然叫黑泥鳅帮她看住这个房子,但她绝对不会让她去杀人。她只是想和黑泥鳅交换一些东西。只要她隔三岔五出现在58号附近,她就给她送点儿吃的穿的。谁让蔡婆要涨房租,还涨那么多。一开始是五十,然后是一百,三百,五百,一千,现在还想涨到两千。也不看看这破房子值不值?要不是她还在这儿做生意,政府都要把它当危房处理了。可谁让她对这破房子有了感情。她在这儿住了十六年,她的孩子从这儿去上学,她就站在水果店门口看着,眼神不离开一步。她的孩子出远门回来,下了车就有一个歇脚的地方,就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重要的是,她的水果店从一个门面开成两个门面,人人都知道这儿有一个水果西施,她家的水果又便宜又新鲜。她不甘心,为什么她不能在这个小镇上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
“是谁……伤了谁?”
“不好说。”那个人挠挠头,“我胆子小。听说有血,我都不敢去看。李嫂去得最快,她应该一清二楚。”
“李嫂呢?”叶秋田四处张望。
“刚被带走了。警察要她去问话。”
叶秋田向人群望去,高高低低,男男女女,或站或坐,他们互相交换着信息,企图摸索出事故的全貌。只有叶秋田害怕了,黑泥鳅可别供出她来。叶秋田跺跺脚,让自己别多想,这么多年,她都没见过黑泥鳅说话呢。哪怕是她家人来找她回去,她都没说过一句话。可是黑泥鳅要是因此丧了命,或者坐了牢,她怎么过得去?她是罪人啊!她这种人,会不会下地狱?她打了阵寒战,心里觉得逼压,脚一软,瘫坐在地。她开口喊了一句,老王女人——又接一句,老王女人——声音凄凉。两个年轻的警察回过头,让她快起来,说没出人命,而且谁伤了谁,还未下定论呢。叶秋田一听,眼泪流了下来。
只有天知道,蔡婆当时拿砖头敲自己的脑袋时下了多大的劲儿。她认定,疯子打人也是要坐牢的。
责任编辑 申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