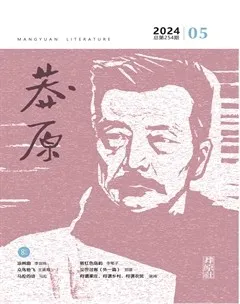尘世过客(外一篇)
温暖而孤独的旅途
1
黑夜来临,列车启动。我的旅行又一次开始了。
我的心沉入黑夜之中。这样的黑夜,让我感到孤独,也让我感到了温暖。
这是我熟悉的感觉,是我在无数个这样的夜里透过窗棂,透过林立的高楼苦苦寻找的感觉。
音乐响起。站台上的灯光与人影已然不见,城市的喧哗与噪声恍然远去。透过车窗我看见了远天上的星星。虽然它们还有点儿模糊,但我毕竟看到了。这是城市之外的星星,远离了日常生活的星星。它们远离了污染,它们是一些纯净的星星。
这样的旅途,我已经经历了无数次;这样的旅途,在以后的生活中我还将继续经历。
2
我热爱这样的旅途,不管终点在哪里。
并不是想做个地理意义上的旅行者。山水之美对我虽然极具诱惑,但它们并不能让我感到深入骨髓的欢乐。我分明知道,无论什么样的山水,都不能融入我的血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也并非怀着一种“理念的乡愁”上路,想要在陌生的旅途寻找所谓“梦中的家园”。我已经过了爱做梦的年龄,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找到什么。
但我还是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你为什么喜欢这样的旅途?
我一遍又一遍欣喜地对自己说:这是一种感觉呀。有哪一种感觉能够如此深刻地进入你的魂灵之中?有哪种感觉能够让你感到如此孤独又如此温暖?——而这种孤独和温暖正是你想要的。
我只知道,我喜欢变化。我不喜欢所有的日子都一模一样。我不喜欢让我的周围天天都出现同样的面孔、同样的事情。对于一成不变的生活,我感到的只有两个字:恐惧。对于那些过于熟悉的环境,我下意识地想到了两个字:逃离。
岁月在流逝,在以一种不为我的意志所左右的方式引领我一步步移向黑暗的深渊。在这种流逝中如果看不见新鲜的气息,那无异于时间的停滞。如果时间真的能够停滞,也许我可以从容地选择一些满意的生活细节。但现在,它像飞驰的列车,不回头地冲向了黑暗,留下一个孤零零的我在站台上寂寞地重复着数枕木的工作。我不愿意。
3
所以,当我在这个城市里待了太久的时候,我就渴望着开始我的旅途。
也并非是因为对所谓“城市文明”的厌弃。在我看来,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古典”还是“现代”,都包容了让我感到“厌弃”的内容,但同时,也让我看到了文明中美好的一面。对于我来说,住在城市里,想要逃避僵虫一样的生活,我必须尽可能地离这个城市远一点儿。
不能长途旅行,我就坐上通往郊区的公交车。公交车载着我,穿过一节节尘土飞扬的道路,穿过一个个村庄,来到一个长满了荒草的土坡前。我会静静地坐上半天,听着草长莺飞的声音,听着血液在血管里汩汩流动的声音,我仿佛找到了一个真正的自我。
不能开始旅途,我就采取其他的方式。无论去哪里,只要我能够寻找一些变化,找到一些与我的庸常生活不同的内容。
有时候,我的寻找到了疯狂的地步。
每过一段日子,我就要收拾一回屋子。桌子已经好久没擦了,上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把上面的东西移开,把桌面的灰尘抹去。桌子露出了本来的面目,显出了与往日所不同的亮色。我还是感到烦闷,我把它换一个位置。
过一段时间,我把桌子再移回来。
我把拉乱了的书归位;我把书架上层的书移到下层,再把下层的书移到上层;让所有的书脊排成一条线;再把移到上层的书移回下层,把下层的书移回上层。
4
在一个广场。
一边,一个盲人在拉二胡。听不出来是什么曲子,像是某一首流行歌曲吧。旋律并不算优美,盲人的手法也并不很娴熟,但是他拉得投入。虽然匆匆而过的人们并没有几个向他投来关切的目光,但他依然很投入。他似乎对此情此景毫无感知,他只是一个劲儿地拉着,脸色平静而温和。
广场的另一边,有一群年轻的姑娘。这群姑娘穿着简单大方,领着一群孩子在跳舞。在音乐的鼓点中,在众人的围观中,看得出,她们跳得高兴极了。她们跳的是什么舞我不知道,她们的动作并不整齐,她们中有的人一边跳一边还伸伸舌头摇摇脑袋。有的人跳错了,就发出一阵笑,惹得围观的人也跟着笑。
我呆呆地望着广场上的一切——一个盲人、几个姑娘、一群围观的人。
我想加入到这些人群之中。我想坐在盲人的身边,用僵硬的手指拨动那深情的琴弦;我想加入到这群姑娘之中,用笨拙的身体扭出忘情的舞姿;我想加入到围观的人群之中,用张大的嘴巴传达出会心的笑。
但是我不能够。我不属于他们之中的任何一方。沧桑不属于我,年轻不属于我,历练尘世之后的沉静、温和,毫无来由的欢乐都不属于我。甚至,连片刻的忘情都不属于我。
我只有选择一个人离开,寻找那种属于我的熟悉的陌生。
此刻,我感到了沉静,感到了旅行的快乐。我有一种飞翔的感觉。这是我孤独的旅途,也是我温暖的旅途。因了这种孤独我感到温暖;因了这种温暖我更感到了孤独的快意。
尘世过客
一个大男孩把一个木球高高抛起,然后用固定在额头的橡皮坑接住。橡皮坑刚刚容纳下那个木球。男孩把木球扔得一次比一次高,然后一次一次地接住。旁边敲锣助阵的人在吆喝着:小心球落下来砸着眼,把眼砸瞎了;砸着鼻子,把鼻子砸断了……
两个十二三岁的女孩,躺在两张鞍马形的宽凳上,一次次把两口大缸蹬向高处。最后,她们竟然互相把缸蹬向对方,而对方很容易地用脚接到了……
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开始表演“软功”。她先把身体弯成蛇的形状,一点一点把臀部放在自己的头顶。接着她弯下腰,用牙齿咬住一个铁环作支撑,让自己的身体腾空而起……
这是在一个名叫“民俗旅游文化节”的现场。
这是一个露天的场地,一块红地毯区分开舞台与空地,演员与观众。
人很多,声音很嘈杂。人们在欢笑着,为这样的演出而倾倒。他们鼓着掌,跺着脚,挥着手,为这样的演出喝彩。
一瞬间,我仿佛回到了多年以前。
多年以前,我多次看过这样的演出,多次为这样的演出喝彩。
那时候我在南阳的乡下。隔一段时间,我们的村庄总会来几个人。他们放下不多的行李,敲一阵锣、打一通鼓之后,就在村子中间的空地上开始表演。
他们把一柄长长的铁剑吞到肚子里;他们含一口煤油,从口里吐出火焰;他们用嘴唇顶着在空中乱转的碟子;他们牵着猴子,让它作揖、磕头;他们用布把自己围起来,在布幔里进行木偶表演……
偏僻的乡间,平时几乎没有什么娱乐。他们的到来让我的村庄充满了节日的气氛。村民们聚集到那片空地上,用一种喜悦的目光注视着他们眼中的明星。在那种目光里,劳作的疲累与生活的艰辛似乎已经远去,他们的眼里只剩下欣喜。
锣鼓的声音落下来,这些浪迹天涯的人们一边收拾着自己的东西,一边派一个或两个人提着口袋,一家一家收取“演出的报酬”。
乡间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他们收取的,无非就是馒头、粮食。没有人会给他们钱,也根本没有人有钱给他们。他们就提着这些馒头、粮食离开了我们的村庄。他们从什么地方来没有人知道,他们将要到哪里去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只是村庄的一个过客。在这里停留一下,便永远消失在村民们的视野之外。
的确,我从来没有看到同一支队伍再次来到我们村庄,也从来没有看到同一个人表演两次。他们只是偶尔出现了一下,带给我们半天的快乐就不见了。望着那条通向远方的道路,你可能恍然产生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他们真的来过?
我们的村庄,已经没有他们留下的一丝痕迹,此生我将永远不可能再看见他们。他们的形象将在我的头脑里渐渐模糊,我将再也想不起来他们那谦恭的眼神、游移的眼神,只有他们的身影,将会随着一朵云、一缕阳光,在我的眼前飘动。我只知道,尘世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来无影,去无踪,他们曾经给我带来了欢乐,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只是我生命中匆匆的过客。很多年之后,我只能不太准确地回想起这个日子,回想起这个日子给我带来的惊讶和激动。
从小时候开始,对于这些浪迹天涯的人们,我就心怀羡慕。我为他们的技能而倾倒,心想自己什么时候能够从袖口里变出一只鸽子就好了。并且我更希望自己脑袋的硬度能够使几块砖一齐断开。
即便是长大之后远离了我的乡村,我也时时怀着一种接近他们的冲动。我曾在一个拉着 《二泉映月》 的盲人面前站了半天,倾听着曲子犹如听着一个千年之前的旅者的诉说。那哀婉的调子让我不由得泪流满面,让我在一瞬间产生一种浪迹天涯的冲动。
但是我不能够。我只能按照被设计好的轨道,周而复始地进行着每天的日常生活;我只能按捺下焦虑与无聊,忍受着乏味和疲惫,忍受着洪水一样漫无尽头的空虚。
他们表演的时候离我这么近,我可以轻易地看到他们脸上最细微的变化;但是他们离我又那么遥远,我走不进他们的内心。我难以知道,在他们的笑容背后藏着什么内容,就像我永远也不知道明天的生活到底怎样。
我不止一次想到,他们没有家吗?
肯定不会的。他们有家。他们有自己的父母,有自己的妻子儿女,他们和所有人一样盼望着天伦之乐。我坚信。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自己那片涌动着柔情的土地,选择了出发?他们的心灵已经足够坚硬,已经可以抵抗任何外来力量的伤害了吗?难道他们不害怕思乡的愁绪像贼头贼脑的蛇一样盘踞着,等待着在每一个闲暇的时刻来噬咬他们的内心吗?
表演结束了,那个接木球的大男孩蹲在城隍庙的廊柱下。
他默默地注视着这里的人。人们已经转移了注意力。人们在看下一场表演。没有人再注意他。他的表演只存在于一个叫作“刚才”的时间段里。“刚才”已去,他和他的表演已经像一阵风一样,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了。
我也蹲过去,问他是哪里人,学习这样的表演需要多长时间。我问他们这个小团队的情况。
他回答了我。是那种简短的回答。他很谦恭地说他们的表演水平不行,这样的表演其实很简单,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学会。
我问他:你们这个团体里有没有人因为表演得好而被选入专业的杂技团,能成为在正规场馆里演出的演员。
他说:没有。从来没有。
短暂的沉默后,我接着问他:你这样一直演下去,等你年龄大了,不能演出的时候怎么办?
他说:不能表演了就教别人练。还可以带团。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从他的眼神里看不出来,对于这样的生活,他究竟是充满了欣喜还是心怀不满。
很明显,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他已经习惯于从另一个地方来,在这里作短暂的停留之后再一次出发。他不属于这里。他甚至不属于任何地方。没有一个地方的山水、风习可以挡住他远行的步伐。
自然,他们是为了生活,为了在艰难尘世寻找到放置一个碗、一双筷子的空地。
但是,还有那么多人,同样面临着生存的压力,同样需要应对活着的艰辛。为什么偏偏是这样一些人浪迹天涯,而另外一些人在一片狭小的土地上哭喊着出生、躁动着成长,而后寂寂地死去?
这是一种选择。他们选择了做滚滚红尘中的一名过客。他们所想做,所能够做的就只能如此。
我不可能走近他们,更不可能走进他们的内心,所以,他们让我产生了神秘的感觉,让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是一种诗意的生活。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我看见的所谓诗意,本来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诗意也就是艰难的另一种说法。天下没有永远诗意的生存,就像没有人能够永远保持脸庞上的笑靥。更何况他们永远风尘仆仆、行色匆匆,也许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生活已经令他们麻木。
但是我知道,总会有一些像我一样的人,在表演的场地之外,默默地注视着这些尘世中的过客。他们注视着这些行走在江湖上的人们,怀着一种亲近的心,为他们所感动,并为他们祝福。
责任编辑 刘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