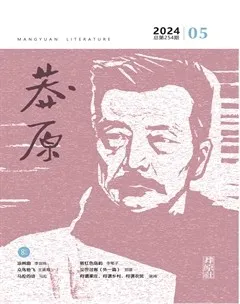飘移
红色的夜晚升起来。他拉上办公室的窗帘,把信纸分出六张,写满三页,用两副即将磨透的刹车片压住,挨着刹车片的是化妆包,这个象征成功人士精致妆容的东西,看起来滑稽得要命。他抬起脑袋,对着镜子照了照尚服帖的妆容,又一次郑重地拿起笔,写着思忖已久的话。上司若再不回信,那么他的位子就摇摇欲坠了。
自从进了车行,他始终没有朋友,只有一本画册时刻相伴,那是他的主心骨。后来信纸、刹车片、化妆包才加入进来,他让这些东西包围着画册,就像画册需要它们保驾护航。画册每页都画着一只猫跋扈的身姿,钢笔画的草图,简洁有力,越看越回味无穷——仅对他而言。他苦笑一下,拿起刹车片,往画册上一敲,又开始写信,四页,五页,六页,写罢,他推门出去,不久,楼道里一片火光。
次日,展厅一片沸腾,几名警察围着圆鼓鼓的他。他原以为会围上来许多人,因此不停地整理把身子束得像桶一样的西装。终于,他停止手上的动作,奋力迎接李立似笑非笑的脸、下属偷看李立的眼色,以及透过脑袋与脑袋间的空隙最终喷向他的那股气流。他把脸仰得很高,一对用过精致眼霜的小眼睛正雾气腾腾地扑闪着。
李立笑了,而且笑得发颤,他便把脸垂了下去,但打扮得比女人还闪耀的脑袋愈发醒目。同事都说这脑袋里外都有毛病,谁都知道画册上的那只猫来自这颗脑袋的杜撰,不过为了“玩”有所依,直到升官发财。
他不承认,非得说确有其事:那猫是自个儿养的,早年,那猫喜好追着轻若翎羽的尾巴玩儿,整条身子时常盘着,四只毛茸茸的小爪子藏起锋利的甲刀,显得软萌可爱。但在雷雨季,两枚火炬般的猫眼就会拧成一束光,光内藏有鳞片,哗啦啦作响。尤其当雨帘击打窗子,雷吼肆虐时,鳞片潜入腹腔,生成螺旋,带风,拍击喉舌,喷出的音色,盘曲着,飞升着,令他瞬间感受到骨骼分离般的震荡和重生的喜悦。可惜的是,在闹得最欢时,那猫像一团被投掷的毛线球,毁于车辙中。为了纪念那猫的本领,他把它搬到纸上,作为他现有功夫的秘籍。
伸长脖子的,咬住嘴唇的,支棱耳朵的,看得出他不打头阵,没人愿意主动出招。不过等他一开口,情势就变了,喧闹声排山倒海,看得出,想堵住他话头的大有人在。
李立大手一挥,很有气力地在空中画了个圈,当初李立竞岗时,也是这个动作。李立懂市场,会写方案,就连设备上出现的英文故障代码都读得懂,竞岗说这些就像唱歌时一个调子唱下来,哪个懂汽车的能不会这些?他当时暗笑李立的彪劲儿,因为他心中早就有底。而此时,他心中没了底,不敢喜滋滋地回忆毛遂自荐那次的盛况。他只得干咳两下,与李立的笑声碰出一串像岔气一般的火花。
这事应该汇报上司。李立声音高过众人。他喘了一口气说,不行,我们自己处理。先汇报吧!警察给出建议。大家都想早些结束这个晦气的清晨。怎么和上司解释,还有这次未完成的信,还有必要发出去吗?不管有无必要,他都要抢在汇报的前面,就像当初毛遂自荐一样。
他记得上司第一次约见他,他声情并茂地讲述那只猫,他说三年内要给上司建一支队伍,可他作为一个后勤人员没有用车调配权,并当面感叹用武之地尽失。说这些时,他的小眼睛紧凑而积极地眨着,隐约还会听到他轻叹一声,他说自己属于空气为之上弦的一类人,有使不完的劲儿。后来,他就越说越激动,像一只缺了几条腿的螃蟹在奋力舞蹈,令场面一下子凝住了。上司闷声不语,种下心思。他继续谈着,在他红着眼圈出来后,不几日,便做了销售助理,有了摸车的机会。那晚,车在院子里发出撒泼样的嚎叫。后来,他靠这个出尽风头,各地经销商代表纷纷说这才是会玩儿车的人。呜——呜——,发动机轰鸣,隐约振翅,离地面巴掌高,卷起的微尘像绝命的舞蹈。回来后,没有一个人不高看他。高人配高位,他当选总经理,谁的舌头也不会长出一截。可真正从事工作时,那些舌头一时也没停下来过,他心里苦。
眼见着警戒线撤走,他便一头钻进办公室,直到下班才出来。一整天,他抱着画册不撒手,不知这次该如何毛遂自荐,他认为自己的决定下早了,并且大错特错,还有三百多天呢。人真是个奇怪的动物,前不久还感觉三百多天没人配合,就和一天差不多,现在却觉得三百多天就是三百多个机会,怎么能自剪羽翼呢?他一边伤心地捻着画册,一边拿出信纸接着写,话锋一转,不再引咎辞职,而是讲述这场火灾的意外性,表达他会处理好善后事宜的决心,并且再次保证了车队一事,笔到之处少不了汗渍,由此毁掉好多“最后”一页纸。写信时,门外发出好大的声响,细听原委,像唱,像说,像笑。心烦意乱地放下笔,他把门悄悄拉开一条缝:每个同事都像拜年,搓着手前往事发地一番观察品鉴,然后兴高采烈地下楼,等着李立发话。车好卖,不是他的功劳,是车的功劳,更是李立的功劳,他和同事们唯一的联系就是报表和周二的中层会,何况中层会早成了李立的部门会,他被撇得远远的。砰!他摔门用的力气过大,手腕酸麻,再提笔时,胳膊也跟着痛起来。他朝着桌子俯下身,重重地把前额砸在桌面上,额上顿时一片青红。再开门时,动静全无。
他用胳膊夹着画册朝前走,至车前,低头弯腰坐了进去,发动车子,顺势猛打猛收方向盘,撕完大地,撕空气。
近傍晚,天空又是一片红色,但仍然不肯痛快地下一场雨。雨天玩儿车,能量翻倍,画册后面的故事,就是这个理,没有说理的地方怎么行——猫在雨天变异,他更会变异,晃瞎李立的眼才好,这理也就通了。李立不服他,是尽人皆知的,但李立写信给上司,恐怕只有他能猜得到,否则他的信怎会石沉大海。他挪了一下位置,看了看陆续下班的同事,一个个照旧兴高采烈。他祈祷下雨,渴望在狂风暴雨的夜晚,来一场火后盛况。妈的,这两年,天都跟他作对,就是不给水,他朝天翻了个白眼,余光收尽李立的身影。这家伙出来转了个圈,又回去了。他把身子往下压了压,装作休息的样子,一只手摸向手机,拨了上司的电话,无人接,再拨,还是无人接。留言后,几分钟过去,未有回复,这不亚于往他的心头又放了一把火。沉默了一阵子,他觉得上司一定会找他,换谁出了这样的问题,都得提前通气的。上司找他,他就说线路起火,他找上司,也是说一样的话。
拿定主意后,他便掂着手机,直起身子,心里充满了渴望,就像当初他渴望李立主动退出竞岗一样。李立那人不识相,非得用业绩抗衡他,尚未搬进预备办公室时,二人就吵得不可开交,他上位后,李立不吵了,继续在新店保持原职位,但一直没闲着,下班后常到某个地方,一待就是一宿。他这次早些下来,还是想盯李立的梢,他相信李立每回前往之处,一定与工作有关,或者与他有关。过去,他弄不明白,也不愿多想,但这回他要借着这场大火搞清楚李立究竟在干什么,否则,在上司面前,他会跟不上话的。话说回来,具体地点他再熟悉不过,在新店开业后的近七百天里,他们常会同一时间出院门,然后各奔东西,而自己开出千米左右,会果决调头跟上李立,把车停在一栋居民楼不远处,居民楼前面有一大片望不着边的场地,适合练车,他常不无嘲讽地远远看着李立。
今晚,李立仍然把车停在楼前,车内亮起些许红光,忽暗忽明。
天黑得彻底了。车内也完全黑了。
嘀嘀,一条短信息进来,吓得他差点儿从车顶翻出去。一串省略号,李立发的。他的位置与那栋楼之间的视野并不好,他深信李立看不到他。
手机又响了,有了刚才的经验,这回他没被吓到,而是懒洋洋地拿起手机,上司让他明早到集团。他一阵狂喜,也无心弄清李立到底要在这里做什么,只是感觉眼前的楼更像是一片废墟,也只有李立适合常来常往。驱车返回时,他又觉得后悔,应该多待一会儿的,说不定李立也收到了上司的短信,现在正掉头返回,急着补写未完成的信。他的信也还没完成,想到这儿,一拍脑壳,再想,再拍脑壳,脚下使劲,悔意全无,车简直像要飞起来般赶了回去。
他用几乎磨透的刹车片继续压住剩余不多的信纸,重复写道:我会把这支队伍建成。写完,又随手在空白处画了两副相向的刹车片。他决定明天一早就走,现在他想睡会儿,到时候可以精神饱满地去见上司,红光满面更好,说明他心底无私。
他枕着胳膊,闭上眼睛,不知睡了多久,一阵错位的撕地声充斥耳道,一听就是没有好好研读画册。刚开业时,他要店里同事人手一本,新同事以为他爱猫,便爱不释手;老同事则把画册送给李立,李立会论功行赏。时间一长,新同事拿画册不再当回事,有一回,他竟发现有人拿画册来垫工具车。至于李立回收的那些去了哪里,同事守口如瓶。他的信就是碾着这份迷茫,才开始不断输送的。信中,他不断地讲那只猫于他的重大意义,那是他赫赫战功的标志性证据,还有血液在皮下的挣扎,骨骼的扭矩。妈的,他气这份心血无人看,现在他正盯着已完成的信,竟不好意思补写这些了。不,重复的东西,才有力量,他又添了一页信纸。
院外“哐啷”一声,正扭圈的车,凹下一大片。他连忙拿出手机开始录像。李立先是下车,围着车转了一圈,又往墙上瞅。他“扑哧”一声笑了,从没听说撞坏墙的,这外行,吓得不轻。这让他一时间又不气了,收了手机,拍了拍口袋里的七页信纸和画册,不想补写了,李立那副尊容,能玩儿出什么花?!
第二天一早,他去见上司,免不了寒暄一阵。他想短时间内把上司对此次失火的态度弄清,很难,尤其上司的两道目光频繁直射,弹幕一般,激得他既想哭又想笑,这是把他当车玩儿。这时,他看到桌上有一个装得鼓鼓的信封,顿时有些手足无措,一只手彻底插进口袋,“唰唰”声四起,他突然觉得不应该来。若上司问他这两年在业务上有哪些进步,他还是不会操作电脑,更看不懂简单的英文,还有普通话也不标准。他先前的思考在他看来,就像那场火一样多余。果然上司问了业务上的事,他支支吾吾,“唰唰”声更剧烈了。
他说,一切听从安排。上司伸过手,他主动上交了口袋里的信,上司把信塞进信封,快要被压爆的一堆纸,发出拥挤的声音。业务弄不好,什么也不用说。上司说这话时,眼神里是一团黑色的幕布。
远处雷声震耳,红了几十个夜晚的天空,终于有了声音。他说,要下雨。待上司凝视窗外,转过脸时,雨帘已扑向了窗台。他三步并作两步去关了窗。有豆子打在油布上的声音,他说。还有呢?上司问。他想再说点儿什么,嘴里却跑不出词儿,就像真话说多了,会消耗真话的力量,与造作的假话反而成了亲缘。他理不清这个道理,但知道把嘴闭上。
咔嚓!轰隆!雷电齐鸣。上司急速地抬眼,直视窗外,探身拿信,一边故作开启状一边问道,那场火烧得大吗?开始装修了吗?他实在不知道要怎么解释。警察走后,李立的电话就打到上司这里了,事故的情形,上司比他了解得清楚。此时,他脸上的妆容早掉了,要能多挤出点儿时间,起码脸色会好看点儿,现在他确实把自己推到了另一端,离不离职,喊一声就行了,这场难过的谈话,会在变本加厉的天气中显得波澜不惊的。他咬紧牙关这样想着。上司走过去,和他握了几下手,然后开门,用目光送他走。他上了车,透过雨幕看见窗户里上司模糊的后脑勺。
雨丝打在前风挡玻璃上,想着由会议、酒桌、西装、漱口水、高光笔,鬼斧神工凿出的日常,他也想化作细流,做一次毁灭性的逃离。他的头因此碰得青肿,车子像只发了疯的狗,呜咽着向前冲。
被风雨扯掉的枝杈散落在院子各处。他一边撑起伞,一边向站在不远处的李立打了个招呼。李立扭头回去了。二楼已投入装修,他的心更烦了,想先回去化个妆。回到房间,他却推开化妆包,把剩下的几页信纸全撕了。信纸似乎一直引他剥开内心,仿佛脱光了衣服,各个角度地展示。恐怕李立也看到了,他打了一个冷战。别看李立比他矮一级,但在上司那里的待遇不比他低。看刚才他那副胸有成竹的模样,八成知道他去上司那儿了,现在上司和李立可能已经在说他了。就像他写过的信,多半意思不就为了把李立说得不具备应有的能力吗。这就是人与人交往中看不见扯不断的烂绳索。
李立在门外喊,请不要跟着我。他不知道声源冲着哪里,也不想过问,反正要走的人了。
这场雨看样子一时半会儿不会停,东投西窜,雨丝极其不正常。他提心吊胆地摸出手机,给上司报了个平安,立马收到一个“好”字。
他欣喜了一会儿,就夹着化妆包转向洗手间。李立跟过来,侧着脸说,一起去吧。他想,肯定上司刚发来的“好”,李立也收到了。他挤出一丝笑,问,有事吗?李立说,有。
先上了妆再说,走也得走得漂亮。镜前的他满脸水珠,用毛巾揩干后,先是水,再是乳,后是霜,他小心地扭动着同事取笑他的发源地——高光笔,合紧盖子后,他又看了看上司的那个“好”字,再次笑了笑。可能上司回心转意了呢。
刚想舒一口气,紧箍身子的西服下摆的两粒扣突然砸向地面,在此之前,它们常来回扯锯,他不在乎这些小玩意儿在不在身上,只觉得这样一来,舒服多了,掀开的衣角像两只小翅。
走吧,李立在门外喊。由于天气不好,天暗得快。他揉揉眼,掀开帘子,黑黄色的天像大地上的泥石流,连续劈向东方的闪电,碎成无数根银针。他说,这天不好。李立笑了笑,玩儿车的人还怕这个?探手向前,他接住递来的两粒纽扣,未等开口,李立说起信的事,问他去读了多少。他脑瓜子一紧,为自己猜对了而难过。
两人一前一后上了同一辆车,他推到一边的画册被李立挪至两人中间,似乎要有一场争夺。他不想在李立面前说画册了,这个被李立像废品一样收购的东西,令他气短心虚,但李立的表现却是另一番模样:一阵翻书声,就几页,搞得车内像是一场读书会。李立问,他答,李立从未有的谦虚在他面前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吸着鼻子,觉得李立只是为借画册上讲过的在雷雨天的变异羞辱他而已。他也没客气,直接问,你的车呢。李立说车坏了,正让售后加班修理。他扭头,说,撞得不轻吧。说罢内心一番喜悦,这是他两年来第一次有赢了李立的新感觉。
待他轻车熟路地奔向空场地时,李立放下画册,摸出一把钥匙,指了指那栋楼一扇未关的窗户,说,进去看看吧。闻言,他将车停在那栋楼前。像培训基地吗?李立略有所思地问。他不回答,急吼吼地进了单元门,谁知脚底一软,打了个趔趄,待爬到五楼时,更是瘫坐了一会儿。他觉得自己是惊吓过度。他不知道自己怕什么,就像某些人一直把担忧储备在心上,好像时刻都在怕。他的画册,就是他的怕。最早,他怕画册在上司心中不受重视;前两年,他怕画册不能树立总经理的威信,巩固权力;现在,他怕画册的谎言被彻底拆穿。所以当下,他一定要用行动,使谎言变成真实,这么一想,身体就得到信号了,瘫软后,他开始连续深呼吸。
满室灰尘,跳跃飞扬。这间房子不是住人的,他嘀咕着跟在后边。一排架子上全是牛皮纸包的书,有的纸已经起毛了,像他车上那本。部分书立在墙边,垒出一道形状,看着很像今天雷雨下的某幢建筑。他转到另一侧,另一侧也是书,他正想顺手拿起一本时,听到有人拍掌,声音断断续续,好像每一声都在决定下一声拍还是不拍。李立离他很近,他说,我认识这些书。李立说,可它们不认识你。他的目光从书架移到李立背后,思量了好久,说了一句,什么意思。这些书加了钢尺,压不断。说着,李立捧起一本,用书脊敲着书架,书页扬起漂亮的弧度,趁着电闪雷鸣,那猫身变化无限,让一旁的他及时地把恐惧挂上毛茸茸的脸颊。
殷小波,你把它当发财猫了,呸!李立吐了一口。他整个身子弓成一只虾米的形状,似一个拜金者,乞求更多的钱。突然,他发疯样的嚎叫,就像第一次玩儿车,三魂吓走六魄,待耳鼓能正常输入闪电的噼啪声时,他才安静下来,说,刚才七八只猫围着他,混着乳猫的奶味,成年猫的胆识,还有在春季的撒欢,因为鼻腔与耳道通着,便有了湿漉漉的悲鸣,这才一下一下地叫着。李立冷笑,故事里的人和猫,从来没有讲到尽头的时候。
风刮响了窗户,树影咆哮如雷,他冲下楼,十指并行各归其位,照方向盘一拨拉,原地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子时的夜空喷出更威猛的飓风和暴雨,房檐上的沙石,打落的叶子,叮当,咚咚,刺啦,轰——,和轮子一起扭着双麻花飞舞起来的空中交响,像无数骨头的错节声。
李立俯视数股水辙子被暴雨秒删,又被轮胎秒印,后来就只剩下一片稀泥。再然后,就是他的身子突然被电击般地抽搐,黄的、绿的、红的,一股脑地喷射,车轮下一片争奇斗艳。良久无声无息。
听到什么声音了?他虚弱地问走过来的李立。
了不得,了不得!一脸雨水的李立说,怪不得做了总经理,没人玩儿得过你。又说,确是群猫起舞。
一团灰色的光晕从乌云里迫切地游离着,地上的雨水涨得很满,又急匆匆地向四处分散。他,这个从车内探出大半个身子直发抖的男人,张着嘴,任凭雨水冲进他的喉咙。吞着雨水的男人,像是吞了铁,竟然一动不动,转瞬,直接“扑通”一声仰躺在水洼里。李立揽起他的腰,连拉带拖,扶着他上楼。浑身瘫软的人格外沉,李立喘着气,每上一个台阶,两个男人的胸都会贴紧一次。
回到五楼,他醒了,捂着脸抽泣,说吓死他了。天上那团灰色的光晕依然晃动不止,李立趴在窗台往下看,水涨得更高了,李立从窗台撤回脑袋说。
什么天气,这样会感冒的。李立拉了拉他满身泥浆的衣服,攥了一手泥。
谁也好不到哪儿去,他握了握李立的手,泥掉了,手又凉又硬。尚未关闭的骨节像被什么刺到,一番难以遏制的绞痛。
那些信,不全是你的,李立说。他说,知道。
写信、发消息,早已不算是独门绝学,就像走在街上,随手捡个硬玩意儿在土上划几笔那么简单,只是他这几笔,险象环生,他苦笑着,搓着刚与李立握过的、正渐渐变暖的手。
他说回去吧,他不想听另一个关于信的故事。
然后,他们在雨中,疾驰。湿闷的驾驶室里淌出酸浊气,任谁都不想多说一句。这台玩儿得相当体面的车,像战马对不对?他问,然后就睡着了。他的胃和心脏机能大不如以前,觉得可疏通的气孔越来越少。
车停在院中央。他们各自回去冲了热水澡,换了衣服。他上了妆,等天明就让出职务。
雨一直下。他摁着胸口和胃睡着了。一早,李立来找他,让他例行检查,预备办改了模样,这装修简直是神速,地板光亮,玻璃晶透,广告彩页扬出美丽的菱形,轻轻地摩擦着高处的琉璃灯柱,他穿着笔挺的西装,瘦成一道闪电,往车间走去。他们亲切地喊他殷总,然后职级高的会请教他问题,此时他则会拿一支铅笔在白纸上画草图,甚至他会操作车间的设备,英文也看得懂。他和他们再提起摸车的事,争先恐后自不必说。有人敲门,他醒了,是李立上来请他下班后一起喝酒,这话一出,谁也没再看谁。
他知道喝酒意味着对谈的双方要有雅量,就像当初李立失败后的退出。这回要退出的是他。
刚下班,他就坐进车里,李立也坐了过来,他让李立开,两人换了位子。李立原地飞车,晃得二人像快镜头下的交谊舞,待停稳后,李立凝视前方。不要想离职的事,李立的话比持续的雨弹多了些温度。谁不会客套呢?他想。对谈讲技巧。难不成耳边要听“快离职”这类的话?那把火就足够了,他往窗外看了一眼陆续掉下来的枝杈。
信上没写什么,放心。他想留个好名声,怕信里的只言片语招来另一场冰冷的雨。李立也说信上没写什么,放心。能听到对方心跳是早晚的事,没想到这么响,这么急,一直在耳畔沸沸扬扬。坦诚说了吧,他的信不就是冲着这些话不断地矫枉过正,上司才没有信心读下去吗。第一次见面,上司就摸清了他的脾气,多愁善感,把心思编成故事,跑去摇尾乞怜,也算是工于心计的一把好手,可李立的眼睛比上司更毒,将早已看出的眉目,不断通过信件宣讲,过犹不及,也被上司扔到一边。他们嗅出上司对彼此的看法:李立可以稳坐销售经理,却不具备提升的机会,而他,没让他下来,是因为没有更合适的人接替。想到这里,他从容地看向窗外,又转过脸看李立,想来个不吐不快。
别说了,都过去了,李立说。
听着,就行了……他把刚才所想到的毫不见外地一股脑儿往外喷,他的话似乎是个无底洞,直到他打了一个很响的喷嚏,才摇下车窗,闭了嘴,侧过头朝外看。
我得辞职了,他说。
竞岗后再说吧,李立的声音低得要命,
三年一竞岗,上司惯用优胜劣汰的法子,好像专给他们制定的。情况多了不咬人,李立很有把握地说。
你一直在想车队的事?他问。
两人对视很久,目光一个比一个细腻,像透过薄纱的光。雨小了,灰色光晕露出金黄色的芯,半根豆芽状。
他把车又开到楼前,接过钥匙,李立刚说了,他想来就来。他立在书架前,将书挨个扒拉,然后指向小腹部位空着的两枚扣眼,不知为什么,新换的一身干净西装也被他残忍地揪去两枚扣子,这时他口里的苦杏仁味道渐渐扩散到肩胛和趾骨。这样能舒服些,他说。
这些书早晚得烂,李立说,别看了。他停下手,红了眼圈,觉得谎言的尽头就是无法兑现的现实。
回去的路上,光滑的车辙映出浮光,形如黑夜里一块长满苔痕的石头,李立边翻书边说,你愿意写故事,写得却很烂,其实,你不用写,你就是一个故事。
他把头埋向方向盘,移开了掌控方向的手,汽车在雷雨中滑行。待他稍稍安静时,见李立正琢磨着那副磨透的刹车片,他没吱声。过去,每当他迎向李立落在刹车片上的目光,都会轻咳一声,希望有个契机。当下,他说拿去吧。雷声远了,闪电累了,剩下连串的雨滴不厌其烦地敲着玻璃。
李立现在想什么,他不想知道,就像这雨停在哪年哪月哪日一样不必关心。
李立并没回应他的话,而是继续举着刹车片仔细地看,把刹车片上的锈色直接晃进了脸颊。待汽车开回院子,李立丢下他,冲向车间。那台被留在车间的车大灯忽然亮起来,轻啼一声飞出院子。他连忙开车跟了出去,动作格外敏捷。前面李立开的车在雨幕中几乎飘起来,他驾着后车猛追不止,轻微地眩晕感袭上脚踝、肚子、两肩和脑壳,他从不晕车的,刚骂了一句,一侧雨刮刷因为摇得太猛,忽然折成两截,雪上加霜,他又骂了句。他拨了李立的电话,想让前车停下,却寻不到信号,再拨,就变成无应答了。
他只得摇下车窗,寻着新的视线,呐喊。画册被风掀湿,闪电劈开猫身,分解成数条弯曲的小蛇。风雨擦着肩膀,又相互被击碎,电闪雷鸣擦着肩膀,也相互被击碎。
当前车的轮胎喷出一扇两边厚中间薄的水帘时,车头也随之扬起,飞得更快了。腾天入海,是他从未有过的眼见为实。他朝着窗外尖叫着,嘶嚎着,瞬间,眼前爆出比那晚大出不知多少倍的火光。
嘀嘀,又一条信息进来。
责任编辑 刘淑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