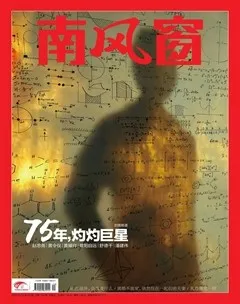她花七年时间,研究外卖骑手
《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
孙萍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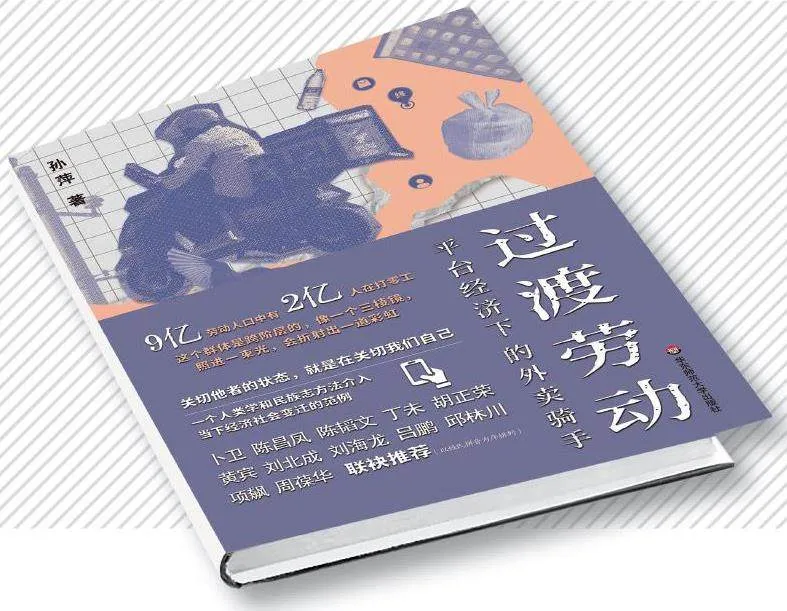
平台经济和零工化已经成为中国不可忽视的现象,外卖骑手是其中非常典型的群体。从不被人了解,到成为影视文学作品常常书写的群体,外卖骑手已经成为当下舆论场内的热词。
《过渡劳动》是关于这一群体的最新研究,作者孙萍和她的学生在写作前做了大量调查,涉足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成都、昆明、勐海、盘锦等多座城市,囊括了大中小城市等不同层级。
在论证骑手的流动性时,孙萍与调查小组对北京地区外卖员的劳动状况进行调查,发现仅有12.9% 的外卖员愿意一直送外卖,而超过八成的人表示自己会在两年之内换工作。骑手的流动性几乎是现有的零工劳动职业之最。进而言之,这份劳动带有很强的“有待确认性”,“它的存在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而是一种悬浮状态”。
与工厂生活相比,数字时代的零工彻底模糊了生活与工作的界限,他们的劳动与生活前所未有地紧密相连在一起。它创造了看似自由的牢笼,让劳动者的活动面积变得如此广阔,却又更加窒息。一方面,骑手处在无保障、疲于奔命的生活里。另一方面,它成为从乡村、工厂、倒闭实体店、学校离开的人的权宜之计。
它刷新了人们对工作、自由、流动的想象,又客观上给了农村和女工另一种挣钱选择。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专门列出一章来讨论“女骑手”的生存现状,占据了书中近50 页的篇幅,这在以前的同类型书籍中是很少见的。
为了增加此书的可读性,孙萍在每一章都加入了骑手的具体故事。比如第二章里写到骑手老高与智能技术的交锋,他原来是一个完全不会用智能手机的人,如今已经能熟练地刷手机、挑单子、浏览各种APP。难得的是,作者在写下这些个人故事时并未陷入直白的抒情,而是依然保持学者的审慎与冷静,这让《过渡劳动》里的个人关怀不至于流于滥情。
外卖骑手被分为专职、众包、乐跑(优选)等类别,这些骑手有的属于站点管,有的属于散养模式。为了刺激骑手的积极性,平台将游戏与骑手评级结合,设置王者、黄金骑手、青铜骑手等段位,将送外卖叙述成一场通关游戏,用游戏的术语,淡化外卖工作的肉身危险。在后现代的数字经济时代里,平台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自我实现与游戏的话术,将它们与资本的管理、对于个人剩余价值的榨取有效结合起来。
针对大众对外卖骑手的一些印象流看法,这本书也给出了回答。譬如收入问题,根据2021年调研小组的调查,仅有8.85%的外卖骑手表示自己每月可以拿到9000元以上的收入,外卖产业“先烧钱后垄断”的发展模式并不利于骑手的收入增加,其实不少骑手反映自己近几年的收入有下降趋势。
与过往关于外卖骑手的论述相比,这本书对女性骑手的关注和研究也颇为亮眼。送外卖的女性,大多数来自农村、乡镇,从前以家务劳动、干农活为主。作者采访的30位女骑手中,有27位来自农村,3位来自城市,超过1/3的女骑手表示,自己来到大城市是因为丈夫也在这里打工,他们需要一起挣钱,寄回家里,养老人和孩子。之所以跑外卖,是因为“找工作困难”,外卖来钱快,不容易出现拖欠。这其中有6人还是外卖“夫妻档”。
此外,有近三成女骑手是因为离异、家庭变故等原因而不得不外出跑外卖。这些女性受到乡土社会伦理的困扰,当她们最初跑外卖时,心理上仍伴随着羞耻感与自我蔑视。
由于男性占外卖骑手的多数,男性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也笼罩在女骑手的身上。比如他们认为女人开车不如男人,女人更容易出交通事故。外卖领域的“男性审视”,也会加剧她们的自我贬低。
其中,有的女骑手选择承受孤独,哪怕显得不合群,有的人则尝试学习外卖骑手的话术,与男性打成一片。为了提高效率,聪明的女性骑手有时候会选择“示弱”策略,利用男性对她们的刻板印象,帮助自己生存下来。孙萍指出:“女骑手在‘示弱劳动’中并没有极力压制自己的性别身份,而是有效地将性别身份与骑手身份进行对接和融合。”女骑手将这些刻板印象转换成“弱者的武器”,不过也要认识到,它更多是迫于无奈的生存策略,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她们的生存弱势。
在快速流动的城市森林,部分骑手们组成群组,女骑手也在寻求社群的组建,给自己一个“说话的地儿”。在群里,她们以姐妹相称,如“大姐”“小妹”等,会分享自己的定位、订单截图,也会聊养生、育儿、美容等话题。有一位热心的顾大姐,会定期组织大家吃饭、唱K、爬山,还把自己的送外卖生活制作成短视频。在这样的社群文化里,传统乡土社会话语对女人们的束缚产生了松动,追寻自由、独立自主、敢于挑战、团结互助成为了新的价值认同。
在“算法与系统”一章中,孙萍提到一个有趣的点叫“养系统”。简单来说,系统也是分层级的,如果能把数据弄好,系统就能把更好的单子派给骑手,后台通过数据积累来对骑手进行等级评定和派单,骑手需要坚持跑单,摸索出更好的数据,才有机会“弄好自己的数据”。
这是一套鼓励内卷的规则,在平台的逻辑下,送单多、时效快的骑手会得到更多的订单,而单量小、“挑单子”的骑手就会被系统边缘化,收入愈发下降。
作家埃里克·迈耶提出过“无意的算法残酷”,原本是指计算机设计中的一个缺陷——缺乏共情的能力。而在外卖骑手与系统的关系中,算法固然是中立的、无意的,但设计算法、打价格战、通过持续缩减个体成本和疯狂扩张来挤占市场份额的平台,则绝非无心。
那么,在系统严格控制时间,逼迫骑手只能逆行来避免超时的前提下,骑手怎样发挥有限的能动性,去争取一定的灵活度呢?第六章“数字韧性”里关于“逆算法”的实践策略,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长期的送单劳动中,骑手“以身试法”,通过实践来摸索出系统的漏洞,并加以利用。来自北京房山的一位外卖骑手,偶然发现一个远程切换账号的系统漏洞,就通过微信群告诉房山区的众包骑手,让他们集体抢单、相互捎单,以此提高工作效率。
不过后来平台发现了这一漏洞,并对相关骑手封号。通过这个案例,我们能发现骑手与平台之间的“斗智斗勇”,骑手的互助也在悄然间松动个体的严苛处境,尽管它仍然易碎。类似的是,书中还提到了孟天河、汾哥、驴哥、小王等人的故事,来展现外卖骑手“逆算法”的劳动实践。比起个体与个体之间绝对的内耗式竞争,互助与联合,才有希望为劳动者争取更多权益。
作者还讨论了一个问题——人数众多的外卖骑手为何很难团结在一起,对抗不公平的平台规则,而往往只能进行日常中有限的迂回抵抗?
这一方面与骑手巨大的流动性和原子化有关。另一方面,骑手的类别被不断细分,骑手被平台诱导去竞争和互害,在这种不断分化与竞争的氛围下,骑手往往只能形成小的互助群体,很难结成囊括成百上千人的团结阵营,与中介公司与平台博弈。
以2019年前后北京出现的“乐跑骑手”为例,平台通过宣传高单量、高收入、低权益保障的乐跑骑手,诱惑众包骑手进行转型。“乐跑”与“众包”骑手间互生嫌隙,就连各地站长也使用诸多小手段,招揽“众包”骑手变成“乐跑”,代价是骑手将失去自由上下线、自由选单、自由拒单的权利。到了2022年,孙萍跟一位名叫赵武的众包骑手聊天时,对方笑着说:“众包已经快被平台杀死了,挣不了几个钱,我再这么下去,连自己家的狗都养活不了。”
过渡劳动不是未来,而是眼前的现实,不是特殊情形,而是笼罩在今日劳动者头上的云层。因此,对于过渡劳动、零工、算法和平台经济的研究很有必要。“碎片式无助”使今日的劳动者渴望新的认同,技术创新为何没有让大部分人更加轻松,反而陷入新的困惑和疲惫,这是我们在阅读此书时,需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