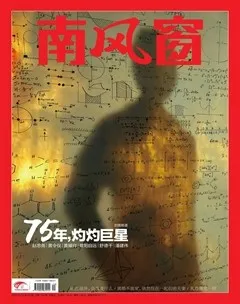在青春之城深圳,他们共创一座百年名院

唯理想与责任,使人忘我;亦唯忘我之士,群贤毕至,可创造奇迹。
一个奇迹在深圳诞生了。
2015年,何裕隆教授突然受命,将中山大学医学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以下简称“中山七院”)落地深圳,建设一座未来的百年名院。
从深圳光明区猪婆山的一片芳草萋萋起步,数年之间,一座现代化三甲医院磅礴崛起。
物质形态内部,是强大的科研与实践。启用6年,就在《Nature》杂志发表科研论文,揭开困扰全球医学界百年的恶性肿瘤化疗耐药谜题,开展了世界首例肝癌定向治疗术,示范探索业内专家奔走呼吁多年的普惠性安宁疗护服务……
好的医院,既是救死扶伤的实践场,也是科研教学的象牙塔,大医皆名师,传道受业,仰望星空,一起探索科学与人文可抵达的辽远边界。
何以可能?这些人原本在广州,在全国各地,有最好的环境,最好的待遇,为何决定来到这里,把双脚踩进泥泞?因为他们坚信并且想象着一片繁花,知道这里必然成为后人称道的百年名院。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之梦,因为那是一种求道的精神,它的超越性,让人生变得格外值得,医者亦不自外。

不由人不想起宋代书院来。那些人出则为家国担当,退则共研学问,为苍生细究未来。师生揣摩,如切如磋,虽苦犹乐。
一次情怀召唤的风云际会
2015年,何裕隆已经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作了30多年。受命之时,第一反应是“茫然”。
同时他也知道,这一使命重要而神圣。
深圳的经济奇迹、创新奇迹举世瞩目,但奇迹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出现在教育和医疗领域。深圳需要中山七院,需要更多医学精英。同时,中山大学的“双一流”建设也需要再造新局面。
深圳是有强大决心的。2016年6月,深圳市政府与中山大学签署了《共建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协议》,明确要将医院建设成为深圳区域医疗卫生中心、公共卫生灾难救治中心、国家级保健中心。
中大系列附属医院医疗服务水平蜚声国内,中大七院希望至少齐平,甚至更优。定位于深圳地区规模最大、临床专科门类最齐全、诊疗技术最先进、高层次医护人员最多等,后来中山大学校领导又为中山七院加了一个相当有分量的“最”:医德医风最好。
2015年10月,四人组成的中山七院筹备小组出发了,从广州前往深圳进行“二次创业”。
2018年开业,仅用了4年零2个月,成为“三甲”,创下全国最快纪录。
光明区猪婆山,可谓荒僻之地。何裕隆倒吸一口冷气,但士不可不弘毅,他们的目光越过了荒凉,“这里正是读书的好地方”。
这群从广州来的全球知名专家、教授,戴着安全帽、提着手电筒整日穿梭在工地。设计病区,修改图纸,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评估这些建筑和设备是否能满足一个高水平医院的需求。
中山七院副院长张常华回忆,第一次跟着何裕隆来到光明所见到的场景,不是现在的绿水青山。那时一片泥泞,生活不便。“何院长是具有大情怀和奉献精神的人。共产党员都应该有这种情怀。”
庄思齐,中山七院儿童医学中心学科带头人、儿科学教研室主任,9年前她曾成功救治了广东最小的新生儿。那时她即将退休,安享闲适时光,不想却被一份理想激励,一头扎进了工地。
“当时很多人认为我在中山一院已经有相当高的学术地位,没有必要再跑到深圳为新医院操劳,但何院长非常具有开拓和引领精神,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鞭策。”她说。
庄思齐教授来了,接着,中山七院现任副院长陈纯、儿科主任薛红漫,从中山二院来了;现任新生儿科主任房晓祎,从汕头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来了;十余位专科护士长和护理骨干,从中山一院来了……
每一个科室,莫不如是。万涓成流,情怀驱使,专家们一个个义无反顾。安稳的平台不要了,原有的编制不留恋,一心要在一片旷野上共同创立一个新的百年名院。
他们传承精神,“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世”;他们放眼未来,“崇德、求是、传承、超越”。
4个人,到2000多人,三间农民房的破旧办公室,到崭新的医院大楼,“中大情怀,深圳速度”,中山七院巍然出世。2018年开业,仅用了4年零2个月,成为“三甲”,创下全国最快纪录。
“如果将医院比喻成一个人,七院担负的使命不允许他从幼儿园小朋友慢慢成长到研究生,因为它的诞生就是研究生的水平,必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山七院党委书记陈起坤强调,来自中山医科系统各大专家、学者在最初就是带着三甲的思维、作风和规范,来创办这所医院的。
三甲只是一个起点,这群人眼里看到的,是一百年的事业。
科研突破,全新的希望
医学不是万能,但医学上有无垠空间等待突破。每一步突破,都将给百万千万人以希望。
中山七院的专家、教授均为各自领域、全国范围的代表人物,以专业、严苛、谨慎闻名。作为胃肠肿瘤诊治的佼佼者,中国医师奖的获得者何裕隆,率先将国际领先的胃肠肿瘤诊治技术带到了深圳。中山七院胃肠外科的“三名工程”团队,连续三年在深圳市排名第一。
复杂、疑难,是中山七院的定位。何裕隆分享了一组数据,自建院开业6年以来,中山七院的疑难重症占比超过80%,三四级手术占比为66%。
恶性肿瘤是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去年10月,中山七院成功实施了“肝癌定向治疗术”,这是世界首例。它在医学界石破天惊,也让悲观的患者重拾希望。
来自江西的农村53岁的赵叔,在中山七院被确诊为肝细胞癌,已属中晚期。一次讨论会上,中山七院普外科专家汤地创造性地提出了引入器官隔离治疗技术想法。
这项技术是由中山一院的何晓顺教授团队在2017年首创的,能长时间维持离体器官的活力和功能。如果将其与肝脏切手术结合起来,有机会降低肿瘤转移扩散和术后复发的概率,同时保留侧肝脏不受到高浓度化疗药物影响。
这项技术此前还未有人开展过,但赵叔愿意冒险。为此,专家团队制定了详细的方案。最终,手术成功了,赵叔直言自己像是做了一场梦,如获新生。中山七院在世界范围内首创了半肝隔离养护、化疗术,真正实现了肝癌的精准治疗。
复杂疾病的治疗不能靠个人经验,而需要最为核心的医生资源的组合,赵叔的病例正是经过了多学科讨论。
如今,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MDT)已成为中山七院日常运行的核心部分。每周三,全院多个领域的顶尖专家都聚集在中山七院的一间会议室里讨论各种复杂的病例,医生们形成一个发挥各自特长的团队,具有针对性的讨论很多都成为了解决疑难问题的希望。
从临床研究中发现问题、最终回到临床应用中解决实际问题,这对疑难杂症的治疗来说至关重要。
“我们的医生不能一边看病人,一边摇试管。”何裕隆说,中山七院在建院之初就下定决心组建自己的科研团队,引进专职科研人员,鼓励科研向临床的快速转化。
自建院开业6年以来,中山七院的疑难重症占比超过80%,三四级手术占比为66%。
这种鼓励在今年7月取得了重大成果——全球最知名的科学期刊《自然》杂志刊登了中山七院何裕隆、张常华教授团队主导的关于全球肿瘤疾病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性成果,为化疗耐药患者寻找到了生机。
又是一次世界医学难题的突破。张常华向南风窗介绍,开院6年来,这一研究跨越了4年,终于揭开了困扰全球医学界的“百年谜题”。
他们通过大量实验发现,在DNA修复和化疗耐药中“乳酸”起着关键作用,最终首次筛选出一种能够有效阻断这种耐药机制的靶向药物。
这种药物是一种治疗小孩癫痫的“老药”。“关于老药的研究如果能实现成果转化,将造福数以千万计的肿瘤耐药患者”,张常华表示,“老药新用也是一种新质生产力”。
接受采访的周日晚上,张常华所在的会议室仍坐满了专家。他们的世界一度非常简单,诊治疾病,总结经验,交流学界最前沿的研究和技术。
正是因为他们,生命才有了更多希望。
医者仁心,“把身上最硬的鳞给深圳”
今年8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迎来5周年。过去的5年里,深圳聚焦于重点民生领域,持续深化改革,在推进健康中国方面先行示范,推动由“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战略机遇宝贵,中山七院也在建设中承担了更大的历史使命。
何裕隆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中山大学把自己身上最硬的鳞给了深圳,让它在这片医疗洼地发挥更大作用,助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引领癌症的早诊早治至关重要,我国已经将癌症等慢性病防控纳入了国家战略。何裕隆带领的团队曾在1994年率先建立国内最大宗、项目最齐全的胃癌数据库。在中山七院,他也在带头建设消化系统疾病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为健康中国打造“深圳样板”。
深圳的“先行示范”不是独善其身,在深圳的经验也被中山七院带到了云南。从2017年起,中山七院在对口帮扶的云南凤庆逐步构建了胃癌风险评分系统和“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家庭”三位一体的胃癌预防系统。
数据显示,凤庆人民医院就医的早期胃癌患者翻了近2倍,癌前病变和早癌的发现率明显提高、有效改善了预后,减轻了个人和社会的经济负担。
今年7月,中山七院“探索消化肿瘤‘一站式’服务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的经验做法入选了“2024健康中国实践案例”。
病人首先是人,不管处于何种境况,都有对尊严与关怀的需求。《“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在2016年提出安宁疗护事业发展的战略要求。事实上,早在2015年中山七院筹建之际,就提出在院内建立临终关爱病房。
2019年,国家卫健委发布了第二批全国安宁疗护试点城市名单,深圳是其中之一。同年,中山七院率先启动了安宁疗护试点工作。2022年,中山七院获批立项,牵头制订《广东省安宁疗护社会工作规范》地方标准。
当治愈做不到时,安宁疗护是对终末期病人的关怀、对生命质量的关注,是中山七院能够给予绝症患者的最无价的尊重。
郭艳汝,安宁疗护专家,也加盟了中山七院。她专门提出了为医院量身定制的三甲医院安宁疗护模式——“安宁门诊—院内共照病床—院外医联体病房”方案。
从医“生”到医“死”,这种区域安宁疗护中心结合医联体的模式在深圳落地,它在为国家节省医保费用、释放三甲医院优质医疗资源的同时,还为患者家庭显著减少医疗的总费用。最关键的是,它让患者不疼痛,有尊严。
“好的医疗,一半是技术,一半是人文。”何裕隆相信,一个医生把该做的都做了,病人肯定能感知到。
传承,创新,体面地救死扶伤
所有成果的取得都得益于医院的发展理念。
回溯中山七院这段跨越式发展的历程,离不开它对于创新的全方位探索——不仅需要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构筑科技研发的新优势,还需要在管理上创新突破。
“如果你一直跟随其他传统医院,永远无法实现我们的目标和使命”,陈起坤说,“高层次医院,管理比临床业务专业更加重要。医院里所有的资源都需要优化和整合,来创造更大的价值。”
中山七院正在实践“互相成就”的理念。这一方面基于80%以上的业务骨干来自中大各个附属医院,个人的自主意识较强,而凝聚其工作合力,才能形成人才资源优势。另一方面,优化整合既也是中山医科文化的传承。当年,中山医学院由三个不同的医学院整合而成,汇聚了不同流派的专家,在优化整合人才的过程中铸就了辉煌。
开院6年来,这一研究跨越了4年,终于揭开了困扰全球医学界的“百年谜题”。
“互相成就”,这既是中山七院的文化,也是管理和治理医院的一种理念。陈起2s8Cy5hVrXuV3ttw6h6a7kCQ7dHmk2hWLb1lJ88PJ3U=坤在制度建设中提出,中山七院需要进行集成创新,让所有人员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进行对标世界一流的“研究”,从单一主体的管理思维转向多元主体的治理思维,进而实现共建、共管、共治的“互相成就”。
对此,张常华也提出了“全民创新”。“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行政人员都要创新,从新模式和新理论出发,思考如何使工作更加高效和有意义,这样你面对工作才能充满动力和激情。”
采访中,中山七院的领导都毫不避讳地谈到员工的待遇问题。在他们看来,医生一定要有高尚的理念;与此同时,为他们免除后顾之忧,是医院托举他们追求更高理想和情怀的应有力量。
“我们尊重每一位员工。我们要努力实现党和国家、老百姓和员工‘三个满意’,并将‘员工满意’放在重要位置,他们会对医院产生归属感。”何裕隆表示,“所以,我们提出要给全体员工带来有尊严的收入,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
“七院除了优化业务结构、拓展科技成果转化等,还要严格成本控制。”何裕隆指出,“在医院筹备过程中,我们非常明确的一点是不能触碰红线。”在中山七院,医疗设备等都由设备委员会负责,牢筑廉洁防火墙。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中山七院正是靠着对知识分子的深刻理解,用情怀感染、蓝图打动、创新管理吸引到一大批志同道合的精英共同加入“百年名院”的创业进程,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要问“中山七院何以能”,离不开中山医科“救人救国救世,医病医身医心”的精神传承。一代人传一代人,中山医科就是这么走过了上百年。
医者,师者,传承者也。几位受访者虽然来自医教研管这些不同岗位,但他们都在以“师者”身份将个人的从医理想,终其一生的勤奋专注,将其身先示范、孤勇前行的大医精神传授给加入这片创业热土的青年学子们。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在中山大学百年华诞之际,他们正毫不懈怠地奔赴下一个百年名院的目标。无论前路如何艰辛,他们都会抵达那个最终向往的方向,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谱写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篇章。
(文中赵叔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