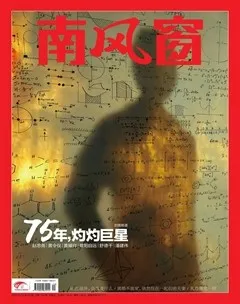中国和美国一个档次,欧洲明显落后

欧洲央行前行长、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前不久在布鲁塞尔着实掀起了一股旋风。9月9日,他大张旗鼓地发布了由他主持撰写的一份报告,题为《欧洲竞争力的未来》,一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这实际上是一份政策建议书,分上下两部分,洋洋洒洒共400多页,对欧洲竞争力的现状和挑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由于德拉吉是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年前的委托起草的这份文件,相信它将会对欧委会未来的政策走向产生实质性影响。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德拉吉在他的报告书中虽然提及中国近40处,但采用的口吻和方式与冯德莱恩有天壤之别。没有意识形态的敌对情绪,技术官僚型的压力分析代替了意气用事的指责。
中美一个档次
和许多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看法不一样,在德拉吉的眼中,中国和美国在科学技术创新方面已经大幅领先欧洲。他把美国和中国看作是一个档次,而欧洲则是一个明显地落后于中美的老大陆。
基于这一判断,他建议欧盟采用联合借贷、共同担责的方式,以每年投资8000亿欧元的力度来缩小与美国和中国的创新差距。德拉吉认为,和中美相比,特别是在先进技术领域,欧洲陷入了一种产业结构的静态之中。他指出,在欧洲,很少有创新公司横空出世并颠覆现有行业结构,形成新的增长引擎。
德拉吉认为,中国的绿色技术和电动汽车对欧洲既是威胁也是机遇。他认为,全球脱碳运动给欧盟工业带来了巨大的增长机会,但这个机会有可能因为中国的强势崛起而从欧洲的手中跑掉。欧盟在风力涡轮机、电解器和低碳燃料等清洁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全球超过五分之一的清洁和可持续技术都在这里开发出来。然而,他认为欧洲是否能抓住这个机会并不板上钉钉,大规模的产业政策和补贴、快速创新、原材料控制和规模生产能力使中国在清洁技术和电动汽车等行业成为欧洲强大的竞争对手。
权衡两难
德拉吉告诫欧委会,面对中国,欧盟要做出两难的权衡:越来越依赖中国可能是实现脱碳目标的最便宜、最有效的途径;中国由国家支持的竞争也对我们高效的清洁技术和汽车行业构成了威胁。
换句话说,中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与一味把中国看成是风险并不遗余力地要求成员国们“去风险”的冯德莱恩相比,德拉吉显得中肯和温和得多。在他看来,中国虽然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但体制优势并不见得超越欧洲。他分析道:欧洲模式将开放的经济、高度的市场竞争、强有力的法律框架和积极的政策结合起来,以消除贫困并重新分配财富。
和一些把中国的竞争力简单归结为国家补贴的政治家不一样,他并不相信欧洲竞争力的下降是由于国家补贴不够。
按照他的逻辑,正是这一模式使欧盟能够将高水平的经济一体化和人类发展与低水平的不平等结合起来。他信心百倍地指出,欧洲已经建立了一个由4.4亿消费者和2300万家企业组成的单一市场,约占全球GDP的17%,与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中国持平。
在比较了中国、美国和欧洲的一些指标后,德拉吉得出结论,欧洲收入不平等率比美国和中国低约10个百分点。在法治实施方面,全球得分最高的10个国家中,有8个是欧盟成员国。在预期寿命和低婴儿死亡率方面,欧洲领先于美中;而且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已经完成了高等教育;欧盟在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标准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这个充满自信的观点可以反证,德拉吉与一些整天鼓吹“中国威胁论”的民粹主义政治家有所区别。甚至与“志同道合”的冯德莱恩相比,德拉吉也显得“淡定”得多。
报告通篇不见冯德莱恩天天挂在口上的对华“去风险论”,而是建议欧盟冷静权衡,在“中国机遇”和“中国风险”中找到平衡。从他的角度看,欧盟作为一个开放度极高的经济体似乎不应过度强调“风险”,避免自觉不自觉地关闭同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合作的大门。
“不忘初心”

如果从学术流派的角度评价德拉吉的报告,这位前欧洲央行行长明显是一位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捍卫者。鉴于许多从前崇尚自由贸易的西方政治家如美国总统拜登、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都成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急先锋”,德拉吉“不忘初心”的表现还是令人惊讶的。
德拉吉并不否认中国向世界出口的产品对欧洲向世界出口的产品越来越产生挤压效应。按照他的数据,中国与欧元区出口产品直接构成竞争的行业和板块直线上升,行业的比例现已接近40%,而2002年时这一比例仅为25%。
然而这一竞争的白热化好像并没有让他丧失对自由贸易的信仰。在欧盟是否应对中国采取更强硬贸易政策这个问题上,德拉吉在记者会上表现得非常审慎。他强调,“贸易政策必须务实”,布鲁塞尔不应采取非黑即白的政策,更不能在所有领域都持非软即硬的态度,而是要下沉到具体领域中,进行仔细的行业分析,然后才决定做什么。
德拉吉的“心病”是欧洲在与中国和美国的竞争中日益下降的竞争力。和一些把中国的竞争力简单归结为国家补贴的政治家不一样,他并不相信欧洲竞争力的下降是由于国家补贴不够。德拉吉表现出对自由市场的信任和对国家过度干预市场的强烈反感。他认为,欧洲竞争力下降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乏创新能力,而是市场不能迅速规模化,将创新思想和方案顺利转换成商业成果,其原因不在于国家关心不够,而恰恰相反,在于国家“关心太多”,“过度监管”。
创新生命周期
德拉吉在报告中多次提及中国的市场规模化能力。对他来讲,这就是一个“创新的生命周期”问题。一个产品从创意的产生到完成商业化的时间越短,市场竞争力就越强。欧洲创新生命周期与中美相比太长了,发布报告当天,他还独自在《经济学人》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欧洲如果想提高全球竞争力,必须缩短“创新生命周期”。
他建议进行根本性改革:从让研究人员更容易将创意商业化,到对突破性技术进行公共投资,到消除创新型企业扩大规模的障碍,再到投资计算和连接基础设施以降低开发人工智能的成本,应改尽改。
有意思的是,在德拉吉看来,欧洲最大的竞争对手是美国,而不是中国。这一点与很少公开提及美国是欧洲的主要竞争对手的亲美派冯德莱恩相比显得格外醒目。德拉吉认为欧洲想要重新崛起,当务之急是要缩小与美国的创新差距。中国的崛起并没有让他感到特别的不安,不像美国政治家一样对中国的“恐惧”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
中国有个特点,就是不钻牛角尖,而是总体思维。
德拉吉认为美国在科技方面把欧洲远远地甩在身后对欧洲的全球竞争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这个问题上,德拉吉的分析是技术官僚型的冷静,丝毫没有美国人在谈论中国优势时的情绪化失态。他在《经济学人》的文章中分析道,欧洲在很大程度上错过了互联网引领的数字革命及其带来的生产力提升。自2000年以来,欧盟与美国之间的生产力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科技行业造成的。
他指出,正是因为科技行业落后于美国,而科技又是推动当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欧盟的经济增长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因为欧盟在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兴技术领域仍然会很薄弱,欧洲公司专注于成熟技术,突破创新的潜力有限。德拉吉并不认为欧洲缺乏创意或野心,而是认为创新有余,衔接不足。每每在创新成功之后,下一阶段受到阻碍,许多创新成果要么夭折,要么出走美国。
按照这个分析,欧洲的创新障碍主要来自没有将创新转化为商业化成果的生态环境,想要扩大规模的创新型公司受到欧盟和欧盟各国不一致和限制性法规的阻碍。所以,许多欧洲企业家更愿意从美国风险投资家那里寻求融资,并在美国市场扩大规模。
成本组合拳
欧洲对中国的电动车谈虎色变,德拉吉的态度则从容不迫。相比把欧洲电动车竞争力下降归咎于中国补贴的欧盟委员会,他的分析方式显得更为专业和理性。
德拉吉认为,欧盟在汽车行业竞争力的丧失有许多原因,外部环境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他认为,同中国相比,欧盟电动车的生态环境和供应链出了大问题。中国在整个电动汽车价值链的打造上下了大功夫,比欧洲更快而且规模宏大,协调有序,能够打出技术领先、规模效应和低价劳力的成本组合拳。中国有个特点,就是不钻牛角尖,而是总体思维。
与美国截然不同,德拉吉有关中国的讨论,出发点都是如何靠提升欧洲的竞争力来振兴欧洲,而不是靠遏制中国来拯救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