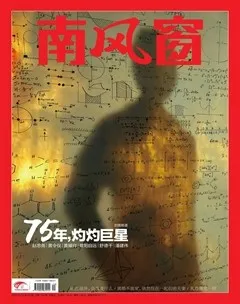文献
12欧洲社交媒体平台“缺位”之痛
董一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节选自公众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2024年9月
当前全球的头部社交媒体中,欧洲可谓无立身之地,全球月活用户超过1亿人的35家社交媒体中,美国和中国分别有20家和9家。欧洲仅孵化出塞浦路斯团队所开发的Viber,但它也被日本企业收购。欧洲本土社交媒体市场几乎是美国数字巨头的天下,如脸书占欧洲社交媒体市场份额达79.41%,甚至高于其在美国本土水平(46.57%)。欧洲在社交数字巨头方面的缺位,恰恰暴露其长期以来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环境的短板。

其一,欧盟数字市场碎片化严重。欧盟对其资本、劳动力、商品、服务四大要素自由流动的单一市场引以为傲,但在数字经济市场却存在诸多有形或无形壁垒。法国企业家尼古拉斯·科林指出,欧洲各国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地域性和特殊性,使得其数字服务产品很难迅速向周边市场扩散,也意味着欧洲数字市场在“流动性质量”和规模经济效应上难以与美、中等国相媲美。在此背景下,欧洲一些在本国取得成功的社交媒体,却难同已经形成规模效应的美国数字巨头竞争,比如芬兰的“IRC Galleria”、荷兰的“Hyves”、匈牙利的“iwiw”等社交媒体都曾一度是本国网民的心头好,但最终都被挤得销声匿迹。
其二,欧洲投资环境不利于初创企业发展壮大。相对于美国拥有发达的风险投资市场,金融资本与硅谷创业者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圈子,欧洲各国金融体系的基石仍是大型银行,这些金融机构往往以质疑和审视的眼光看待初创企业的融资需求,难以接受发展前景不确定性较大的企业和项目,也缺乏看待新生事物的长期主义视角。在此背景下,欧洲有创新潜力的群体纷纷到纽约等地寻找投资者。风险投资公司Atomico发布报告称,2023年欧洲初创企业获得的投资(450亿美元)不及美国企业的融资额(1380亿美元)的1/3。资本的外移也带走了欧洲本土的人才和创新团队。法国顶尖理工院校的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高材生,往往会选择新加坡或硅谷工作而不是留在欧洲。
其三,欧洲科技界没有意识到社交媒体的战略意义。欧洲政界和知识界纷纷呼吁构建“承载欧洲价值观且不被资本裹挟”的社交媒体平台,但欧洲主流媒体往往更关注自动驾驶、量子计算、云技术等“高大上”的数字经济赛道,认为社交媒体仅仅是聊天交友、分享视频的工具。科林称,“欧洲的势利眼”阻碍了本土社交媒体企业家取得成功。
2从父职视角推动生育支持政策完善
王向贤 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节选自2024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网”
父亲生育支持政策在国外先行一步,促使国内学界高度关注国际经验。例如,对于北欧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父职政策和日韩、新加坡等东亚邻国自90年代以来的父亲生育保障建设,国内学界目前已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生育支持政策的特征深嵌于政治、经济、文化脉络之中,因此,良好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必然立足于本国经验。
在家庭层面,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父职排序—以经济抚养为优先和很少提供日常照顾,使得众多深感工作与育儿紧张冲突的女性,迫切期待丈夫能够积极提供日常照顾。向广大父亲提供带薪生育假,既缓解了他们赚钱养家的压力,也提供了日常照顾的时间。其中,子女出生伊始的陪产假是广大父亲形成父职认同、与新生儿建立情感依恋、分担日常照顾的关键阶段;父亲在子女一定年龄内享有的育儿假则促进父亲提供日常照顾;年度护理假还为父母照顾生病或发生意外的子女提供时间和津贴。

在职场层面,需要变革用工机制,即从认为男性是无须照顾家庭、可随传随到的“理想”工作者,转为承认已育男性需要承担经济抚养和日常照顾的双重父职。短期之内,向男性员工提供生育支持会增加用人单位的雇员人数、管理难度和生产成本。但长远来看,这将降低员工流失率和提高生产力。不过,北欧和东亚的经验表明,制定父亲生育支持政策固然不易,但如何推动用人单位真正予以落实更需攻坚。其中,政府如何推动职场有效转变用工机制是关键环节。
在政府层面,向广大父亲提供生育支持,将推动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一是通过设立天数较多和津贴较高的父亲带薪生育假,缓解女性的工作与育儿冲突,消减阻碍生育的照顾赤字,从而促进适度生育。二是通过提供父亲带薪生育假,促进父亲积极参与育儿。三是通过推动父亲生育支持政策向平衡且充分的方向不断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下一步,我们要向“人”要分数
刘长铭 北京四中原校长、北京金融街润泽学校校长
本文节选自“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
事实上,我们的难题与挑战不是分数,我们每天遇到的最大问题和最大的挑战是学生厌学。东北的一位老师从一个重点学校的初中抽样做调查,结果平均厌学率大约是66%,男孩子厌学大约70%,女孩子厌学大约62%,而且随着年级的升高,比例在提高。也就是说,我们所面对的孩子里面,每天有差不多2/3的孩子不爱学习,他们每天都不得不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你说他们学习的效率能高吗?如果换成你,每天让你做自己特别不愿意做的事情,你的心情能好吗?
什么是影响成绩特别重要的因素呢?是师生关系。良好的师生关系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成绩。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关键是老师要关注人,而不仅仅是书本、课标和分数。调查数据显示,小学生更看重老师和学生情感之间的连接。老师对小学生温柔、体贴、关心、关爱,小学生就觉得老师很好。但对于大孩子来说,他们的要求就要高一些。他们对老师的学识修养、讲课方法、能力和语言会有更高的要求。过去在北京四中做调查,我们发现越是高年级学生,越是看重教师的人格魅力。
新西兰教育学者约翰·哈蒂用了15年,研究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因素,提出了138个,并按照重要性从1到第138做了个排序。排名第一的是最重要的,叫作“自评成绩”。什么是“自评成绩”呢?她提出的关键词语是“学生的目标和对自己的期望”“自信”“自我的价值感”等等。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影响动机的重要因素。这些数据值得我们思考。我们通过工作改变学生的精神状态,表面看起来不是直接提高分数,但是对提高分数却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比如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比如激发学生积极乐观的情绪状态。
向方法、向工具要分数的做法已经到头了,下一步,我们要向“人”要分数。就是说,我们的教育教学要关注人,关注人的内心世界,改变人的状态,激发积极、热情的精神和情绪状态。那样的话,学生的学习状态一定会发生改变,学生在积极的精神、情绪状态中,一定能实现高效的学习,取得更好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