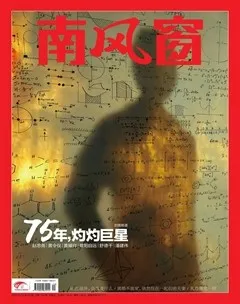出海中东,宜更慎重
中国的企业和机构必须有清晰的认知:中国人出海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实打实的工业基础。
在中国的企业界和金融界,中东概念差不多火了三四年。出海中东,好像是一幅极其美好的图景。
企业界的人告诉我们:中东的消费者很富,中产都是土豪级的,家里有几台豪车,一不小心还养着狮子。他们根本不懂得讲价,只要最贵。投资家则告诉我们:中东的机构投资者最有钱,最小的主权基金也有千亿美元的资产管理规模。他们投孙正义的软银巨亏,现在只相信中国人,抢着要当中国VC的有限合伙人。
如果仔细分析,以上两点都值得商榷。中东上镜率较高的国家,的确有不少石油富国,但不能忽视,中东的人口规模的确太过有限,没有任何国家称得上“大国市场”。沙特是中东的第一经济大国,人口其实刚超过3500万,大概是广州加深圳的人口,却没有广州加深圳那么多的中产阶层消费者。
在沙特的人口中,30%都是外来的劳工。他们薪酬并不高,而且会把薪酬作为外汇,寄回印度、巴基斯坦或者孟加拉国。也就是说,他们基本上不会为当地的消费做太多的贡献。除了沙特,在其他的中东国家,这种情况也十分常见。
因此,有个极其有意思的现象是,南亚国家特别鼓励青壮年去中东做劳工,在出入境程序上大开绿灯,好让这些人为国家赚取外汇收入。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都是如此。
这一点和中国的农民工,完全不同。中国的农民工在挣钱之后,很多人会带着家庭不断向城市进军,哪怕是租住城中村或者住在城郊,也无所谓。除了在城市进行日常消费,他们的子女甚至还会在城市上课外补习班,最后真的成为了城市消费者的一部分。但在中东,高比例的外籍劳工和中产消费市场是完全割裂的。这意味着中东的经济发展,所对应的消费市场扩大程度,远远低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第二个问题,中东的投资机构的确有钱,但拿到他们的投资,真的那么容易吗?显然不是。中东年轻一代的政商精英,很多都在英美接受教育,在最顶级的金融机构工作过,在一流的战略咨询公司当过分析师,对全球金融市场的规则和地缘政治的变化,了如指掌。
对中国来的客人,他们非常清楚:你想要什么,但你有什么?要忽悠这样的人,很难。因此,上海和深圳的很多VC从中东回来都抱怨,“土豪”的钱,没想象的好拿。
实际上,研究一个地区的历史,才能让人真正懂得这个地区。在工业文明崛起之前,中东是全球商业的要冲,中东商人是全球财商最高的商人群体。
在元朝,帝国财经系统的官员,很多都是阿拉伯人。来自中东的理财官员知道:为皇帝贡献税收,商业税远比农业税的“征收成本”更低。中国的动乱,很多都源自向农民征税。于是,皇帝看中他们这种商业头脑和理财经验,让他们帮助建立了以商业税为重要支柱的元帝国税收体系。
中东人还是技术牛人,哥伦布的航海技术受益于阿拉伯的航海传统,因为阿拉伯人统治了西班牙近800年。在中世纪,西方的航海家擅长在地中海和波罗的海航行,无论是南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还是北方汉萨商业同盟的繁荣,都和航海技术息息相关。然而,同时代的阿拉伯航海家明显技高一筹,他们早已不局限于内海,而是进入印度洋和大西洋这样的大洋,成为全球技术最好的航海大师。
也就是说,在工业革命之前几百年的历史中,中东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技术和财商都很厉害。他们是东西方“信息不对称”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全球贸易典型的“吃差价中间商”。这种文化传统的长期熏陶之下,现在中东政商精英基本上不可能被忽悠。要吃他们的“差价”,要做他们的“中间商”,难度很大。
因此,中国的企业和机构必须有清晰的认知:中国人出海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实打实的工业基础,并不在于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