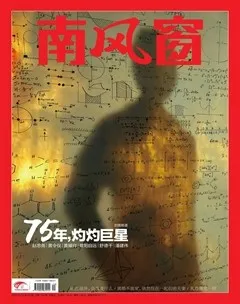提防美国“政治暴力化”外溢
上届美国大选后,正进行当选总统认证的美国国会,被暴力短暂淹没;本届大选投票前,总统候选人遭遇相隔两个月的两场刺杀事件。昔日难得一见的黑天鹅事件,现在似乎变成了“灰犀牛”般可预期的危机。
当年,民主党指控特朗普煽动暴徒冲击国会山;而今,特朗普埋怨是民主党方面关于他威胁民主的指控诱发了刺杀。追究起来,暴力行为的源头都是言语暴力,而后者正成为美国总统竞选中的常态。两党集会上的口号里,前有针对希拉里的“把她关起来”,后有针对特朗普的“把他关起来”,彼此彼此。
如果上述现象停留于美国的内政层面,我们大可以作壁上观,或一笑置之。但这种政治生态的劣质化,正波及国际层面。从拜登对普京的“杀手”称呼,到万斯诬指中国使用“奴隶”劳工,两党当红政客竞相使用极端词汇,让“绰号大王”特朗普给拜登、哈里斯贴的“奸诈”“撒谎”标签都相形见绌。
就连不该深度介入政治的企业家,也在两极化的政治生态中难以自拔。首富马斯克先是针对背书哈里斯的霉霉宣泄道,“我会给你一个孩子,并以我的生命守护你的猫”,后又针对特朗普遭遇二次刺杀事件抖机灵道,“甚至没有人试图暗杀拜登或卡玛拉”。
尽管拜登在每次刺杀事件后都致电慰问特朗普,甚至当众戴上了绣有“特朗普2024”字样的帽子,但在拜登任内,特朗普两个前顶级助手先后入狱服刑,成了政治犯。纳瓦罗和班农从座上宾到阶下囚,如此戏剧性,足见“政治暴力化”的另一个表征就是“司法武器化”。后者比言语暴力、行为暴力更能体现国家的暴力机器色彩。
虽然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爱说“暴力在美国没有容身之地”,但她在因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明尼苏达州打砸抢烧事件后,为相关罪犯设立了保释基金,也相当于纵容了此类暴力的发生(这跟特朗普承诺当选后特赦冲击国会山的人异曲同工)。她在诸多问题上180度的政策转弯,并不能掩盖她所谓“进步主义”的激进议程。早有论者指出,她若当选,更有可能选择“奥巴马式激进路线”,而非“拜登式温和路线”。
这种“激进路线”也体现在对外关系上,哪怕哈里斯在对华经贸关系上会继承拜登的做法,她在其他方向和领域带来的国际关系风险还是不容小觑。
以奥巴马执政时期为例,民主党当时的激进路线,导致美国政府支持所谓“阿拉伯之春”,推翻强人主导多年的埃及穆巴拉克政权、也门萨利赫政权,并WUs6u0KhVytdhYdueTBikQ==且尝试推翻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造成绵延至今的中东祸乱—由此,严重干扰了国际海运的正常航路,间接推高了国际油价,并且制造了难民危机,诱发了欧洲的极右势力回潮。
可是有了拜登执政期这层滤镜,部分分析人士对于哈里斯执政的想象过于粉红色,甚至期待有正向突破。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认为,正如1972年的尼克松能暂时放下意识形态偏见,与中国开展接触,曾在中国教书的蒂姆·沃尔兹,也有可能协助哈里斯一举扭转对华政策的僵局。
相反的观点,则关注美国与北约、欧盟、日韩等传统盟友的合作,认为哈里斯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的外交政策宣示是鹰派的,不仅是针对俄罗斯,也影射了其他不合作的大国;而且相比已经为世界熟知的特朗普,哈里斯的不可预测性其实并不低,与她打交道的学习成本会更高。这样看来,或许美国国会两院分别落入两党之手,从而对总统的施政形成牵制,才是部分人更愿意看到的。
美国政治的暴力化倾向,在两党相互斗争的层面,的确有上述牵制作用。但不容低估的是,两党同时激进化的能量一旦不能在内部抵消,就有形成合力向外部倾泻的可能性。当朝野两党在对华关系上协同一致时,我们就会看到如当前美国众议院在“反华周”接连通过25项涉华法案的极端情况。这在中间理性派日渐式微的西方政坛,有可能演变成一个长期趋势。也就是说,美国宁愿转嫁其国内的政治暴力,通过言语攻击、军事威慑、司法长臂管辖等手段,输出“非友即敌”的新冷战思维,以求其国内的相忍为安。
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美国把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去的冲动,恐怕不会因为谁当选下届总统就受到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