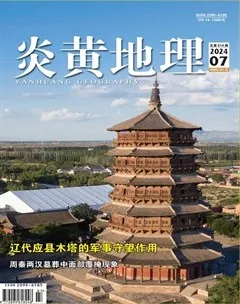民国歙县救济贪污案




对于民国贪污腐败研究不少,但具体到某地的个案研究却略显不足,文章以民国三十六年安徽歙县水利赈米九十六吨舞弊案为例,对贪污的形式及处理进行分析研究,以警示后人。
学界对民国时期研究颇多,对于民国贪污腐败研究也有,但具体到某地的个案研究却略显不足。民国标榜为“民主共和”“主权在民”,宣扬“法治”,但从揭露出的情况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吏治腐败比之民国前期更加触目惊心。学界对此并未有所过多研究关注,鉴于此,文章以民国三十六年安徽歙县水利赈米九十六吨舞弊案为例,对贪污的形式及处理进行分析研究。
歙县水利赈米九十六吨舞弊案经过
民国三十六年(1947)四月,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日本已经占领东三省并紧逼华北,地方上各地自民国十八年来长期遭受天灾,例如水灾旱灾等。歙县“自抗战以来人民忙于军运兵役,‘按本县兵力配额,占贵徽师管区所辖各县全额三分之一,强地当杭徽芜屯省屯三路中心,河道亦为新安江上游,总长百数十里,通浙东,金卫,严兰唯一水路运输’担负之重为皖南各县冠,且人民向多经商在外,田园荒芜,一切水利失修,致引起三十一年空前水患”,由此可见歙县人民所遭受苦难之深重。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虽有一些救灾慈善团体,还有联合国对中国进行救助。然而,“三十三年严重旱灾,胜利后各盟邦发动联合救济,吾歙县亦受到不少赈衣赈粉及各种赈品,但每为承办人员从中刻扣舞弊,未能确实施赈到苦难人民,自上弊端屡现,虽经人民一再向县政府控诉,奈何上行下效,咸皆不了了之”。
直至民国三十六年,为了救济救灾,实行以工代赈,“嗣至本年行改,消极性救济为续极发展,交通水利工程以工代赈,吾歙经皖经济分署配给水利振米九十六吨,即以此数遍修全县塘土曷沟渠及疏通河流之用,仍不呰杯水车薪,然能橝主要而捐壤,重大者加以修善,运用得法,实多补益,故全县人民莫不注视殷切,遒知承办之县政府于奉到最后期限须于四月十五日前赴芜具领,方由县党书记长兼议员鲍騄,县政府社会科长兼议会秘书黄昌照二人。于四月十四日乘车赴芜,六月十二日返县,时为两个半月,比闻全部赈米售得仅一亿千余元,按徽地时值米价(每石二十五万左右),难说还三十吨,其中暧昧显系,贪污乃激于公义,依法检举并公告全县父老,暨旅外同乡不料,彼等自七月十三日经歙县地方法院检察处传唤保出听候,备查在案,尚借烧熟具有势力者将部令调剂,民食已分配各乡镇办理,平耀之晓,谷九百担抵债购入,作抵此项赈米,值此青黄不接之时,又不呰强夺贫民贫粮。本县灾黎非但不能受赈济实,反蒙如此剥削,亦可云惨矣。”
上述即是歙县水利赈米九十六吨舞弊案大概经过,由安徽救济分署向歙县发放救济赈米九十六吨,经芜湖关运送至歙县。歙县县府方面派鲍黄二人于民国三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动身前往,于六月十二日返县时,全县人民听闻赈米已被就地变价,群情激愤,于是将鲍黄二人一纸状告。
倒卖赈米诡谋
鲍黄二人此次倒卖赈米是经过长期谋划而成。据鲍騄、黄昌照在本县参议会第一届第五次大会中报告:“騄等二人于四月十四日自歙城动身,十五日午后二时到达,芜湖当日即将代领及代电送呈分署,以手续繁重迟至二十五日始将提单领出,三十日始由招商码头三号仓库领出,暹罗糙米九百六十包,雇驳船四艘,分运恒泰、广盛源两米厂堆存(旅芜湖同乡会理事长汪岳年,理事方佩常介绍)并由方理事委托同乡汪菊三,汪公寿等六人帮忙洽领及过磅计数,直至午夜12时始行办理就绪,查彼等到时并未逾限,救济机关阅,岂有如此繁重手续,迟至半月方始领取就绪,可云罕有。而赈米领出不在公路附近便于装运地点,租栈存放,一着手即运至恒泰、广盛源二米厂分存其”,蓄意图售,情形可知。
参阅鲍黄报告“该项赈米九十六吨于四月三十日午夜十二时始行领放就绪过磅,结果合计整米毛重六二,三一八公斤,碎米毛重二四,八一二公斤。翌早即将所领数字电告县府,嗣以芜湖五月五日清晨发生大规模抢米风潮,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除旅芜湖同乡会电告县府外,县等一面央请同乡派人看守,一面电告县府请示办决县府粮据,参会之决议先以急电催促就地处分”。歙工赈会启事内称“……米甫领出,适逢芜湖发生大规模抢米风潮,本会与参会送接芜湖同乡会理事长汪岳年及鲍黄二君,函电告急当以情势严重,即由县府提请本县第一届第四次参议会临时动议决定,由县府根据议案急函鲍黄二君会同乡会将项赈米就地变价,价款即汇县补购粮食抵充,此种主张法理人情兼顾……”。据知本县第一届第四次参议会于五月一日开幕,五月五日闭幕(五日会议为最后延长之一天)县府所发急电系五月六日芜湖抢米风潮,乃发生五月五日上午十时另五十分钟,下午三时芜湖米联会即暂设平糶处数所,定次日分十三镇设平糶处,四时后即告平息,更因该地当局处理适当,则未继续发现,十二日六区专保公署召开南宣繁当芜五县县长会议,决定处理米潮及治安等各问题,后吴市已复常态,如彼等所言须非事实。
据本县参议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第七次会议(以每日分上下午各一次,则第七次会议当在五月四日提案“准县府转旅芜同乡会理事长汪岳年暨工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鲍騄施赈组长黄昌照由芜湖发来急电,称芜湖抢米风潮甚,本县所领救济分署存,芜赈米亟待处置,提出核议‘议决案云’为安全,订由县府电鲍主任委员騄,黄组长昌照会同旅芜同乡会就地变价,随即汇歙交工赈委员会,会同县府随时补购粮食应用”赈品不得售卖,联合国物资救济章则已有规定,中央亦有令知参议会对是项不合法令之议案遵附讨论,系与县参议会组织暂行条例第三条县参议会议决事项与中央法令事项抵触者无效,而县长陈道生接到是项议案,不认为不当,查经参议会组织暂行条例第二十二条,县长对于县参议会之决议案,如认为不当,得附理由送请复议,对于复议结果,如认为不当时,得呈送请省政府核办,县参议会与县政府对是批赈米不遵法令执行……以急电催促就地处分,究不知贫,事前预设机谋,抑为经检举后奖图饰,非但事实胜于雄辩,适增其欲盖弥彰而暴露彼等串通舞弊预谋倒卖赈米之诡计。由此可知,该案有鲍黄二人抓住米市波动之现象,极力促成参议会决定将赈米就地变价,以此方便二人从中牟利。而参议会方面,不仅没有对此察觉有所不妥,而且也极力催促就地处分,可见参议会对于法治程序的概念也是相当的薄弱,也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人治大于法治的政治特点。
贪污情形及数字
关于本案设计的具体金额数字也相当骇人,时人许卫民对此进行精确计算。据鲍黄报告:碎米六万八千四百元售出,除归垫驳运卸力麻袋,保证金及騄等旅费外,仅余八百万元,整米于五月下旬分四批售出,计平均价格为净盘十五万元(芜湖售米惯例,居间米号每元抽七分五厘,佣金上述净盘系已将此项费用除去)共计一亿零二百五十三万九千九百元(内栈租保险费一百五十八万两已扣除)并未将脱售之米价是照市石论,或吨数论,并售出若干数量,说明并又称“在赈米内提取十二石作芜湖平糶基金及彼等往返之旅费,约在一千一百万元之绪,是否又另作开支,此种会计法及报销方式实前所未见”,查据芜湖复兴日报五月六日载‘平糶米每升一千二百元(合十二万元一石)’,又九日载‘平糶米闻有霉烂,米色红黄甚糙,但一般受惠者未闻有怨言’,又二十二日载‘记者访问办理平糶之,据购业工会负责人谈平糶米,旨十日起是从河下买米来平糶,每石买进的价格在十六万到十七万,是糙米平糶价格是十二万每石的差额便是五万元,据他们说麦金莱后还经中粮公司米厂加工,并且还机过,这样又售价九折,但是平糶米质还是很坏’足证芜湖当时米价仍未见低,据鲍黄二君所称,碎米六万八千四百元售出,整米十五万售出,绪有不实,再据云提取十二石作平糶基金,并为不确芜湖复兴日报五月九日载“第四次平糶会议关于平糶基金筹备问题由杨专员高铁君等八人于明(十)日假新生食堂设宴招待本市各银行钱庄负责人”,又十九日载“芜县府于十八日上午十时邀集有关各机关及地方士绅,到四十余人议决案,食米开禁凡在本市采购,现尚未运出者,据等级约米七万石,每石抽一斗共七千石以作办理平糶之用”,今后只在本市采运者每石抽三升予以“乐捐”名义,本县所领赈米,当非兴在芜湖采购未运者可比据报告所云“以公私存米提出10%为平糶基金,查无此论,据当时芜市统计中粮公司所存约三万包,农民银行存米约九万包,未见云每石抽一斗且据云‘未发价款’应作浮开论,兹照芜湖五月上下旬市价与鲍黄二君所报告售脱之米价及公斤数为制成比较表,其比较数相加不实,销耗及除麻袋伙重所得不符数字为一亿四千六百八十六万八千五百八十元,据其所举公斤数及售脱之价格所得币值总数应为一亿四千七百二十六万一千七百二十元,再加上级所报不实销耗及麻袋伙重米共九千八百三十公斤,方得核除所用杂项旅费开支,案查芜湖当时限(市)价彼等所报数量之米售出应得币值总数为二亿六千三百零八万三千三百元,加上级所报不实销耗及麻袋伙重米共九千八百三十公斤,应为二亿九千四百十三万零三百元,再核除所用杂项旅费开支,又据报告云米款迄今尚未全数汇到,以此巨款照普通行息大二分以二个月计算据报告共收一亿一千零五十三万九千九百元,再除列等往返旅费一千一百万现存仅九千九百五十三万九千九百元,其贪污数当在三亿元以上。”
证据并所犯法条
检察院方面对于该案的认定有所不一,首先是“被告鲍騄,黄昌照,共同领取安徽救济分署所发给之工赈米九十六吨,分装九百六十大袋,每袋一百公斤,除袋皮九百六十公斤(每袋一公斤),应为净米九万五千零四十公斤,以一公斤折合二市斤,则为一十九万零八十市斤,内除3%蚀耗,应得净米一十八万四千三百七十八市斤,折合市石为一千二百二十九市石一斗八升六合强,再以八五五折,合芜湖米市斛石,每石为一百四十八斤(十六两老秤订算),应得净米一千零五十石九斗五升四合强(斛石),今被告等交行糙米,为2315公斤,碎米为24812公斤,按照上述计算标准,仅折合九百九十三石,二斗四升七合强(斛石),相差五十七石七斗零四合强(斗石),相差额竟达到9%强,超过安徽救济分署历来发放赈米记录。”并经本案检察官亲往芜市调查,取有恒泰行经理叶受之、广盛源行经理曹友恭之述词,实在可稽。该被告等,“虽以袋皮破裂,每袋斤重不一,及沿途被贫民抢夺等情为辩解之论据,但查阅安徽救济分署有关档卷,关于歙县工赈米分发单存查联,并未签注短少数量(其他各县有短少者,多已签注),即被告所呈之政执联,亦未加以注明,面所述被贫民抢夺,又属毫无佐证,空言饰辩,何足置信。况查当日领出之际,并未凭同安徽救济分署人员,会同过磅,即自行起运交行,而于四月二十九日,致歙县长陈道生一函,亦称一所堪注意者,乃技术问题耳,是该被告等事前既以注意到技术问题,何以于领出后交行前,一转手间,遂短少五十余石之多,谓据所犯贪污惩治条例第三条第六二款之罪嫌”。
关于方佩常部分,按受公务机关委托,承办事务,而有犯罪行为者,应以贪污罪论。“惩治贪污条例第一条第一项,定有明文,该被告方佩常,受歙县县政府之委托协助处理工赈米,有县卷所附往来函电可证。乃该被告对于此项工赈米,售价一亿一千四百一十三万零一百元,除支付鲍黄出差旅费一千一百万元及汇八百万元外,下余九千五百一十三万零一百元,竟籍故延不汇出,擅自运用,亦有恒泰等两行所开货款两讫之发票,及该被告收汇款项日期,足兹认定。”从该被告先后汇到九千七百万元,计溢一汇百八十六万元九千九百元,並据具状并称“已给付法定利息”,然究以何项标准计算及何时为起讫日期,均未说明,䫏不足採,且据恒泰行经理叶受之述称“一价款系六月二日交清”,广盛源行经理曹友恭述称“价款系随卖随交”。而该被告六月八日,致歙县长陈道生函,犹谓“芜湖银根吃紧,收解尚需时日”,兹复于九月十八日状称“听有价款代保管,并未送存银行”等语。则其利用歙县政府电示划汇往返磋商之机会,从中图利。再该被告为芜湖仁裕绸布庄经理,“以现时物价高涨不已,莫不利市十倍,以最低三分利润言之。该被告于七月五日交汇四千万,计已迟延一个月,可获利一千二百万元,又于同月十五日交汇九千七百万元,计已迟延四十日,可获利二千二百万元,两共净得不法利润三千四百万元,除溢汇一百八十万元九百九十元外,尚得叁仟二百一十三万零一百元,更难谓无触犯惩治贪污条例第三条第七款之罪嫌”。
民国时期贪污腐败盛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更是令人发指触目惊心,粮食贪污腐败十分常见。民国时期的粮食贪污固然与当时腐败的社会风气有关,但也受粮食紧缺,粮价飞涨的影响。民国连年兵灾,农业生产遭受极大破坏,造成田园荒芜,生产低落,再加之各地水陆交通被破坏,粮食运输困难,以致粮食紧缺,粮价扶摇直上,官商勾结,盗卖公粮;侵亏公粮,囤积居奇;捏报损失,冒领运费等不断发生,本案中就是倒卖公粮的典型。
分析整个案件不难看出贪污腐败屡禁不止的原因,其一便是制度上的缺陷,民国时期制度并不完善,国民政府从上到下都没有强力有效地控制;第二便是人事,国民政府本身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其阶级局限性注定其人员会出现贪污腐败的情况;最后便是处置问题,本案中对其他人员没有相应的追责处罚。“政府与官员之间的上下其手默不作声,导致众多的粮政贪污舞弊案件;损害了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同时也逐渐拉开农民与国家之间的裂痕。政府对于粮政贪污舞弊的制裁不力是其一大败笔,同时这一失败也将广大农民推向了国民政府的对立面,当时我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业的国家,农民要占总人口的80%左右,大多数农民对国民政府的失望,甚至后来对国民政府的背离,某种程度也预示着国民政府命运的终结”。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