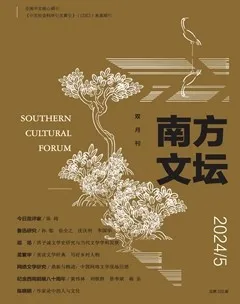中国雕塑的本土化:文化策略与当代实践
一、何为雕塑“本土化”?
“本土化”的英文为“indigenization”(名词),“indigenize”(动词),其含义非常宽泛,相较于“全球化”而言具有“国产化”“本地化”“在地化”或“民族化”等含义。针对“拿来”或“进口”的现当代中国雕塑而言,具有“中国特色”的雕塑是其目标指向,因为社会的驱动力不仅仅要满足对西方文化“嫁接”或“移植”,更重要的是要满足不断“创新”与“创造”的终极诉求。因此,“本土化”与“全球化”应该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也应当是与“现代化”“科学化”“先进化”“国际化”的统一,是民族“独立性”与他者“移植性”的统一。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本土化”不仅仅是雕塑所面临的课题,而是涉及各个学科门类的宏大课题。当下,“本土化”已经成为学术界讨论的较为普遍的课题,不同学科领域对“本土化”有着不同的诠释。有的学者认为“本土化”是在全球化视野下,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引进和融合,最终形成以本土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的过程①;有的认为“本土化”是“一种文化重组”,也意味着在本土地域中形成了“具备独特性的新质”②;有的认为“本土化”是民族文化具有的“本土的、个性的或传统的”特点以及“另指外来文化融入本土”③;有的认为“本土化”是“异域异族异质的‘他者’理论在满足本土化的条件之下,经过本土化机制的规约、融合、内化、操作与变革,使外来理论顺利引入、借鉴与转化的本土理论与实践的生成过程”④。还有的学者认为“本土”不同于“地域”,“本土性”不同于“地方性”,“地域”是地理学意义上的,而“本土”是精神性的,它有着文化意义上强大的主体意识,正是因这种主体意识的存在,才形成令人仰望的精神地貌⑤。以上阐述虽对“本土化”的内涵侧重不同,但其本质是相同的。
再来从全球化经济文化视角下来看“本土化”,“全球化”(glocalization)与“本土化”是相对的概念,“既指视角也指行为,主要关注特殊性和地方性”⑥。早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学界出现了“全球化”这一学术主语,主要是强调全球化的商品要结合本土文化才能获得成功,“麦当劳”的成功就是全球本土化的经典案例,遍布全球连锁店的菜品根据各地饮食文化而各有不同。《全球化:社会理论与全球文化》的作者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将“全球化”概念带到了文化领域,为全球化理论拓展了新的维度。他的灵感来源于一个日语单词“dochakuka”。“这个词指根据不同地域状况而调整自身耕种技术的一种耕种策略,20世纪80年代,它成了日本企业中的专业术语——‘微观市场营销’(micro-marketing)策略,指跨国性产品必须根据不同地域的特殊文化、习俗与特色而做适当的调整,以契合和打入地方市场的一种策略。”⑦他深受启发,认为词汇的内涵超越了全球化理论中的宏观与微观的二元对立论,“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普遍的特殊化和特殊的普遍化”⑧。由此可见,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雕塑“本土化”内涵也要放到“全球化”的语境中阐释才能找到相应的坐标。
通过以上的分析能够基本地揣摩到“本土化”的内涵,但是要完整地揭示中国雕塑“本土化”的内涵,还要将其放到中国雕塑发展的历史维度之中。从中国现代雕塑到当代雕塑的发展脉络来划分,不难看出中国雕塑“本土化”的内涵是不断深化和丰富的。第一个阶段,“本土化”内涵是引进西方的雕塑方法来做中国主题的内容。这一阶段的中国雕塑的主要任务是“启蒙”“强调科学、理性的精神”,是将西方雕塑“观念”与“趣味”向大众灌输和普及⑨。第二个阶段,是经过一段时期对西方雕塑的学习与消化,雕塑家在具备扎实的西式雕塑基本功的条件下,将中国古代雕塑的语言和民间艺术的造型样式与西式雕塑造型相融合的探索过程。这一阶段,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民族化”文艺方针到《论十大关系》和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全国文艺界掀起了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回归的浪潮。第三个阶段,“本土化”内涵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是传统造型、传统文化与物质符号、传统审美、传统哲学、地域人文与民族精神的全面探索。这一阶段可谓是“多元对话”语境,此时的“本土化”内涵不仅仅是一百年以前的西学东渐,更多的是代表着一种创新与开拓精神,中国当代雕塑的本土化既是对全球化的抵抗,又是其发展的产物。这不单纯是西方雕塑如何在中国生根结果与中国雕塑的优化和当代化的问题,最重要的终极问题是中国气派与中国特色的形成与持续发展。
综上,本文探讨的中国当代雕塑的“本土化”内涵包含上述丰富的内容,总结出两个特征:一是对异质雕塑文化的吸纳,二是在吸纳异质雕塑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具有民族精神内核的中国当代雕塑。这两点是与全球化博弈与对话的前提,可见,“本土化”的目的就是“全球化”。
二、雕塑本土化的生成逻辑与文化策略
近代的中国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从清末到民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之下,“救亡和启蒙”便成为时代主题。从魏源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王国维提出的“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不难看出对西方科学技术、社会体制、文化思想的向往与效仿,社会意识转型使一大批有识之士坚持不懈地师法西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由此而开启。伴随而来的还有“民族化”“民族主义”“民族精神”等思想观念,在激荡的社会变革与东西方思想文化碰撞的时代背景之下,文化“本土化”的问题开始被世人思考,成为中国学术界共同面临的重要命题之一。
雕塑的“本土化”及相关的思想观念彰显出文化自觉的强大内生动力,既是对传统文化将崩塌弥留之际的拯救与重构,又是对强势的西方文化话语的无声抵抗。中国思想界在20世纪20年代关于“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文化本位论”的争论对文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争论之激烈既体现出当时文艺工作的文化焦虑,又反映了他们对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捍卫与复兴的诉求。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中作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他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宣传“民族化”的号召,“创造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39年,延安的宣传与文化界开展了一场“旧形式的利用”与创作文艺“民族形式”的文化运动,“民族形式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积极响应。1940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其内容和性质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此之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文艺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的方针,其后‘民族化’逐渐成为一种显性和主流的话语”⑩。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讲话。这一讲话中,他首次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指导方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再一次推动了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回归的进程。2014年,习近平同志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11讲话是新时代文艺工作的风向标,再次为文化的“本土化”进程指明了方向。
20世纪初,“雕塑”一词由日本传入中国,与此同时西方雕塑体系被留洋学子带回国内。雕塑“本土化”问题成为摆在雕塑家面前的命题。中国雕塑历经百年之变迁发展至今,经过多次艺术观念的传入、学习、探索、转型,即是雕塑“本土化”的历程。1979年改革开放,西方艺术再次涌入,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次是以西方的现代主义为先导的各种艺术思潮的同时涌入,并且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多样化的艺术思潮纷纷涌现,形成了一种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且多元共生的局面。刘骁纯提出“如果说‘五四’以来的中西之争,以西方古典艺术的中国化和新美术的几度荣衰为最终成果的话,那么,这一次则以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涌入为先导,经过难以预料的波折起伏,最终将以对古今中外文化成果自由吸取的、多元化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振兴为辉煌成果”12。孙振华在谈论中国雕塑近30年的发展脉络时,把1979年以前的中国雕塑总结出了三个传统:一是“西方古典主义”的雕塑传统;二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雕塑传统;三是“西方现代主义”的雕塑传统。“在以上三个传统中,最有张力、最有冲击性和颠覆性、最富于变革精神的,应该是西方现代主义的雕塑传统。因为它针对过去而言,代表了一种新的知识形态,对它的关注、研究和实践,成为当时中国雕塑发展的重要线索。”13这条重要的线索也是中国雕塑“本土化”的前提条件。
从1979年至今,中国当代雕塑的发展得到了优越的社会环境与丰富的文化资源的支持。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文化交流呈现多元化的发展特征,各个种族、国家、地区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整体上呈现融合趋势,但又带有文化的对抗与冲突。面对新时代的文化发展形势,2014年,习近平发表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国文化指明了发展方向,他提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4。中国雕塑“本土化”过程中也要面对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问题,中国雕塑的创造性转化即是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转化,就是文中提出的“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在转化过程中要以自身的文化立场为中心,强调民族性与时代性。
“古为今用”不能将传统文化原封不动地拿来,要符合当代价值观才能为今所用,根据现当代时代精神与价值追求来取舍,并运用当代文化表现形式来呈现,在时代精神的框架下对其内涵进行阐释。“洋为中用”的思想早在100多年前魏源、林则徐等人士就开始提出,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洋为中用”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又有新的语境,即以民族性为内核。因此,避免崇洋媚外和盲目排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共识。民族性为内核是对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首先,外来文化的融入需要符合中华民族文化自身的表现形式,吸收对自身文化发展有益且符合社会集体价值取向的部分,去其糟粕;其次,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外来文化,要对其本土化转化,同时要符合传统文脉的承接与当下社会大众的精神诉求。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中具有强烈的文化指向,既代表了坚定的民族立场,又有着开放的国际视野。转化和创新并不是分开的,也不能以静态的眼光来对待,它们是以一种动态的并且面向未来的方式,推进中国文化创新性的持续发展。因此,“本土化”并不是让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它是包含着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新时代进行创造性可持续发展,形成新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
纵观历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实践与探索,中国雕塑已经由“外来之物”在本土化的进程中融入了“民族的血液”,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门类。回望中国雕塑“本土化”发展,取得了许多成就的同时,也经历了许多挫折。总结中国雕塑各个时期的“本土化”历程所呈现的不同特点和转化规律,并揭示蕴含在中国雕塑本土化过程中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脉络的深层谱系,研究分析中国雕塑“本土化”的具体面貌的内在联系与动因,在当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中国雕塑发展到今天已然进入了崭新篇章,过往成就毋庸置疑,但是“本土化”过程中也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与困惑,依旧在何去何从中徘徊。
面对中国雕塑的过往与当下,中西方文化、中西方雕塑体系及当今世界经济文化之格局,这些既构成了中国当代雕塑“本土化”和对其研究的统一背景,又是中国当代雕塑实践与理论研究所面临的问题与要求。
三、雕塑本土化的创作路径
民国时期中西方文化进行过激烈地碰撞,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尚未打开国门。滑田友、王临乙、杨英风、文楼、熊秉明、朱铭为代表的港、台及留(旅)洋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在本土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实践经验,雕塑呈现的创作路径以及在当代雕塑中的拓展,亦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港台艺术家和身在海外的中国艺术家不约而同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突破口,将传统符号作为艺术创作的源泉,希望能创作出带有浓郁东方神韵并能被西方所理解和接受的现代艺术作品。艺术家追根溯源,在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进而创作出具有东方神韵和现代情怀的佳作。通过比较发现有几条重要的本土化的雕塑创作路径:
(一)传统雕塑的本体语言的转化
传统雕塑语言最早的探索者是滑田友与王临乙。滑田友学习研究西方雕塑的同时把中国传统画论中的“六法”融入其中,他发现中西方艺术作品都是做到了“通体‘贯气’”15。早在留法期间创作的浮雕《长跪问故夫》已经颇具中国之风。之后,他用“气韵生动”之法创作了《轰炸》《农夫》《母爱》,形体上的凝练与汉俑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形式上均以高度概括的手法对雕塑的轮廓及细节进行归纳,强调大块面的形态转折及人物面部的神韵,达到了整体贯通、气韵生动的效果。
王临乙在留法期间并没有停留在对西方雕塑的研究,而是探索中西方雕塑相通之处。他创作的《供养》《大禹治水》《孔子像》等吸收了汉代画像石(砖)及汉魏雕塑的表现手法,作品浑厚、有力、简约、古雅,对整体气势和意蕴的追求体现出他对古代雕塑的深刻认知。在作品《五卅运动》中,他并未采用常用的人物分组方式,而是借鉴了北魏浮雕《帝后礼佛图》的构图精髓,巧妙地运用了平行构图法,营造出一种连绵不绝、横向流动的视觉效果。这一创新设计使观者仿佛置身于行进中的工人队伍之中,感受到他们向画面外无尽延伸的磅礴气势。浮雕中巧妙构建人物层次,通过精心组合不同人物,巧妙形成了三个层次分明的空间,为画面增添了厚重的历史感。
当代雕塑继续对传统雕塑的本体语言进行学习与探索。例如:邢永川的《杨虎城将军》汲取了汉代茂陵石刻的“怪”与“野”,以及唐陵石刻的“拙”与“憨”,形成了独特的雕塑语言;曾成钢的作品揭示了青铜器中线条的力量感与生命力,他将这些富有动感和节奏的线条称为“青铜线”,并巧妙地将这一雕塑元素融入自己的作品中;蔡志松的《故国》系列作品独树一帜,其融合了兵马俑的庄重、古埃及的神秘、希腊古风时期的典雅以及玛雅时期的原始韵味。
(二)传统哲学的转化
杨英风是中国台湾20世纪60年代以来具有国际影响的雕塑家之一,他崇尚自然之美,将中国“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作为自己追求的终极目标16。坐落在美国纽约的《东西门》,天圆地方(方形墙面加圆洞),以中国园林的“借景”手法通过不锈钢材料的反光效果,观念虽然极为前卫,“但所依托的仍然是东方庭园中的月门造型。至于细节处,如墙面转折的地方有意借鉴了中国卷轴画的装裱形式……这一切既在形式上与西方极少主义雕塑有别,又在含义上恰好吻合贝聿铭设计的东方海外大厦的环境”17。杨英风的“太鲁阁山水系列”自1969年起孕育而生,历经十数载,通过山川、水流、田野、晨曦与微风等抽象形式,深刻映射出他对东方哲学的独到见解。
在当代雕塑中,这条路径也有不少雕塑家在努力探索。例如:傅中望的作品巧妙展现了传统榫卯结构的独特魅力。他深知榫与卯,一凸一凹,恰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关系,相互依存、相辅相成;陈辉的《高山流水》系列作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理念的深刻诠释;郅敏作品从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出发,对河洛易数、四神天象,以及二十四节气进行抽象表达。
(三)传统文人审美的转化
文楼是中国香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数不多且颇具影响力的雕塑家,他以金属直接焊接的方式,将西方现代主义的抽象语言与中国传统文人审美结合。他的《荷》《竹》系列作品表现出文人风骨之精神。《竹》系列从中国画中汲取养分,作品以线条的流畅、墨色的层次和空间的布局展示了传统国画构图方法,为缺乏传统西方艺术欣赏基础的中国人提供了一条新的欣赏雕塑作品的途径。此外,在《荷》系列作品中,一方面展示了对材料特性的深刻理解和运用;另一方面又充满了传统绘画中文人画荷的韵味,使得这些作品在展现出金属雕塑的硬朗与精致的同时,也流露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柔与深邃。
这条路径在当代雕塑中也得到了拓展,例如:霍波洋的作品中多构造巨石、枯木、悬崖、孤竹、残荷、野桥、荒渡等文人精神世界的场域,将人物极简,随意组合,人与境交融,尽显出传统文人的精神追求;展望的不锈钢“假山石”挑战了人们对于“真实”的传统认知,通过不锈钢复制的赏石,让我们重新思考,哪一种山石更能真实地反映当代中国的文化面貌,它们虽非自然之物,却真实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审美观念和文化趋势;谭勋的作品通过对日常物品进行文人化改造,让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些物品背后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同时也让我们更加关注和反思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文化身份。
(四)传统笔墨与意象的转化
熊秉明的铁鹤系列雕塑展现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将中国书法线条的精髓与雕塑的构成完美融合。他以书法的思维方式为指引,精心组合铁条的形态、弯曲、长短以及位置摆放、比例关系、间架结构等要素,从而创作出富有东方韵味的线条艺术。为了实现雕塑与书法艺术的和谐统一,他选用了方棱的铁条作为创作材料,这种材料经过压、弯、曲、折等工艺加工后,所形成的形体韵律与中国书法的线条在形态上高度契合。线条状的材料使得“东方式”的抽象线条得以更好地展现,赋予了雕塑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铁鹤系列雕塑不仅展现了雕塑艺术的独特魅力,也体现了书法艺术的深厚底蕴。
当代雕塑把这种写意美学往前推动了一步:孙家钵的雕塑充满了写意的风采,体现了古代雕塑中的“得意忘象”,同时又体现出传统绘画中的“意笔草草、不求形似”,他在木雕上留下即兴的削砍痕迹,与水墨画中的“斧劈皴”有异曲同工之妙;陈云岗对线的运用是采用中国写意山水乃至书法的方法,以线入塑,具有一种书写性,在其作品《老子》中,一道道如涟漪般的线自眉眼处往外延伸,由细变粗,由少变多,正契合老子道生万物的哲思;吴为山将水墨画大写意精神带入雕塑创作之中,“写”这一技法充满了书法笔法的深远意境,其“雕塑笔触”如同书法家的笔触一般挥洒自如。
(五)传统文化符号的转化
朱铭在青年时期开始练习太极,与太极结下了不解之缘。太极代表着一种动态平衡的运动与变化,其中阴阳相互对立、渗透、作用、转化,生生不息。这种哲学体现了宇宙对立统一的规律,是最原始的古代哲理之一;同时,它也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特点,即重视感悟而非论证,既非依附科学亦非依附宗教。太极的哲学深深吸引了朱铭,使他开始创作“太极”系列作品。朱铭在“太极”系列作品中,不仅展示了太极的动态平衡和阴阳变化,还传达了宇宙间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这种独特传统符号,使他的作品受到广泛的赞誉和认可。
当代雕塑利用传统符号进行艺术创作成为一种趋势:董书兵的作品《无界》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内涵,成功地将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中唐代《经变画》的精髓融入现代艺术创作之中,作品所传达的“无界”理念,也是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界限的一种突破和超越;何镇海的《门闩》《门》《陶木结合》系列作品都是在寻根传统文化,运用传统符号进行结构与重组,唤起强烈的民族集体记忆;刘永刚对汉字进行立体化创作,其作品绝不是简单嫁接、挪用,每个雕塑形态都经过反复的推敲,抽取文字中线与立的因素,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站立的文字。
四、结语
中国雕塑的“本土化”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更是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转化。它体现了中国艺术家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展现了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雕塑如何与世界艺术对话,如何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和创造性。面向未来,中国雕塑的“本土化”将继续在探索与实践中前行,寻求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艺术表达,通过不断地自我革新和开放包容,中国雕塑将在世界艺术舞台上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东方与世界的桥梁。
【注释】
①王丽新:《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本土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2,第18页。
②梁江:《本土化:百年中国油画的主题词》,《文艺研究》2005年第8期。
③李国庆、宋国彬:《平面设计及其设计元素的本土化与再造》,《包装工程》2004年第6期。
④龚孟伟:《当代课程理论本土化探析》,《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7期。
⑤邱正伦:《构建,必须从本土立场开始》,《美术观察》2009年第2期。
⑥安娜贝拉·穆尼、贝琪·埃文斯:《全球化关键词》,王德斌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81页。
⑦单波、姜可雨:《“全球本土化”的跨文化悖论及其解决路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⑧金惠敏:《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全球化——约翰·汤姆林森教授访谈录》,《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⑨孙振华:《中国当代雕塑》,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第4页。
⑩李竹:《文化自觉与身份认同:重庆雕塑的民族化探索(1940—1960)》,《中国美术》2022年第1期。
111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12刘骁纯:《解体与重建》,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第293-294页。
13孙振华:《资源与拓展——近三十年中国雕塑的发展脉络》,《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
15滑田友:《谈雕塑的组织结构》,《美术》1959年第8期。
16王志刚:《略论杨英风雕塑艺术美学风格》,《西北美术》2002年第2期。
17丁宁:《杨英风:一个有思想的雕塑家》,《中国美术》2012年第2期。
[刘宇航,广西艺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胡筠,通讯作者,广西艺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本文系“广西高等学校千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人文社会学科类立项课题“数字技术植入雕塑创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21QGRW049;2022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传统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抽象雕塑研究(1979—2020)”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22KY0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