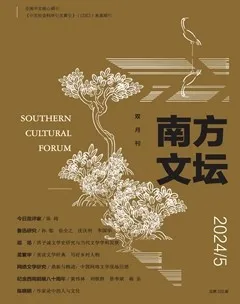人世幻相、生命实在与神性赋格
作为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朱辉继承发扬了江苏作家对日常生活细致写实的传统。印象中朱辉擅写短篇小说,也因短篇小说获鲁迅文学奖,但长篇小说是另一种挑战。长篇小说《万川归》,从题目到规模看,应该蕴含了作者的文学雄心以及长期的人生感悟。“万川归”者,从字面上理解,是人生纷扰,如百川到海,总有归处;从文本来理解,可能喻指万风和、丁恩川与归霞所代表的人生殊途。整体而言,《万川归》首先是摹写世俗日常的世情小说。小说没有慷慨的英雄叙事,也没有尖锐的精英立场,围绕几个主要人物的人生历程,分分合合,草蛇灰线,以串珠式的多线程叙事呈现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当下近40年的跨度里,不同人物与时代谐振的俗世画卷。小说其次也可归入近年来一些学者所谓的“暮年叙事”。一方面,小说集中展示了几位主人公从中年到老年十多年的变化;另一方面,小说有鲜明的暮年回顾视角与人生易逝的惆怅基调。但“暮年”并不意味着“暮气沉沉”式的贬义,关键取决于对人生作何种领悟。作者朱辉生于1963年,现已年过六十,根据如今国际公认的看法,其实还算中年;但作为一个有思考的作家,这个年龄足以使其完成对人生的深层次思考。沿用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意象,人生其实是面向死亡的“跳水”。生命的尺度已经确定,人生的意义在于从起跳到入水的过程。同样,这部小说也是作家直面人生的一次写作跳水,世俗人生,似乎没有太多新意,但《万川归》却从三个维度,体现了作家穿透人生的努力。
一、追溯之眼与人世幻相
回忆是暮年写作的典型特征。彻悟是一种智慧,智慧来自记忆,记忆来自经历。表面看,小说的叙述时间从2006年开始,一直延续到当下,是一种线性发展叙事。但隐藏于文本之中的诸多预叙,诸如“他当然没有想到,他自己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把另外几个陌生人联系到了一起”等,意味着小说世界匍匐于全知的“追溯之眼”之下。事实上,凝视无处不在,构成小说的叙述基调。例如有两个代表凝视的典型意象。其一是于生活中无处不在、代表生命的蝉之复眼。当万风和生无可恋有自杀倾向时,小说让他的灵魂与蝉伴飞,通过蝉眼回顾了其生命的重要时刻。其二是于高空中无远弗届、代表智慧的月亮之眼。如后所述,李弘毅的灵魂与月亮融合,并使月亮成为巨大的凝视之眼。
小说的第一个事件是万风和“失忆”。就叙事功能而言,“失忆”的意义在于赋予“追忆”以合法性。从心理层面,“失忆”恰恰便于裸现最遥远和最深刻的“记忆”,正如催眠对于潜意识的召唤那样。失忆前万风和下意识地拨通暌违18年之久的同学李璟然的电话,暴露了其作为外表光鲜的“成功人士”的缺憾,那就是“爱情”的亏欠。如小说所言,他的家庭也生病了——万风和甚至跟妻子刻意隐瞒了自己住院手术的事。李璟然则是青年万风和纯粹而浪漫的爱情记忆的见证——尽管是单相思式失败的恋爱。“爱情”的亏欠还有另一个佐证:失忆后最早召唤的是少年时代的“洞穴记忆”。表面看,“洞穴记忆”唤起的是辛苦而不失美好的少年复读时光,但如弗洛伊德指出,童年琐碎记忆之所以存在,其实是作为某些更重要印象的替身或转移出现的①。事实上,洞穴是同学转让的爱情小窝;少年无意看到蝉交媾的细节,以及寻找油菜花上“一袭红衣”的惯性,表明“洞穴记忆”掩盖的是青春与爱情的欠缺。
从主题层面,“失忆”其实并不构成重要的事件,它没有促成万风和人生或人生观的根本性改变。其情节功能是突出了“亏欠”:李璟然的出现表面看弥补了万风和爱情的亏欠,但依然只是“徒有其表”;这一情节还引发了万风和对儿子“非血缘”的发现——这是更大的亏欠;自然,失忆作为疾病本身也指向了身体的亏欠,更大的打击即将到来,如作者的预叙:“这一次的手术只是一次彩排,一场预演。”②根据传统民间伦理,人生圆满在于光宗耀祖、父慈子孝、儿孙满堂、身体健康,这些都是万风和重视和追求的方面——这也证明了万风和俗世之人的特性——但恰恰在这些方面,中年万风和都存在着难以弥补的亏欠:虚假的婚姻爱情、虚假的血脉以及背叛的身体。当万风和与李璟然在病区悠然散步时,一股臭味侵袭了原本美好的花香(同样的臭气也侵袭过万风和与杜衡温馨的散步之路),作者于此已经埋下了作品的基调:“鼻息里有万般味道,但刚才那臭味,世俗的味道却如影随形。这也是人世真相的味道。”③亏欠或虚假,正是生活之臭。
不动声色的追溯之眼,残忍地展现着“人世真相”:万风和与杜衡无爱而背叛的婚姻;李弘毅向女友隐瞒实际工作同时兼职代人体检(本质也是欺骗);万风和用印章换取贷款以及用身体换取土地批文;李弘毅的短期老婆马艳或者说归霞家的保姆齐红艳,身份来路成疑;婚姻对归霞无非是理性的权衡,而对周雨田而言则是合作伙伴关系,后者因此没有心理负担地隐瞒房产并包养情人;李璟然在万风和换心的节骨眼上远走高飞;等等。更琐碎地看,无论是万风和制售盗版的发家史,或者周雨田指导学生的敲诈与反敲诈,乃至堂姐建议拆自己家房子重建的信手一笔,都透露着作者的戏谑与冷峻。人世真相,正如老孔的红木家具、掮客卓红的高干背景一样真假莫辨。从更宏大的尺度,虚幻借助科技颠覆并重建着人们新的世界观。小说中,财富的数字化、虚幻化曾引发万风和的焦虑,也提及最新的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虚拟世界,还指出通过脑机接口可以删除甚至修改人脑记忆。所有这些,有力烘托了小说关于世俗人生一切皆虚的重要命题。
“虚假”在小说中无处不在,发展为小说不可或缺的叙事美学。首先是鲜明的情境反讽。在万风和为房地产批文而进行的性贿赂中,油菜花加白衬衫的幻觉,与浮动在油菜花上的一袭红衣的少年纯真记忆互相叠印;万风和对繁衍后代、延续血脉的执着,与最终自身的“领养”真相构成了鲜明的撕裂。其次是潜在的震惊效应。“换心”作为小说的核心事件,无疑具有隐喻性。小说中多次出现血淋淋的器官意象,如万风和住院期间的噩梦、医院里的真人器官标本、李弘毅关于器官的白日梦等,同样构成了对虚幻之美的解构,具有“生活之臭”的语指功能。换心(万风和)、换肾(归霞)与换眼角膜(老孔),最为可靠的身体遭受侵袭和被替换,几乎是寓言般地彰显了虚假的无处不在。“器官聚会”拜访原主人,这一情节在现当代小说中极为罕见。来自未知身体的心脏(肾、眼角膜、肝等),取代了身体原配的心脏,显然带着鲜明的“异质”性。这一重要意象在小说中有着双重和声。和声之一,是万风和与李璟然共建的房产“万璟家园”,本来似乎是美满爱情的见证,但其建成却伴随着李璟然的出走与爱情的崩塌,换言之,原配的家园之“心”没了,只留下了徒有其表的实体;和声之二是关于万风和与万杜松的血脉,万风和的领养身份与万杜松来历不明的父亲,使他们双双成为“万氏”纯正的血脉传承历史中的“异质”。万风和关于老孔收藏的反思也是同类隐喻:“琴案是祖上传下来的,他就肯定是真的,那他的这些东西今后传给他儿子,不也是祖上传下去的吗?这算怎么回事?”④因此,历史其实也来路可疑,具有不堪细究的特性,人世“真相”即是人世幻相。
二、穿透幻想与拥抱实在
一切皆虚,这似乎是“暮年”普遍性的人生感悟,算不上新鲜。回到小说中多次出现的“臭味侵袭了原本美好的花香”的场景。齐泽克在《事件》中剖析电影《忧郁症》时提到过类似的例子:“昆虫、蚯蚓和蟑螂这些令人厌恶的生物纷纷从地底爬到草坪上,揭示出隐藏在优美光鲜的草坪下那些令人作呕的生物。”齐泽克对此总结说:“在此,实在物(the Real)侵入了现实生活(reality),摧毁了后者的表象。”⑤现实生活的表象,正是人世幻相;而实在物则是拉康意义上的、破坏与拒绝现实象征的纯粹之物。“臭味”如同昆虫、蚯蚓和蟑螂,是拒绝象征的实在,它把诗意而虚幻的爱情还原为人世真相。在这个意义上,杜松的亲子鉴定报告、写着万风和生日的红纸片等,都是实在物,它们通过对人类所谓的亲情、血脉、体面等的否定,揭示着人世的虚幻及人类惯有的自我欺骗。这种否定,也容易让人坠入虚无。中年万风和面对儿子非亲生的事实,曾一度产生自杀之念;知道自己身世真相的老年万风和则在鸡鸣寺援引《金刚经》所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与看风水出身的老孔“看破不说破”的体会相呼应。诚如是,人生的意义何在?或者说对“空”的彻悟便是《万川归》的终极主题?上述核心问题关乎着《万川归》所能达到的思考深度。
事实上,就佛家理论而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意味着不惟现实生活之美好是空,虚假也是空。那么,需要注意到,在“臭味”的另一面,《万川归》中还有一类纯粹之物,从与“臭味”截然不同的方向,参与了对日常生活表象的摧毁以及重建。鸡血石与城砖便是这样的实在物。二者在小说中占据着显然非常重要的地位。鸡血石是万风和继承自父亲。如果通过追溯之眼来审视,父亲把鸡血石传给抱养的儿子万风和而非亲生儿子,表明了父亲对纯正可靠的亲情的确证。吊诡的是,正是可靠的品质使鸡血石在虚伪的利益交换中具备了价值。但正如小说指出的,鸡血石可能不断被转手,字迹可能不断被磨洗,但其真实性不可磨灭,谁也没有真正拥有它。性质类似的是由万家先人烧制并烙有指印的城砖。它穿越历史而与万风和邂逅,又将与那些仿制城砖一起混在不再可见的某处,但它的真实存在是确定无疑的。当然,这需要将自己从狭隘的现实中解放出来,从更宏观的高度才能理解:对于历史或人类而言,无论是鸡血石还是城砖,它们的真实性无可置疑,而且也从未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心脏”由于其独特性,注定了也是实在之物。健康的心脏代替了生病的(因而也是虚假的)心脏,尽管对万风和而言这个外来的“异质”是真中之假,但它有力的跳动维系着个体生命,真实不虚,因而也是绝对之“真”。
再次回到小说开头,失忆中的万风和“裸现”的是少年河岸洞穴的记忆——说“裸现”,是因为它是经受了失忆的磨洗最早呈现在记忆之海的,这一事实突显了它的坚固或实在。每个人记忆深处其实都有一个“洞穴”,它是祖父的老宅,是母亲的子宫,是孩子的魔法城堡,是成年人心灵深处的柔软或本真。哪怕是小说中惊鸿一瞥、老于世故的掮客卓红,也有她的“洞穴”,那是她关于穿白衬衫的小学语文老师的记忆。少年洞穴在现实中注定已经并不存在,但万风和依旧有寻找的冲动。这种下意识的寻找代表了纯真与初心的吸引力。月亮也是具有“洞穴”性质的实在,并具有正向的引力:“月亮绕着地球转,但它永远只把正面对着地球,背面你永远看不见。”⑥“月亮在广阔的水面上显示出它巨大的引力。”⑦月亮的引力牵动的不只是江水还有记忆的潮汐:“他被母亲抱在怀里指着月亮说,灯!”“灯”正是小型的月亮。作为个体记忆原点的“洞穴”,与“代代无穷已”、具有历史高度的“月亮”,在小说的首尾遥想张望,赋予了“万川归”以历史的、哲学的乃至宇宙的宏大视野。
客观地说,有限的实在之物的锚点,难以对抗庸常生活的洪流。经验生活需要靠表象的“伪饰”。天主教让教徒远离肉欲的方式,类似中国佛家的“白骨观”,其逻辑是,借助腐烂的身体避免诱人身体的致命诱惑,但如果真去掉了一切的“表象”只剩下本质之“真”或“空”,那么日常生活的意义又在哪里?对此,齐泽克提出了具有颠覆性的观点,他逆转了柏拉图关于理念是实在的看法,指出“女性之美是绝对的,它是绝对物的表象:这种美——无论是多么的虚假与脆弱——乃是位于实质性的真实层面,它流露和渗透着绝对之物,换言之,这种美的表象比其所隐藏的东西揭示了更多的真理”⑧,齐泽克同时引用了拉康“知者反失”的观点,指出“愤世嫉俗者错过了表象本身的实在性,无论这些表象是多么的脆弱、缥缈和稍纵即逝;相反,真正信任他人者不但相信这些表象,而且相信那能‘照透’这些表象的神奇维度”⑨,对此,后期列斐伏尔强调“瞬间”对日常生活的超越和否定意义,可视为对齐泽克观点的补充:“(瞬间)它是一种节日,一种惊奇,但不是一种奇迹。只有在日常生活的单调无奇之处,瞬间才有大显身手的地方与舞台。”⑩换言之,世俗生活中那些短暂而闪光的瞬间是重要的,它们拥有实在的光辉,因而构成了生命的意义和实在。因此,可以重新理解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中,促成白流苏与苏柳原在战争中放下面具达成谅解的那个“瞬间”:“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11这一发现其实体现了张爱玲对其所钟爱的世俗生活的理解与直觉。
《万川归》中,赖以与虚假或亏欠的实存对抗的,正是若干这样的瞬间。归霞无疑是小说中最具小市民气的,小说中对她的许多描述是张爱玲式的,诸如“这是个实实在在的男人,跟自己过日子的男人,她自己选的男人”。她在年轻时就在爱与被爱之间做了现世安稳的选择,但这并不能保证她的幸福。以追溯之眼看,她的幸福恰恰在于那些瞬间,比如她与周雨田的激情之夜,比如师兄在她被绑架时倾囊相助的真诚,比如她年轻时与丁恩川的模型之夜——有点像《金锁记》中曹七巧回忆起年轻时屠夫对她的喜欢。万风和同样拥有过那些沐浴着实在光辉的瞬间,比如油菜花上一袭红衣、怦然心动的单恋、失态的体育馆之夜,以及六岁时看“海”的记忆,等等。小说很遗憾没有更深入或更有意识地揭示这些瞬间对于归霞或万风和的意义。归霞的不幸可能在于,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曾经拥有过这些美丽的现实,因而无法找到内心的真正平静。小说指出,她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在为身体苦苦挣扎(周雨田被她逼着去鸡鸣寺祈求健康)。万风和显然比归霞对生命更有所领会。他走出了璟然出走的痛苦,也走出了因发现自己被领养而发生的认同崩塌。小说最后第一次提及六岁时父亲带他看海的记忆,是富有深意的。长大后的万风和明白了,当时看的其实是湖而非海,但他从来没有戳破过这梦。——这是沐浴着实在光辉的瞬间,梦的背后是父亲真实不虚的亲情,这正是生活虚与实的辩证法。小说最后这样表述:“万风和的心脏如波浪般沉稳地律动,他心中澄澈,一片宁静。”12异质的心脏终于和身体和谐共存,这意味着万风和完全接纳了“异质”的儿子,接纳了作为“异质”的自己,也彻底接纳了这个充满着异质的现实世界。
由此,无处不在的虚假或亏欠的现实,与实在物及沐浴着实在光辉的瞬间,构成了世俗生活对抗而平衡的二维,也代表着作者对俗世人生的重要理解。
三、神性赋格与世界复调
但上述领会并不是《万川归》试图表达的全部。如前所述,《万川归》采用了全知视角下的多线程叙事方式。从叙述学的角度,全知视角一般隐含着统治作品世界的作家意志;多线程叙事往往服务于统一的主题。但《万川归》并非如此。万风和并不是作者在小说中的代言人,小说保持了一种奇异的沉默、清冷和封闭。细究之下,尽管小说角色众多且生命轨迹时有交叉,但无论是夫妻、情人、同学、父子、兄弟、同事抑或路人,彼此间几乎都没有发生过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即便小说最后,所有重要人物都因归霞葬礼而汇聚到江轮甲板上,关于人生的寒暄也只是在万风和与丁恩川这两个相对陌生的人之间展开,且彼此依旧没有本质上的敞开。因此,小说于俗世的纷扰中透露着孤独。如小说所言:“生活如流水,一条河里的鱼不认识另一条河里的鱼,一滴水不认识另一滴水。”13个体本质上是孤独的,人与人之间本质上难以沟通,就像万风和从未认清璟然或杜衡,而归霞与丁恩川自始至终都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这种孤独其实带着神性,因为神不在外界而在每个人内心,孤独意味着不向外求而直面内心。小说的多线叙事则由此而于封闭沉默中呈现出世界的复调,它平等地呈现出诸多孤独的个体各自与自身“上帝”的对话。
在此意义上,李弘毅代表了小说的一条独立与奇特的线索。他从一个起初并不引人注意的保安,最终灵魂上升到与月亮之眼同在,在《万川归》实在与现实对峙的二维日常生活世界中矗立起一个尖峰、一个垂直的神性维度。李弘毅是由“憨”变“傻”。如小说指出,起码在跑保险以及代人体检的阶段,他还是相对正常的。但“正常”恰恰代表了俗世的污染。与女友分手之后,他“从此特别痛恨骗人”——也是从此开始,他的傻慢慢变得明显。俗话说,傻能通神,变傻的过程,实质是袪除世俗性、神性不断增强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超越日常因果的宿命性与必然性——这正是神性的特点。一方面,他走向捐献肉身具有宿命的成分:代人体检反复验证了器官的健康;“白日梦”暗示了其捐献器官的使命;救人已经成为他的自觉行动——他甚至专门绘制表格;最后他的遭遇车祸与捐献心脏、肾、肝、眼角膜等,只是水到渠成,是佛家“布施生命救众生”理念的具现,如一般民间所言,救人是“菩萨”行径。另一方面,他的神性不来自外界而来自内在:在一次与器官有关的白日梦中,李弘毅听到了没有性别的声音对他的召唤,伴随着天花坠落、光追在他身上——无性别正是神的特征;在另一处,小说提到他对鸡鸣寺的梵音觉得耳熟,暗示着他的“佛缘”——因而也是神性。
李弘毅因此几乎注定不会死去。一方面,他的肉身在万风和、归霞、老孔等人身上得到了延续;另一方面,肉身解体只是促成灵魂飞升。小说用不少篇幅提及李弘毅生前对灵魂的研究,诸如科学家称出了灵魂的重量,人死后灵魂将在四维空间继续存在,人其实是永生的,等等,是有深意的。因此小说下部出现了一章李弘毅的魂灵叙事并不突兀,上节曾经指出月亮作为实在之物的纯粹性,也就是神性。灵魂、月亮与生命,都具有不灭的神性。这也让我们注意到遍布小说的蝉鸣。即便是在万风和失忆的过程中,蝉鸣也从童年鸣响到现实,从未停止。如作者指出,蝉表面在秋天死去,“到树下的土里,新一轮蝉鸣正在孕育生长”14。蝉是生命的天使与永生的歌者;正如现实世界中,万风和儿子的生衔接着母亲的死,归霞的死又跟着丁恩川孙子的生,人类的生死衔接也具有永恒性,这构成了这部复调小说的生命咏叹调。
万风和自然并不知晓或领会李弘毅的神性,就像我们并不确知孤悬的月亮意味着什么。但李弘毅确乎救了万风和两次:第一次是长江大桥那次,万风和其实本来是抱着自杀之念的;第二次则是心脏的捐献。刻意的巧合证明了神性的“拯救”意义。李弘毅对万风和的拯救不只是身体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万风和要求杜松寻访器官主人,发生在万风和发现自身系被领养的真相之际。他亟需用全新的血脉重建,来挽救濒于崩溃的自我认同。小说没有揭示万风和发现器官主人是李弘毅后复杂的内心,但给予了行动的证明:他向同伴语无伦次地介绍李弘毅,带着杜松跪拜,并着手解决李家住房的问题(在此之前他曾想重建自己的祖宅),这一行为带着血脉归宗的仪式意味。
沿着李弘毅这条线索,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个人物:丁恩川。万、川、归中,丁恩川似乎着墨最少,但如果说李弘毅的存在是给予世俗化的世界以神性赋格,那么,丁恩川则在此意义上构成了李弘毅的副线或和声。丁恩川与李弘毅都具有热爱科学的求“真”气质;丁恩川醉心于水利工程的理想与激情,无疑具有“痴”气,而痴与傻具有相似的性质,丁恩川身上因而同样带着神性的光辉,这也正是归霞选择离开丁恩川,后来又气恼他乃至屏蔽他朋友圈的深层原因:神性有一种难以正视、不能靠近的面向,也是逼使她返视自身现实的实在。丁恩川在母校图书馆讲座的感染力、映衬在蓝天下的彩虹式拱坝,在召唤着另一个完全陌生的、曾经的或想象的自己。归霞对丁恩川的回避,本质上是对自身庸人化现实的回避。但回避本身恰恰意味着吸引。或者说,俗世表面上回避神性,但神性之为神性,恰恰在于其引力的亘古存在与不可抗拒。归霞临终作出的将骨灰撒江的决定,很容易被忽视。海德格尔指出,死“作为生存之最极端的可能性而悬临在它(——指本真的存在)面前”15。常人会在“死”前有所闪避,一种常见的方式就是用死生交替的循环证明生命的温暖,正如小说中,但对归霞本人而言,“死”是绝对性事件,无法闪避,只能基于本真的选择。骨灰撒江,表明她最终选择拥抱生命的本真,向曾经的青春梦想敞开自身。
小说最后:“西边红霞满天。正上方的天空出现了一轮圆月。”16红霞短暂,圆月永恒。“归霞”代表了作为个体的归霞对神性的拥抱,但作者明智地对此不再置喙。所谓大道无言大音希声。全知的追溯之眸,凝视着热闹而孤独的诸多种俗世人生。而圆月再次升起,这是属于朱辉的月亮,它不只是一轮文学的月亮,同时也是凝聚着神性、承载着古往今来无数生命和灵魂、牵引着俗世不至于沉沦的月亮。
【注释】
①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第36页。
②③④⑥⑦12131416朱辉:《万川归》,《钟山》2023年第1期。
⑤⑧⑨斯拉沃热·齐泽克:《事件》,王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第23、100、104页。
⑩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第234-235页。
11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第199页。
15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第303页。
(刘志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平民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当代平民文学史建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1BZW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