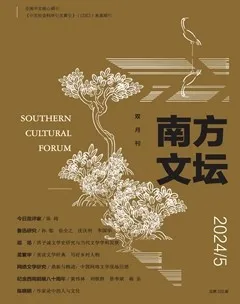海洋书写的新南方之维
近年来,林森将自己的笔触转向了海洋,他有关海洋的作品占了相当的比例,以《海里岸上》《唯水年轻》《岛》等为代表的海洋文学作品更是能够代表林森现阶段的关注重点,为读者和评论者所津津乐道。从《海里岸上》到《唯水年轻》再到《岛》,林森对海洋的认知不断发展:从对“海”“岸”关系的反思到重构一种向海而生的生活方式,再到发掘一种源自海洋的文化底色并以之为契机对海南文化进行反思,海洋已经成为林森创作中的一个视角或者一种方法,借由海水的折射,林森看到了更多有关人类与世界关系的隐喻。
要理解林森的海洋文学创作,则需要将其置于“新南方写作”的范畴之内。林森是“新南方写作”作家群中的一员大将,也是这一文学浪潮的重要发起者与实践者,其本人对此也有着很强的自觉,他将自己的创作称为“走入南方蓬勃的陌生”①。“新南方”是一个极为丰富的概念,以某种本质性的概念来对其进行总结本身就是不现实的,但是,就林森的文学创作而言,“海洋”的确赋予了他比其他作家更“南方”的精神气质,“新南方”与“海洋”在林森的创作中融合,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学气质。林森的海洋文学显示出“更南”的气质便是源自于此,通过海洋,林森用笔建构着自己的“新南方”,并眺望着更辽远的“新南方”之南。
一、非建构的新南方之海
“南北之别”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建构,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建构。这一建构大致起源于魏晋时期,直至唐代“南北之别”方成其形②,这一文化格局持续了千年,而到了晚清,“南北之别”有了一定的松动。钱基博称:“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汇合于蜀(吴虞)。”③钱基博所列举的近代学术谱系则皆在长江之南,这足以证明这种文化建构并非一成不变。“新南方”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对这种文化建构中“南北之别”的反思,“新南方”之“新”,其中本就蕴含着这种非建构性的特质。“新南方”是不证自明的,是自为的,不需要依靠所谓“南北之别”便能够充分地展示自己。“新南方写作”有着一种源自于世界视野的开放性,当那些执着于“南北之别”的作家们还在紧盯着地理意义上的界线之时,“新南方写作”的作家们则越过重洋,将目光投向了与南北无关的远方。海洋,在此时承载着新南方的意义。
林森的海洋文学创作正是这样,他写海,但并不仅仅是写海岸边的生活,而是用更多的笔墨去描写不同身份的人群在海上的生涯,这在很大程度上便避免了在描述海洋时代入一种“陆地心态”。人类是生活在陆地上的生物,漫长的时光已经使“陆地心态”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形成一种话语上的霸权,人类总喜欢用陆地上的思维方式和尺度去衡量身边的一切,使一切成为陆地上的“景观”。不可否认,这种思维方式在大多数时候是有效的,但是对海洋文学而言,这种心态却面临着失语的尴尬。海洋文学所处理的问题很多时候超出了“陆地心态”的经验范畴,《海里岸上》中写渔民要“习惯晕船”,《唯水年轻》中写一家几代男丁都葬身海中却又前赴后继,《岛》中写一个人在孤岛上渐渐习惯孤独皆出自于此。林森笔下的海洋不是景观式的、固化的意象,而是需要用生命去体验的情境。
事实上,仅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范畴内,海洋文学的经典作品就不算少,郭沫若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写到了汹涌澎湃的海,庐隐在《海滨故人》中写到了浪漫感伤的海,冰心在《繁星》中写到了平和安宁的海。到了21世纪,海洋文学掀起了一股热潮,王蒙有《海的梦》,张炜有《黑鲨洋》,舒婷的《惠安女子》更是将海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在这些作品中大多存在着一个共性问题,即文本中的海看似在场,实则缺席,也就是说,海洋并未能作为一个主体出现在文本中,而是作为一个被观察、被凝视的客体,静静地、被动地等待着作家的拣选。而在林森“新南方”观照之下的海洋文学创作中,海洋主动参与到小说剧情的演进当中,不再是一个失却主动性的、场域性的存在,而是小说的一个主体,是除了叙述主人公之外的另一个主人公。
在林森的海洋文学创作中,人与海洋的关系是平等的、对话性的。在《海里岸上》中,老渔民阿黄一生与海相伴,甚至因为捕鱼而疾病缠身,但是,在阿黄对海洋的言语中仍能感受到他对这位相伴一生的朋友与对手的尊重:“大家靠海吃海,但现在没人祭海了,大家都信仪器,不信仪式。一门心思只想着钱,渔村没有了……没有了……”人与海洋之间需要一种互动,需要一种灵魂的直接交流,是有温度的,而不是通过冰冷冷的所谓“现代”仪器而达成的掠夺。而渔村的存在也正是这种交流后的产物,人与海洋达成了某种共识,双方互相敬重,互相生成。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冲突是林森在书写海洋时重点关注的问题,现代科技总以为能通过所谓“理性”来解释整个世界,然而,它在面对海洋时是无力的,在面对海洋与人在精神维度的对话时是无力的。“大海养人也埋人”,“养人”与“埋人”也是互为表里的,那些被“埋”在海洋之中的灵魂是海的使者,通过各种方式提醒、护佑着后辈向海讨生活的人们,而海边渔民也将海视为自己最终的归宿,渔民老苏手抄的《更路经》最后一页便是“自大潭往正东,直行一更半,我的坟墓”,在那些真正了解海洋的人们心中,海洋与人最终将合二为一。在《岛》中,林森将海洋与人的对话关系书写得更为惊心动魄,他仍是写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以“现代”为借口,人们倾覆了海边的博济村,倾覆了记载着主人公吴志山一生的“鬼岛”,甚至赋予这座荒岛以“海星现代城”的名字,可是,就算是建设得再现代、霓虹灯再明亮,也无法还原海洋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不再是一个岛,这是一块被机器横扫过的工地。这里不再有生命的呼吸;不再有人在这里天天捡起石块垒积,犹如西西弗斯;同样,这里不会再有人刻下‘半生心事秋凉春暖愁岁月,永世恩情林秀风清忆海天’这样的话”,在所谓“现代”的冲突之下,海洋与人之间的关系被人为割裂,从人类的角度出发,海洋失去了主体性,成为被欣赏、凝视的景观,任人摆布;而从海洋的角度出发,人类也将不再为其所护佑,《岛》中写到了一系列人与海洋之间关系破裂后的异象——猪狗鸡鸭的烦躁、鱼群的死亡、幻觉中从海底而来的声音和海怪,而这只不过是预警,更大的灾难也许正在路上。
在林森的海洋文学写作中,“新南方写作”的视域带给他更多的思考空间,在他的笔下,海洋因着其非建构性而丰富,也因着人类总想着要“建构”海洋、“赋予”海洋某种自己喜欢的文化景观而苍凉。林森书写着海洋从非建构到被迫受建构的转变,并呼吁能够重构人与海洋的关系,但是,林森的海洋文学创作也并不是那种以环境保护为核心的“生态文学”,他所反思的是人,是那些生活在“新南方”的人,他们曾经习惯于被建构,而今,他们需要重新找寻一种能够自我言说的方式,而这便是新南方之海的重要性,它打破了一种源自于陆地的话语霸权并对其进行反思,提供了一个可以观察“被建构”过程的样本,并搭建了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平台。
二、内化的新南方之海
在对“新南方写作”研究的过程中,很多评论者注意到了普遍存在于其中的“幻想”特质,并称“他们的文字、故事和意象充斥着潮湿的、阴郁的、魔幻的、混沌的南方气息”④,而如果深入发掘就会发现这种“幻想”特质的源头——“新南方”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个无法被本质化思维所言说的文化空间,它的存在不仅仅是一个方位,更是一种集体认同或集体想象。人类喜爱为万事万物归类,这样方能获得作为万物灵长的安全感。近几百年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用“科学”去审视身边的一切,并称之为“理性”,殊不知,此时的“理性”已经形成了一种话语霸权,它将一切对象化、物质化,但在物质世界之外,尚有“心”这一重空间是所谓“理性”所无法完全驾驭的。“新南方写作”中的“幻想”特质则来自于此,“新南方”有很强的外向性,但首先它是向内而生的,它扎根于作家与主人公的“心”中。
林森笔下的海洋也正是这样,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场域”,而是一个“心域”,所谓“心域”,包含着外部的客观世界与作家的主观世界,同时,还包括了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林森的海洋文学书写有一种自叙的性质,这并不是单指其小说常以“我”为主人公,更是指其在作品中常会安插一些自我抒怀性的文字。例如在《岛》中,上来就是一句“有谁见过夜色苍茫中,从海上漂浮而起的鬼火吗?”《唯水年轻》中的“海神……顶天立地的海神……并没有身躯立起,可海面下不绝的涌动,是不是他在潜游、叹息和伺机而动?那么多年里,打骂的阻碍和拦截,没能让我完全隔绝于那片海”。这样的叙述方式对很多小说而言是个大忌——能指过于宽泛的抒怀往往会让读者有一种漫无边际的说教感,但是,对林森的海洋文学书写而言,这种叙述方式却构成了其艺术特色。在“新南方写作”的视域下,林森在文本中的抒怀并非空有无限大的能指,相反,它是有着明确的对话对象的,这个对话对象是自己、是海洋也是读者、是作品中的人物,这四者又在文本中达成了统一,使整部作品沉浸在一种被海洋环绕的氛围之中。换句话说,在林森的海洋文学书写中,写海就是在写自己。
“新南方”是自足的、非建构的,新南方之海亦然,这也意味着林森笔下的海洋并不是一个已经被概念化、本质化、定型了的景观,而是一个在不断运动、不断更新、不断突破自身原有形态的活的生命体。那些理性、科学的归纳对这片海洋是失效的,唯有不断发展的经验与内心世界的灵感能够解释这片海域中发生的故事。在《海里岸上》中,林森写到了《更路经》的生成过程,与那些一经写就则一字不易的所谓“经书”不同,《更路经》是伴随着渔民的每一次出海而不断成长,它与渔民的生命是紧密相连的。而对《更路经》的增补则更是一个不能用“定量分析”的“现代理性”所框定的过程,它与每一位渔民的一生紧紧相连,并通过捕鱼这一行为反作用于渔民的一生。“一位船长,不仅需要掌舵,也是一个记录者,随时记下海上发生的一切。航行路线附近的水况、最新发现的鱼群位置、岛礁的位置……甚至云层也是观测的对象。云天的变化,很少记录在《更路经》上,那是出海人一种口口相传的骨血经验。白天,可以通过瞭望水面的颜色来判断海水的深浅,判断附近是否有礁盘——有礁盘的水要浅一些,日光下,是一种翡翠蓝;没有月亮的夜里,那些经历了生死的老船长,通过云层的反光来分辨岛屿、珊瑚礁以及水下的鱼群。”这些叙述向读者们证明着经验的重要,这种经验并不是群体性的,而是与每一个独立个体对世界的理解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这样说,在林森的海洋文学书写中,每一位小说人物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南方之海”,而读者阅读这些作品的过程其实也正是在寻找自己心中的那片海。
难能可贵的是,林森并未将这种海洋在人心理上的内化看作是一个理所应当的过程,相反的,他在多部作品中都尝试梳理人与海洋之间密切联系的脉络谱系。《唯水年轻》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因为生活在海边,人们不得不向海而生,由于向海而生,于是有人死于海上。由于有死亡的可能性,父亲便一生不敢下海,而在海边的生活早就把大海的回响印进了父亲的生命,使他一生都生活在对海的恐惧与向往之中,最终,父亲鼓起勇气走向了海洋。这一行动线索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洄游,它是非强制性的,同时也是极大的蛊惑和召唤,人们自由地选择自己与海的关系,但是,如果要真正面对自己、找回自己,则还需要勇敢地面对海洋。人与海洋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浪漫的、精致的,而是现实的、粗糙的,甚至带着一点残酷,而这种残酷也许正是人生的本相。
在“新南方”的写作体系中,知识论往往是失效的,对“新南方”世界的理解需要生命来感悟,是需要以肉身作为媒介去体验、去经历的。而林森所构建的新南方之海也是如此,事实上,它本身就是建构在经验与情感之上的,是具有生命的,而生活在海边的人们通过劳作,将自己的生命与新南方之海紧密相连,经过了千百年的岁月沉淀,早已无法分割,这也是所谓“现代理性”所无法驾驭的。
三、新南方之海的可能性
《岛》是林森海洋文学的重要作品,也代表了其对海洋理解的深度。通过“新南方”的视域,林森寻找到了“岛”这个可以代表自己对海洋认知的意象。从这个意象出发,林森书写了一片流动着的海洋,而流动,则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
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其能够不断对自己的生存状态进行反思,随着20世纪以来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人对自身生存状态反思的节奏也越来越急促,当人类目睹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后,蓦然发现“动”和“变”也许才是观察世界的最合理角度。当20世纪末由“空间”“移动”构成的理论视野方兴未艾之时,“流动”“间性”等理论范畴则进一步发展和更新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流动性虽然强调跨界、强调变动,但是它并不是不及物的,跨界和变动需要一个可以承载这种行动的主体,这个主体必然是人或被人格化的事物,同时,它也需要一类可以承载流动本身的主体,它必须能够承载起流动行为的动因、结果以及其内涵,换句话说,它必须以一种文学意象的姿态承载着流动性,而这一点对林森而言,便是“岛”。
在《岛》中,岛屿构成了小说中一系列人物行为中流动性的起源,作为独立于陆地的空间,人在岛屿上的生存方式本身就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政治结构。如果对生存与岛上的人进行一番谱系学意义上的考察,不难发现,岛屿生活平淡和传统的背后,是先祖们对于传统人伦关系的破碎、想象和重组,而这一文化基因实际上对后世岛民生存状态的影响是深刻的,《岛》中的人物向海而生、向海而死,要做“一世祖”等思维方式皆出自其中。尤其是小说中主人公吴志山与故乡村庄隔海相望却有着无法抹平隔阂的生存状态,更是这种流动性的具体表现,人际关系的破碎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单子化,正像小说中描写的场景一样,在海南岛之外还有一个个的小岛,而这些小岛却因着看不见的大陆架而与海南岛乃至大陆息息相关,没有人能彻底逃脱。正如《岛》这本书的封面上所言,“no man is an island”,这是一句约翰·多恩的诗,“没有人是一座独立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陆的其中一片,就像组成陆地的土块,如果有哪一颗被海水带走,整个欧罗巴都会减小”。这也正是“岛”作为流动性文学意象的意义,“岛”是一个有着很强反合性的存在,看似一个个的孤岛,其背后不是与大陆的断裂,而是与大陆在更深层次上的跨界和弥合,看似生活在“他人即地狱”里的个人,也可以看作是这样的一座座岛屿,他们互相保持着距离,而在深处却息息相关。《岛》并不仅仅是一部关于海南的题材型小说,也不仅仅是一部反映城乡转型期间阵痛的小说,也不仅仅是一部反映个人生存境遇的小说,而是一部通过“岛”这个流动性意象来重新探索人类生存方式的小说。而在这个意象的建构过程中,“新南方”是一个重要的视域和立足点。
对林森而言,海洋是其实践“新南方写作”的试验场,他通过写海洋来将“新南方”之“南”推向了一个极限,并通过建构人与海洋的关系来突破这种“南”的极限,将探索的笔触伸向了更为遥远的空间。其实,林森所思考的问题并不是如何去写海洋,甚至是如何去写“新南方”,他所关注的是如何将在“现代”侵袭下,被本质化、单一化理解方式所遮蔽的我们的真实生活状态重新激活,使生活本身重新丰富起来。而在这一过程中,自南方而来的流动性以及其对人际关系与空间关联的新视角将使读者在这片现代性的荒芜中重拾对“人类再生之自信”。
【注释】
①林森:《蓬勃的陌生——我所理解的新南方写作》,《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②刘晓:《唐代南方士人的身份表达与士族认同——兼谈中古时期“南北之别”的内涵演变》,《人文杂志》2020年第1期。
③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第509-510页。
④梁宝星:《“新南方写作”以及幻想文学的可能性》,《广州文艺》2022年第4期。
(曾小娟,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