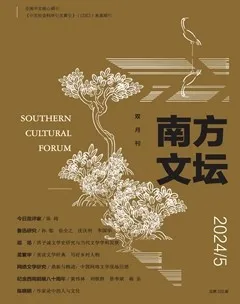文学模仿的复兴
创作工艺与文学评论相结合:
从阅读到讲故事
文学模仿与非自然叙事模式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复杂且备受争议。布赖恩·理查德森(Brian Richardson)和扬·阿尔伯(Jan Alber)都将非自然叙事学(unnatural narratology)的使命定义为阐明反现实主义的、极富想象力和创新性的故事如何扩展我们对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理解。阿尔伯将非自然性(unnaturalness)与违反“物理定律、逻辑原则或标准的拟人化知识限制”联系到一起”①。阿尔伯眼中的“不可能”和非自然性是指文本外的世界中不可能存在的虚构事件和场景。理查德森与阿尔伯一样,希望重塑文本和文本外现实的理论框架,但他将非自然性定义为反文学模仿论或者反拟态(anti-mimesis)。在理查德森看来,反拟态表述“违反了对现实世界的模拟和现实主义的实践”,呼吁人们关注它们打破常规的发明创造②。尽管理查德森将非自然叙事定位为与拟态完全不同的叙事,但他的方法是包容和辩证的:“当非自然元素被其他拟态叙事元素框定、结合或与其他拟态叙事元素形成辩证关系时,非自然元素在文学语境中才能发挥最佳作用。”③根据同样的逻辑,理查德森呼吁建立一个能够解释拟态与反拟态之间动态互动的综合理论模型。非自然范式中的细微差别有助于理解实验性叙事模式如何挑战我们的成见并重塑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理查德森的“非自然范式”将“模仿”与“反模仿”这两个极端对立的概念综合在一起,与此同时,电影编剧教程也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暗示真实的、引起生命共鸣的故事同样具有创造性和变革性。罗伯特·麦基(Robert McKee)在其经典著作《故事》(Story)中建议有抱负的编剧利用观众“与生俱来的对真相的敏感”,并以道德感来处理故事——剧本中最重要的元素。麦基认为,一个讲得好的故事可以协调我们的情感和认知体验,并通过赋予其更多的深度和意义来刷新和重塑我们混乱的庸常生活④。换句话说,讲故事通过“对生活的创造性隐喻”将作家的想象世界与观众的参与世界融为一体⑤。编剧约翰·特鲁比(John Truby)同意麦基的观点,即高超的故事形式具有普遍性,因为特鲁比强调的是传达道德真理的修辞手法或对生活复杂性的高度洞察力⑥。特鲁比将故事定义为一种交流形式,它将人们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形象化,并展示“人类想象中的生活”⑦。布莱恩·麦克唐纳(Brian McDonald)也强调了这一点,他建议编剧们构建一个“支架”(armature)——一个支撑整个作品的总体道德信息⑧。这是一种无形的真理,它比我们的普通知识更能引起共鸣,也更深刻,只有通过我们努力分享艺术工艺和想象力的世界,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
这篇文章将文学评论家和电影编剧对叙事变革现实的视角交织在一起,提出了我所理解的非自然和修复性叙事——将能够互补、改造生活中枯竭漏洞的智慧形象化,将黑暗的现实同化为一幅创意、辽阔、富于希望和共鸣的画面。我将对电影剧本《坠落的审判》进行跨学科解读,解析故事是如何围绕一个无形的“支架”——通过心灵之眼从难以捉摸的现实中汲取爱与养分的寓意——进行雕琢的。然后,我的论点将向外延伸,讨论更具复制性、偏执警惕性的叙事模式与更具模拟性、治愈修复性的叙事模式之间的互动,以及文学批评与创意写作之间的互动。非自然叙事学家善于将拟态和反拟态分割开来再加以综合,而编剧则倾向于融合非自然性和模拟性为故事的传播成就制定原则。亚里士多德的“拟态”概念关注的不是对现实精确、机械的复制,而是关注叙事拓展我们道德理解的能力,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代入感和革新感。
文学模仿的创造性改革:《坠落的审判》
中的敏感警惕性叙事和治愈修复性叙事
《坠落的审判》的核心可以理解为警惕性、现实主义故事与修复性、非自然主义故事的并置。前者揭露黑暗的事实以避免惊讶和痛苦,后者则通过感同身受的想象力将严峻的现实重新组合成一个健康的整体。故事将观众带入一段破案过程,调查隐藏在塞缪尔·马勒斯基(Samuel Maleski)从阁楼窗户坠落事件背后的事实,以及坠落前的一次受伤。由于有几项证据——包括他与妻子桑德拉·沃伊特(Sandra Voyter)的恶性争吵的秘密录音——证明桑德拉可能与他的死亡有关,因此桑德拉需要用令人信服的叙述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塞缪尔的自杀倾向。在审判过程中,这对夫妇的生活故事开始展开:在一次事故中,他们的儿子丹尼尔(Daniel)的视神经受损,之后他们的婚姻每况愈下。塞缪尔承担了这次事故的责任,他设法通过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儿子来弥补,但他仍然饱受内疚之苦,这使他成为一名专职作家的理想变得更具挑战性。桑德拉通过沉浸式的小说写作和婚外性爱来排解情感压力。虽然我们几乎不可能真实客观地描述他们婚姻的衰落,但影片却让我们看到了眼睛看不清楚的美丽和希望。这起棘手的案件最终归结于丹尼尔的最后证词。虽然丹尼尔缺乏精辟的事实信息,但他决定用心、远见和同理心去正确看待这个婚姻悲剧。丹尼尔将父亲的离开可视化、想象化:父亲选择了自杀是因为他已经度过了丰富、充实、非凡的一生,照顾儿子,保护儿子远离危险。丹尼尔极富想象力而又高度真实的叙述,让人产生无限的希望。塞缪尔成了一个英雄,他总是为了他人的需要而牺牲自己的需要;而桑德拉则被免除了罪责。在保护父母的过程中,丹尼尔讲述了一个关于故事讲述的富有远见的真理:生命之所以对我们有权力或者影响力,是因为它不可预测、沉重,并反映了死亡的不可避免。讲故事的人可以用爱和同理心来修复和拼凑生命的碎片,而不是通过复制生命的有害力量来夺取对生命的控制权。丹尼尔的证词是一个具有修复性的非自然故事的典范。丹尼尔并不刻意追求事实,而是扩大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范围,将灰暗的生活片段转化为重新开始的机会。
在我全面解读案例中的修复性叙事之前,让我先解释一下这个概念是如何建立在伊芙·塞奇威克(Eve Sedgwick)的修复性阅读概念之上的。塞奇威克在她关于偏执、警惕性阅读(paranoid reading)与治愈、修复性阅读(reparative reading)的文章中并列了两种批判/认识论实践。偏执的批判实践旨在揭露“大规模、真正系统性压迫”的现实⑨。偏执警惕的阅读虽然具有严谨的知识性和承诺的真实性,但它专注于客观事实的揭露,因此会使我们对知识的创造性能力以及文本、认识者和讲述者之间的修辞互动视而不见⑩。偏执的读者在坚持单一的主导方法时,只能通过复制环境中的有害力量来保持对危险的警惕。相比之下,修复型读者能够将那些原本会引起恐惧的意外和不公正整合到一个具有广阔视野的框架中。读者能够转化并滋养“一个人自卫性地投射到世界中、从世界中雕刻出来并从世界中摄取的可恨和嫉妒的部分对象”,重新组合自己的资源修复“具有谋杀性的部分对象,使其成为一个整体……不一定是任何预先存在的整体”11。在将容易引起质疑、恐慌的现实碎片恢复到重新完整的状态时,修复性阅读将爱与希望从不利于其成长的环境中提取出来12。由于偏执、警惕性阅读和治愈、修复性阅读是寻求、提供和组织知识的相互影响的实践,它们在认识论上的意义可以应用于创作领域。正如我的案例研究将证明的那样,偏执的复制性故事通过揭露和再现现实的敌对动态,对现实产生了破坏力。而治愈的模拟性叙事将对生活真相的比喻同化为一个由知情者、角色和讲述者共同感受的想象世界。它的非自然性在于其足智多谋的全景式创造力。正如理查德森所言,非自然叙事观可能会让我们超越对现实的理解,转而形成对“包含拟态和反拟态叙事实践”的全方位理解13。我对偏执性、修复性和非自然性叙事的构想,凸显了将语言作为塑造生活和改变现实的机构的伦理利害关系。
在《坠落的审判》中,桑德拉是一位以现实主义风格著称的成功作家。剧本以一位文学系学生对桑德拉小说的描述开篇:
佐伊:老实说,你描述儿子事故的方式令人不安。你描述得如此详细生动,就像纪录片一样。这让读者感到不安,也许是因为这就是你的生活。14
虽然桑德拉并没有亲身经历丹尼尔的事故,但她通过想象事故发生时一定发生了什么,对事故进行了真实客观的描述。因此,桑德拉的小说写作方法符合现实主义美学——文学作品通过忠实反映我们的世界,增强读者身临其境的体验15。作为19世纪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和更广泛的艺术表现理念,现实主义已成为一种讲故事的模式,其特点是客观、系统地揭开“关于生活的固有假设”的神秘面纱,以及“我们一直都知道的经验真相,无论多么朦胧”16。在整个故事中,桑德拉反复强调看清现实的重要性,而她所说的看清现实是指对复杂的材料进行平衡而深入的观察:
桑德拉:那不是现实。如果你专注于一个在生活中极端的时刻、情绪的高峰,它会粉碎现实。它可能看起来像无可辩驳的证据,但它实际上扭曲了一切。这不是现实。17
虽然桑德拉希望对生活和她与塞缪尔的关系保持一种合乎逻辑、不偏不倚的看法,但她坚持要破译和揭露他们之间隐藏的动态关系,这暴露了她对惊讶和痛苦的偏执厌恶。塞奇威克解释说,偏执狂既是复制性的,又是预期性的。它“要求总是已经知道坏消息”,强调“以暴露的形式获得知识”,并通过体现危险的可能性来理解生活18。当被问及丹尼尔出事后她对塞缪尔是否有怨恨时,桑德拉先是回避了这个问题,然后表示她只是怨恨了他几天。然而,这种细腻的表面张力却蕴含着丰富的潜台词。在他们的录音对话中,桑德拉拒绝听从塞缪尔的要求,即重新调整他们分担育儿和家庭责任的方式,以便他能有更多的时间写作。她说:“首先,我不相信夫妻间的互惠概念。这种想法太天真了,说白了就是令人沮丧。是的,考虑到你们现在的状态,我认为讨论这个问题是浪费时间,真的。”19桑德拉所说的“状态”指的是塞缪尔未能实现自己作为作家的愿望,也无法摆脱对事故的内疚。她指出,塞缪尔看似对家庭的奉献,其实“掩盖了更肮脏、更卑鄙的东西”——那就是他对失败的恐惧20。桑德拉还推翻了塞缪尔心理医生的证词,否认她让塞缪尔放弃写作来为事故买单,否认她对塞缪尔痛苦的冷漠给他造成了心理负担21。桑德拉一再揭露丈夫的脆弱和平庸:“他的痛苦来自更深的地方/他的痛苦追溯到更远的地方。”22编剧通过大量细节描写桑德拉看似冷漠的态度,以及她同时揭露现实和回避现实的执着、矛盾的努力,带领我们进入故事的潜台词:桑德拉无法表达的、过度的悲伤。她从未原谅塞缪尔在对丹尼尔造成严重、永久性视力损伤的事故中承担的责任。尽管塞缪尔从阁楼坠落的事实原因不清晰,但她的叙事清楚地摧毁了他现实中的幸福与希冀23。
尽管桑德拉以复制现实/敏感警惕的方式创作小说,但她为保护丹尼尔而承受现实重压的方式,却闪耀着她的修复与治愈动机。让我们倾听她的心声:
桑德拉:早些时候,医生说这是个悲剧。我很快就不这么认为了。我从不认为丹尼尔是残疾人。我想保护他不被认为是残疾人。一旦你对一个孩子有了这样的看法,你就注定了他不会把自己的生活想象成自己的生活;而事实上,他应该觉得这是最好的生活,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生活。他和其他孩子一样看书,上社交媒体,他做梦,他玩耍,他哭,他笑……他是一个活泼的孩子。24
桑德拉从悲惨的境遇中挖掘出了生命的无限可能,证明了爱可以让视力残缺的孩子看到永恒的希望。然而,桑德拉对事故的修复性解读不同于塞奇威克理解的修复性解读,也没有达到我对非自然叙事的标准。桑德拉拒绝接受生活中痛苦和悲剧的片段,她也没有将这些片段吸收到一个更加健康、包容的框架中。同样重要的是,要谨慎对待桑德拉的话,因为她的目的是在审判过程中尽可能表现出无辜。从她创作的故事中可以看出,语言可以成为掩盖、构建或粉碎现实的强大工具。
虽然桑德拉和塞缪尔都有用权力控制生活的偏执倾向,但他们的脆弱其实源于曾经勇敢分享的爱和承诺。和妻子一样,塞缪尔也通过创作一部关于悲惨事故的小说来应对悲伤。桑德拉描述了他草稿中的一段话:
桑德拉:这个段落讲的是一个人在想象,如果没有那场害死他哥哥的事故,他的生活会是怎样。有一天他醒来,发现自己在两个平行的现实中:一个是事故是他生活的中心,另一个是事故从未发生过。25
塞缪尔的故事与桑德拉的故事产生了共鸣,他也是通过同时复制和回避生活中的坏意外来应对丹尼尔的事故。塞缪尔采用逃避痛苦和复制痛苦的矛盾方式,渴望修复和重塑破碎的家庭故事,但却以失败告终。受到桑德拉写实美学的启发,塞缪尔还记录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纪录片项目收集素材。然而,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记录下他们最后的争吵,是为了诬陷桑德拉,用他的虚构来摧毁她的现实世界。这对夫妇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对语言和讲故事的热情——他们现在用来复仇的创造性武器——曾经是如何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并产生共鸣的26。在一次私人谈话中,桑德拉向她的老朋友兼律师坦白:“我一生都不理解我的家人和朋友,然后他出现了……我觉得我理解了他在说什么。”27曾经孤独迷茫的桑德拉在塞缪尔身上找到了遗失的自己。他们的母语不同,但他们能够跨越差异,分享彼此的语言、希望和抱负。然而,正是他们彼此结合的勇气,也产生了脆弱性。布蕾妮·布朗(Brené Brown)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脆弱是“有意义的人类体验的核心、心脏和中心”。脆弱意味着一个人有可能在情感上暴露于不确定性和受挫的期望28。因此,桑德拉-塞缪尔的悲剧最终在于他们对共同的脆弱视而不见。毕竟,去爱——向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失望和不确定性敞开心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这两个人物都没有能力重新构建、拼接生活从美好婚姻愿景上撕裂的美丽面料。
故事讲到丹尼尔的最后证词时,突然充满了远见卓识的能量。在丹尼尔叙述的情节中,塞缪尔把自己比作他们的狗史努比。他告诉丹尼尔,史努比是一只非同寻常的狗,因为它一生都在照顾家人,想象别人的需要。有一天,史努比会死去,它的能量也会在某一时刻耗尽;但丹尼尔能够从不可避免的失去史努比的痛苦中恢复过来。虽然丹尼尔缺乏对现实的准确描述,但他证明了共情想象的真相性。当我们无法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时,我们可以想象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29。通过感同身受的努力,我们可以超越粗糙和客观的事实、把关于失去和死亡的生活碎片整合成一个包罗万象的视角。丹尼尔重新理解了父亲的死亡,想象着父亲如何陪他长大,帮他理解生命的起承转合、规律轮回。丹尼尔的叙事重新燃起了希望,推动着他们的故事向前发展。倾向治愈与修复性的作者将人物视为“既善良,又受损,既是理想整体的一部分,需要爱和关怀,又能引起爱和关怀”,并接受希望本身是“一种破碎的,甚至是创伤性的体验”30。丹尼尔认识到,生命的美好希望——成长、爱和家庭——总是与有害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因此,讲故事的人需要想象一个“本可以与实际情况不同的方式发生”的过去,以及一个勇敢和自由的未来,以拓展重塑固定的、痛苦的现实31。剧本最后以宽阔的视角描绘了整个家庭。丹尼尔的证词为桑德拉开脱,两人和解;史努比靠着桑德拉躺下,桑德拉抚摸着它。在治愈的愿景中,史努比实现了塞缪尔的梦想,就是去创造并分享一个非凡的家庭故事。
正如电影编剧书籍所展示的那样,有意义且精心制作的故事能将深刻、真实的情感形象化,从而与观众产生共振。普莱斯(Price)借用亚里士多德关于经典故事的观点,引导当代编剧全面了解作者与观众之间的交流。他的跨流派、跨历史的方法将编剧置于“更广阔的故事背景”中,揭示了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元素,这些元素也是好剧本的要素32。具体来说,普莱斯将好故事理解为人类共同经历的代表。当观众看到并感受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东西反映到他们身上”时,他们就会在认知和情感层面上与这些真理产生共鸣,从而满足他们“作为个人、社会和物种,为了成长和发展”而了解自己的共同需求33。普莱斯证明,高超的故事既是模仿性的,也是修复性的。拟态的亲和力不仅能促进观众的共情参与,还能推动他们改变和成长。与《坠落的审判》一样,编剧们的创造性写作挖掘了难以捉摸的人类经历,从复杂的经历中找出引起共鸣、可以代入理解的真理。通过感同身受丹尼尔的视角,我们理解了我们是如何渴望爱和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尽管承受脆弱是艰难的。我们渴望一种联系感和整体感,希望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拼凑起来,开辟出一片充满可能性的风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亚里士多德的模仿概念(mimesis),就会感受到它非同寻常的独创性:亚里士多德并不主张历史性地复制实际发生的事情,而是主张改革性地、面向未来地畅想应该发生的事情或诗歌可能使之发生的事情34。
同样,麦基(McKee)和麦克唐纳(McDonald)的编剧技艺书籍也坚决区分了事实(fact)与真相(truth)。麦基将讲故事的人/编剧比作生活诗人,他的故事“必须从生活中抽象出来,发现生活的本质……,但又不能逐字逐句,以至于除了街上每个人都看得见的东西之外,没有任何深度或意义”35。换一种说法,fNlvx5S1BnEjPj0q0mv0iczYCMtKi88QKRzKBWzcu0w=故事是生活的隐喻,而不是事实中的生活。事实只是发生的事件,而真相则是作家对所发生事件的深刻而富有创造性的思考。麦克唐纳同样认为,讲故事/剧本创作关注的不是事实,而是真相——作家传递给观众的重要生存信息36。麦克唐纳将连接不同流派和历史时期故事的一个基本真理称为黄金主题:我们都是一样的。麦克唐纳写道:“我坚信,故事越是接近揭示这一真理,它就越有力量,越具有普遍性,越能打动人心。”37麦克唐纳通过这一金色信息,说明了极具亲和力的故事能够跨越差异,将个人和群体联系在一起。通过创造性地展示不同人群的共性,以及他们之间潜在的关系,讲故事可以让观众想象自己站在虚构人物的立场上,用心去感受这一黄金真理。在麦克唐纳所描述的情景中,让观众对非洲饥饿儿童产生共鸣的方法是将他们的贫困现实与普遍、易懂的活动画面结合起来,比如“一位父亲在孩子们散步前帮他们系鞋带”,这样做有助于观众与这些儿童产生共鸣,并想象自己身处陌生的环境中38。正如麦克唐纳如此有力的指出那样,讲故事人的责任是以新颖的、具有修辞影响力的方式向观众传递黄金主题。生与死的随机性令人不安,但故事可以让我们分享感受,拉近彼此的距离,从而治愈沉默和孤独的时刻39。
碰巧的是,《坠落的审判》的总体构架与这一黄金真理极为接近。这部电影告诉我们,讲故事的大师不是通过复制、偏执地揭露我们如何分裂,而是通过模仿、修复性地想象我们可能分享的东西,来改写生活中美丽而令人望而却步的奥秘。无论我们的视角和背景如何不同,我们——就像桑德拉和塞缪尔——都需要被看见、被理解、被从过去的错误中解脱出来,并获得前进的机会。丹尼尔的叙事具有前瞻性,可以启迪和治愈偏执的读者,邀请他们进入深层次的不确定性,然后重塑、复兴他们的人生故事前景。因此,剧本对现实的沉思所带来的非自然性是一种深刻的智慧和对改变、希望的包容性。
阅读即讲故事:文学批评指导创意写作
在细读《坠落的审判》剧本时,我试图延续非自然理论对叙述文本外世界新可能的探索。我想再次强调,“非自然”一词的使用语境多种多样。阿尔伯对“非自然”的理解充实了叙事事件如何偏离既定的物理定律和逻辑原则,拓展了我们现实世界知识的边界。理查德森将非自然理解为反拟态,并将其与非拟态区分开来。在理查德森看来,非拟态表述只是在“对现实世界的拟态描写”中加入了文体创新或超自然的幻想元素40。相比之下,反拟态叙事几乎拥有了自己的生命,摆脱了我们生活经验的束缚。理查德森认为,“仅仅有自我意识是不够的,作品必须打破讲述真实世界的幻觉”41。他批判了叙事理论的拟态偏见,这种偏见可以追溯到《诗学》,他将亚里士多德对史诗和悲剧的拟态观点与俄国形式主义者的陌生化观点并列在一起对比区别——后者是非自然叙事学的基础灵感来源42。然而,理查德森可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模仿和陌生化都关注的是艺术技巧如何将外在的真相还原到生活中。
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在他的名作《作为技巧的艺术》(Art as Technique)中,认为艺术作品通过创造陌生感丰富和扩展观众对日常生活的看法。为了解读这一概念,什克洛夫斯基举例说明了列夫-托尔斯泰如何从熟悉的事物中剥离名称、形式和通常意义,将它们置于新的视野中。通过延长读者审美体验的持续时间和难度,陌生化刷新了他们对“生活中那些变幻莫测的复杂性”的感知,使他们有能力去探索那些超越其可识别轮廓的事物43。艺术手段非但不会分散我们对惯常现实的注意力,反而会恰如其分地恢复我们被遮蔽的感觉,让我们以更大的意识回归生活的美和奥秘44。小说家查尔斯·巴克斯特(Charles Baxter)从什克洛夫斯基的批判智慧中获得了实用的经验,他建议职业作家将人物和叙事事件陌生化、变形,使其不符合整齐划一的模式。这种矛盾的人物和不稳定的、自相矛盾的意义,可以重新激发体验未知和适度陌生的审美乐趣45。巴克斯特还说,“陌生化”只能适度地使用,因为文学是一种“陌生化”透镜,可以重新聚焦平凡的生活。正如他所说:“你看到镜子里映出的某个人的一瞥,过了一会儿你才意识到那个人就是你自己。文学就存在于这样的时刻。”46陌生化非但不会转移读者对日常现实的关注,反而会让读者重新认识到生活背后的复杂性。
与巴克斯特从什克洛夫斯基的文学批评中汲取营养的方式类似,普莱斯也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转化为电影编剧的永恒范式。正如他所说,“(亚里士多德的)论文实际上是对我们为什么要讲故事的研究,并从这一功能出发,分析了什么是好故事,以及如何以最佳方式讲故事”47。普莱斯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中加入了自己的评论和案例研究,如讲故事的创造性与真相性和戏剧设计的整体性和封闭性,将亚里士多德的批判性语言转化为电影剧本建议。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的模仿理论很好地诠释了制作生命共鸣故事的基本原则。他认为,艺术家对现实的创造性渲染利用了观众的共同倾向,即通过对生活的模仿获取知识,并在推理中获得乐趣48。为了让观众获得连贯的情感体验,悲剧作家设计了一个连贯的情节流程,从开头到中间,再到最终的高潮——情感宣泄。这种情节设计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启蒙过程,以结构感、整体感和更高的道德感雕琢人生。讲故事的大师对“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和适合的东西”进行哲学模仿,并培养出“比我们更好”的人物49。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亚里士多德与什克洛夫斯基一样关注艺术如何深刻地展示生活,这迎合了观众从审美体验中获得启示和成长的共同倾向。
非自然叙事学的一个理论突破是,它明确强调叙事实验能够不断更新故事资源,拓展我们对世界运作方式的理解。非自然叙事学涵盖了不同流派和历史时期的例子,有可能为那些寻求叙事不同可能性的创意作家提供指导。例如,编剧的目标是创作出精湛的故事,挖掘我们的生活经验,重现共同学习和找到情感共鸣的承诺。麦克唐纳警告说,对创新的渴望可能会让作家们远离他们的技艺;只有通过艺术家们孜孜不倦地探寻写作与观众交流的可能,创造力才能迸发出生命的火花50。非自然叙事学作为叙事学理论中的一个开创性新范式,为读者揭示了创造性叙事所能带来的巨大的改造世界的可能性,但其与文学模仿的根本对立的框架却掩盖了作者与读者的交流能力。毕竟,“陌生化”牢牢植根于其模仿的基础,而非自然叙事正是通过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将观众与他们的生活重新联结起来而获得修辞力量的。因此,我建议将非自然叙事理解为将生活的缺憾创造性地转化为丰富人生的情感智慧51。例如,非自然叙事可以将对不公正现象的偏执描绘转化为对人生悲剧的道德远景。与其将我们试图改造的生命特质搁置一旁,或者将文学模仿与非自然对立起来,我们可以将它们的定义重新加工,并重组成一个跨学科的框架,最终重新唤起改变生命的治愈修复之火。
【注释】
①Alber,Jan.“Unnatural Narrative.”The Living Handbook of Narratology,17 Nov. 2014,https://www-archiv.fdm.uni-hamburg.de/lhn/node/104.html.
②③134041Richardson,Brian. Unnatural Narrative:Theory,History,and Practic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5,p.3,p.4,pp.20-21,pp.23-25,p.93.
④⑤35McKee,Robert. Story:Substance,Structure,Style,and the Principles of Screenwriting.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1997,p.25,pp.111-112.
⑥⑦Truby,John. The Anatomy of Story:22 Steps to Becoming a Master Storyteller. Faber and Faber,2007,p.3,p.9,pp.7-9。特鲁比区分了两种讲故事的方法,一种是更现实的讲故事的方法,这种方法产生的是“生活原貌的复制品”;另一种是更富有想象力和远见卓识的方法,这种方法描绘的是“浓缩和提升的人类生活,以便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生活本身是如何运作的”。特鲁比从工艺的角度指出,在超越现实世界知识参数的过程中,一种更为非自然或更具创造性的叙事方法不是为了疏远读者,而是为了让读者回到熟悉的地方,增强对文本外现实的把握。因此,拟态与反拟态之间的界限是不固定的。
⑧36Invisible Ink:A Practical Guide to Building Stories that Resonate. Libertary,2010,p.20,p.76.
⑨⑩111218293031Sedgwick,Eve Kosofsky. Touching Feelings:Affect,Pedagogy,Performativ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3,p.124,p.128,p.130,p.131,p.136,p.138,p.146.
141719202122242527Triet,Justine,and Arthur Harari. Anatomy of a Fall. Directed by Justine Triet,Troutdale,Independent Publisher,2023,p.21,p.43,p.48,p.86,p.88,p.103,p.107,p.116,p.117.
1516Martin,Wallace. 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p.57,p.58,p.60.
23剧本一半用英语写,一半用法语写,反映了培养一种共同的、包容的理解与弥合不同文化和观点之间裂痕的重要性。
26在《诗学》的诺顿批评版中,米歇尔·泽尔巴和戴维·戈尔曼指出:诗人的功能不是报告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讲述可能发生的事情,按照概率或必然性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诗歌比历史更哲学、更高级,因为诗歌倾向于表达普遍性,而历史倾向于表达特殊性。
28Brown,Brené. Daring Greatly:How the Courage to Be Vulnerable Transforms the Way We Live,Love,Parent,and Lead. Penguin Random House,2012,p.12,p.34.
323347Classical Storytelling and Contemporary Screen-writing:Aristotle and the Modern Scriptwriter. Routledge,2018,p.3,p.10,xiv.
34桑德拉的前两部小说也与她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有关:母亲的去世和与父亲的分歧。桑德拉还明确表示,她致力于创作对现实具有破坏力的小说。她的第二部作品加剧了与父亲的裂痕。
373839McDonald,Brian. The Golden Theme:How to Make Your Writing Appeal to the Highest Common Denominator. Libertary,2010,p.4,pp.87-89,p.102,p.104.
42尽管如此,理查德森承认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的创造性巧思有可能为文本外的现实增添色彩。理查德森还指出,亚里士多德对文学表现中的不可能性以及文学模仿的创造性持开放态度。尽管理查德森承认可以通过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视角来理解非自然叙事,但他认为非自然叙事脱离了现实基础,而不是牢牢扎根于生活本身。
4344Shklovsky,Victor.“Art as Technique.”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Four Essays. Translated by Lee T. Lemon and Marion J. Reis,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5,pp.11-12,p.18.
4546Burning Down the House:Essays on Fiction. 2 ed.,Graywolf Press,2008,p.28,p.39.
4849Zerba,Michelle,and David Gorman. Aristotle POETICS. W.W. Norton and Company,2018,p.6,pp.12-13,p.21.
50Ink Spots:Collected Writings on Story Structure,Filmmaking,and Craftsmanship. Concierge Marketing,2017,p.44.
51乌托邦文学是非自然叙事的典范,前提是我们将其理解为一系列针对当代社会问题并设想未来改革的创意作品。乌托邦文学充满了一种远大的希望,一种将不理想的现实转变为有力量的现实并使现实世界的变革成为可能的愿望。
(金紫琪,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