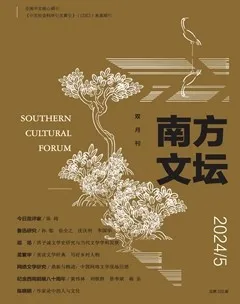寻找“回响”的真相
东西,这位1966年出生的作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坛已被纳入“新生代小说家”阵营。他的小说如同他的笔名一样,以种种充满感性的文字,执着于表达当代人在当今这个时代中的身心安放。有时,读出“东西”这个名字的时候,不免会冒出个想法:“为什么不叫‘南北’?”想来却感觉“东西”更给人一种方向上的模糊感,就像其作品中的许多主人公一样,生活中常常是一种摸不着“南北”的状态。有时,也想小说字里行间那种直击现实生存的质感,应该狠狠地对生活说一句“什么东西!”然而,这算不上是东西的风格,东西的作品虽然描述出了现实的种种不堪和困顿,却大体上是个体的向内生长,在寻找中,展示个体的存在真相和内心困境,并不直接追求批判现实的爽快,倒有种沉重的真实和无奈。
最近,东西的小说《回响》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其书页上写着“你能勘破你自己吗”,字体却小到几乎看不见,如同隐藏在这个侦探故事背后的那种极致的心理探索。于是,拨开“他者”的世界,走向“自我”的内心,是东西隐含在《回响》故事背后的一种底层逻辑,也是我们解读这个故事的重要入口。
一、情节链条中隐藏的“冰山”
《回响》的故事情节围绕着冉咚咚侦破夏冰清被杀案而展开,整个故事情节按照凶手的浮现而推进,或者,更确切地说,按照冉咚咚对凶手的推断而推进。这样的情节设置,必是悬疑迭起、扣人心弦。然而,这并不是一部常规意义上的悬疑小说,更像是情感剖析小说。小说有两条情节线索,一条是夏冰清的案件,情节故事中出现的一个个人物串出了故事情节走向的珠线,如果将人物视作这个珠线上的珠子的话,那么,每颗珠子的下面几乎都有一座巨大的冰山,而真相恰是在水下的冰山中。另一个情节线索是冉咚咚与丈夫的情感变故。小说在冉咚咚与丈夫的婚姻关系中,对冉咚咚的种种行为做出了回归原生家庭及潜意识层面的探索,亦是深入了水下的冰山之中。这桩刑事案件的办案过程中,似乎一开始冉咚咚就有直觉凶手是谁,接下来的情节推进,无非是要不断地去证明凶手就是凶手,所以,小说呈现的与其说是侦探故事,不如说是对人性及人的心灵剖析。这种注重人物内心的书写以及由此形成的心理小说的特点,正是东西写作的一大特征,而《回响》这部小说中构成的冰山式情节铺排特点,既极好地完成了对人物心理世界的探索,又使得整个故事有了立体感,超越了传统侦探小说将叙事重心放置于故事情节的起伏性的特点。
说到底,东西的小说总是力图透过生活的表象去探究深层的逻辑,于是,有了种直击现实和自我心灵的震撼。《回响》这部小说的立意更倾向于对于人物的过往经历、特别是原生家庭的影响的探究。小说呈现给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决定你今天的行为的,正是昨天甚至是童年的种种经历、创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的“回响”这一书名,有了种内观的意味——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从情节上看,依次出现在夏冰清谋杀案件中的关键人物是徐山川、徐海涛、吴文超、刘青、易春阳,从徐山川的起念到易春阳的动手,构成了一个多米诺骨牌。从徐山川“借钱”给徐海涛,到徐海涛付钱给吴文超,到吴文超付钱给刘青,再到刘青付钱给易春阳。徐海涛、吴文超、刘青都在设法搞定夏冰清,说的只是“让她别再来烦我”,却没有一个人说自己要置夏冰清于死地,没有人承认自己的犯罪。正如小说中写的:“冉咚咚想他们都把做这件事当成做生意,徐海涛是这么说的,吴文超也是这么说的,每个人都说得轻描淡写,好像夏冰清的命是一件商品。”①最终动手的是易春阳——一个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的杀人犯。暂先不谈,最终冉咚咚还是究出了这个多米诺骨牌的推动者徐山川——谋杀案的真正凶手。有意思的是,在情节的推进中,小说情节的生动之处倒不在于破解案件过程的惊心动魄,而在于对每个人物的心理以及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的呈现,这也就是前文言及的水面下的冰山。徐海涛在贫穷中长大,从小打架、混社会、活得憋屈,却因着曾晓玲的爱而想改变,他需要一大笔钱来创造他俩的美好未来;吴文超自小父母离异并被忽视,在不断被否定和缺爱的成长环境中形成了自卑又要强的性格,他极力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刘青的童年充满了父亲的冷嘲热讽,一直想过远离尘嚣的生活,当大学时期的恋人再次出现的时候,可想而知他的内心充满了怎样的向往;靠体力活为生的易春阳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精神病患者,他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从小到大,围绕着他的是被歧视的冷,所以,当刘青给他烟抽时,他瞬间就能对他肝脑涂地。无论是他的诗歌,还是对爱的妄想,都充满了少年的创伤,这也自然导致了他轻易走向杀人的路径,并变态地割下了夏冰清的手。可以说,小说提供了刑事案侦破的过程,更提供了每个人对世界的理解以及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正是因为这个链接中各个人物的这种内在生存逻辑,才推动了夏冰清的被谋害。换言之,小说借助夏冰清这个案件,探讨了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探讨了世界上的每个人的形态。
拨开作案者在刑事案中的种种行为表象,深入人物行为背后的内在心理的分析,直抵人性的幽深之处,这使探案本身变得更加惊心动魄。作品在侦察者冉咚咚身上同样体现了这种探索,随着探案的推进,冉咚咚对自己的丈夫产生了怀疑,而且,在她的世界里,这种怀疑一步步地被证实,甚至于在刘青的女朋友卜之兰的故事中,丈夫慕达夫也被怀疑为那个出轨的男性教师。在小说中并没有交代这种怀疑是否是真实,也没有交代慕达夫有没有真正的出轨,因为小说要呈现的更重要的内容是冉咚咚为什么会对自己的家庭如此的不安?探案者被案件影响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显然,小说对冉咚咚的童年呈现是一个重心,年少时怀疑父亲出轨的隐秘经历才是冉咚咚的内在创伤,这样的创伤最终影响她的婚姻和当下的生活,所以,她怀疑慕达夫的出轨,源自于原生家庭建立的对男性(丈夫)的质疑。有意思的是,作品还留了一个冉咚咚的搭档邵天伟悄悄爱慕冉咚咚的线索。这个线索也是激发冉咚咚离婚的另一个隐秘推进力,但从心理学分析,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冉咚咚这位女性对爱的强烈渴望及其背后隐含的安全感的不足。
从整个故事的建构来看,东西在《回响》中借助于一个刑事案件,向我们开拓了人性和心理探索的空间,而这个空间不仅呈现了人性的病态和心理的非健康状态,更是从人物的成长经历中去探究这种病态心理的原因,去揭示水面下的冰山。在一条故事链中,实际上呈现出多个故事,使得小说情节变得丰富而生动。东西在最近的访谈中说及《回响》的结构,认为“回响”跟小说结构特别吻合:“因为它写的是心灵,那么它是现实的‘回响’,然后又写了两条线,两条线互相呼应,它也是‘回响’。”②《回响》在叙事结构上做出的独特的探索,使小说呈现出事物的表象与表象下的内在逻辑。
二、迎向人性的黑暗与人生的亮光
每一位成熟的写作者,都会通过作品向读者呈现出其处理现实世界的方法。东西自20世纪90年代进入文坛后,一直在创作技法上不断进行探索,其中,对现实困境的直面及承担是东西在创作中坚守的一抹精神底色。有评论者曾评价东西的作品:“对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和人性的复杂性、善与恶、焦虑和无奈的命运,做出了深刻的反省和精神性整饬。”③的确,东西小说中的“当下感”呼之欲出,甚至,至今为止,东西的每一部小说都以当下社会现实为题材,那么,东西是如何做出这样的深刻反思和精神整饬的呢?
从“新生代作家”的群体特征来看,他们执着于表达个体对时代和社会的生存体验感,用诸多“感性”的话语来表达生命的感觉。这种话语表述的极致呈现者如林白、陈染。像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这样的作品,就完全将焦点集中于自身的成长(生理和心理的),通过主人公多米对自己生理变化及周遭人事的感悟来确认自我的存在。在东西的创作中,也存在着不断确认自我身份的主题,不过,与林白、陈染相比,东西更指向于探索个人的命运在当前时代和社会中的痛苦、孤独及荒谬。比如,2000年的中篇小说《不要问我》,书写了一位因为失去身份证件而无法证明自己是谁的主人公卫国的故事。一位大学副教授,因为喝醉酒表达了内心的爱恋而引发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人生遭遇。当卫国因为没有身份证而无法证明自己是谁并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作品直露露地呈现了个体在社会中身份缺失的人生困境,并且,给出了一个充满荒诞意味的结尾:因喝酒而失去一切的卫国,最后找了一个替人喝酒的工作,并死于酒精中毒。同样,在《篡改的命》《后悔录》等作品中,也明显地体现出这种寻找自我、确证身份的主题书写,前者的主人公汪大志,作为警察要侦破自己的身份,最终发现了自己就是杀人犯林方生的儿子后,却将能确认自我身份的童年照片等一切证据都投入江中;后者的主人公曾广贤,不断地在“自我”篡改和修复中,完成个人的记忆和历史荒诞的杂糅,作品也在这种“后悔录”中完成了个体生命的软弱性的表达。所以,在作家这样处理现实世界的逻辑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东西作品带来的现实压抑感和黑暗感。《回响》这部作品也依然如此。在夏冰清的案件中,几乎每个人物都参与了谋杀,甚至包括夏的父母。然而,作家在书写现实的恶的另一面是,作家始终寻找着现实困境的突围。东西说过的一段话挺有意思,他说:“我是个短期悲观,但长期乐观的人,由无数个小悲观组成大乐观。我经常牢骚满腹、杞人忧天,但我确实热爱这个世界,热爱亲人和朋友。”④显然,在这位自身也充满了成长的磨砺及生活的艰辛的作家身上,恰是因为对世界的热爱,才更有勇气去面对黑暗。
相较于东西以往的作品,《回响》这部小说更侧重于向个体的内心创伤“开刀”,拨开层层生活的表象以及个体的生活感知,不断深入到“自我”的心灵深处或者个体的潜意识中,去打开和解决来自个体成长经验深处的问题。夏冰清以及与她的案件相关的人物徐山川、徐海涛、吴文超、刘青、易春阳,甚至包括徐山川的妻子沈小迎,他们的生活中都有着隐秘的一面,这隐秘的一面是黑暗的、痛苦的、困顿的、无奈的,夏冰清的被谋杀既是一切隐秘的结果,也是揭开一切隐秘的起始。而一切被揭开的过程,也是一个面对黑暗甚至是疗愈个体疼痛的过程。在这样的叙事中,我们看到了东西面对现实困境的勇气及心之所善。那么,小说作品中真正着力最多、最能体现作者心思的人物显然是冉咚咚,因为她不仅是撬动这一切的一个引擎,而且,她成为一定意义上终结黑暗的执行者。东西说:“无论是案件线还是感情线,《回响》都让人感到现实的沉重与无奈,但结尾还是有一个地方给出了一点光,就是夏冰清被杀的缘起——徐山川,终究是被冉咚咚找出了谋害的证据。……所有的铺垫就是为了这道光,因此,这道光才显得明亮。”⑤那么,冉咚咚何以具备这样的能力?在一个以刑侦案为线索的叙述结构中,冉咚咚既是作者呈现的作品核心,同时,冉咚咚的自我认知又成为作者所要表达的叙事着力点。虽然,我们尚不明白,一位男性作家何以在此以一位女性为对象进行如此深入的心灵剖析,但是,故事的结果的确让我们看到了冉咚咚自我认识的突围、个体创伤的疗愈以及人生的重启。或者,确切地说,冉咚咚的理智和直面自我的勇气和能力,也使她拥有了在断案中保持着清醒、执着及直面真相的勇气和能力,这也使作品最终有了那束光亮。这束光亮照进了刑侦案,也照进了冉咚咚的人生。
冉咚咚的认知和觉醒,映照着个体对时代的“回响”,即在一个物质逐渐丰盈及被满足的时代中,人的身心安放成为一件备受关注的事件。在《回响》中,这种安放显然跟自我的认知有关、跟人的潜意识有关,这恰是如何“勘破自己”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冉咚咚生活稳定、工作顺利、家庭幸福,然而,这“顺达”中却始终暗含着不安和困顿,如果不解决人的认知的深层次问题,这种“顺达”迟早有一天会崩塌,就像小说中冉咚咚对丈夫的怀疑以及对女儿的未来的担忧一样。冉咚咚通过处理自己的童年创伤来实现了对个体的潜意识的发掘,并通过自我成长的疗愈来达到自我认知的提升,或者说,认知的过程便是疗愈的过程。小说的结尾并没有交代冉咚咚是否能与慕达夫复合,但是,显然一个拥有爱的能力的冉咚咚诞生了。在关于《回响》的一次对话中,评论者如此写道:“东西说,写完《回响》后,他不仅从自己写的人物身上获得了崭新的认知,也在写作中自我成长。通过对日常生活和心理世界的书写,他重铸了爱的信念,对人性的希望更加坚定。而在他的笔下,我看到了生命的浩广与幽深,看到了广阔而丰富的时代形象,更看到一个作家甚至作家群体对于价值的追寻和执着。”⑥
所以,《回响》的内在逻辑带给我们的是作家用一种提升自我认知的方式来处理面对世界的方式的问题。主人公冉咚咚认知自我的过程,便是探究自我存在的真相、重塑对世界的认知及追求生命价值的过程,也是作者认知世界的过程。无论故事多么晦暗,终会有光出现,这便是《回响》迎向人性的黑暗的勇气与寻找人生亮光的执着。
三、心理分析建构探索世界的新方式
在《回响》的故事建构逻辑中,读者不难感受到作者对心理学知识的运用,在深邃的人性的探究中,人性内外的黑暗、不可捉摸的恶、成长的勇气和对创伤的直面及疗愈,都借助了心理学。东西自己也在《回响》的后记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之前,我从来没碰过推理,也从来没有把心理学知识用于小说创作,但这次我想试一试。”⑦其实,在东西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对人物的心理世界的呈现,他的小说一直保持着一种关注当代人无限复杂的内心世界并将个体的自我主体性书写放在重要位置的书写姿态。从另一个层面来讲,东西这种借助于心理分析的方式,使作品拥有了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艺术特征,然而,作品体现出的现实主义题材、主题、情节节奏等,却让我们无法简单地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或现实主义来进行界定。实际上,这不仅是东西小说带给评论界的一次挑战,也是当下许许多多的小说带来的挑战。不得不说,当下中国小说创作技法的丰富性和成熟性,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特征范畴,正在为认知和表达世界提供新的维度。
从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来看,心理书写是开启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标志,是中国现代小说转型的重要一部分。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通过狂人的内心独白,不仅打开了认识现实的新视角,而且开启了确立现代人学观念的新时代;五四时期的其他作家也无不借助于个体心理的关注,通过诉诸“自我”的形象呈现,表达现代性个体的苦闷、压抑、颓废和追求;又如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等人则直接将心理分析方法呈现于作品中。可以说,心理书写为中国的现代小说找到了新的话语资源,其背后是独特的人的发现及“个人”的显现。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小说艺术形式变革的推动中,小说语言的“感性”特质被彰显,90年代的新生代小说家们便成为生命个体的感性化表达的积极实践者,这也推动了将人物个体的心理描述放置于显要位置的书写方式。东西的小说便一直注重个体的生存体验以及对世界的“感觉”。
在《回响》中,东西用了格式塔心理学、防御机制、童年创伤、疗愈等诸多心理学知识,故事内容不断指向对人物行为背后的潜意识的发掘,在情节链条中,形成了水面下的冰山式的延展结构。因为不断地发掘人物的潜意识,世界的现实就与心理的现实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正如皮亚杰认为的:“对主体来说,客体只能是客体显示于主体的那个样子,而不能是别的什么,但同时也证明,从客体的观点来看,主体也不能跟现在有什么不同。”⑧冉咚咚的世界一直投射着自我的心理世界,小说情节的推进伴随着冉咚咚的潜意识的流动,同样,谋杀案的相关犯罪者,也被置于表象行为下的潜意识分析中,书页上揭示的“勘破”就像一个警示灯,时时提示着小说的叙事意旨。然而,值得重视的是,小说注重于潜意识的呈现,用了许多心理学的知识,也用了心理学分析方法,但确切地说,这里的心理学分析方法更多的是小说完成其故事叙事逻辑的一种手段而已,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流派的心理分析,因为整个小说保持着线性叙事的完整性、清晰感以及人物形象的鲜明性,处处体现出小说在心理分析手法上的克制及点到即止。可以说,一切潜意识的呈现,皆是为了推进故事的可阅读性而存在的。这恰可以解释东西自己所说的“推理”和“心理”的结合。在笔者看来,这也说明,小说建构的一个重要创作原则还是在于表达一个让普通读者能够轻松读懂的精彩故事。此外,小说被改编成了悬疑网剧也说明了这点,在悬疑网剧的类型化创作中,融入人性、人心、情感的剖析,既大大拓展了故事的精神深度和广度,又增加了看点。
于是,当我们再次看待《回响》中心理世界的艺术呈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作者依然保持着对现实主义原理的热衷,小说中线性叙事性的保留J5WQzpGcDOkrn44eHzxpqJt96bi+QycY9PD4fXRerXE=以及通过完整的故事展开对人性、人情的勘探,进一步引领我们关注东西表达现实的真实的方式。一定意义上,与真实相处的作家,内心拥有更多的疑惑。东西选择通过勘察人物个体的潜意识来实践对世界的探索,正是打破了主观和客观二元对立的现代认知观的体现,这使当代人更科学和全面地关注自我的心灵世界和自我的存在形态。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中,作家们也总是力图去把握作品中人物的行为动机,但往往从行动中去推断他们的心理状态,而在东西这里,作家的心理分析渗透到行为表象的底下,甚至于到了通过心理分析(潜意识)来呈现行为结果的真实性探求的深度。冉咚咚、慕达夫、吴文超、刘青、沈小迎、夏冰清等人物,作为当下文化和生活的某类缩影,稳固地扎根于我们生活的世界中。盖伊在《现实主义的报复:历史学家读〈荒凉山庄〉〈包法利夫人〉〈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写道:“现实主义小说之所以具有如此丰富的综合意义,正是因为它让其人物经历特定的时空考验,好像这些人物都是作为其文化和历史缩影的真实的个人,他们稳固地扎根于他们所生存的世界之中。”⑨“现实主义小说家们必然要让其小说中的人物符合这样的基本生活事实。”⑩在一个对个体的存在以及自我的成长充满好奇的时代,借助心理学知识来书写现实成为一种有效的方式。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写作也成为当下现实主义流变的一个面向,阅读者们也总是期待通过小说的某种方式来得知更深刻的现实。
如果与当年现代主义写作大师伍尔夫、普鲁斯特、乔伊斯等人对现实主义的不满比起来,当代小说叙事中呈现的心理现实无疑在弥补他们所认为的缺失并强化现实主义的表现力度。这让我们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段话:“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不对,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即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的全部奥秘。”11进一步而言,中国现代小说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文学文体文类的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了,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当代小说家们在如何实践现实主义方面做出了颇有成效的探索。比如,余华突围“就事论事”的现实主义,通过近乎客观记录式的生活呈现,书写了时代中渺小的个体的苦难人生,现实主义手法的背后,划过丝丝现代主义式的残酷或后现代主义式的接纳。莫言通过近似于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以“感觉”呈现为手段,找到了中国百姓的生存之道及言说方式,将对生命内在的悲悯感深深地揉入了“滔滔不绝”的话语言说中;阎连科以他用力极猛的“神实主义”指向伤痛的原欲力量和生活的苦难,书写独特历史时期充满政治隐喻的复杂现实;刘震云将当代现实生活中种种不合常理的细节揉进充满幽默感的话语中,讲述生活的“拧巴”和活着的种种样态,等等。
显然,在现实主义的当代流变中,东西的小说也占据着一席之地。无论称其为心理现实主义,还是说“写出了内心的真实”,作为20世纪90年代崛起于文坛的“新生代小说家”的代表,东西一直走在叙事变革的路上。他的写作正在为我们当下中国瞬息变幻的现实寻找着新的表达视角和方式。小说故事中展示出的写实、变形、夸张甚至荒诞等,皆隐含着当代人对当下生活切切实实的伤心、感动、恐惧、后悔等真实情绪,直指当代人的生存体验。从这一意义上说,《回响》这部小说在寻找生活的真相上做出了“回响”,也在中国小说艺术变革之路上做出了“回响”。
【注释】
①东西:《回响》,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第311页。
②东西、何娴:《念念不忘,终有“回响”——对话广西首位“双料”作家东西》,腾讯网,https://new.qq.com/rain/a/20230924V0756P00。
③张学昕:《无法“篡改”的叙述——东西小说论》,《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
④韩春燕:《写作是有经验的思想——作家东西访谈录》,《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⑤罗昕:《茅盾文学奖·专访|东西〈回响〉:写镜子里面的人》,澎湃新闻2023年8月11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179951。
⑥《聆听〈回响〉——对话作家东西》,新浪网,2022年12月28日,https://k.sina.com.cn/article_1723167603_66b5737301901u5ck.html。
⑦东西:《回响·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第348页。
⑧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95-96页。
⑨⑩彼得·盖伊:《现实主义的报复:历史学家读〈荒凉山庄〉〈包法利夫人〉〈布登勃洛克一家〉》,刘森尧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第9-10、10页。
11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冯增义、徐振亚译,漓江出版社,1988,第390页。
(俞敏华,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浙江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