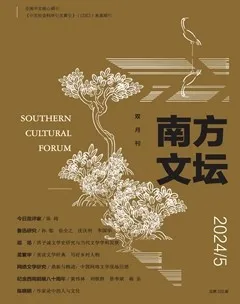从西南走向全国
2024年是欧阳予倩、田汉发起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以下简称西南剧展)召开80周年。数十年来,学界关于西南剧展的研究不断深入,但多借文献整理、回忆记述、理论梳理等方式关注西南剧展本身的来龙去脉,对于西南剧展对新中国文艺产生的影响关注不足。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西南剧展的主要发起人欧阳予倩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田汉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二人是新中国戏剧发展的主要构建者。自然,新中国17年最重要的第一次文代会演出、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的举办与欧阳予倩、田汉密切相关。欧阳予倩、田汉从西南剧展中得来的经验与启示,必然在新中国戏剧展演的举办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对后来戏剧节的举办提供了借鉴。那么,欧阳予倩、田汉是如何将西南剧展的经验运用在新中国文艺发展的实际过程中的呢?
一
我们先从西南剧展谈起。
在西南剧展召开之前,欧阳予倩与田汉已对戏剧展演有了深入认识和组织经验。1933年6月,欧阳予倩作为中国唯一的戏剧工作者以私人的身份参加了苏联第一届戏剧节,这一次的戏剧节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苏联第一届戏剧节有几个特点,其一有世界影响,美国、英国、西班牙、芬兰、法国、日本等国家的导演及戏剧评论家均前来观摩演出;其二活动较多,苏联除招待宾客观看演出外,还带领他们参观剧场、舞台和资料室,并召开茶话会,与戏剧同仁交流;其三演出剧目丰富,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泰伊洛夫等人的话剧外,还包括舞剧、歌剧及儿童剧,苏联其他民族的演出。泰伊洛夫因欧阳予倩独身一人参加戏剧节,颇为感动,于是特地在一张节目单上写下了“不要忘记莫斯科”赠送留念。欧阳予倩并未忘怀这次戏剧节,10年之后还在《广西日报》(昭平版)的“怀旧录”专栏发表了《苏联第一届的戏剧节》一文(连载七期),但他也指出苏联第一次戏剧节的不足,如犹太剧团、吉卜西剧团等没有参加演出,红军剧团等几个剧团演出的多为宣传剧目。田汉作为中国话剧界知名的“田老大”,对组织大规模演出早已轻车熟路,1938年4月,他组织了武汉宣传周,包括歌咏、文字、戏剧、美术、电影日及大游行等活动,10万余人被动员起来参加,这体现了田汉高超的组织能力。
1944年2月15日—5月19日,欧阳予倩、田汉等人在桂林举办了西南剧展,通过剧目展演(包括戏剧表演、活报大会串和化装火炬大游行)、戏剧工作者大会、资料展览三项活动展示了七年以来抗战戏剧运动的光辉成果。剧目展演包含的艺术门类极其丰富,有话剧、京剧、桂剧、傀儡戏、魔术、马戏等;戏剧工作者大会包括各地戏剧运动报告、团队工作报告、专题讲演、座谈会、提案讨论等;资料展览包括照片、剧作原稿、海报、说明书、论文、舞台模型等。三项主要活动的设置颇能看出苏联第一届戏剧节和武汉宣传周的部分影响,但更多的是欧阳予倩、田汉结合桂林实际的创新,这也为后来新中国的戏剧展演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模式。
艰苦的环境下能有如此空前规模的戏剧展览会,实属不易。但欧阳予倩和田汉对取得重大成绩的西南剧展仍不满足。欧阳予倩认为剧展的缺点在于没有利用团结来发挥更大的力量,共同切磋,学术性的研究不够,演出展览之节目缺乏计划性①。田汉认为剧展的不足之一在于西南剧展超过发起时预定的规模,一步一步扩大规模后,显得计划性与指导性不足。不足之二在于缺乏学术性,论文收到的只有某君的一个大纲,对学术的兴趣无疑的是不够的,对自我检讨的兴趣也是不够。把大会在文化运动上的意义看得太低。不足之三在于缺乏整体性,话剧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很多地方戏都没有参加。旧剧工作者有40万人以上,话剧工作者只有6万多人,所以由此显得比例有些失调②。我们发现欧阳予倩和田汉对于西南剧展不足的认识基本一致,二人希望未来的剧展能够在学术研究、节目的计划性上更加深入,同时能够扩大范围,团结起全中国的戏剧工作者。在戏剧工作者大会提案中,便体现了二人的意图。田汉提出“成立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西南支会,并组织三十四年度(1945年)戏剧工作者年会筹备会,每月出版会报,每年出版年鉴等工作”的提案。大会的第三十五条提案是“请确定西南第二届戏剧展览会及戏剧工作者大会日期地点案”,并且通过了“戏剧展览会每两年于戏剧节时举行一次,戏剧工作者大会每年于戏剧节时举行一次并于剧工大会时决定翌年举行之展览会地点”③的决议。如果能够按照欧阳予倩与田汉的设想,有了充足准备时间的西南第二届戏剧展览会,定然能够弥补第一届西南剧展的不足。
但很快,桂林遭遇日军侵略,欧阳予倩、田汉分别疏散至贺州、贵阳等地。1946年欧阳予倩离开桂林前往上海,西南第二届戏剧展览会无疾而终。1946年,田汉在给李健吾的信中说道:“桂林举行的‘西南剧展’,使话剧、地方剧以及苗瑶罗各民族剧互相观摩学习,有了极大影响。当时曾决议每两年举行一次。我们想能在上海来一次‘东南剧展’,除了我们自己的话剧、地方剧、民族剧外,还希望能综合许多东方民族和欧美的戏剧。由这样大规模的观摩学习来丰富、来提高我们的民族剧。”④这代表了田汉对于西南剧展之后另办一次戏剧展览会的期待,他不仅希望能够有中国的不同剧种参加,还希望世界各国的戏剧能够加入戏剧展览会中。这样的愿景在战争的背景下很难实现,甚至东南剧展也只是停留在想象中,并未落地。
二
1949年,中国大部已经解放,新中国的建设逐渐列上日程。欧阳予倩、田汉除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外,还参与组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二人担任筹委会委员,并分别担任南方代表第一团团长及副团长。第一次文代会筹委会下设文学艺术作品评选委员会、演出委员会、展览委员会、章程与重要文件起草委员会⑤。演出委员会负责文代会期间的演出管理工作,因欧阳予倩有着举办西南剧展的经验,于是他担任了演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负责第一次文代会的演出工作。虽然第一次文代会期间的演出为招待代表性质,不完全是专门的戏剧展演会,但欧阳予倩借鉴了之前西南剧展的经验,在节目设置、代表交流等方面付出了心血,因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欧阳予倩领导的演出委员会下设秘书组、节目组、技术组、宣传组和学习组,主要负责演出、学习、演出资料展览的征集三部分工作,这与西南剧展时期的剧目展演、戏剧工作者大会、资料展览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具体来看:节目组负责邀请参演剧目,要求演出剧目的题材可以是歌剧、话剧、秧歌剧、地方剧、快板、活报等,长剧、短剧皆可,这体现了欧阳予倩广阔的视野,不以剧种和长短作为限定条件,希望能够从各个方面反映解放区戏剧的风貌。学习组负责组织学习,采取报告、座谈等形式,组织解放区、新解放区、待解放区的戏剧工作者互相交流,欧阳予倩亲自参加了学习组的工作,与吴雪、王负图等人共同计划内容,体现了他对于学习组工作的重视。在欧阳予倩的设计中,预定学习的内容包括:第一,报告:(1)如何为兵服务,(2)如何为工服务,(3)如何为农服务,(4)国统区的斗争经验,(5)国统区的学生剧运。第二,座谈,一种是以一个戏为中心,一种是以工作形式分别举行。学习组还负责整理戏剧展览资料,由展览委员会组织举行,征集的内容为团队史实、工作成绩、剧照、海报、说明书、剧本、出版物、手迹、模型、牺牲同志遗物等,共搜集了750余件。
第一次文代会期间,演出团队20余个,人数近2000人,包括西北、东北、华中、华北等地的剧团,每天不同的节目连续演出了一个月,甚至有几天是上午、下午、晚上连演三场,给参演剧团之间提供了良好的交流与学习机会,并且老解放区的演出能够为新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戏剧工作者提供经验,因此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由于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的人员很多,所以在演出上只能尽量招待来宾,一般的观众没有可能看戏,意味着演出无法为广大市民服务,这是第一次文代会演出上的遗憾。学习组同样面临时间紧的问题,报告会和座谈会都只举行了两次,大家的热情极高,在谈话会上提出了25个戏剧问题希望专家能够解决,但因为时间缘故均未讨论。但欧阳予倩能在忙碌的文代会期间,花费精力协调、组织一场内容丰富的演出、学习及展览,实属不易,堪称新演剧运动史上空前的盛举。文代会演出的成功离不开欧阳予倩对西南剧展经验的借鉴。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全国性的戏剧展览因为规模巨大,一般是戏曲和话剧分开进行,直到1979年的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话剧、歌剧、舞剧、音乐、舞蹈、杂技、木偶、曲艺及京剧和地方戏曲才汇聚一堂。戏曲与话剧鼎足而立的局面与文化部的机构设置有关,话剧相关业务最早归于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周扬兼任局长)戏剧音乐处主管,戏曲相关业务由戏曲改进局(田汉担任局长)主管,后来艺术事业管理局与戏曲改进局合并,但戏剧音乐处和戏曲改进处、戏曲审定处仍属平行部门。十七年(1949—1966年)间,艺术事业管理局的下设机构又陆续演变为戏剧处与戏曲杂技处、话剧处与戏曲处等不同阶段,但话剧与戏曲主管部门并列存在的事实始终存在。所以,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和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彼此间并无剧种的交叉。话剧和戏曲各安其位,其实并不符合欧阳予倩、田汉二人的戏剧理念,在西南剧展时期话剧以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戏参与演出,但由于艺术管理机制的变化,二人只能在不同样式的观摩演出中施展抱负。
三
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性的戏曲会演。这一次会演的召开,与1950年12月1日田汉在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密不可分,他提议“每年戏剧节举行全国戏曲竞赛公演,展览地方戏及各民族戏改进成绩,奖励其优秀作品与演出,指导其发展”⑥,并且田汉提出由他领导的戏曲改进局预备1951年度主办第一次全国戏曲展览。1951年5月5日,周恩来署名发出《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在结合全国戏曲工作会议报告的基础上JQlVSXT7pxkxpfcHiMGKy6Op2+fipx9Bejv8kKeDoaw=,肯定了田汉的提议,认为“在可能条件下,每年应举行全国戏曲竞赛公演一次,展览各剧种改进成绩,奖励其优秀作品与演出,以指导其发展”⑦。1952年7月,结合戏曲改革运动的实际,由田汉担任局长的艺术事业管理局拟稿,计划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在1952年10月召开,并很快向全国各大行政区发出通知,遴选参演剧目。
田汉和欧阳予倩积极参与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的筹备与组织,并担任筹备委员会委员。筹委会对观摩期间的生活招待、剧种剧目、会演日期、票务等问题形成统一决议。在观摩大会的筹备期间,田汉负责中南区剧目审查和挑选工作,沙可夫、张庚、马彦祥、张光年等人分别负责其他区域。因此,田汉参加了1952年9月召开的中南区第一届戏曲观摩会,从思想到技术上指导了楚剧、桂剧、汉剧、湘剧、粤剧、赣南采茶戏等剧目,其中田汉指导过的《宇宙锋》《拾玉镯》《醉打山门》《抢伞》《葛麻》《百日缘》《刘海砍樵》入选了中南区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的剧目。值得一提的是,中南区选送了7个剧种的剧目,是所有行政区中最为丰富的,体现了田汉宽广的视野。最终专家们共同选取了23个剧种的80个剧目参加观摩大会,反映了中国地方剧种的丰富和戏曲改革的成就。
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与之前的西南剧展相比,有一个新的设置,那就是评奖委员会。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担任评奖委员会主任委员,周扬、丁西林、梅兰芳、田汉、欧阳予倩、沙可夫担任评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负责观摩大会的评奖工作。为戏剧展演剧目进行评奖,在西南剧展的报道里曾经谈及,1944年2月12日《广西日报》上刊登了一条新闻:“剧人大会会期定一周,除在互相交换工作意见经验外,还对参加团队的成绩评判给奖,奖励的级别大致为:一、忠勤奖——指坚持岗位的忠勤人员;二、技术奖——包括剧作,导演,表演,舞台工作等;三、特种奖——指新发明及新实验。我们从这些奖品的质与量方面,大可为中国戏剧前途作一个起码的测验。”⑧但直至西南剧展落幕也未实行。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弥补了西南剧展未能奖励剧人的遗憾,它将奖项设置为荣誉奖、剧本奖、演出奖、演员奖、奖状等5种,分别表彰演员、编剧、导演、音乐及舞台美术工作者。
评奖委员会除评奖工作外,还设置了4个业务小组:政策、剧目、表演、研究。其中田汉担任剧目组组长,负责对京剧及其他主要地方剧优秀节目的上演目录、整理会演中比较优秀的剧本,予以校订刊行。1953年,田汉担任主席的中国戏剧家协会主持出版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戏曲剧本选集》,选印了演出大会中上演过的26种戏曲剧本,对优秀剧目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欧阳予倩担任研究组组长,负责研究各剧种的源流、变革及发展情况,对参演的20多个剧种分别进行调查,收集材料并加以整理,将研究结果写成有系统的文章。欧阳予倩领导的研究组在大会结束后继续工作,在一年后改由中国戏剧家协会领导,继续从事中国戏曲研究的工作,在数年后将调查研究的成果结集出版,这就是1957年出版的《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体现了欧阳予倩对于学术工作的高度重视。
与西南剧展相比,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在剧目的选择上更加多元,有条件派出专家前往全国各地挑选剧目,23个剧种80个剧目的数量是战争年代很难达到的。从会议组织上来看,西南剧展由广西省立艺术馆和新中国剧社成员主要负责筹办,缺乏政府实际支持,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怀,周恩来出席典礼并讲话,除文化部主持观摩大会外,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市文化事业管理处等单位,抽调数10位干部协同工作⑨,整个会议得到了最充足的保障。从欧阳予倩和田汉所希望解决西南剧展的学术氛围不足、扩大范围、团结全中国的戏剧工作者的问题,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不仅邀请由各地区戏曲专家、戏曲改革工作者和文化艺术工作主管机关负责人等所组成的观摩团,将在大会期间来京观摩,还支持欧阳予倩和田汉等人长达数年的调查研究及图书出版工作。正因为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的号召作用,全国各地后来陆续组织了不同级别的戏曲会演,对于中国民族传统剧种的保存和剧目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
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结束后,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也正式列上日程。1955年9月,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筹备委员会成立,由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担任主任委员,田汉、周巍峙、马彦祥、张光年担任副主任委员,欧阳予倩等29人担任委员,负责整个话剧观摩演出会的筹备工作。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召开的目的是推广新创作的优秀剧目,交流艺术创作和艺术实践经验,奖励优秀的话剧作者、演员、导演和舞台美术设计者;以繁荣话剧创作,提高话剧演剧艺术质量,使其更好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服务⑩。西南剧展的主要构成剧目是话剧,所以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在形式上与剧展的形态有相同之处,但又有大量的创新。
在剧目组织上,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筹备委员会对观摩会的剧目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剧目规模上,规定了:文化部所属国营话剧团,共参加23个晚会的节目,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附属少年儿童剧团及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共参加1个晚会的儿童剧目,电影演员剧团共参加1个晚会的剧目,部队系统话剧团共参加3个晚会的剧目,工会系统专业话剧团共参加2个晚会的剧目11。1956年3月1日,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共有41个专业话剧团参加演出,演出49个剧目(其中30个多幕剧、19个独幕剧),共160场,观众达18万之多(其中三分之一为首都各界观众,其余为观摩人员)。参加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的剧团遍及全国各地,还包括维吾尔剧团和内蒙古歌舞剧团,二者均使用民族语言进行演出。与西南剧展时相比,全国各地的话剧剧目济济一堂,体现了新中国话剧发展的繁荣。
在展览上,大会召开前筹委会已向各剧团发出“会演期间不拟举办话剧资料展览会”的通知,各剧团的演出资料交至大会办公室,只做学术研究资料使用。但西南剧展时的资料展览已深入人心,作为最好的介绍和推广方式,在京的某些剧团仍组织了资料展览。如:解放军总政文工团在会演期间,将《万水千山》《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等剧的资料(包括文字资料、剧照、座谈会记录、设计图、评论文章等)整理,在排练场的休息室内举行了一个小型资料展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展览陈列将重点放在了六年来工作概括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两部分,在3个陈列室展出了舞台模型、排演日记、演出手记、设计图。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陈列内容和形式与青艺相同,但加入了演员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等照片。为了弥补大会展览的不足,1957年1月,夏衍、田汉、欧阳予倩和阳翰笙发起了举办话剧运动50年纪念及搜集整理话剧运动史资料的活动,将搜集而来的材料在全国各地展览,使得各地的戏剧工作者和群众感受到了50年话剧运动史的波澜壮阔。
在学术研究与交流上,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又创造了新的形式。2月5日,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会刊编辑室成立,向话剧工作者征稿,可以是短论、杂文、通讯、特写、访问,目的是通过会刊来征集大家对于话剧艺术的意见,展开讨论,并且深入交流。田汉在观摩会开始之前,和话剧界大量专家交谈了许久,征集他们关于话剧的问题,涉及演员、导演、戏剧教学和批评讨论等问题,希望能够在大会的学术交流中解决问题。大会委员会对于学习与交流十分重视,规定每天要有2个小时的固定时间进行学习,各代表团学习讨论氛围十分浓重,除了按大会规定每天组织两个小时学习,有的团体还组织了核心组和专门小组,并且选择了重点戏进行了讨论12。上海人艺将全团39人分为2个演员组、2个舞台工作组,一同学习。北京人艺的夏淳、梅阡、演员胡宗温、朱琳及设计组、文学组等9位同志组成核心小组,虚心向各兄弟团体学习。大会的研究处召集了舞台美术会、演员座谈会、剧作者工作会。3月23日,大会举行第一次专题报告会,邀请张光年作专题报告。3月24日,大会举行第二次专题报告会,邀请孙维世作专题报告。3月26日,大会举办舞台美术创作专题报告会,邀请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主任刘露作报告。3月28日,欧阳予倩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略谈青年话剧演员的修养》一文,这是专为话剧观摩演出会而作,希望能够帮助青年演员解决工作与学习中的问题。3月31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对首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的全体报告作了报告,代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话剧工作的重视。
与西南剧展和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相比,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还组织了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朝鲜、蒙古、越南、南斯拉夫12国的戏剧家代表参加了话剧观摩团,扩大了中国话剧的国际营销。3月9日,夏衍、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在新侨饭店的座谈会上向外宾们介绍了中国话剧运动的发展状况。3月12日,田汉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邀请了外国专家参加座谈,并向外国专家介绍了戏剧家协会的组织和具体情况。3月22日,大会邀请苏联剧作家阿尔布卓夫和俄罗斯人民演员斯科皮娜为参加观摩的剧作者、导演和演员700余人作报告。3月29日,阿尔布卓夫作了“关于会演的总结意见”的报告。4月1日,刘芝明、田汉等人邀请各国戏剧家举行京剧座谈会,向外国专家介绍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大会期间,欧阳予倩还邀请外国专家参观中央戏剧学院并座谈,向他们介绍新中国高等戏剧教育的发展情况。外国戏剧家认为话剧观摩演出会大多数剧目缺乏民族特点,或者(表现民族特征)不够,这一宝贵意见促进了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发展,年内便有《虎符》《桃花扇》等一批具有中国美学的剧目开始创排演出。
欧阳予倩、田汉深度参与了新中国的第一次文代会演出、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的举办,这三次重要的戏剧展演在组织形式上借鉴了西南剧展的经验,不同侧面体现了西南剧展设定的剧目展演、戏剧工作者交流、资料展览的基本架构,同时又结合实际情况在扩大剧目范围、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上有所创新,这弥补了欧阳予倩和田汉主办西南剧展时的遗憾,为后来戏剧展演和戏剧节的举办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参考。但令人唏嘘的是,1962年7月,欧阳予倩在北京阜外医院治疗时向女儿欧阳敬如讲述了许多往事,其中很长时间谈到西南剧展,他希望有生之年能够认真总结、探讨剧展的得失。两个月后,欧阳予倩离开了人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萦绕在他脑海中的依旧是桂林旧梦。
【注释】
①⑧广西戏剧研究室、广西桂林图书馆主编《西南剧展》上册,漓江出版社,1985,第187、194页。
②田汉、李门:《西南剧工大会主席团对各团队工作报告的总结》,《文化新闻》1944年4月8日。
③《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戏剧工作者大会议案讨论记录》,油印资料。
④⑥田汉:《田汉全集·文论》,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第57、190页。
⑤王秀涛:《历史的细节》,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第91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第226页。
⑨王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全程描述》,《中国音乐学》2009年第3期。
⑩11吉林省文化厅办公室、吉林省文化厅文化艺术志编辑室编《吉林省文化工作文件选编·艺术(1951—1959)》(内部文件),第247页。
12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首届话剧会演会刊 10》,油印资料。
(杨乐,中央戏剧学院戏剧艺术研究所。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欧阳予倩与新中国戏剧的构建”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2AB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