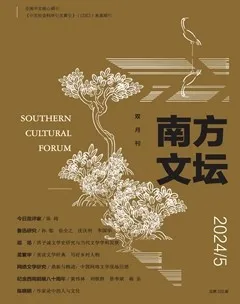“散文诗”的误区以及真正的诗
在近代以来文学文体的演变过程中,“散文诗”的出现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国古代有“诗”“文”之说,并无“散文诗”这一概念。所谓“文”,也是一个十分宽泛的说法,是指除诗赋之外的所有散体文章。姚鼐在《古文辞类纂》里,将“文”分为13类,即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可以说包容性极大。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刘半农等人提出要将“文字的散文”变成“文学的散文”,周作人提出“美文”的概念,将大多数散体文章从“美文”中剥离,只留下个人化、艺术化的叙事抒情类文章,将其圈定起来,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构成现代文学的四大体裁,自认为“确认了文学性散文的地位”。可见,现代散文是将传统的“文”进行窄化、瘦身的结果。这一操作在当时或许有时代的进步意义,但也导致后来的散文创作出现诸多问题。至于诗,众所周知,从旧体诗到“新诗”的转变,是用白话作诗(新文化运动初期叫“白话诗”),完全打破四言、五言、七言的限制,不讲格律,提倡“诗体大解放”,从语言体式上看,实则就是诗歌的散文化过程。诗的散文化,其中有人为鼓吹,也体现了历史的必然,因为传统诗词从唐诗到宋词,虽然也讲格律,但已经“长短句”了,语言出现“散化”趋向,到了元曲,即便散曲部分,抛开音乐性只就文字本身而言,基本没什么格律了,也不讲对仗,可以说,是进一步散文化了。后面经过“同光体”诗歌的试验,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等人从理论上鼓吹、创作上“尝试”,将诗歌的散文化空前推动了一大步,做得很是彻底。如此一来,也引起新诗形式的诸多争议,有些话题一直纠结到今天。
散文要艺术化,或者美文化,其语言审美追求诗化;同时,诗歌则追求散文化,要打破格律限制。这两种潮流的会合,即散文的艺术化与诗的散文化合流,催生了文学在形式上的多种变化。其中之一,即是人们常说的“散文诗”。在“散文诗”诞生的同时,中国古典诗词借着散文化转变,由韵文诗到白话诗,原先的格律转变为“分行”——不讲格律,只讲分行。“分行”成为白话诗在语体形式上的显著特点。分行之中包含着经验、学问,诗的停留感、节奏感得以微妙体现。“分行”成为新诗创作者们的共识,延续至今日。然而,“散文诗”却是不分行,只分段,之所以称其为“诗”,在“文学革命”的历史背景下,无疑反映了人们在当时的一种激进企图,他们想通过“增多诗体”的方式,促进新诗的更加散文化,以彻底否定旧体诗的格律传统。正如安敏轩在《交换隐喻:20世纪汉语散文诗与文学史再分期》一文中所言:“‘五四’时期的诗歌不再是传统的押韵诗,这对作家和读者而言都相当重要。按照更当代的定义,它们是否是散文诗是存在争议的。虽然作者不具备明确的体裁意识,我们却不能排除作者写出了我们可称之为散文诗的作品的可能性,但将‘散文诗’这个标签贴在他们身上,则会稀释‘五四’作家们的真正意图:他们希望粉碎古老的押韵诗传统。”①
“散文诗”这一文体的兴盛,也与外来文学思潮的介入密切相关,可以说,“散文诗”是本土性与外来性的结合。作为一种近代文体,在19世纪以前,欧洲并无“散文诗”这一说法存在,只是到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那里,他为了“适应心灵的抒情的冲动,幻想的波动和意识的跳跃”,尝试写出《论色彩》那样有“应和论”的文字。1864年,波德莱尔在报刊发表《巴黎的忧郁》,在其去世两年后即1869年结集出版,引起巨大反响。《巴黎的忧郁》是波德莱尔“散文诗”的代表作,其文本价值,可与1857年出版的《恶之花》相提并论。在此前,“法国文学的影响力在于它的散文作家,而英国文学的影响力在于它的诗人”(阿诺德语),正是波德莱尔和他的两部作品集,大大抬升了法国诗歌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此后,经过兰波、马拉美,散文诗在“启悟”“灵视”“怪诞”以及题材审美方面,有了崭新的突破。兰波是一个谵妄的诗人,他的作品,往往给人惊魂一瞥的感觉。他的散文诗集《彩画集》,错愕随处可见。其中一篇《言语炼金术》,颇有自我告解的意思:
我喜欢愚拙的画作,门帘,装饰,街头艺人的布景,招牌,民俗彩画;过时的古文,教会的拉丁文,不带字的色情书,祖辈的小说,仙女的童话,儿时的小人书,古老的歌剧,幼稚的小曲,天真的节奏。
我梦到了十字军,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旅行,没有历史的共和国,被镇压的宗教战争,习俗的变革,种族迁徙和洲际板块的腾挪:这些神奇都让我深信不疑。
我发明了母音字母约色彩!——A黑,E白,I红,O蓝,U绿——我规定了每一个字音的形式和变化,不是吹嘘,我认为我利用本能的节奏还发明了一整套诗的语言,这种诗的语言迟早有一天可直接诉诸感官意识。我保留解释的权利。②
这些文字,展现了许多狂乱的臆想和词语的跳跃,很“任性”地将不同意象拼贴在一起,制造出某种反逻辑的效果。同样,马拉美的《秋》也充满意象的迷境,还有反逻辑的想象。他们的作品,与以前理性主义的欧洲文学传统大相径庭,是有意要以怪诞的感性标出自我,反叛过去。为此,在文体形式上也要立异求新,写出来的既不像是散文,也不像是诗,而是一种炼金术式的混合。他们故意捣乱原本明晰的文类界线,就像波德莱尔故意将已经写好的分行诗打乱,变成散文化的呓语一样。
通过王尔德的引介,这些法国天才的作品进入英国,而后传播至俄国,催生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和普里什文的“牧神写作”;传至印度,催生了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并获得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随后,“散文诗”进入中国。最早的译介者是刘半农。从1915年开始,刘半农开始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在《中华小说界》等刊物发表。1917年5月,刘半农在《新青年》撰文《我之文学改良观》,其中专门谈到一个“增多诗体”的问题,认为:
吾国现有之诗体,除律诗、排律当然废除外,其余绝诗、古风、乐府三种(曲、吟、歌、行、篇、叹、骚等,均乐府之分支。名目虽异,体格互相类似),已尽足供新文学上之诗之发挥之地乎?此不佞之所决不敢信也。尝谓诗律愈严,诗体愈少,则诗的精神所受之束缚愈甚,诗学决无发达之望。试以英、法二国为比较:英国诗体极多,且有不限音节、不限押韵之散文诗。故诗人辈出。长篇记事或咏物之诗,每章长至十数万言,刻为专书行世者,亦多至不可胜数。若法国之诗,则戒律极严。任取何人诗集观之,决不敢变化其一定之音节,或作一无韵诗者。因之法国文学史中,诗人之成绩,决不能与英国比,长篇之诗亦鲜乎不可多得。此非因法国诗人之本领、魄力不及英人也,以戒律械其手足,虽有本领、魄力,终无所发展也。
刘半农关于“增多诗体”的立论颇有见解,说到了问题的要害,不过他对法国诗人的认识,明显是陈旧了。法国曾经是“诗人之成绩,决不能与英国比”,可是自从贝特朗、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等人横空出世后,法国诗坛的格局就大为改变了。法国诗歌不仅不是“无所发展”,而且有了令人刮目的发展,以至影响到英国的诗歌。刘半农写此文时,可能并不了解法国的状况,不认识波德莱尔、兰波等人的作品,所以如此看低法国诗歌,倒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刘半农将英国17世纪以来那些“不限音节、不限押韵”的作品命名为“散文诗”,其实是不准确的,甚至就是一个错误。在当时,那些作品被称为“诗意的散文”“诗散文”(“Prose in Poem”,“Poemsi Prose”),而不是“散文诗”(“Prose Poetry”)。那些作品的本质是散文,诗化的散文,而不是什么诗。
实际上,波德莱尔就将自己创作出来的那种东西,叫作“诗的散文”(“Petits poemes en prose”):“在那雄心勃发的日子里,我们谁不曾梦想着一种诗意散文的奇迹呢?没有节奏和韵律而有音乐性,相当灵活,相当生硬,足以适应灵魂的充满激情的运动、梦幻的起伏和意识的惊厥。”③我们读他的《巴黎的忧郁》,里面50篇,其实都是散文,只不过那些散文篇幅短小,结撰独异,去掉了情节的“椎骨”,意识的跳跃性强,意味深厚,很具有诗性。于是,人们以讹传讹,习惯地称其为“散文诗”了。
1922年的《文学旬刊》(总第24期、27期),分别发表了郑振铎、滕固的两篇评论,题目都叫《论散文诗》。郑振铎的文章一开头便说:“散文诗在现在的根基,已经是很稳固的了。在一世纪以前,说散文诗不是诗,也许还有许多人赞成。但是立在现在说这句话,不惟‘无征’,而且是太不合理。因为许多散文诗家已经把‘不韵则非诗’的信条打得粉碎了。”其实,在郑振铎所说的一个世纪以前即1822年左右,世界上还没有“散文诗”的这个说法,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等人的那些后来被误认为“散文诗”的作品还没有问世,不会有人去讨论“散文诗”到底是不是诗。郑振铎反驳“无韵则非诗”,这没有问题。他在下文指出“即以古代而论,诗也不一定必用韵”,这也没有问题。可是他以此为据来证明“散文诗”的合法性,似乎就有了问题。“散文诗”首先是关乎“散文”与“诗”的问题,是这两种文体各自属己、属他以及合流的问题,而非有韵无韵的问题。要说无韵,“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没有严格的韵,越到后来越没有韵。要说散文化的诗,“新诗”相对于古诗,最大的特征就是散文化,打破了格律。到了今天,无韵成了“新诗”的主流。但“新诗”是诗,“散文诗”则不一定。尽管郑振铎认为“散文诗”的本质是诗,他专门从“情绪”“想象”“思想”“形式”等方面来论述“诗的要素”,然而这些要素,“新诗”已经具足,何需再由“散文诗”来别开一家分店。
滕固在《论散文诗》中认为:“散文诗这个名词,我国没有的;是散文与诗两体,拼为诗中的一体,犹之诗剧两体,拼为诗剧,Poeticai drama,没有什么奇怪。”说没有什么奇怪,也有点奇怪,因为“诗剧”是“剧”,而不是“诗”,“诗”与“剧”两体为一,成为诗化之剧。同样,Poemsi Prose,“诗”与“散文”两体为一,成为诗化散文,其本质为散文,该叫“诗散文”才对。令人不解的是,这种文体传到中国,从名称到写法,都反过来了。
中国的第一篇“散文诗”,是刘半农的《晓》,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五卷二号。请看这篇《晓》:
天色渐渐明;不觉得长夜已过,只觉得车中的灯,一点点的暗下来。
车窗外面:
起初是昏沉沉一片黑,慢慢露出微光,——露出鱼肚白的天,——露出紫色、红色、金色的彩霞。天上是疏疏密密的云?是地上的池沼、丘陵、草木,是流霞?是初出林的群鸟?依旧模模糊糊,辨不出。太阳的光线,一丝丝的透出来,照见一片平原,罩着层白朦朦的薄雾;雾中隐隐约约,有几墩绿油油的矮树;雾顶上,托着些淡淡的远山;几处炊烟,在山墩里徐徐动荡。
这样的景致,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
晓风轻轻吹来,很凉快,很清静,叫我不甘心睡。
回看车中,大家车横西倒,鼾声呼呼,现出那干——枯——黄——白——死灰似的脸色,只有一个三岁的女孩,躺在我手臂上,笑弥弥的,两颊像苹果,映着朝阳。
是诗吗?显然不是。它不过是一篇散文,至多是带有诗性的散文。
鲁迅的《野草》是诗吗?也不是。《野草》里面23篇,除了《我的失恋》刻意有点打油诗的味道,《秋夜》《影的告别》《雪》等诗性较重,其余皆是散文,不过是特殊的散文。鲁迅自己也从未把《野草》当诗来看。《野草》的创作,深受屠格涅夫的影响。1920年前后,在发表屠格涅夫作品的那些刊物上,如《晨报·副刊》《小说月报》《语丝》等,经常出现鲁迅的作品。可以说,通过刘半农、沈颖等人的翻译,鲁迅“第一时间”了解到屠格涅夫的创作(鲁迅也“第一时间”了解泰戈尔的创作,只是审美趣味有些不投)。屠格涅夫的那些作品,比起兰波、马拉美等人,从结构到语体形式,更加符合鲁迅的口味,更加是“诗散文”,而不是“散文诗”了。
那么,是“诗散文”如何,是“散文诗”又如何?二者的区别那么大吗?这首先关系到写作的向度问题,即把诗往散文的方向写,还是把散文往诗的方向写。这也关系到文体的内质问题,即究竟什么样的作品是诗,什么样的作品是散文,什么样的作品又是特殊的散文。
“散文诗”并不是诗,它在诗的意义上并不成立。除了在翻译之初以及流行过程中出现的名称讹误,这一命名还关涉到人们如何认识诗特别是“新诗”,怎样界定“新诗”。从“新诗”诞生之日起,其诗体本身就发生诸多争议,譬如当初章太炎等人认为“中国自古无无韵之诗”,白话诗不讲押韵,所以不能称其为诗,应该称其为“燕语”。这一观点在当时即遭到不少人的反驳,其中胡适当年谈韵的问题,认为新诗有三种自由:第一,用现代的韵,不拘古韵,更不拘平仄韵。第二,平仄可以互相押韵,这是词曲通用的例,不单是新诗如此。第三,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无妨。新诗的声调既在骨子里——在自然的轻重高下,在语气的自然区分——故有无韵脚都不成问题④。在新诗发展的最初时段,使用“现代韵”的作品占了绝大部分,人们熟知的《再别康桥》《雨巷》等便是如此。越到后来,没有韵的作品越来越多,乃至今天占了绝大多数。当然,新诗100多年的历史中,总有一部分诗人坚持有韵的写作。因此,有韵无韵,在今天看来确实不是什么问题。那么,新诗讲不讲音乐性,讲不讲节奏感?宗白华当年在《新诗略谈》中认为,诗的内容可分为“形”与“质”两部分,诗就是“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底情绪中的意境”。诗的“形”就是诗中的音节和词句构造诗的;“质”就是诗人的感想情绪。诗形的凭借是文字,而文字能具有两种作用:音乐的作用,文字中可以听出音乐式的节奏与谐和;绘画的作用,文字中可以表写出空间的形象与色彩。新诗的创造,是用自然的形式,自然的音节,表写天真的诗意与天真的诗境⑤。可以说,宗白华对新诗的认知是很到位的,他的“形”“质”之论,抓住了诗的文体特征。其中关于“绘画的作用”,无论古诗还是新诗,都体现得比较充分,因为中国诗总体上讲意象,用意象说话,文字产生的那种画面感就很强。至于“音乐的作用”,在古诗与新诗中都讲究,新诗虽然不刻意追求押韵,但“自然的形式”和“自然的音节”还是需要的。问题在于,新诗是完全打破格律的诗,它的自然形式、自然音节,究竟怎样具体显现呢?
首先当然在于分行。除了分行,还有分节、分句。此三者,是体现新诗自然形式、自然音节的最有力工具。很多人谈新诗,只谈分行,不谈分节、分句,是不全面的。其实,创作一首新诗,其中分不分节,分几节,大有讲究。一句话怎样分句,句子中间怎样标点,怎样空格,也体现创作者的经验和技艺,对一首诗的成功十分重要。在当代新诗中,关于分节、分句的出彩例子,不胜枚举。当然,最显眼的或许还是分行。吴思敬在《新诗形式的底线在哪里》一文中引用现代诗人废名当年的话,即“新诗唯一的形式是分行”,对新诗的分行功能进行了总结,吴思敬认为:新诗的分行,使之在外形上同古典诗歌有了明显区别;从心理学上说,分行可以提供一种信息,引起读者的审美注意,并唤起读者阅读新诗的审美期待;分行排列的诗句,是诗人奔腾的情绪之流的凝结和外化;新诗采取分行的形式,虽来自西方,却并非是对西洋诗的简单模仿,从根本上说是由汉语诗歌的内在特征决定的;从诗人的创作角度看,分行排列可以把视觉间隔转化为听觉间隔,从而更好地显示诗的节奏⑥。窃以为,吴思敬此文是自新诗诞生以来对分行这一问题最详全、最深刻的阐解,他将原来倾向过的“分行+自然的节奏”的说法做了修改,觉得“自然的节奏”这一条,可以归结到“分行”这一要求中。因为“内在的韵律”属于诗人内心的活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通过“外化”转化为“外形式”的时候,必然要产生节奏感。这一说法不仅在推理上站得住脚,也符合新诗创作的现实,因为有过新诗创作经验的人不难体会到,所谓“自然的节奏”确实是通过分行(再加上分节、分句)在技术上得以实现的,可以说,分行、分节、分句就是节奏,就是“内在的韵律”以及“情绪流”的外显。不过,吴思敬关于新诗分行的言论一出,还是引起一些争论,罗小凤等人发文与之商榷,认为“分行的自由体”未必都是新诗,除了外形式,新诗应该有“内形式”的底线,新诗的内形式底线在于“自然节韵”⑦。其实仔细想来,新诗的内形式与外形式是一回事,都属于“形”的范畴,统一于某种技术性手段,能够通过分行、分节、分句等加以解决。分行、分节、分句既是新诗的外形式,也体现着新诗的内形式。
“分行的自由体”未必都是新诗,这没错。在现实的作品,也存在着不少虽然分行却不是诗的情况。分行是新诗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分行的未必是诗(新诗),但新诗必须分行。文字要成为诗(新诗),除了分行,还需具备其他条件。在笔者看来,这个条件并不是什么“内形式”,不是什么“情绪流”“自然节韵”之类。诗有“形”“质”之分,既然“形”已经包括了内形式、外形式,成为诗的其他条件,就需要从“质”的方面去考虑。一首诗或一首新诗的“质”,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截至目前,也无定论,说法众多。有人认为诗是最高的语言,但何谓“最高的语言”也难以界定清楚。有人认为诗应该有强烈的情感,有优美的意境、高雅的审美等,这些也只是某一类新诗具有的特质,新诗百年流派众多,各种实验层出,许多诗人并不追求这样的特质甚至反对如此写诗,照样创作出优秀的代表性作品。新诗史的一个现象是,有人提出某种诗学主张,践行不远,就有人提出相反的主张并且大张旗鼓地用创作响应(如“第三代诗派”针对“朦胧诗”便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要寻求新诗的质的最大公约数,颇不容易,说出来的往往只是一家之言。笔者亦不揣冒昧,说出自己的一点想法,即:新诗之所以成为新诗,除了分行、分节、分句等形式上的讲究,在质的方面所具备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文字中的“诗味”,或者说,要有一定的意味感。古诗讲求言外之意、味外之旨,讲求有限的空间中表达无限的意味,令读者遐想。新诗使用的是白话,白话不讲求一点意味,语言没有味道,就真是大白话了。要将大白话写出味道,写出彩,其实是更有难度的。有些文字,譬如生活中常见的那些请假条、留言条等,因为缺少诗所要求的那种意味感,再怎么分行、分节、分句,也变不成诗,只是在顺着生活逻辑在传达实际信息。请假条、留言条能变成诗,一定要包含超出实际信息之外的某种诗意的因素,也就是某种意味感。试以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特此说明》(又译《便条》)为例:“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们/可能是你/留着/当早餐用的//请原谅/它们太好吃了/那么甜/又那么凉。”这是一首世界著名的“便条诗”,它之所以是“诗”而不仅仅是“便条”,就在于它于便条的信息功能之外,还释放了语言的诗性功能,即那种意味感。这首诗的语言简单清晰,像日常语体,首先传达的是一个日常信息,“我”吃了“你”放在冰箱里的梅子,但留了一张“特此说明”,微妙地反映出两个人的关系,反映出生命欲望与礼节规约之间的平衡,以及人的生活处境,在窘迫的物质条件中,冰箱里的梅子“那么甜/又那么凉”。
意味感是内质,它与分行、分节、分句等形式要素一起,构成新诗的文体基础。具此二者,语言处理得当,新诗可成。此二者也是新诗区别于散文、小说、戏剧等其他文体的关键所在,抑或是诗区别于非诗的关键所在。以这两个标准去衡量“散文诗”,不难发现“散文诗”这种东西既不具有诗的形式要求,也常常不具备诗的内质要求。“散文诗”并不是诗。从“内质”方面看,许多作品缺少诗味,蕴藉性明显不足。
吴思敬在《新诗形式的底线在哪里》中也谈到“散文诗”,试图对“散文诗”与诗的关系进行调和,他将“散文诗”从新诗中提出来,与旧体诗词、歌词、剧诗(诗剧)放入“大诗歌观”中去看待:“在我看来,新诗与散文诗都是诗,在诗性的根本要求上,没有区别。”“分行写的是新诗,不分行的就是散文诗。”这样,新诗与“散文诗”并列,在大诗歌的范畴之内重新给“散文诗”划了一块“自留地”,承认“散文诗”也是诗,可谓煞费苦心。只不过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划分既没有必要,也不太科学。
前面说到,“散文诗”的出现,是“诗的散文化”与“散文的诗化”两股思潮合流的结果。时至今日,关于“诗的散文化”仍在探索,但是“散文诗”在诗的意义上站不住脚,它是失败的实验。“散文的诗化”则带来更大的问题。当年从“文字的散文”到“文学的散文”,似乎是一种差强人意的转变。散文的“美文化”导致了后来散文的写作路子越来越窄、越来越狭隘,“散文的诗化”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散文的困境。到了“诗散文”,算是走到了极致,甚至走到极端。无论“散文诗”还是“诗散文”,都变成两边打擦边球又两边不沾的东西,其地位不伦不类,十分尴尬。余光中说:“在一切文体之中,最可厌的莫过于所谓‘散文诗’了。这是一种高不成低不就,非驴非马的东西。它是一匹不名誉的骡子,一个阴阳人,一只半人半羊的faun。往往,它缺乏两者的美德,但兼具两者的弱点。往往,它没有诗的紧凑和散文的从容,却留下前者的空洞和后者的松散。”⑧此论以“非驴非马”“阴阳人”等作比,尖刻之极,却也戳中了“散文诗”的要害。相对而言,西渡在《散文诗的性质与可能》一文的观点要平和一些,但同样揭出弊病所在:“在散文中,形式本身是一个累赘的、多余的存在,一旦散文的形式获得了某种独立的意义,散文也就获得了某种诗的性质。这就是我们说某些小说、剧本、散文具有诗性的原因。这个意义上的诗是一种广泛的存在,当然它是一种不完全的诗,是诗向散文的渗透。也可以说,是散文向诗偷来的东西。无疑,这种诗性提升了散文的品质。但如果这种偷来的东西变得过分,以至有碍于散文实现自己的实用目的,也会把散文压垮,成为非驴非马的东西,譬如种种华而不实的应试文章、官样文章。”⑨笔者也深切感受到,当代“散文诗”已在某种程度上沦落为“花瓶文体”,唯美而空洞,华丽而做作。在鲁迅那里,因其卓越的文体能力,除了创作出《朝花夕拾》那样一般人都认为是散文的散文,还有不像散文的《野草》,后者以表现生命哲学的幽暗、诡美而令人称奇,文体上达到高峰。今天的“散文诗”既没有鲁迅那样深刻的思想,也没有那种语言的独特,大多只是华而不实的修辞,读多了极容易产生审美厌倦。
这是“散文的诗化”走到极端所造成的后果。将散文往诗的方向刻意去写,刻意追求“向诗偷来的东西”,追求所谓“诗意”,只能使文字越来越“花瓶”。100多年来白话散文演变的历史,已说明这一点,已充分暴露出弊端所在。或许将目光回返,向中国盛大的古典散文传统寻找灵感和方法论,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近年来,评论家兼“新锐散文家”李敬泽在多个场合谈散文的转型问题,他认为文学的散文实际上也是广大无边的“文”的一部分,散文写作要“回到子部”,重回现代的诸子之道:“现代的文学散文,周作人他们起了很大的建构作用,经史子集,他们实际上是独取集部,而且是集部的晚明。而鲁迅后无来者,他是走了‘子部’。后无来者也是正常的,集部人人可走,子部可不是人人能‘子’的。但是现在,我确实认为有一种子部复活的前景,在互联网背景下、自媒体背景下,现在最重要的书写不在我们这些传统的散文家这里……而在很多公号文章、很多自媒体的书写里,他们有‘杂’而‘子’的气象。”⑩四库全书中关于《子部》的分类,包括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艺术、谱录、类书等10多种,确实是“杂”而“子”,古文的弹性与跨界书写达到非常丰富驳杂的地步,应用性广阔,文言的典雅自适,也得到极大发挥。后来,“文”变成“文学”,“文字的散文”变成“文学的散文”,状况就急转直下,乃至有今日之困。
以是观之,散文不妨重开眼界、格局与方法,向着“文”那里去,至少应该向“杂的文学”那里去,恢复弹性与活力。作为散文的“散文诗”,在诞生之初是有着“杂”的企图的,它想融诗的因素与散文的因素为一体,兼具更多表达形式,从而形成一个新的种类。它的“越界”“中间态”“文本间性”,具有实验性质。但它不是“杂”而“子”,而是“杂”而“诗”,将自古并立的“诗”“文”强行糅合,变相地往极端化艺术上走,越到后来,产生的作品似乎越糟,书写越没有出路。那种病态的精致,是愈来愈明显了,有文而无质的状况,愈来愈严重了。
还是要回到“散文诗”产生的那个起点上,重新看待它被接受和理解的过程,它的命名,以及它在具体书写中存在的巨大误区,重新追问它的文本性。它究竟是“散文诗”还是“诗散文”,抑或别的什么,甚至什么都不是。
【注释】
①安敏轩:《交换隐喻:20世纪汉语散文诗与文学史再分期》,杨东伟译,《长江学术》2021年第3期。
②兰波:《彩画集:兰波散文诗全集》,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第103页。
③夏尔·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郭宏安译,商务印书馆,2022,第3、4页。
④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载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论选》第1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21页。
⑤宗白华:《新诗略谈》,载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论选》第1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27-29页。
⑥吴思敬:《新诗形式的底线在哪里》,《名作欣赏》2021年第19期。
⑦罗小凤:《新诗形式的底线是什么?——兼与吴思敬先生商榷》,《南方文坛》2023年第3期。
⑧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辫子》,载黄维樑、江弱水编选《余光中选集(第三卷)·文学评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第24页。
⑨西渡:《散文诗的性质与可能》,《诗刊》2020年第5期。
⑩李敬泽、李蔚超:《杂的文学,及向现在与未来敞开的文学史——对话李敬泽》,《小说评论》2018年第4期。
(唐翰存,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新边塞诗’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1BZW141;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抗战时期‘西北诗运’及甘肃‘新边塞诗’的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21YB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