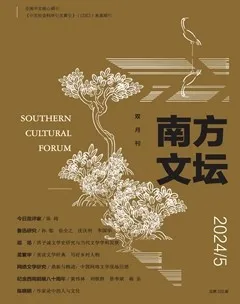新乡土叙事中的“主体性”问题探析
“新乡土叙事”抑或“新乡土文学”并不是当下才出现的新话题,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就有相关讨论,但至今却仍然还是一个“未完成”的、开放的、热议中的命题。这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仍在持续。这一变化是包含方方面面在内的整体性、结构性、根本性的转型。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的发展呈现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科技化的进一步深入,召唤着新发展格局的不断生成与演进,也加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新山乡巨变”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镜像。
一、“新乡土”与“新主体”的生成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早已成为现代化转型中的重要一环。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实践进一步深化,乡村的面貌也在不断产生新变。这一变化是剧烈而深刻的,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生态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变革。而“新乡土”之现实的改变,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生活于其间的人们,引起他们在伦理秩序、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生产方式、情感认同等方面的革命性转变,而人的变化又能反过来重塑乡土的格局。因而,“新主体”与“新乡土”是相伴相生、互为因果、互相建构的关系。
可以说,当下的“新乡土”是一个巨大的“召唤结构”,没有固定的形态,并且正在不断“增殖”。因此,“新乡土叙事”具有丰富的言说空间、强大的生命力和珍贵的价值意义。它不仅能够反映当代中国的“新山乡巨变”,还能以文学的形式提供一份鲜活的乡土经验。现实主义的“幽灵”在“新乡土叙事”中重新获得栖身之地,并且在作家的叙事中达成与现代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的“合谋”,深化“新乡土叙事”的时代命题与哲学品格。正如曾攀所说:“‘新乡土叙事’脱胎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乡土文学的多元转向,尤其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的山乡巨变背景下,在主体性、实践性、发展性与时代性四个层面,建构起了自身的艺术理念和意义系统,并且不断生产出迥异于既往乡土小说的沿革诉求、主体建构、话语伦理和价值谱系。”①而“主体性”的建构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因为“‘新乡土’的形成离不开‘主体’的‘实践’参与以及‘时代’的‘发展意志’”②。质言之,只有准确把握处于大变局之中的新质主体形象,才能够锚定深入叙写“新乡土”之结构变化、思维方式、精神内涵的靶位。
从这个意义而言,“新乡土”背景下的新质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李约热《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中的李作家、滕贞甫《战国红》中的陈放、忽培元《乡村第一书记》中的白朗、李田野《我是扶贫书记》中的张荣超等。他们有的是大学生村官,有的是驻村第一书记,共同点是都带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回到乡村,从多方面统筹发展,带领大家摆脱贫困。另一类是乔叶《宝水》中的地青萍、付秀莹《野望》中的二妞、关仁山《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九月还乡》里的九月等。他们返乡后带回自己最新的学识、技术以及现代经验,或投资办厂或直播带货,以多元灵活的方式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新人”主体。这两类主体,一般都在城市中受到过良好的现代教育,有敏锐的商业触角、知晓法制经营的规则、拥有知识、懂得技术、能够将互联网+运用到乡村发展的实际中,明白现代社会运行流转的逻辑,可以多维助推乡村发展。
此外,鬼子暌违18年之久的长篇小说《买话》也贡献了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新质主体——刘耳。刘耳是不同于以上两类的新一类,说刘耳新是因为他并不是经济意义上将现代科技与新型管理模式、生产关系带回乡村的经济主体、行政主体或新型劳动者,而是指他在“城乡关系”中的身份与处境,以及他“返乡”后的遭遇、行为与选择。重塑“城乡关系”这一新的历史“卡夫丁峡谷”并不容易,鬼子以文学的形式进行了一次探索。在《买话》中,城与乡不是简单的对立结构,也与以往将小镇空间作为二者结合的“中间地带”不同,这次,刘耳这一人物成为鬼子安置城与乡的矛盾与融合的“装置”。
总的来说,以上几类主体形象,不论是因为何种原因而融入“新山乡巨变”的大潮中而获得“新质”的主体性质素,都不可逆地彰显着他们作为现代化主体正在经历的由内到外、从上到下的嬗变。并且他们的新变正在与大时代的潮流同频共振。讨论他们的主体性如何得以赋形的具体过程,就是对“新乡土”之丰富样态与具体“风景”的一次“打开”与“发现”。
二、新质主体的形象赋形
首先,讨论“新乡土叙事”中主体形象的建构问题,必须要处理好“新乡土”与旧传统之间的关系。毕竟,任何发展的过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整体呈现出有先有后、有常有变的规律。不能因为一个“新”字,就忽略了所有还留有“乡土性”的乡村样态,这样反而会造成对“新乡土”之丰富性与复杂性的遮蔽。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所说的“新”绝不是对“旧”的全盘否定。“新乡土”的“新”与“旧”之间,存在着辩证法。正如李壮所说:“乡土世界中存在的新与旧文化观念的交织、碰撞,也使得‘旧乡土叙事’成为我们创作和阐释‘新乡土叙事’时不可能绕开的‘潜文本’‘前文本’。”③在我们言“新”的今天,百年乡土文学传统无疑是不可逾越的传统资源。在一种历时性的发展对照的眼光中,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新乡土”的内涵,由此才能更贴切地阐释与探赜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的主体。
其次,还需要注意的是孟繁华所指出的“超稳定文化结构”,这是指“在中国乡村社会一直延续的乡村的风俗风情、道德伦理、人际关系、生活方式或情感方式等,世风代变,政治文化符号在表面上也流行于农村不同的时段,这些政治文化符号的变化告知着我们时代风云的演变。但我们同样被告知的还有,无论政治文化怎样变化,乡土中国积淀的超稳定文化结构并不因此改变,它依然顽强地缓慢流淌,政治文化没有取代乡土文化”④。不能因为要写“新乡土”,就完全忽略这些因素,先行预设一个“新”的框架,把叙事套僵套牢。值得欣喜的是,目前的一批优秀作品,都很好地注意到了这些关系。
《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中的李作家,是一名驻村的“第一书记”。最开始,八度屯的村民们并不信任李作家,认为他只是作秀,不能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李作家并没有因此而急于批判他们,而是以一个倾听者的身份进入八度屯,在耐心“听”的过程观察村民们的精神状态与现实困境,让村民们在诉说中减压、放下防备,继而逐渐与村民们建立起信任并展开工作。正如李约热自己所说,《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表达出一位扶贫工作者如何“在一个废墟上,完成和村民情感的对接”⑤。同时,李约热也不避讳书写八度屯村民们性格上莽撞的一面和思想中落后的部分。比如村里的青壮年村民会为了争取利益,去堵县政府大门,也会因为土地纠纷和邻村的村民打架。但同时,李约热又写出了对他们的理解:“忠深说,八度的人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坏,其实就是想多得些好处。……各家各户的难处最终都是各家各户自己解决,也不能全部都靠政府,这点八度屯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也不要八度人一提什么要求,就把他当刁民……”⑥这是李作家全方位深入八度屯以后对村民们爱护的理解。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现实主义创作的品格下,李作家这一主体获得了与时代紧密勾连的“当下性”。
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则塑造了千年村村主任麻青蒿这一扎根乡村的主体。麻青蒿原本是村里的一名老师,他也曾因为贫穷而想要到城里打拼,但为了孩子,他还是留了下来,随后凭借自己的踏实负责,当选村主任。他熟悉村里的一切人和事,能够真正做到为乡民排忧解难,并且富有牺牲精神。当相关工作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时,他没有动用权力,而是积极配合,最终使得工作顺利推行。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他身上的挣扎,但全新的理念已经逐渐成为他这一主体人格的代表面。他是一个不断求新求变,积极主动学习科学管理并反哺乡村的新人形象。
关仁山《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九月还乡》里的九月,乔叶《宝水》中的地青萍,付秀莹《野望》中的二妞等人,则是一批克服困难、回乡创业的主体形象。其中的范少山,原本是一个农民,在北京昌平卖菜,亲眼看见在雪灾和贫困的威胁下村民老德安的自杀后,大为震颤。从此他毅然回乡,在一番艰苦的研究和科研力量的支持下,他终于成功引领乡亲们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原本即将消失的小村子也因此变为声名远扬的旅游观光村。更为难得的是,他还不止于此,在“新农人”的道路上,他越走越远,建立万亩金谷子种植基地,想要让更多的农民共享新型农业的成果。
从辩证的眼光来思考上述两类主体的形象,对其主体性之“新质”的产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新”的一方面是相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鲁迅开创的“乡土文学”而言的,即回乡主体们不再以“侨寓”的身份和“启蒙”的姿态自上而下地审视和批判乡土的凋敝与乡民的愚昧,而是以平实的眼光、平等的姿态融入乡村中,近距离地感受转型期乡村的现状,关注乡民与自我的精神状态,思索建设乡村的新途径,归来后也不再离去。另一方面是相对于由路遥塑造的高加林、孙少平而言的,新时代、新乡土背景下的“回乡”,不是“城市梦”破碎后出于痛苦无奈而被迫的选择,此时地青萍们怀揣着建设美丽乡村的新愿景,主动且愉悦地投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大潮中,并在乡村中获得疗愈的力量。而在脉络上,又批判地接续了《创业史》时期梁生宝们的高觉悟,以及20世纪80年代《乔厂长上任记》中改革新人乔光朴的创新精神。总体上呈现出新时代浪潮中,他们对乡土的新眼光、新态度与新理念。
此外,有学者认为,“新乡土叙事”中“没有地方感,这也可能是它最受人诟病的地方”⑦。《买话》《野望》的出现则进一步修正了这一弊病。鬼子在充满地方性的饮食文化与日常民俗的书写中,复苏刘耳对“瓦村”与生俱来的味觉与心灵记忆,同时也勾勒出一个充满风俗民情,依旧保留着“熟人社会”模式的“瓦村”。在这一体认的基础上走进“刘耳”,则能更准确地挖掘出他身上的“新质”之所在,从而看到他背后那个作为“异乡”的“故乡”世界。于焉,刘耳重返故土之艰难得以言说,并在这种艰难与隐秘中,映射出乡村的人事伦理、认知结构与情感认同的模式。用两句话概括他的现实处境与精神状态就是——“你是村里的人,但你不算是村里的人。”⑧“他的孤独,城市没人听,故乡没人懂。”可见,刘耳既是城里人眼里的“乡下人”,又是瓦村人眼里的“城里人”。事实上,他两头的转化都不彻底,身上既留有瓦村人的习性,又有城里人的生活与行为方式,应当说,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融合者”抑或是“阴阳人”。至此,城与乡的对立互嵌在刘耳身上得以实现,他是身处其间一个孤独而隐秘的“新质”回乡主体。《野望》题目本身就自带浓厚的民间乡土气息,以及浓郁的传统文化之脉。而目录则是以二十四节气为根茎,以自然主义的笔法缓缓展开横亘于其间的乡土日常。“芳村”的日常起居、饮食男女、风俗民情、人情世故……都与遵循农时的节气有关。也正是在付秀莹这样脉脉如流而又热气腾腾的叙事中,“芳村”细部那些微小细腻、丰富绵长的“微表情”得以被看见。在细细点染的新与旧、常与变之间,二妞这个念过大学的年轻姑娘逆了母亲的意,以青春的热情和智识投入“芳村”的建设中,成为与母亲相向而行的新式主体。
三、具有时代性的精神描摹与人性幽探
最后,要深入讨论“新乡土叙事”中的主体性问题,我们还是需要回到主体所处的时代本身。当下时代的结构性、根本性转型已经强烈地改变了每个人的生存处境和命运,作为大时代的一分子,我们都身处奔涌的时代洪流中,一方面为向好的嬗变而欣喜不已,一方面也在“加速时代”中难避焦虑。由现代的生活方式而产生的病症,实际上也是一种现代性的“时代病”。
查尔斯·泰勒指出,现代性是一次“大融合”现象:“‘现代性’指的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大融合(amalgam),包括全新的实践和各种制度形式(科学、技术、工业生产、城市化)全新的生活方式(个人主义、世俗化、工具理性等)以及全新的烦恼(malaise)形式等(异化、无意义、迫在眉睫的社会分裂感等)。”⑨我们现在就正处在这样一种“大融合”的过渡阶段。特别在当下,中国处于“加速”转型期,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征程中,尤其是在要加快乡村转型的时代诉求下,考察身处其间的主体之精神状态与幽微人性,有助于体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而种种“现代病”的隐喻,则是一把把打开主体深层之精神与人性的钥匙。《宝水》和《买话》中的病症,是现代人极具代表性的两种表征。
乔叶《宝水》中的地青萍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并且还伴有多梦的现象。失眠是一种典型的都市病,暗含人长期处在高压和深度焦虑的状态。这一病症对人的折磨是极其痛苦的,睡不好,意味着人生都失去了活力与动力。失眠症已经严重困扰到她的生活,以至于让她提出了病退申请。而地青萍的梦,大都是和过往乡村生活里的人与事相关。或许这就是梦的隐喻,指涉着缓解地青萍失眠症的方向。果然,在来到宝水村帮朋友经营民宿的过程中,她的病症得到了疗愈并渐渐好转。乡土的气息,甚至是粪便的气味都使她感到放松与心安。至此,她名字中的“地”终于与梦境中魂牵梦萦的“地”合二为一,她也最终在宝水村落地生根,成为建设宝水文旅特色产业的重要一员。在“新乡土”的语境下,“宝水”也不再是那个凋敝萧瑟的“故乡”,而是具有了精神的治愈与心灵的抚慰之功能的宝地。
鬼子《买话》中的刘耳整天因儿子贪污的事情焦灼不已,遂决定回乡,逃避一切。他患有前列腺炎,排尿不畅通。“根”的发炎与堵塞不仅是刘耳身体的疾病症候,也预示着他返乡寻根之路的不畅通。刚返乡的刘耳,是被瓦村的话语系统和饮食系统拒斥在外的。而也正是刘耳年轻时的欲望,间接导致竹子失去了生命。暮年时的尿潴留,事实上也是对刘耳的一种惩罚。吊诡的是,瓦村能够解决这一病症的人就是老人家(竹子的母亲)。她用一根葱花和一只竹筷,为刘耳治疗根部的堵塞。这显然带有民间的巫玄色彩,但在文学世界里,无疑也是一种可能和寓言。小说末尾,刘耳说:“可他刘耳还需要壮阳吗?不要了,不要了,要来干什么呢?只要天天能够顺畅地撒尿吃饭,就谢天谢地了!谁想壮阳就让他们壮去吧!我刘耳,真的不要了!”⑩不要“壮阳”,是刘耳对人性中欲念的放下,以及与焦灼的过去和解,只求最基本的功能与畅通,实际上也是求心理的畅通。
令人欣喜的是,地青萍、刘耳不再是那个短暂返乡后感到悲观、痛心、愤懑后又彻底离乡的返乡者,而是一个想从生活与精神上都重新在故土扎根的人。而在《买话》中需要反省与改变的,不是乡民,而正是刘耳自己。从刘耳返乡的动因,返乡后在瓦村人际伦理中的窘境,心灵深处的孤独与煎熬、反思与自我救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几代人的缩影,还能够窥见城与乡在逐步融合的过程中所存在的裂隙,反思如何重建现代人与故乡的关系。正如丁帆所说的那样:“《买话》在人性的拷问上更具有时代性,也更有深刻的哲学意蕴,这是一般乡土小说作家难以企及的境界——思想的烈度足以震撼文坛,且是从形下到形上、再到形下二度循环艺术化抒写。”11刘耳的孤独,不是个例,而是一种具有典型性的时代病症,刘耳的现实处境与精神样态在离乡谋发展又返乡的一批人中是不少见的,甚至可以说勾连着他们内心深处的记忆与生命体验。相信不少有过相似经验的人都能从刘耳身上感受到一种心灵的震颤,看到曾经的自己。从这一层面而言,刘耳无疑是具有“新乡土叙事”中一个具有时代性的人物。
李震曾言:“在新文学史上,乡村叙事的每一次发展,都是由富有典型意义和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的诞生为标志的。如何以乡村社会第三次文化裂变的文化逻辑,去创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型乡村人物形象,便成为新乡村叙事的作家们亟待发力的重要叙事支点。”12乔叶、鬼子、付秀莹、李约热、关仁山、周大新、滕贞甫等作家正是在这一支点上深入生活、潜心打磨,成功塑造出一个个极具时代性、典型性和阐释性的“新质”主体形象。他们能不能成为“新乡土叙事”中被记入文学史的人物,还有待时间来验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确代表了新时代中国“新质”主体的新样态、新面貌、新质素。并且以其实践,重塑和推动了“新乡土”的时代面貌,代表着一代人的心灵史和精神史。
【注释】
①②曾攀:《新乡土叙事:主体、实践与历史的发展意志》,《小说评论》2023年第3期。
③李壮:《历史逻辑、题材风格及“缝隙体验”:关于“新乡土叙事”》,《南方文坛》2022年第5期。
④孟繁华:《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⑤李约热:《我曾穿过“百家衣”——〈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创作手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4期。
⑥李约热:《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第80页。
⑦刘文祥:《新时代语境下的“新乡土写作”现状及其未来进路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⑧⑩鬼子:《买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第208页。
⑨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想象》,王利译,载许纪霖主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第33页。
11丁帆:《漂浮在瓦村麦田上空的灵魂》,《文艺报》2024年6月14日。
12李震:《新乡村叙事及其文化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
(周丽华,厦门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