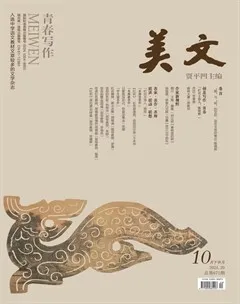十四号线
他仿佛找到了这样混沌地活着的缘由。
荒诞,这种原因存在的意义在于:难以解释,难以教你如何去做。于是选择将一切扔向天空,趁世界不注意偷偷溜走,通往机场的地铁,遇到的第一个车窗。
这辆飞驰的机器,越过城市中无数灯光里的建筑,突破黑暗冲出地面,回到地上,已是遥远的郊区。从车窗里向外看,这里并非人烟罕见,田地,村庄,郁郁葱葱的绿色,陌生而又熟悉,让人有了第一次间离的感受。他仿佛从无数的要做什么,追求什么,准备什么中脱离,回到了生活当中,或者说,回到了生活的另一面。再向前,到开发区,精心的匠工,无数钢筋环绕制成的宏伟建筑,却和宁静无比的街景匹配。路边无人监管的车辆随意摆着,好像城市突然失去了人。不知在这里工作是什么感受,能看见的也只有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不同于城里的地铁挤得人无所适从,可能一天都没有几人在这里下车,他们却要在每次开门时细心关注着。这样的景象或许挺好,因为终于从人群中,从无数的人中逃离出来。
乘着的士赶往机场,赶往车站,从车窗里向外看,红色字体的城市名字,像淮河一般,成为人类社会所约定的界限,一种定义的意义。于是每每到这里都有一种使命感,你曾在这里耕耘过什么,收获过什么,这趟行程将带来什么,这是第一层告别,这种感觉将在行程的一半消失。更重要的是,你是否准备好接受这样一种感觉:好像进入一个偌大的电梯,闭眼,或是等待一会儿,一群人被束缚在自己的座椅上,等待精神和肉体分离,再被量子传输到另一个时空。这不像是电影CG,屏幕一黑就能转场,当你下车或下机,人们就会告诉你,我们已经跨越千里。是的,这必须是别人告知的,你也必须知道这是物质的,这正是一种无奈。从而,画面在你的视野里,从这个场景转到密闭的舱室,再传到另一个场景,程序员的工作便完成了。
人应当明白这一切,这是生而为人被要求的。正如应当明白,花费再多钱购买的宝石也并不属于你,即便法律如此规定。所以有时他也会想,人的一生是不是太长了,是不是不应长到能意识到自己与世界的不完美。这无法定义,但作为一个不完美的完美主义者,他必须力求走得更远。苦恼之处在于,人脑要一边模糊地学习,模糊地认识世界,一边要不停地记住,要在脑中打下钉子。于是幼儿时,我们遇见什么,就记下什么,轻触琴键,我们就欣赏音乐,筑起泥墙,就敢说理想是成为建筑家;而长大了呢?人变得多疑,遇见金融,会想到次贷危机,遇见新科技,会想到电子产品衰退的速度。人们永远活在过去和未来,这无疑是可悲的。而人的能力限制于此,除去每个时代生产的固定数量的天才,一般人所能做的事,二三十年也就做的草草了,不能做的,求其一生,最后连自己都忘了航向。我们无法认知太多,偶尔提醒自己这一点,尊重这个世界,以及它所给予的,这一定是这个世界的选择。
从宝石归属权推演的第二个点在于,后代的更迭速度是难以把握的。人们总惊讶于青年,又害怕青年,但终究要将一切拱手让人。问题在于,如何将这种秩序从为私人利益转换到对自然法则的普遍认可。不要到年迈时侃侃而谈:是的,早该让给他们了,再把没有培养继承人一事当作人生中普通的遗憾。年华一旦匆匆逝去,就有理由假借寿命搪塞许多应该去做而未做的事,譬如说未尽孝,或是与人诀别。我很好奇,如果两人甚好却不再谋面,只借书信、电报、网络系其余生,再回首会不会也是一种间离呢?
还有一点,我在此不想多说,选择未尝不也是这般。我们总是会碰到选择——如果你想做些什么的话,却总只是从二择或多择中思索,去了解选项,再删去那些确不会做的(可能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了),随后在剩下的选项里掷骰子。这可不同于做一套试卷,如果你是感性的,再加上一些疑虑,你的选择就变得没有意义,因为事物大多矛盾,总会有好有坏,却没有能衡量好坏的尺,直到你决定的那一刻,比如下单买一件东西,原因才坍塌到某一个理由:哦,原来我更在意这个。但事实呢?可能并非如此。选择的结果也是如此,一个再有把握的人,即便能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选出“正确”选项,也要等待着结果,才知道自己的对错。这背后是不是一张定好的数表,我们从不断试错中找其规律呢?或许更好的做法是不要去选择,而将所有后果纳入规划,像全能的神一样活着。哦,所以这般也有理由,那就是人的无能,选择是一种被动的境遇。
荒诞的是,我现在每次执笔都会想,今天所写下的一切在千百年前都被人“破解”了。没有人教我们认识世界。这不正和写此文的目的相合吗?但在此,便不多如加缪般赘述越是荒诞越要好好活着这一奥义了,我意同在此。
那天在机场醒来,我提醒自己要多看看日出,平凡之路有如盲人摸象,常在黑夜中缓行。一生出走,在荒诞中归于平庸,奋进不止却好似无所得,这都是生活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