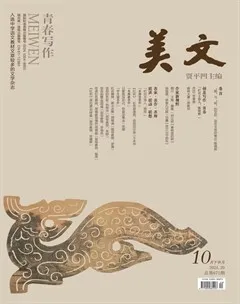辋川·王维·桑蚕
出古城西安,沿高速逶迤向南,途经灞河,途经白鹿原,一个小时后,我们抵达王维笔下的诗画山水“辋川”。
辋川,地处蓝田县城南秦岭“辋峪”的一处川道,是王维晚年安放身心的居所。秦岭七十二峪中,辋峪深且阔,钟灵毓秀,川水自尧关口流出后,蜿蜒入灞河。当年,数条小河同时流向峪底,蓄水成“欹湖”,王维和好友裴迪曾数次荡舟往来。从高山上俯瞰,欹湖水波悠悠环绕,涟漪层层,恰如“辋”形,故取名“辋川”。“辋”,是车轮外周同辐条相连的圆框。
彼时,辋川山清水秀,“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奇花、野藤、瀑布、溪流在川道里随处可见。王维四十四岁时在辋川购得唐代诗人宋之问的“蓝田别墅”,与友人吟诗作画、参禅修心,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在这里,王维创作出了《辋川集》《辋川图》,诗里画外,青山似黛,绿水如眸。
王维的诗,空灵,淡然,禅意,诗风多变,有“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的豪放不羁,也有“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的宁静超脱,还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随缘平淡。辋川,改变了诗人,诗人,成就了辋川。
当年,欹湖边上有个“临湖亭”,王维常乘轻舟接送宾客,一起在临湖亭里把酒言欢。举目荷花朵朵,清香怡人:“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尊酒,四面芙蓉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日暮时分,酒足饭饱,王维吹箫送客后,挥笔写下《欹湖》:“吹箫凌极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山青卷白云。”一个“卷”字,写活了静态的青山与白云,也暗和了诗人的离愁别绪。
如今的“欹湖”,是一条水流清浅的河。
站立桥头,秋风习习,水流潺潺,四周层林尽染,分明就是诗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里的场景。河水在脚下冲刷出一个大大的“S”河道后,向北蜿蜒而去,白皮松铺满了眼前的台地。台地之南,如画的树木掩映着青青房舍。
这里最大的一处台地在河之南,台地上的村子,就是河口村。
河口村里,有王维笔下“辋川二十景”中的金屑泉、欹湖、北垞和鹿柴,留下了广为传诵的诗句:“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一棵参天古树,就站在村口。
这是一棵三四个大人牵手才能合围的桑树,上挂一牌,书“西安市一级保护古树”,也就是说,它的树龄至少500岁,当地有人说它已愈千岁。树身挺拔,巨臂虬枝。树叶被秋风洇染得斑斓,金黄、棕褐与残绿交织,在头顶簌簌作响,古意森森,仙风道骨。
这是西安市最大也最年长的一棵桑树,它诞生时,人间还是明朝,它以木质之躯直入苍穹,眼见了至少五个世纪的苍茫世事。如今,它已不仅仅是一棵树,是河口村人的树神,护佑着村里的日子和烟火,枝叶间悬挂着村民的敬畏、依赖和期许。
在村子里转悠时,我还发现了一棵古槐。
望着古槐身上斑驳的树皮和绿苔,脑海里浮起《宫槐陌》:“仄径荫宫槐,幽阴多绿苔。应门但迎扫,畏有山僧来。”王维一定是在对着一棵古槐,表达自己对尘世的超脱和对山僧的敬重。
记得一位蓝田籍同学曾说过,王维的《茱萸沜》也是写这块台地的。
“结实红且绿,复如花更开。山中傥留客,置此芙蓉杯。”大意是,秋天里,那山茱萸的果实或红或绿,明丽犹如花朵再次盛开。把山茱萸的红果泡在芙蓉酒杯里,等待客人的到来。
我在河口村的周围并未遇见山茱萸和它的红果。很多原因吧,当年的气候环境与物种分布,与现在已有很大差别。
令我惊喜的是,在辋川镇白家坪的鹿苑寺,我遇见了一棵王维手植银杏,挂牌上显示此银杏树1200余岁,属西安市一级保护古树。
树高二十多米,粗可四人合围,树冠阔大,枝叶繁茂。秋风里,时有银杏叶缓缓飘落,似“去作人间雨”般飘飘洒洒,落下漫天满地温暖的金黄。想必多少个夜晚,王维就坐在这棵树下,望着苍穹的月,嗅着山涧的风,听幽幽鸟鸣,写下“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距古银杏所在地不足百米,是王维的长眠之地,幽静的辋川接纳了诗人,他也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秋阳从老树擎在半空的枝叶间洒落,我站在树下,任由思绪在心底涌动。一棵大树,可以长成千千万万人的庇护所,也可以长成一首禅意的诗篇,“一树擎天,圈圈点点文章”(苏东坡)。树木不仅扎根于土壤,更深深扎根于人类的历史与文明。
古人常将桑树和梓树栽种在住宅四周,母用桑叶养蚕,父用梓树制作家具,桑梓,因此成为充满诗意与深情的字眼,桑梓即父母,后来又引申为故乡。桑梓之地,有炊烟缭绕的老屋,有儿时的玩伴,有父母,有乡邻。“乡禽何事亦来此,令我生心忆桑梓”,乡野的鸟儿啊,你们为何也来到这里?让我(唐代诗人柳宗元)心生思念,想起了故乡。《诗经·小雅》中有“惟桑与梓,必恭敬之”,见到桑树、梓树,如同见到了故乡与父母,必毕恭毕敬。
桑树,在周商时已是宗庙祭祀时的神木。《淮南子·修务训》中记载了商朝开国君主成汤在桑树林中为民祈雨;古时的许多仪礼谋议也都在桑林中举行,“昔者尧见舜于草茅之中,席陇亩而阴庇桑,阴移而授天下传”(《战国策》);尧在桑树下将天下禅让给舜……
让我曾经惊骇并停下来认真思考的,是桑树一名的来历。
桑树之名源于“少女化蚕”的神话传说,载于晋代干宝的《搜神记》里。
古时,父女二人相依为命。父亲远征迟迟不归,女儿在家中独自与一匹白马相伴,马是她日常孤寂时倾诉心事的伙伴。一天,她对马再次诉说自己对父亲的思念,并说,如果白马能把她的父亲接回来,她就嫁给它。那马听懂了她的话,挣脱缰绳狂奔而去。不久,白马果真把少女的父亲接回了家。念及白马助父女团聚,父亲好生伺候白马,马却不吃不喝,郁郁寡欢,只有见到少女时方奋蹄嘶鸣,兴奋异常。父亲颇感怪异,问女儿原因,得知实情后勃然大怒,用弩弓将白马射杀,并把马皮剥下来晾晒在院子里。少女像往常那样玩耍时,忽地看到了马皮,她走上前用脚踢它,边踢边骂它作为一头畜生不该有非分之想。不曾想,马皮一下子动了起来,起身紧紧地裹住少女,往远处飞去。几天后,马皮裹着少女落在了一棵树上,少女已死,与马皮合而为一,变成了新的生物——蚕。蚕头如马,蚕身柔软纤细如少女,肤白。
这是一个凄美且令人深思的故事。
故事表明了桑树之名的来历:蚕的诞生建立在少女死亡的基础上,蚕所赖以生存的树,是少女的丧命之所,于是这种树被称为“桑”。
然而当初读这个故事时,我的第一感觉是惊悚。
我是同情马的,少女之死多少有点咎由自取。
从马的角度来看,它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对少女有着深厚情感。它听到了少女的承诺后,努力去寻找她的父亲并成功带回。马的行为,始终出于对少女的爱与忠诚。
然少女与马的感情并不对等。她忘记了马的恩情,辜负了马的信任;重要的,她忘记了自己的承诺。对曾经给予过自己慰藉的伙伴的死亡,她也没有表现出丝毫悲伤,甚至用脚踢马,鄙夷马对她的深情。少女根本没有意识到,正是自己的失信,导致了马的死亡和后续的悲剧。
我想,假如少女兑现承诺,可否有一个相对美满的结局?比如,少女与马结合后,化身为蚕,少女的牺牲感天动地,上天赐予了她某种超能力,让她在化蚕后,能正常生活繁衍,也拥有了造福一方的力量。
传说中关于生命轮回与延续的观点,我是赞同的:正是少女和马的死亡迎来了蚕的诞生;桑树,为蚕提供了食物及栖息地,让新生命得以滋养和延续。
回到现实。我国商代的甲骨文中已出现桑、蚕、丝、帛等字形。到了周代,采桑养蚕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先秦时期,桑树已是遍布田野的一种植物了。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可见,农耕社会里的“吃”与“穿”,只需栽桑养蚕,就可以轻松实现了……
我女儿小时候喜欢养蚕。每年春上,她总要带回家几只蚕宝宝。多半是同学送的,也有花一两元钱买的。有一年,她拿回家巴掌大一片纸,纸上,是一堆黑芝麻般即将破壳的蚕卵。她给蚕宝宝建房子,采桑叶,洗桑叶,换桑叶,清理蚕沙。忙前忙后,体贴入微,俨然一位称职的蚕妈妈。
女儿用毛笔将发丝一样细小的黑色蚁蚕,轻轻扫到纸盒里新鲜的桑叶上。从此,这些蚕宝宝就在片片桑叶上吃穿住行,完成忙忙碌碌的一生。
四五天后,蚂蚁大小的蚁蚕脱胎换骨,变长变粗,穿上了灰绿的衣裳。除过蜕皮期间,蚕宝宝的嘴巴一刻也不曾停歇,沙、沙、沙,恍若春雨,沙、沙、沙,声似天籁。蚕们吃相优雅:用“手”握住桑叶,脑袋扬起来、嘴巴蠕动着沿桑叶画下去,每画一个圆弧,桑叶上的洞洞就扩大一圈。
春风里,吃货们扭动发福的躯体眼看着一天天肥胖起来。一个月后,蚕宝宝变身胖乎乎的白娘子,身子亮亮的,灯光下闪耀着玉的质感。和最初的蚁蚕比起来,大了不止一万倍。之后的日子,用女儿的话说,白娘子是在完成三个成语:春蚕吐丝、作茧自缚、破茧成蝶。
这该是城里的孩子与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了。桑树,也一跃成为女儿生命中最为关注的草木。她开始关心桑树的季相,关心它何时吐芽、展叶,何时开花结果,何时冬眠。
桑树,也曾经是我生命里重要的陪伴。那棵老桑树,居于村子的南端,腰身粗壮,远看像把绿色的巨伞。当年,家乡人不懂得养蚕,我们小孩子只惦记树上的桑葚。那时候生活清苦,除过野果,基本上没有其他水果,桑葚是上天赐予乡村孩子最甜蜜的礼物。记得吃罢桑葚,嘴巴、牙齿、舌头和手都变成了紫色。有时心急,吃了尚未熟透的桑葚,牙齿酸得好几天都不能吃饭。
学了植物后才知道,看起来绿油油没什么特别的桑叶,其实颇有内涵,它们拥有强大的制造蛋白质的能力。蚕在吃罢桑叶后,会吐出精美的蚕丝,正是这些优质的蛋白纤维,织就了中华民族千年的文明长卷。其貌不扬的桑树,也站成了一条名闻世界、连接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丝绸古道。
桑蚕间的博弈,充满了传奇。这是一出惊险刺激、曲折动人的大片,关乎动植物间的相爱、相杀,展现了桑树非比寻常的生存智慧。没有哪种生物在被蚕食时愿意束手就擒,哪怕是一种植物。
一旦桑树感觉到有野蚕偷吃桑叶,即刻分泌出让昆虫消化不良的汁液,这汁液里富含一种名叫蛋白酶的物质,这种物质还能迅速合成生物信号,将自身遭受攻击的消息,传递给周围的桑树邻居,提醒大伙进入备战状态。
浓郁的气味盘桓在桑树周围,这气味,也是桑树发给马蜂的邀请函。别以为马蜂和蜜蜂一样,以花蜜为食。马蜂其实是一种凶猛的食肉者,桑树知道。野蚕,正是马蜂爱吃的一道“硬菜”。
无数马蜂寻味而来,刀枪剑戟并用,开始在桑树上享用丰盛的大餐。野蚕痛苦地扭动、挣扎,但哪里能逃出马蜂的掌心。吃不完兜着走,马蜂将最后一只野蚕打包带走后,桑树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桑树应激产生的防御性蛋白十分精准,它会针对不同的攻击者(野蚕、桑毛虫、桑天牛),产生不同的化学物质,使其消化不良,或者,搬来动物救兵。
藉此,在自然状态下,桑树的寿命可达千年,就像辋川河口村里的这棵古桑树一样,可悠然终老。但自从人类发现了桑蚕的秘密后,桑树的寿命就只有几十年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桑树是人类亏欠最多的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