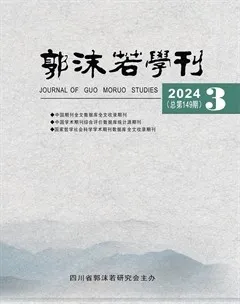郭沫若早期小说的儿童书写
摘 要:辛亥革命后受进步思潮的影响,儿童作为独立的个体进入历史视野,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问题。受中西文化浸润的郭沫若,其儿童观念也出现现代性转变,早期小说创作中的儿童大多身处贫困、漂泊的环境却不失天真个性,特殊的成长境遇使他们有着“双重他者”身份。作者以写实之笔描绘了儿童书写的多样性,表现出儿童关怀和儿童崇拜倾向,但在家国情怀、民族屈辱和生活重压之下,也出现了惊人的弑子意识,呈现出与五四新小说及五四儿童文学迥然不同的格调,书写了新文学小说史上第二代异族“他者”的新形象。
关键词:早期小说;儿童关怀;儿童崇拜;弑子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25(2024)03-0072-05
一、启蒙思想与儿童书写
戊戌变法失败后,1900年梁启超发表了《少年中国说》,对少年中国和中国少年寄予无限希望。“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的智、富、独立、自由、进步直接决定了国家的智、富、独立、自由、进步,把少年的地位上升至影响国家兴亡、民族振兴的高度。辛亥革命后受进步思潮的影响,一些现代文学作家开始发现儿童,关注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
1918年,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其后又和鲁迅先后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儿童的文学》等文章,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明确提出了儿童的独立属性,为儿童立言。鲁迅认为,父母应该顶住“重担”和“黑暗的闸门”,放子女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此外父母还应做到“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①。意即除了担负养育的责任外,还要努力教育孩子,为他们创造解放、自由、幸福的生存空间。在五四思想启蒙者眼里,儿童是在“对旧伦理的挞伐声讨中解救出来的新群体, 儿童被赋予‘新人’的寄托, 也承担着民族发展、社会崛起的重任”,因此思想启蒙者对儿童的重视也就承载着“改变社会现状、构建民族国家未来的希冀”②。从“人的发现”到“儿童的发现”,再到“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的提出与建构,新文化运动从社会历史性因素的视角把儿童推上历史舞台,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大批作家开始书写儿童,形成了两种创作倾向:一是提出儿童文学的概念,为儿童创作专属性的文学作品,像周作人、郭沫若、严既澄、周邦道、陈学佳、魏寿镛、周侯予、王志成等都就儿童文学的概念发表过意见①,部分小说家、诗人、艺术家、新闻记者、科学家等成为儿童文学写作的主体②,冰心、叶圣陶、凌天华等创作了专门的儿童文学作品,促成了儿童观的重构和现代转型;二是在作品中把儿童纳入叙事范围,关注儿童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触及儿童群体的成长与发展。
郭沫若作为新文学的呐喊者,也就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1921年1月他在《儿童文学之管见》提出,“有优美醇洁的个人才有优美醇洁的社会”,这可视为对梁启超“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思想的继承。他主张儿童文学的概念是,“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童话、童谣、戏曲),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由儿童的感官以直愬于其精神堂奥,准依儿童心理的创造性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③。虽然在他早期小说中并没有依此理念纯粹为儿童创作的作品,很少出现儿童叙述者和限定性儿童视角,但受生活环境与写作倾向的限定,儿童作为作者家庭成员的代表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成为新文学小说史上第二代异族“他者”的崭新形象。
二、写实主义与儿童关怀
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关系》中提出“理想派”与“写实派”的概念,此后现实主义以“写实派”的概念被引进中国,1911年“写实主义”作为词条被收入黄人编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使写实主义占据了五四新文学的主流地位④。新文学的先锋属性决定了“文学与社会的对抗性”,是“对旧社会体制的批判和抗争”⑤,儿童启蒙、儿童书写等也成为批判和抗争的工具。郭沫若在《我的童年》中有不少批判自己童年成长与学习经历的文字,特别是不满于某些泯灭儿童或人的天性的教育管理方式。当他自己做了父亲,又受了传统与现代、西洋与东洋文化的浸染,儿童的主体性地位和主体性发展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议题。郭沫若的这种儿童书写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和文化环境因素,也述说了以作家为代表的留洋知识分子儿童观念的现代性转变。
作者早期小说中的儿童大多天真、快乐、无忧无虑,极易得到满足。《圣者》⑥描述了几个期待父亲回家的儿童,看到父亲带回礼物的喜悦之情。这些小礼物(两角钱的花炮)使他们“比得了糖点时更要快乐”“高兴得出乎意外”。孩子们的拍掌欢笑声像“火花”一样“顿时焕发”起来,心机像“彗星”一样“不知一直飞到那处的星球去了”,欢笑声“满了一庭”,“纵有天国,恐怕孩子们也不愿意进去”。这些语言虽是成人视角的叙述,但也极力展示了孩子的快乐与满足。快乐是儿童的天性,天真的童心不受经济困顿与家庭离别的影响。《漂流三部曲》中父亲送孩子返回日本生活,正经受骨肉分离的苦楚,但孩子们到了船上就忘记离别的痛苦,变得“快乐极了”。《行路难》中大人们因生存危机忙着搬家,孩子们“自然自身”“小小的精神随着新鲜的世界盘旋”“消灭在大自然的温暖的怀抱里”。这种经由成人视角书写的儿童没有忧愁和贫富观念,自然快乐的生活理念甚至成为慰藉成人困苦的一种有效诊疗方式。
小说在书写童心时也写实地记录了他们贫困、漂泊的生活处境,这与郭沫若的经历息息相关。被父母包办娶亲的他成婚后马上离开家乡,后赴日留学。在日本期间爱上一位日本牧师的女儿,自由结合并生下孩子。这一结合不为双方家庭所接受,妻子安娜与日本家庭断绝联系,郭沫若的家庭只愿称她是妾,孩子则被称为庶子,这使他不愿再回四川老家,与旧家庭的关系疏离。社会转型、家庭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和生活境状,使郭沫若在家庭的教育功能、情感功能、组织功能等方面都承担重任,由纯粹的留学生变成家庭的担当者,生活费用基本全靠他一人支撑。随着孩子的到来,仅靠“一个月四十八块钱”的留学官费有些入不敷出,学费、买书、置仪器、吃饭、房租等都需要花费。为担起生活的重任,郭沫若在学习之余从事兼职活动,这在小说中也偶有提及,如方平甫在学校开运动会没课时,“早起来便往朝鲜人某君处教中国话去了——平时是晚上去的”。当孩子由一个变为两个、三个,留学官费也随着毕业失去时,他们的生活压力倍增,儿童的贫困生存处境也就更加明显。作者用“乞丐以下”形容孩子的生活水准(《圣者》),在上海五个月贫困、局限的生活环境中,孩子们一个个消瘦下去。面对孩子提出的“天天晚上都引我们”到公园去的“简单的要求”,主人公爱牟因无法实现心生悲哀,“几乎流出了眼泪”,不得不考虑把妻儿送回日本(《月蚀》)。即便如此,生活压力依然存在,“妻儿们的生活费还全无着落”,孩子们在日本也经受着因付不起房租被迫迁居的困境(《漂流三部曲》)。
“漂泊的儿童”在郭沫若的早期小说中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儿童居无定所,搬家的次数多;一是指儿童“没有故乡”,是无根的浮萍。《行路难》中爱牟曾统计孩子们“漂流过的次数”:
六岁的大儿……十九次。
四岁半的二儿……十次。
岁半的三儿……七次。
六年19次搬家,年均约3次,不得不说是极为频繁,作者悲愤地感叹“带着死神在漂泊”(《行路难》)。在租房的经历中,小说主人公因异族身份数次受挫,《行路难·上篇》房主人因他们是中国人,一定要找店保并提出很多苛刻条件;《行路难·中篇》房主发现爱牟身份后发出蔑称,表示宁愿空着放乒乓台也不愿出租,充斥着“轻视”和“极端的恶意”。长年旅日的生活经历使作者生成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的焦虑,并把“对身份危机感同身受的自我体认、自我认同融注于作品之中,演绎出身份转变的尴尬以及建构的艰难”①。他在小说中直言“日本人本来是看不起中国人的”(《行路难》),对中国人“尚能存几分敬意”的只有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和专门研究汉文的学者两种(《月蚀》)。《喀尔美萝姑娘》中“我”喜欢一个日本女孩却不敢和她谈话,只因“怕她晓得我是中国人”后,连现有的“一点情愫都要失掉”。这种异族歧视、民族屈辱使郭沫若在经济窘迫之余还饱受精神创伤和苦闷困扰,加速了民族意识、现代意识的觉醒,生存的漂泊感唤起他对儿童处境的心理认同机制,也对漂泊的儿童更多了一层体谅和担忧。
就儿童而言,作为异族第二代的他们也同样经历着身份认同的危机。儿童有着“双重他者”的身份处境,即相较于成人的“他者”和相较于异族儿童的“他者”。《未央》描写了三岁的大儿“一出门去便要受邻近的儿童们欺侮,骂他是‘中国佬’,要拿棍棒或投石块来打他”“柔弱的神经系统,已经深受了一种不可疗治的创痍”。儿子的“可怜”让爱牟“心痛”,也因为自己异族“他者”的处境更理解儿子的情绪,自愿“牺牲”没课的时间带孩子去海边或邻近的地方走走。边缘群体的寻根情结使爱牟会用“一种沉仰的声音”引导儿童,“大儿,你爹爹的故乡在海那边,远远的海那边,等你长大了之后,爹爹要带你回去呢”。“回去”是对故土的认同和依恋,是化解种族身份危机的策略和对寻根的具体勾勒,虽然“小儿若解若不解地,只是应诺”,但在孩子心中埋下了“故乡”的种子,加深了对家园故土的认知,在日后的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不同于父辈告别家园、融入新族群的痛苦,异族第二代的自我身份认同更为复杂艰难。
作者还关注孩子身份背后的根源问题。作为异族“他者”的第二代,儿童的身份比第一代更为尴尬。他们没有自己的家乡,“远远的海那边”是父辈的故乡,成长的地方又不被他者的族群所接受,即使母亲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他们还是被视为异类,受人欺侮。离开居住地没有亲友送行,只有白鸽“在向这些漂泊的儿童惜别”(《行路难》)。这种现象在回到父亲的国土后也没有好转,他们蜗居上海一隅,“言语也不通,朋友也没有”,还失去了自然的生活环境,“精神一天一天地只是枯寂下去”,让作者更觉可怜。上海租界的各处公园悬有牌示不许华人踏入,他们只能“穿件洋服去假充东洋人”,连“可怜的亡国奴”都算不上。儿童特别是中国儿童的生存遭遇,使作者在《月蚀》中以大段直抒胸臆的论述抒发了悲愤的情绪。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圣者》和《月蚀》中使用了“可怜的孩子们随着自己漂泊到这上海”“言语也不通”的表述,可见对孩子而言上海并不是他们的家乡,父亲的故乡也已早被父辈解构,表现出与母国、原文化的疏离;“假充东洋人”又说明作者并不认为他们是东洋人,在日本的异族身份也呈现出与异国、现文化的疏离。这种矛盾的真实处境决定了这类儿童“漂泊”和“他者”的尴尬身份,所以作者感叹道,“中国人的父亲,日本人的母亲,生来便是没有故乡的流氓!”(《行路难》)这种“没有故乡的流氓”受着他族的欺侮,承受了儿童本不该承担的困苦。
三、浪漫主义、儿童崇拜与弑子意识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既有“诗言志”的传统,也有“诗言情”的抒发。郭沫若认为自己尊重个性、景仰自由”①,受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交叉影响的他主张“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感情终于感情”②,因此他的创作带有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注重自我的表现,反映在小说中则多为家庭生活叙事的身边小说。
1922年4月泰东图书局出版郭沫若翻译的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他在序中列举自己与歌德“所有共鸣的种种思想”,其中之一便是对于小儿的尊崇。“小儿如何有可以尊崇之处?我们请随便就一个小朋友来观察吧,你看他终日之间无时无刻不是在倾倒全我以从事于创造、表现、享乐。小儿的行径正是天才生活的缩型,正是全我生活的规范!”③出于对儿童的崇拜及家庭内部长幼关系的平等化和父子伦理叙事的变迁,他的儿童教育观呈现出民主化和科学化倾向,反映在早期小说中则表现为对儿童行为的赞美,并将个别不正确的言行归结为教养者和社会的责任。他歌颂儿童,认为自己是“在茧中牢束着的蚕蛹”“心里很羡慕他们的自由”(《漂流三部曲》),更用“伟大”一词形容儿童的善良心性(《圣者》)。
但儿童“双重他者”的身份使他们一方面接收了父亲的宠爱,呈现出亲子依恋关系,另一方面也承担了父亲的想象与责罚,表现出亲子疏离,被视作父亲的累赘。这种亲密又紧张的复杂亲子关系,使郭沫若早期小说的“成人—儿童”权力关系呈动态变化,并多次出现弑子意识:
——“他——就在那一年,被他的父——父亲——杀死了!”(《牧羊哀话》,1919年)
——“不好了!不好了!爱牟!爱牟!你还在这儿逗留!你的夫人把你两个孩儿杀了!”
……我看见门下倒睡着我的大儿,身上没有衣裳,全胸都是鲜血……我又回头看见门前井边,倒睡着我第二的一个小儿,身上也没有衣裳,全胸部也都是血液,只是四肢还微微有些蠕动……我抱着两个死儿,在月光之下,四处窜走。(《残春》1922年)
——实在不能活的时候,我们把三个儿子杀死,然后紧紧抱着跳进博多湾里去吧!
我们把可怜的儿子先杀死!/紧紧地拥抱着一跳,/把弥天的悲痛同消。(《漂流三部曲》1924年)
从1919年到1924年间的小说数次出现惊人的“弑子意识”,孩子被最亲近的人——父亲或母亲杀害,或误杀或故意,或被动或主动。“杀子”与“弑父”是古希腊神话的一对原始母题,美狄亚杀子惩夫、俄狄浦斯的父亲为了逃避命运残害婴童和儿子意外弑父等,都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源泉。《残春》的弑子意识出现在爱牟的梦中,妻子以决绝的姿态抗议爱情的不贞,从伦理角度反映女性现代意识的觉醒和对夫权的极端反抗。主人公爱牟在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矛盾中惊醒,在弑子惩夫的意象中结束了对精神自由的渴求。《漂流三部曲》的父亲把儿童视为生活枷锁,幻想与之同归于尽。这是作者在异族霸权与社会压制下重构自我主体的内心呼喊,也是对社会压迫与不公处境的悲剧性反抗。在这里儿童不仅仅是家庭的下一代和民族的未来,更是身份认同危机下父母压力的发泄对象和复仇工具,是作者情绪的具象化表达。这种歇斯底里的情绪还体现在对儿童的语言暴力上,《行路难》有着详细的描述:
——“哭!哭甚么哟!哭死了也没人把饽馅给你!”
——“饽馅!饽馅!就是你们这些小东西要吃甚么饽馅了!你们使我在上海受死了气,又来日本受气!我没有你们,不是东倒西歪随处都可以过活的吗?我便饿死冻死也不会跑到日本来!啊啊!你们这些脚镣手铐!你们这些脚镣手铐哟!你们足足把我锁死了!你们这些肉弹子,肉弹子哟!你们一个个打破我青年时代的好梦。你们都是吃人的小魔王,卖人肉的小屠户,你们赤裸裸地把我暴露在血惨惨的现实里,你们割我的肉去卖钱,吸我的血去卖钱,都是为着你们要吃饽馅,饽馅,饽馅!啊,我简直是你们的肉馒头呀!”
作者使用“脚镣手铐”“吃人的小魔王”“卖人肉的小屠户”等形容孩子,指责他们割人肉吸人血,制约了父亲青年时代的理想与追求。这段“恶狠狠”的痛骂充分发泄了父亲的不满,“锁”字贴切地形容了父亲被束缚的心境和对自由的渴望。但这种浓烈的情绪爆发不是突发的,而是十几年来“前前后后在日本所受的闷气,都集中了起来”,表面上作者痛骂的是孩子,更深层的是宣泄自己在异域所受的民族屈辱、经济困窘、情感压抑和自由束缚的苦闷,是对现代知识青年生存处境和精神压迫的愤懑。作者身为知识分子先驱留学日本,但这些弱国子民的留学生们“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①。发泄后作者又“从极端的憎恨一跃而为极端的爱怜”,“弑子”与“爱子”也就矛盾地集于一体。这种异域生存体验“掺杂着现代知识子的民族觉醒与爱国个性”,有着民族意识、个性意识和现代意识的萌发和滋长②,也使作者无法从现实困境和社会现状中挣脱,情绪发酵后在家庭内部爆发。需要正视的是,这种爆发与国家、民族、种族等社会历史现状有着某种内部牵连,是写实与浪漫的矛盾交叉。
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思潮交织在郭沫若的早期小说创作中,情绪写实成为小说的重要部分。特殊的留学经历和家庭背景使作者更具现代性视野,也更深地体会了经济、种族与身份认同的危机,儿童关怀、儿童崇拜与弑子意识也就矛盾地并存于他早期的小说创作中,成为现代小说一种独特的儿童书写现象。
(责任编辑:陈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