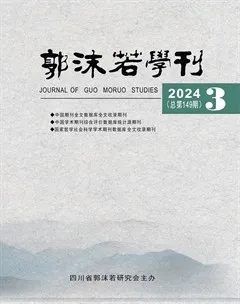主持人语
青年郭沫若在四川求学成长的岁月,正值中学与西学砥砺、旧学与新学斗妍的时代,知识的激增已远超经史子集之范畴,其中不乏别开生面、石破天惊的论断,这些见解乃数千年来所未有,即便是饱学之士、资深儒者也未曾涉猎。郭沫若在为廖平今文经学所吸引崇拜的同时,又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和探索的强烈欲望。在近代蜀学的滋养下,他对儒释道三教和合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领悟,兴机触发便可“醉眼欲穷天下势,揽衣直上最高台”,高台之上更有“大叫狂生郭八来,但听山壑呼长诺”壮志豪情,然而现实毕竟“烽火满目,荆棘丛生,时局沧桑,一日千变”,日渐式微的儒家理想在“黑铁主义”“武力强权”之下难以维持,但青年郭沫若在对新理论新思想新主义充满渴望的同时,仍希望“同胞齐努力,愿汉家四百兆数之文明上族,演出这般事业来!”这便是有为青年在面对民族国家危机时矛盾迷茫而又奋发踔厉的精神姿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来郭沫若赴日留学、弃医从文、投笔从戎、归国抗战等重大人生选择的背后,都可以看到他青年时代精神追求的缩影。新文学家郭沫若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与同情,但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旨归却意在建设和发展新文化。正是源于此种长久的思考与探索,郭沫若于1925年写出了《马克思进文庙》这一戏谑游戏的历史小说,让马克思和孔子这两位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名人跨越遥远的时空距离,在小说中相谈甚欢,引为知己。郭沫若这种穿越戏谑的方式显然不够严肃,被认为“暴露出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a5M3qBXmL1SpgoKMb5J61w==肤浅和含混”,且在宿儒经师和古今儒家眼中也是对圣人的亵渎。赵雨晴同学《戏谑外表下的严肃思考与现实选择——浅析〈马克思进文庙〉》一文,不仅看到了郭沫若游戏之作背后对中西古今之学对话交流的严肃思考,尝试在现代儒学发展的脉络中,呈现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践上的积极探索,也注意回到历史现场,揭示郭沫若在国民革命过程中对国共合作背后潜在话语矛盾的洞悉,以及希望通过“马克思进文庙”的方式进行调和,夯实国民大革命理论合法性基础的努力。同样是在1925年,面对不断喧嚣的“祖传”“老例”“国粹”,鲁迅再一次提出要发动“思想革命”,在搁笔一年后重启《彷徨》的写作,撰写了第五篇《长明灯》及以后余下诸篇。宋骁航同学《“长明灯”:“思想革命”重启中鲁迅对传统的新批判》认为,“长明灯实为鲁迅对1920年代中期兴起的国粹复古思潮的具象描摹”,是鲁迅在这一时期对于传统文化问题的更深入的思考和批判,并进一步呈现鲁迅的传统观,既在内容组成上有“横向”的“完全拒绝”与“某些成分有意义”之分,更有着在精神上“纵向”的“真义”与“僵化”之别。鲁迅、郭沫若等新文学名家对民族文化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的态度无疑具有示范作用。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以沙鸥为代表的青年诗人聚集在一起成立“春草社”,展开“诗歌大众化”试验,在巴蜀之地掀起了一股以方言作诗的风潮,以期进行更为广泛的群众动员和文化传承。郑娟博士《“把诗还给人民”——论沙鸥〈农村的歌〉〈化雪夜〉的农村书写与方言尝试》一文,从刊行和传播的角度考据沙鸥与“春草社”内在关联的同时,以具体诗歌文本校读,展现了沙鸥方言诗歌从《农村的歌》单薄、刻板的农村印象式书写到《化雪夜》不断臻于成熟的创作过程,以地方路径为研究方法重新定位沙鸥在四十年代川渝地区的文化位置。本期“青年论坛”三篇论文并非单纯的“郭沫若研究”,在文献的使用、文本的细读和历史语境的还原等方面尚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然而,诸位青年学者秉承了“郭学长”严谨的学术风范,尤其是在对待现有研究成果的态度上,展现了他们对当前学术动态的深刻理解,以及勇于开展大胆学术对话的气度。这种积极的学术态度,无疑是值得赞赏和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