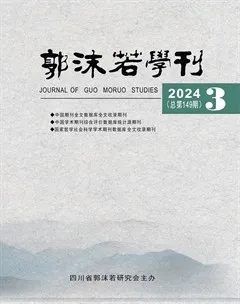“长明灯”:“思想革命”重启中鲁迅对传统的新批判
摘 要:鲁迅在小说《长明灯》从“吹灯”到“放火”的既往解读思路下,长明灯的文学意象内涵常被笼统化、模糊化处理,事实上,对这一意象的分析当结合小说对长明灯的细节描述与特定时空的历史语境。长明灯实为鲁迅对1920年代中期兴起的国粹复古思潮的具象描摹。在这一描摹中,鲁迅借助吉光屯中人与反抗的“他”双重视角,对长明灯的神圣性进行了解构,指出了所谓国粹者事实上的僵化与沦亡。相较晚清留日与投身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在1920年代中期重启“思想革命”下对于传统的批判,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剖析。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当下,鲁迅在重启“思想革命”中的批判性思想尤为值得我们重视,并从中汲取具有启示意义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长明灯》;“思想革命”;鲁迅;传统批判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25(2024)03-0043-08
在鲁迅小说中,《长明灯》与《狂人日记》常因其相似的“狂人”抑或“疯子”形象往往被并置讨论①。实际上,在相似的“狂人”意象外,更值得注意的或许还有其分别在所属小说集文本序列中“位置”的相似。《狂人日记》居于《呐喊》首篇,鲁迅“听将令”而投入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故事人尽皆知,《狂人日记》也成为鲁迅介入新文化运动的第一声号角,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鲁迅由此“诞生”。而《长明灯》在《彷徨》小说集中的“节点”意义却往往被忽视。考察《彷徨》的文本序列,可以清晰地看到鲁迅在小说写作时间上的一次“断裂”,自1924年2月至4月相继撰写《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四篇小说后,鲁迅即搁笔近一年时间,至1925年2月底,鲁迅突然重启小说写作,撰写了《彷徨》的第五篇《长明灯》,而后至年末相继写出《彷徨》余下诸篇。这就不得不引我们深思:在鲁迅的文学与思想世界中,“狂人”抑或“疯子”在文本序列中相似的位置重复出现,是否具有着某种“起点”抑或“檄文”的意味?站在1925年初这一历史关口的鲁迅,如近年有研究者指出,正是准备重启“思想革命”的关键时期②。那么,《长明灯》的写作是否同鲁迅正在酝酿并再起的新的“思想革命”有所关联?又是否在这一进程中升华了思想批判?又升华了哪些批判?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话题。
进行新的讨论,不妨寻找的新的切口。在《长明灯》中,“灯”的意象既常被研究者提及,又往往在讨论中被模糊化处理,更多研究将关注点集中在小说中的“疯子”及其行动上,正如段从学对《长明灯》研究所概括的那样——“既有研究把从‘吹灯’到‘放火’当做核心的思路。”①那么,在这一思路外,《长明灯》的文本又是否有其他阐释空间?此外,关于小说诞生的历史语境,已有相关研究有所涉及,如刘彬将《长明灯》同溥仪出宫与孙中山的北上与去世相联系,但其对于“长明灯”这一中心意象的所指,经过梳理后则认为:“关于长明灯所象征的究竟是礼教文化、封建秩序还是佛教文化、迷信思想,研究者众说不一。本文认为,小说真正关心的并非长明灯的具体象征,而在民众对于灭灯的反应,因此将长明灯的象征意义笼统地以旧文化旧秩序合而论之。”②也有研究者别具心裁,将“长明灯”指涉为“民俗文化的象征符号”,借以指出鲁迅《呐喊》《彷徨》系列小说批判指向的反“庸俗”而非反“礼教”③。
值得深思的是,在《彷徨》十一篇小说中,《长明灯》可以说是唯一一篇“超现实”之作,“长明灯”也是在鲁迅文学世界中仅出现过一次的意象,这样一篇文本序列间断处再起的“起点”之作,风格“超现实”的独特文本,又何以创造一个全新的意象来重弹《呐喊》中已有的“老调”?在“长明灯”意象的背后,又是否带有鲁迅在具体时空中独特的批判指向与关怀?将既往研究大多对“庸众”与“疯子”形象的关注,对从“吹灯”到“放火”的思考,挪向新造的意象“长明灯”,又能否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打开新的阐释空间?本文的阐述即由此展开。
一、“灯”的隐喻:
“长明灯”意象所指细探
面对在文学史中经过层层阐释的鲁迅小说,已经形成的诸多阐释模式或许会限制我们对具体问题的思考。就《长明灯》而言,如果将长明灯的意象笼统概括为鲁迅小说中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旧文化旧秩序”的阐释,或许无法充分释放这一新造意象在特定历史时空中诞生所蕴含的信息,对长明灯意象的探寻,首先还是需要回到文本本身。如果按段落间的自然分割与情节发生的空间进行划分,可以将小说分为“四幕”,关于长明灯的细节描述主要出现在“第一幕”灰五婶的茶馆中。在茶馆中人的讨论里,小说透露了长明灯的若干细节特征。
首先,小说发生的故事世界“吉光屯”的得名与长明灯密切相关。当听闻疯子“他”意图吹灯,胖脸的庄七光嚷道:“吹熄了灯,我们吉光屯还成什么吉光屯。”④对于吉光屯这一小说发生的地点,鲁迅在后文中借助“感到这紧张的人们之口”,透露了吉光屯这一空间背后的隐喻——“他们自然也隐约知道毁灭的不过是吉光屯,但也觉得吉光屯似乎就是天下。”⑤天下,这一宏大的所指指向了吉光屯在地理上的隐喻,就是脚下这片自古以“普天之下”自命的土地,而吉光屯因长明灯而得名,不仅标示出长明灯与吉光屯之为吉光屯密不可分,更是向我们显示了长明灯所具有的“崇高”意义。
此外,小说中还谈到自南朝时梁武帝点起长明灯后,长明灯从未熄灭,即使“长毛造反时也未熄过”,而吉光屯以外的“外路人”经过这里“都称赞……。啧,多么好……”。至于熄灭长明灯的后果,保卫长明灯的村人与意图熄灭长明灯的“他”的反应针锋相对,无论是“他”口中的“不会再有蝗虫与病痛”还是灰五婶嘴里的“这里就要变成海,我们就都要变成泥鳅”,长明灯毁灭的后果都反常地远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凭依的经验,被无限地夸大。
从以上细节梳理出发,我们还可以再审视常常被拿来一起讨论的《长明灯》与《狂人日记》两篇小说的区别,罗华从知识分子“从中心到边缘”,小说写作“精神层面形而上的思辨到世俗生活图景”,先驱者“从放弃到坚守”三个方面探讨了两篇小说的差异之处⑥。在此之外,比起《狂人日记》中狂人同整个外部世界的对立,《长明灯》中的隐喻显然更加具象化,有更多可以细加考索的空间。而对比两部小说中人物关系的图示则可以发现,相较《狂人日记》中狂人同其他人的二元对立,《长明灯》所呈现的人物关系图景则颇为具象化:疯子“他”,阔亭、庄七光等青年,四爷、老娃等占据较高社会地位的乡绅,屯中信息交流“中枢”茶馆的主人灰五婶,还有更广大的在小说中“无名”的“蛰居人”,不同群体对于长明灯的认知则有着一定的差距。比如“年高德劭的郭老娃”对于“他”的吹灯之举,给出的见解便是“社神不安,之故”①,可见长明灯还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折射屯中各类人群心理的作用。
从长明灯的由来、特征诸角度观之,可以说长明灯这一意象应当是有着较为清晰的指向性。如果我们打通鲁迅这一时期小说与其他文体之间的界限并置观之,可以发现在小说写作的1925年初前后,鲁迅的批判思想集中指向了社会上泛起的“国粹”与复古思潮。长明灯的特征与鲁迅对这一时期“国粹”“保古”的批判中,可以找到颇为清晰的对应。在1925年4月18日的《忽然想到(六)》中,鲁迅批判了中国复古借助外国人说辞的行为:“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这虽然可恶,却还不奇,因为他们究竟是外人。而中国竟也有自己还不够,并且要率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者,则真不知是生着怎样的心肝。”②在小说中鲁迅暗示了吉光屯就是“天下”,在茶馆里的庄七光们对“吹灯”予以挞伐的理由之一正是这“天下”以外的“外路人”有着对长明灯啧啧称奇的心理。而“一直传下来,没有熄过的长明灯”,自然是指鼓吹国粹者所称道的“自古以来”“古已有之”。
考察鲁迅这一时期的活动可以发现,著名的《京报副刊》“青年必读书”论争与《长明灯》的写作几乎同时发生,而回顾“青年必读书”事件中的论战双方的发声,则可以发现攻击鲁迅者的逻辑同小说中吉光屯中人有着颇为相似之处。在《长明灯》写就几天后,鲁迅作《聊答“……”》一文,对“青年必读书”事件中对他进行批评的柯伯森加以回击。柯伯森是“青年必读书”论争中对鲁迅发起批判的第二人。鲁迅将柯伯森文中未打出的“......”确定为柯伯森对他“卖国”的攻击。对于柯伯森的批判,鲁迅犀利地回应并说道:“这些声音,可以吓洋车夫,但是无力保存国粹的,或者倒反更丢国粹的脸。”③反对者对鲁迅“不读中国书”的指控,与《长明灯》中群氓笃信长明灯熄灭会带来灾害的信条而对“他”发起攻击的心理与行为逻辑颇为相似:“不读中国书”仅是鲁迅个人在近百条“青年必读书”答卷中个体发声的一家之言,正如李怡所说:“从逻辑上讲,他的第一对话对象应该是这场征求活动本身。其考虑的主要内容也应该是媒体如何参与这样的公众教育问题——可能性?合理性?”④在公共媒体的征文中对文化问题自由发声何以上升至民族国家层面的“卖国”?而“疯子”吹灯在我们日常经验中亦是再普通不过的行为。但无论是以柯伯森为代表的攻击者还是吉光屯中笃信长明灯神威的屯中人,都将其上升为威胁国家民族/吉光屯的“洪水猛兽”,也正如鲁迅所认为的,这种言论“无力保存国粹”实则“反更丢国粹的脸”。
至于在小说中提到的威胁长明灯的“长毛造反”,也许亦非闲笔。“长毛”在鲁迅的生活史和精神史中有着深刻的印记。在鲁迅小说与散文中,“长毛”的故事反复出现。太平天国运动中对经典的批判毁坏,在意识形态上批儒崇耶的历史史实鲁迅想必并不陌生。对鲁迅的家族史而言,太平天国同样扮演了发挥巨大破坏力的角色,丁文在研究鲁迅家族史时征引周作人的回忆并指出“鲁迅的故家”里大半家族藏书“毁于太平天国之战”⑤。有如此关于太平天国历史记忆的鲁迅,在小说中提及“长毛”并将其塑造为象征国粹与传统的长明灯在历史上所受到的威胁,亦颇为顺理成章。
在《长明灯》前后的几篇小说中,姑且不论文体上近似于速写的《示众》,《肥皂》里四铭恭读“恭拟全国人民合词吁请贵大总统特颁明令专重圣经崇祀孟母以挽颓风而存国粹文”与《高老夫子》中高尔础在《大中日报》上发表《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国粹义务论》的情节段落都显示出这一时期国粹复古运动的兴盛。通过“鲁迅博物馆资料查询在线系统”进行词频统计,“国粹”“传统”“国民性”等一般被视为鲁迅笔下文化批判的关键词汇出现的最高频率年份并不是我们一般所认为的“反传统”最甚的“新文化运动”前后,而是恰恰都出现在《彷徨》与《野草》时期的1925年①。在小说中“他”再扑再起,准备“吹灯”之时,鲁迅不无深意地提到在小说所发生的故事之前“他”还有因为被蒙骗而失败的第一次“吹灯”经历,相较于上次,再一次发动“吹灯”的“他”显然有着全新的准备与思考。比起“听将令”的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在这一次“思想革命”中,鲁迅倾注了并不亚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主体性,《彷徨》《野草》中的大半篇目,以及《华盖集》等一系列文化批判名文亦诞生于此年。明乎此,相较于将长明灯的意象笼统纳入《呐喊》《彷徨》所批判的共性命题,不如以长明灯为基点,在细读梳理文本细节的基础上,将其同1925年前后鲁迅的著述加以对应,将鲁迅的各种文体写作看做一个整体,感知鲁迅这一时段时空中的关怀与批判。
二、瓦解神圣:
《长明灯》对“长明灯”的解构
如果对长明灯的分析仅将其文本细节与历史语境相呼应,在此基础上指出其批判意识,未免还是窄化了这一小说中心意象所内蕴的批判能量。关于长明灯的意象,文本中还有更多细节值得进一步深究。
在《长明灯》中,“灰五婶”这一人物在小说世界中的位置颇为特殊。让我们回到小说开篇作者所勾勒出的吉光屯人际格局:不大出行,出门要看黄历的最广大的“蛰居人”,茶馆里“在蛰居人意中却以为个个都是败家子”“以豁达自居的青年人”方头、阔亭,以及后来叙述的掌握权力的老一辈“四爷”“郭老娃”。在这一幅社会关系图景中,茶馆的“主人兼工人”灰五婶似乎在人群中无处安放。相较于“蛰居人”,灰五婶所开的茶馆是“青年人”不拘谈天的地方,灰五婶自然有别于“蛰居人”。与蛰居人“耳朵里心里全没有‘放火’”不同,灰五婶“专注”于灭灯的话题。另一方面,灰五婶见多识广,知道长明灯一灭“这里就要变海,我们就都要变泥鳅”②,知道“他”发疯的全部历史,知道“他”的祖父“捏过印靶子”(这些都是青年人所不知晓的),而她的“死鬼”丈夫则主导了第一次欺骗“他”灭灯的行动。可见灰五婶在小说世界里占据着颇不寻常的社会位置,然而这一人物在现有关于《长明灯》的研究中则较少被讨论到。正是这样一个对“长明灯”与“疯子”极为熟悉的角色,鲁迅借她之口奇怪地说出一段关于长明灯饶有趣味的描述:“那灯不是梁五弟点起来的么?不是说,那灯一灭,这里就要变海,我们就要变泥鳅么?你们快去和四爷商量商量罢,要不......”③
小说前已述及长明灯是由六朝时梁武帝点起的“起源”故事,而熟知长明灯与狂人历史,在屯里占据特殊社会位置,丈夫参与第一次“灭灯”行动的灰五婶却说那灯是“梁五弟”点起来的。“五弟”与“武帝”同音,出于小说人物之口,在小说的世界中当然可以“以假乱真”,但形诸文字却全然不同,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在此突如其来地介入描画了灰五婶的内心,并将其展示给读者,形成了文本中颇为吊诡的一个“结”。
既然“梁五弟”是鲁迅之于灰五婶的“画心”之举,那么作为叙述者的鲁迅对灰五婶心灵世界介入的背后又渗透着怎样的企图?如果“贴近”文本细节进行阐释,深谙长明灯熄灭后果与“他”个人及家族史的灰五婶,显然并非鲁迅一再在小说中提到的不发声的庸众“蛰居人”,而是吉光屯社会里舆论“枢纽”茶馆的掌事者,这样一位吉光屯里见多识广,对吹灯事件“专注于本题”(鲁迅形容灰五婶之语)的人物,对于长明灯的来源和历史却并不真正了解,或者自以为了解而实则愚昧。鲁迅通过深入灰五婶的内心,对小说人物及读者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积极保卫长明灯者,对异端分子“喊打喊杀”者,其实并不真正关注“长明灯”本身。
而另一种可能的阐释方向或许显得更为大胆,那就是灰五婶心中的“五弟”或许是真的是吉光屯里的同辈“五弟”,而长明灯被灰五婶的“死鬼”丈夫用棉被团团围住的举动,或许真的熄灭了长明灯而后又由“五弟”再度点起。此说或许很难得到实证,但其同灰五婶昧于长明灯真正的历史共同导向了同一个阐释方向,那就是小说对长明灯这一中心意象神圣性的解构,换言之,保卫长明灯者所专注的并非是长明灯本身的真义,而不过是在保卫他们心中早已僵死的、流传在世间的、超出日常经验的流言。
在小说的第二个场景——庙门前的对峙中,阔亭在劝说“他”的言语交锋中又一次提到了长明灯:
“你一向是懂事的,这一回可是太糊涂了。让我来开导你罢,你也许能够明白。就是吹熄了灯,那些东西不是还在么?不要这么傻头傻脑了,还是回去!睡觉去!”
“我知道的,熄了也还在。”他忽又现出阴鸷的笑容,但是立即收敛了,沉实地说道,“然而我只能姑且这么办,我先来这么办,容易些。我就要吹熄他,自己熄!”他说着,一面就转过身去竭力地推庙门。①
从小说中“他”这一狂人(疯子)形象出发观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举动同鲁迅这一时期的思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事实上也正是一个月后的1925年4月,在致赵其文的书信中,鲁迅第一次阐释了自己“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不过从一般论者多集中关注“狂人”的阐释方向转向“灯”,会发现鲁迅在又一次解构长明灯的神圣性:无论是保卫长明灯的阔亭还是意图吹灭长明灯的“他”,都认识到无论熄灭长明灯与否“那些东西不是也还在”。
对于这一“解构”的意义,如果把小说“外典”迦尔洵的《红花》纳入对比或许可以看出《长明灯》的独特所在。周作人在《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中第一次谈到《长明灯》与《红花》之间的联系:“狂人把什么东西看作象征,是一切善或恶的根源,用尽心思想去得到或毁灭它,是常有的事,俄国迦尔洵(1855-1888年)有一篇小说《红花》,便是写一个狂人相信病院里的一朵红花是世界上罪恶之源,乘夜力疾潜出摘取,力竭而死,手里捏这花,脸上露出满足的微笑。”②迦尔洵与鲁迅的关联可以追溯至二周留日时期共同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二周在“阅读史”上有着相当大重合的历史事实已为不少研究者所论述③,周作人事后的联想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接近鲁迅在创作小说时进行思考所征用的思想资源。而把“病人”对“红花”与“他”对“长明灯”的认知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鲁迅对这一故事情节的改造与思考。在迦尔洵的《红花》中,小说主人公“病人”毫不怀疑地笃信这朵鲜艳的罂粟花象征了“世界上一切恶”,而当“病人”奋力摘花,力竭而死之时,“他的面容很安详,而且带着喜色”,流露出“自豪的幸福”④。在“病人”眼中,红花就是象征着世界的一切恶,直至“病人”力竭而死,红花所附着的意义也没有与其本体相分离,而《长明灯》中的“他”则相当清晰地认识到长明灯的明灭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威力,在亲身搏斗中,反抗的“他”不仅瓦解了自己的反抗,更以身瓦解了长明灯的崇高。比起迦尔洵,在审视所反抗之物时,鲁迅多了进一步思索。
因此,无论是专注于灭灯事件却昧于长明灯本身的灰五婶,保卫长明灯却亵渎其神圣的阔亭,还是对长明灯本身有着深刻洞察,反抗绝望的“他”,与长明灯密切相关的小说人物的言谈举止均将长明灯神圣的意义指向了无情的解构,神圣传统所携带的意义在反抗者与保卫者眼中都已沦为空虚僵化的符号。在《彷徨》系列文本中,题目常蕴含着丰富的文本信息,并往往暗示着颇为强烈的反讽倾向:《祝福》没有“祝福”最该得到祝福的祥林嫂,《幸福的家庭》中的“幸福”存在于虚构的幻象,《示众》全文始终没有出现被示众者的正脸,《离婚》的主线却是爱姑为了维护婚姻。经过对《长明灯》中有关长明灯描写的细读与分析,我们可以说,标示着吉光屯这一“天下”名号来源的“长明灯”实际上并不神圣。表面烛火幽幽,大放光明的长明灯,实则在人心中早已并不“长明”,坠入幽暗。
三、新的批判:
重启“思想革命”中传统批判的深化
1925年3月12日,鲁迅在致徐旭生的通讯中再一次提出要发动“思想革命”。面对其时“反改革的空气”,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鲁迅说:“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①与再起“思想革命”偕行的,还有十天前在《长明灯》中“狂人”形象的重启。那么我们不禁思考,再起的“思想革命”难道真的只是如鲁迅所说“还是这一句话”又一次的“老调重弹”?虽然因为同狂飙社决裂的缘故,鲁迅日后谈到自己此时“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②,但纵观1925年前后鲁迅的言说,其意图发动“思想革命”的主张已为学界所广泛关注,我们不禁思考,在这一次发动的“思想革命”中鲁迅的批判性思想有何新变。已有研究者指出这一次“思想革命”在遭遇“国民革命”的进程中,其“阵地”“战友”“战法”“方式”“批判对象”等方面的新变③。在此之外,从《长明灯》中关于传统的解构与认知出发,则可以看到鲁迅在这一时期对于传统问题更深入的思考和批判。
可以说,鲁迅绝非是一个笃信新旧二元对立的激进反传统主义者。在鲁迅的思想世界中,对中国固有文化进行批判并非其思考的出发基点。追溯鲁迅对传统问题批判的脉络,早在留日时期的文言论文《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开篇即言道:“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挖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④鲁迅的文化理想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第二维新之声”,新派“近世人士”与“抱守残阙”的旧派同时出现在鲁迅的批判视野当中。然而,无论是《新生》的“夭折”还是《域外小说集》出版的惨淡,无疑都证明了鲁迅这一超前的文化理想在晚清文化与文学的场域中难以实现。
及至民元革命,“新文化运动”勃兴,鲁迅因“听将令”而投身“文学革命”,同新文化阵营同人一道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名为“随感录”的短文。“随感录”可以作为“新青年”时期鲁迅传统批判的代表性文字。在日后整理并以《热风》集结出版时,鲁迅即指出当时的文字“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⑤。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鲁迅对于“国粹”的批判往往通过正面分析其功用的角度进行直接批判。比如在《随感录(三十五)》中针对“保存国粹”,鲁迅即说道“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得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对于国粹之好坏判断,必须与当下的社会情形相连,在文末,鲁迅即总结道:“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⑥类似的思考方式还在其他“随感录”中充分体现,比如“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心费力,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⑦;“那时候,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⑧。围绕着“保存我们”“协同生长”的目的,鲁迅针对“国粹”的“肿毒”展开从功用出发的正面批判,当然,这一批判亦是内在于《新青年》之群言论的“同一战线”当中。
那么,鲁迅1925年致信徐旭生所言的“思想革命”比起从晚清到五四进程中鲁迅的传统批判又有何新变?这一新变又彰显着鲁迅的认识在何种层面上有所深化?在写作《长明灯》二十天前,鲁迅撰写了《看镜有感》一文并发表在《语丝》周刊第16期。引发鲁迅关于“国粹”问题议论的“古铜镜”与“长明灯”同属于古之器物,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较为系统地梳理了自己的“传统观”与“国粹观”。虽然很难有直接证据表明从“镜”到“灯”的意象与二文写作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但将其并置审视,却可以发现在对所谓“国粹”的传统观批判上,二者有着相近的思考脉络与思想演进。如鲁迅所言,《看镜有感》的写作缘起于“因为翻衣箱,翻出几面古铜镜子来”的联想,由这面“汉代的镜子”,鲁迅遥想起“汉人的闳放”,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到了宋代由于国势衰弱而“国粹气味就熏人”①。因为宋代国力的孱弱,“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鲁迅还以“宋镜”与“汉镜”的对比指出:“所以事实上‘今不如古’者,正因为有许多唠叨着‘今不如古’的诸位先生们之故。”可以发现,从鲁迅重启“思想革命”前后发表的文字来看,鲁迅对于国粹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不仅将其放置在整个中国历史朝代兴替的脉络中辩证看待,更是从“功用”“危害”的角度上深入,点出了保卫国粹者内在衰颓的心理,在批判的力度上向纵深处更向前进了一步。
同《看镜有感》相似,在《长明灯》中,鲁迅从语言、外貌、行为等方面刻画了吉光屯里一大批“孱奴”,其惶恐于长明灯将要熄灭所带来的巨大“危险”,躲在笃信长明灯熄灭带来危害的“超现实”流言中,而这正是鲁迅在《看镜有感》中所批判的国人们“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的心理。此外,相较于《看镜有感》中鲁迅揭示“今不如古”是因为“有许多唠叨着今不如古的先生”之故,在《长明灯》中鲁迅进一步指出,认为“今不如古”的先生们实际上唠叨的也不过是心中的“教条”与“流言”,看似关注长明灯的灰五婶昧于长明灯真正的历史,保卫长明灯的阔亭,并不敬畏于长明灯的神圣,而也会劝服“他”说道“就是吹熄了灯,那些东西不是还在么”。从《看镜有感》到《长明灯》,在新一次“思想革命”中,鲁迅以更为深入、锐利的文字,揭示了复古问题来由的历史与心理基础,解构了保卫国粹者们实则保卫的是因心理与国势衰颓而萌发的教条与流言。而真正的传统,无论是汉唐时代雄大的魄力,还是相较于“梁五弟”真正点起长明灯的“梁武帝”,都已经随风而逝,隐没于历史之中。
这一时期鲁迅传统观批判的深化,还体现在《忽然想到》系列杂文中,在《忽然想到(四)》中,鲁迅开篇即说道:“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②“相斫书”语出裴松之注《三国志》,鲁迅所谓先前听到,应当指梁启超在其《新史学》中所言:“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③。梁启超将二十四史比作“相斫书”,称过去的史学为“帝王将相的家谱”,是为了推出他所建构的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史学革命”。在鲁迅的小说中,《狂人日记》“吃人”的意象,对“古久先生的流水铺子”的批判,可以说同梁启超对于中国历史书写模式的批判有着相近的关怀。而到了1925年,鲁迅却说以前“便以为诚然”的如今却“何尝如此”,可见鲁迅在此问题上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对于拥护国粹论者的批判,也超越了直面其危害与新旧对立的思路,从表面的文化对立深入到了文化内在的僵化与更深层次的人性思考。在这篇短文中,鲁迅批判了“自诩古文明者流”“诬告新文明者流”与“假冒新文明者流”,并将他们共同概括为“伶俐人”。所谓新文明古文明,不过是他们一时利用的工具,因此“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久存在”。对“伶俐人”的人性批判取代了单纯的文化新旧对立。
在1925年4月18日《忽然想到(六)》中,鲁迅长叹道“长城久成废物,弱水似乎也不过是理想上的东西。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朽到毫无精力了,还要自相残杀”④。比起新文化运动时期直接正面的功用批判,鲁迅显然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传统的僵化及其内在真义的沦丧是更为严重的问题。从《看镜有感》到《长明灯》,再到《忽然想到》系列共同构成了1925年初鲁迅心中关于重启“思想革命”中传统批判思想的一个“文本群”,昭示了这一时期鲁迅关于传统问题批判性思想的深化。
四、结语
通过对《长明灯》与鲁迅1925年重启“思想革命”前后的言说进行分析研读,可以发现鲁迅的批判性思想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进程,其中的时代语境与思想变化,值得我们细加发掘。同时,由这一发现出发,也可以让我们重审鲁迅与传统的关系。
由鲁迅此时的小说以及其他文体文本的写作出发,更值得我们在此刻思考问题或许是:鲁迅彼时的思想能否为我们看待当下的社会思潮提供可堪借鉴的“精神资源”。在“传统文化复兴”蓬勃潮涌,“国学热”成为时代之“风”的今天,我们所复兴的究竟是何种层面、何种意义上的国学与传统,而这些国学与传统又是否在漫长的历史中真切地释放着思想的动能。以及,在我们的文化复兴中,我们又如何保证其生命力“闳放”而不至沦为僵化,这些问题尤为值得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名家时持续进行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鲁迅作品的解读是说不尽的,鲁迅的文学与当下的学术也能持续不断地为我们今天仍在行进中的社会提供思想的资源。
(责任编辑:陈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