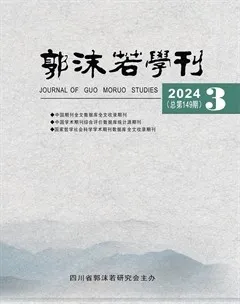戏谑外表下的严肃思考与现实选择
摘 要:在郭沫若的众多作品中,发表于1925年底的历史小说《马克思进文庙》因其戏谑色彩往往受到忽视,其实自有耐人寻味之处。郭沫若以小说的形式辨析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并主动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理论资源,一方面调和传统与外来的关系,另一方面企图通过文艺的方式化解国民大革命中国、共两党之间的主义矛盾。虽然郭沫若对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学理角度有待商榷,但是其论述敏锐地回应了社会历史,充分发挥了文艺的效用,不失为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求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郭沫若;历史小说;《马克思进文庙》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25(2024)03-0050-07
“自古历数干支之支配,以六十年为一周谓之新纪元。”①甲子年之大变局,在酝酿与发酵后,于1925年终于愈演愈烈,渐成燎原之势。是年年初时人便有预言“这中华民国十四年,是最有兴味最关重要的一年”,②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验证,这一判断不可谓不准确:五卅惨案引起全国震动,群情激奋,省港大罢工等工人运动随之渐成声势,掀起又一波反帝高潮;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广东政局为之一新;国民革命军正式成立并迅速东征陈炯明,北伐先声既振。影响甚至决定近代中国走向的重大事件此时或酝酿,或发生,满腔热血已经沸腾,革命高潮即将来临。郭沫若正是在1925年12月——仅仅三个月后他便南下广州,投身革命现场——发表了历史小说《马克思进文庙》。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向来作为弄潮儿的郭沫若却推出一篇“游戏之作”,难免有些怪异和理解上的尴尬。因此长期以来,这篇小说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往往限于为论证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做注脚。然而,郭沫若不仅仅是政治家、马克思主义者,更是敏感的文学家、诗人,有意而为之的文学游戏背后隐藏的欲说还休,可能不正确,却更加意味深长。
一、游戏之作或主动选择
马克思和孔子,两位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名人跨越遥远的时空距离,在《马克斯进文庙》中相谈甚欢,引为知己。如此构想无论对于当世读者还是后代学者,都颇为天马行空,毕竟“‘五四’时代的人……基本上反对以中国的经典来附会西方现代的思想。而且他们老是不客气地要中国的经典传统退出原有的中心地位,由西方的新观念取而代之”①。由此观之,反常的似乎是郭沫若:“五四”余韵尚存,“只手打孔家店”呼声仍在,他何以将马克思请入文庙与孔子并置,置“破坏”的任务于不顾,转而回望儒家?无独有偶,胡适昔日“吾国之旧文明……不适于今日之世界耳”②的慨叹仍在耳畔,1925年9月在武昌大学发表演讲时却将“新文学运动”定义为“中国民族的运动”,乐府、诗词、歌曲、小说均是其资源,“我们运动的人,不过是把二千年之趋势,把自然变化之路,加上了人工,使得快点而已。”③前后变化不可谓不大。新文化运动两位健将此时不约而同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理论资源,这很难看作巧合或无意之举。与其说《马克思进文庙》一文如郭氏所自谦“是带有几分游戏的性质的”④,源于他对共产主义的误解,“暴露出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肤浅和含混”⑤,不如说是郭沫若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之后,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有效性的主动选择。
清末民初以来,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大量、快速涌入中国,导致了一个“主义的时代”,知识青年“如果不研究主义,没有主义的信仰,人家说他是书呆子,甚至于给他一个‘时代落伍者’的头衔……于是大家都立意做一个‘新青年’,做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越‘新’越好,愈‘进步’愈好”⑥。在思想文化“权势转移”⑦的进程中,尊西崇新固然具有天然正义性,然而“西”与“新”的胜利并不是持续、稳固的,对“传统”的体认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根植于国人思想深处,哪怕引领时代风气的精英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承认“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⑧。遑论多数身处“铁屋子”尚不自知的普通民众。对此,郭沫若有着清晰的认知,要想使某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使得一般的、尤其有成见的中国人,要感觉着这并不是外来的异物,而是泛应曲当的真理,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已经有着它的根蒂,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循着那样的规律而来”⑨。如果要为中国传统思想找一个代言人,那么这一角色非孔子莫属。作为至圣先师,孔子的神圣地位延续千年,短时间内难以彻底破除。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统治中国数千年,已然“规定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⑩,成为世代因袭、根深蒂固的生存“惯性”,甚至“能给人们提供一种精神性的安身立命的家园,使众生获得一种道德精神的慰藉的精神化宗教11。”郭沫若对孔子的认同更是横跨文史,纵贯整个学术生涯,他的10篇历史小说中便有两篇与孔子密切相关。除《马克思进文庙》外,《孔夫子吃饭》也集中塑造了独特的孔子形象:小说中,孔子会暗暗计较自己的师长、“领袖”身份,却也不吝在弟子面前承认错误、坦白心声。与《马克思进文庙》中“妻吾妻以及人之妻”的笑话异曲同工,郭沫若心中笔下的孔子和儒家始终鲜活、生动、真实,绝不似拘迂后儒般“凝滞于小节小目而遗其大体”12,而是“出而能入,入而大仁”,“不偏枯,不独善,努力于自我的完成与发展,而同时使别人的自我也一样地得遂其完成与发展”13。堪为哲学典范,甚至是东方文明的唯一代表。所以,郭沫若选择让马克思与孔子对话,一旦二者达成共识,不单马克思主义,包括孔门儒家也更大程度地在中国语境中获得认可,从而达成东西方文化的握手,“西方文化才能生出眼睛,东方文化也才能魂归正宅”14。
沿着这一理路,郭沫若想要证明的自然不是“传统文化在外来思潮冲击下已日薄西山”①而是恰好相反。小说中马克思虽然是个“脸如螃蟹,胡须满腮的西洋人”,“一口的都是南蛮鹬舌之音”,和孔子需要通过翻译才能交流,但主动进入文庙拜访的毕竟是马克思,而且还要合了中国习俗,坐着“一乘朱红漆的四轿②”,这其实就可以视为对中国传统的妥协和顺应。同样,在整场对话中马克思表面上似乎占据主动地位,但实际孔子才是游刃有余的那一个。虽然马克思开篇便“满不客气地开起口来”,直言“特为领教而来”,主动发问孔子“究竟你的思想是怎么样?和我的主义怎样不同?而且不同到怎样的地步?”③然而后文中针对种种问题作答的并非孔子,而是马克思自己。全篇马克思不断阐述观点,孔子往往在马克思的长篇大论后点头称是,再以书经进行“比付”。从逻辑角度来看,以儒家思想比附马克思主义,即以前者证明后者之合理,是以孔子思想的正确性为前提条件的。作者先行预设了儒家思想的“权威”,孔子连连点头、拍手称是,其实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长提供依据:肯定现世人生、追求现世幸福即为“厚生”;共产社会与大同世界不谋而合,自由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同于“天下为公”“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产业增值对应“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反对私有财产集中对应“不患寡而患不均”和节用传统。孔子的回应甚至可以算作对马克思观点的总结概括,颇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小说结尾处颜回与孔子的问答也富有深意:
自始至终如象蠢人一样的颜回到最后才说出了一句话:
——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今日之夫子非昔日之夫子也,亦何言之诞耶?
夫子莞尔而笑曰:前言戏之耳。④
大智若愚、举重若轻如是。与马克思的认真甚至较真相比,孔子似乎漫不经心地将前言一笔带过,赋予“戏之”的性质,前者尚在“独上高楼”“衣带渐宽”,而后者已经“蓦然回首”——在中国传统认知中,这显然属于更高阶段。
郭沫若对儒家的略微偏向固然受到其自身知识结构的影响,但这绝不是他私人化的一厢情愿。在1925年这个特殊的时间点,郭氏的处理是有现实必要性的。该年接连发生的五卅惨案、沙基惨案致使中国全社会反帝情绪达到极点,但凡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不过在当时一般人的认知中,“反帝”与“排外”的区别并不明确,只要非我族类,就足以引起高度警惕。五卅运动时,俄共(布)曾特意指示“一定要防止发生杀害和殴打外国人事件,防止出现诸如‘英国人、日本人和狗不得进入中国公共场所’标语之列的粗野民族主义举动,尤其不要搞大洗劫行动⑤”,局势之一触即发,可见一斑。在这样的敏感时期,运用本国文化资源阐释国外思想理论,并在价值判断上对前者加以倾斜,纵然在学理方面有待商榷,但至少与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毫无抵牾之处,能够避免挑动国人紧绷的神经,不至于宣介马克思主义不成,又适得其反。
二、合理性或有效性
不出意外,郭沫若这篇离经叛道的“戏说”惹怒了一些人。小说发表后不久,大夏大学学生陶其情便提出强烈反对,洋洋洒洒作万字长文,从经学、训诂等角度对郭沫若的观点大肆批驳;巴金则指责“这确实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说的话”⑥。甚至大骂郭为“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关于“马克思进文庙”的合理性,郭沫若坦诚“其实马克思学说和孔子的思想究竟矛不矛盾,……实实在在不是那么容易的问题。……我现在很想费五年功夫把他的《资本论》全译出来,那时候或许我还能够谈得更圆满一点罢”⑦。也就是说,郭沫若自知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并不完善。但他还是作了《马克思进文庙》,不仅这一篇小说,在此前后郭沫若接连发表《共产与共管》《穷汉的穷谈》《新国家的创造》等多篇论文阐述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几乎怀抱一种刻不容缓的激情,希望由自己的作品在“漆黑一团的思想界……发生出一点微光来”①。实际上,一旦涉及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焦点,讨论便很难限于“纯”思想界,甚或可以说,这在当时的中国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共产主义与中国,和国内共产党一类问题,到今天为止,始终是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个大疽,里面的脓水已经汇聚到一个无可再淤的地步”②,关系着国家的国运甚至存亡。郭沫若既然落笔于此,也就不可能如他所言“带有几分游戏的性质”③信笔作文,想必是有意识地通过文学与政治产生联系。
民国初年虽然不乏读书人应“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也”④的主张,但是国家危亡关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显然不切实际,面对国是,学界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其中尤以“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的边缘知识分子”⑤最为活跃。郭沫若早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便凭借《女神》暴得大名,又有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学士光环,按照常理推断,归国后不难名利双收,一跃而进入精英阶层,不至于沦为“边缘”。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鸿沟。1923年,郭沫若携妻带子从日本留学归国,手头资产只有家里寄来的三百元钱,在泰东书局的工作又始终未正式议定薪水。正如《漆园吏游梁》中庄子为了生计向河堤监督贳米,彼时郭沫若生活窘迫到“连坐电车的车费都时常打着饥荒”,不得不“跑到泰东去,十块五块地要。……虽然是应得的报酬,总觉得在讨口一样,有些可耻”⑥。此外,家庭也增加着郭沫若的压力,妻子“很少开朗的日子”,“时常吵着要回日本”,⑦三个儿子体弱多病,医药费用不菲。如此情形投射进小说,便是庄子以妻子为拖累,“因为有了她,所以不得不过些不洁的生活;因为有了她,才去做了一场小官;因为有了她,才教了几个无聊的弟子。”⑧不唯物质上困顿,精神层面也是半斤八两:国内文艺界形势令郭沫若失望;视为精神上的儿子的刊物命途多舛,濒临停刊;郁达夫、成仿吾等同人也与郭沫若产生了分歧,渐行渐远。如此境况可谓边缘知识分子的现实写照。养妻活儿不能,救国兴邦无望,自身生活困顿与民族国家的衰弱带来双重焦虑,因此边缘知识分子“迫切需要寄托于一种较高远的理想,以成为社会上某种更大的事业的一部分。即使生活改善不多,到底是为一种更大更高的目标而生存、而奋斗”⑨。
郭沫若无疑是敏锐的,他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发表于两个月后的《柱下史入关》已经开始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精神上的儿子”固然重要,然而毕竟无法支应生活,“一瓶清水,两张麦饼,它们的功能更在欢乐以上了”⑩。虽然郭沫若在这篇小说中依旧以老子自况,却不再止于情感的宣泄。“我是有妻有子的人,你是晓得的。他们现刻住在魏国的段干,我现刻要往那儿去了。可怜我并没有甚么本事,我只有一肚皮的历史。”11面对现实困境,郭沫若意识到“不出户,究竟不能知天下”12。因此决意“自行改造”,“走向民间去种一茎一穗”13。诗人的绮梦无论再美丽,生活问题总不能不面对。理想中高呼着“为自由而战哟!为人道而战哟!为正义而战哟!”14可是现实中蜗居上海的他连自己的生活都快要负担不起,更遑论诗歌中的宏伟论题。“人生的苦闷,社会的苦闷,全人类的苦闷,都是血泪的源泉,三者可以说是一根直线的三个分段15”,所以郭沫若必然要寻找一个将理想照进现实的方式,摆脱个人困境,同时促成社会进步、世界解放,和全人类一起走向黄金世界。
到了《马克思进文庙》,答案呼之欲出。三个月后,郭沫若南下广州担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继而在随军北伐期间目睹了“宣传”奇效之发挥。北伐时期,“‘宣传’之功用被南北各方视为一种‘无形之战力’,首次受到国人的高度重视与娴熟运用。”16北伐出师时,政工团随军宣传,每当军事占领一地后宣传随即跟上,在城中广泛张贴标语、画报,散发传单、国旗等各类宣传品,“从这些标语看来,就可知道最近国民党的空气,并且他们拿这些标语简单地普遍到民众方面,不知不觉大家都受这些空气笼罩起来,……可见简单的标语,的确是宣传之利器。”①1927年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又设北伐宣传列车,从湖北一路北上至河南,配合开展宣传活动。②如此宣传攻势颇奏奇效,“大多数农工之人,醉心于党军解放之宣传”③,“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之类的口号妇孺皆知,“非但能贯彻地把主义灌输到民众的心坎内,而且……引起民族的奋进”④。“宣传”让郭沫若进一步发现了文艺的功用,文学不再是书斋中的闭门造车,而成为直接参与政治、甚至挽救民族危亡的利器——这对郭沫若的吸引是致命的。沿着这一脉络便能够更好地理解郭沫若为何在尚无充分的理论依据时便让马克思与孔子贸然相遇,其核心观念即文艺要与现实政治对话,与社会问题及时互动,为了达到这个第一要义,其他因素的牺牲都是可以接受的。于是,标语和口号牺牲了文学的优美含蓄,小说《马克思进文庙》虽然保留着天马行空的文学想象,却也不免牺牲了理论的正确与完满。不过在郭沫若看来,这是值得的甚至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最充分地发挥文艺的有效性,使之如匕首和投枪般直击社会现实,从而拯救民族国家,同时推动个人价值的实现。
三、潜在对话与谨慎调和
朱其华在《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一书中,曾描述过一幅有趣的漫画:
一面画着一个“世界公园”,世界公园里陈列了三个座位,中间是马克思的像,左边是列宁的像,右边的座位空着。另一面画着一个孔庙;在世界公园与孔庙的中间,一个穿着中山装的男子背了孙中山的像往孔庙中走去。旁边写着“孙中山应该陈列于革命的世界公园中,但戴XX一定要把他背到孔庙里去”⑤。
在马克思(列宁)和孔子之间,这幅漫画提示了另一位重要人物:孙中山。作为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领导国民党改组,确立“联俄容共”方针,并直接导向国民革命运动。因其在国民党中崇高的“国父”地位,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思想观念在他生前身后都深刻影响着中国国民党,甚至中国近代历史进程。
在中国国民党的理论体系中,“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⑥,其中“民族主义”占据关键地位。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到“五族共和”再到“国族主义”,虽然孙中山对民族主义的具体阐释几经变易,但根本期望一以贯之,乃“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⑦,从而实现“一民族成一国家”⑧。孙中山认为,中国目前急需发展民族主义,恢复民族地位,有效途径即首先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旧道德,恢复古时修齐治平的政治知识和科学能力,然后再学欧美之所长,“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学外国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学得到”⑨。孙中山虽然受过西方教育,但根本立场始终是传统中国的,“中国有一道统,尧、舜、汤、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余之思想基础即承认道统而发扬光大耳。”⑩他延续的是清末“中体西用”的思想脉络,只承认西方近二百年来的物质文明,而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精神文明并不2JYaQxvlnEPH9uZMCHH5jq/Svmz/RiqlzPo0XbX0G9c=推崇,“为什么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找智慧,从中国经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主义的基本思想吗?”11“马克思主义不是真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言论,还没有完全实行,在中国,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①这就决定了孙中山势必与苏共、中共的理论基点南辕北辙。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人以“世界被压迫民族”重新对“民族”进行概念界定,力图以三大政策包含甚至取代三民主义;与之相对,国民党则自认三十余年来革命“顾所成就者,为主义之成就;……民国以前,吾党本主义以建立民国;民国以后,则本主义以捍卫民国”②。试图将苏俄新经济政策乃至共产主义皆统摄于三民主义范围之内,甚至会依据自己的理解,对共产主义进行客观上的“反宣传”。
彼此排斥对方主义的国共合作从一开始就摇摇欲坠,郭沫若显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及其严重后果:国民大革命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如果理论分歧无法弥合,那么国民革命的法理基础势必遭到动摇。如果说孙中山试图“以儒代马”,一些激进的新兴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主张“以马废儒”,那么郭沫若则是凭借其敏锐在小说《马克思进文庙》中左右逢源,一面与孙中山这一文本的潜在在场者对话,延续他从历史传统中寻找文化认同的民族主义心态,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尽量为之正名,在二者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小说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糅合“共产主义”与“爱国主义”。共产主义作为本质上的世界主义,在当时遭受的主要批评之一即“受苏俄的援助,听莫斯科政府的命令,失却中国独立的精神”③,进而会导致中国受苏俄掌控,复落入另一“列强”手中,与独立自由之爱国精神背道而驰。回望鸦片战争以降数十载,中国不断遭受列强侵略瓜分,主权尽失、租界林立,民族危机深重,历史教训带来创伤后应激反应,时人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军事经济实力比较强大的国家,往往警惕和排斥多于善意或接纳。孙中山便是世界主义的激烈反对者,他认为“强盛的国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经雄占全球,无论什么国家和什么民族的利益,都被他们垄断”,他们鼓吹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④。中国民族主义之消亡正是由于被外国人征服。郭沫若在小说中则借由马克思之口声称“这力量(增殖与剥夺产业)的形式起初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而至于国际”⑤。这里,郭氏明确做出了轻重缓急之分,无论发展生产还是节制或废除私产,首先都是在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本国实力增长与人民幸福是首要任务,当本国内部的物质精神需求均能够得到满足后才进入国际范畴,而绝非要求中国以积贫积弱的状态羊入虎口。届时以独立自由之世界强国面貌出现的中国,自然无需再担心帝国主义侵略。这一论述与爱国主义的目的和手段都毫无抵牾之处,和孙中山“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⑥的主张也相当契合。而孙中山强调中国强盛后要担负起济弱扶倾的责任,“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屈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⑦,正类似由国家进而国际,层层发展,达到更高阶段。
同时,郭沫若在小说中对最容易引起警惕的“共产”进行了柔和化处理,指出共产主义“对于产业的增殖却不惟不敢反对,而且还极力提倡。所以我们一方面用莫大的力量去剥夺私人的财产,而同时也要以莫大的力量来增殖社会的产业。要产业增进了,大家有共享的可能,然后大家才能安心一意地平等无私地发展自己的本能和个性”⑧。将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者多认为“要讲共产主义呢,那自然是你衣包里的钱是该我共的,或者我衣包里的钱提防他要来共了”⑨。甚至于不仅“共产”,还要“共妻”。类似的恐惧和排斥虽是由于对共产主义缺乏了解导致的错误,但作为主观情绪,其影响力也不容小觑。因此《马克思进文庙》中的论述弱化了共产主义反对私有财产的成分,转而大力凸显发展生产、创造社会财富的部分。从私产丧失到财富增殖,郭沫若通过转移重点,力图扭转对共产主义的误解,提高接受程度。另外,郭沫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有一定的步骤”⑩的,这点在《穷汉的穷谈》一文中有更详细的阐述。郭氏将共产革命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需要以国家的力量集中资本;第二阶段则以国家的力量发展产业;直到物质极大丰富才能进入第三阶段,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达到终极彼岸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①第三阶段是共产主义的特色之处,也是和其余种种政治理念的分歧所在。然而在此逻辑之下,行进至分歧点的时刻被无限拖延,“要经过多少年辰,我们是无从知道,其实就是马克思自己也无从知道。”②在当下以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共产主义都会以国家资本主义的面目出现,与三民主义“以全民之资力,开发全民之富源”③的要求无甚剧烈冲突。“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大多数有利益,社会才会进步。”④当共产主义暂时搁置争议,专注财富积累时,双方自然能够和睦相处。某种程度上,这虽然是扬汤止沸,没能解决“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这一根本矛盾,但未来历史变化毕竟不可预知,就眼下而言不失为权宜之计。
“当时支配思想界的,就只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治学术的人都不能不有他各自的立场。”⑤郭沫若意识到了国共合作背后潜在的话语矛盾,并希望通过“马克思进文庙”的方式进行调和,夯实国民大革命的理论合法性基础。诗人的敏感体认何其准确,却遗憾地未能完成这个过于艰巨的任务,国共两党之间军事、政治与主义之争不断激化,不足两年之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还是以失败告终,革命再次落潮。
(责任编辑:陈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