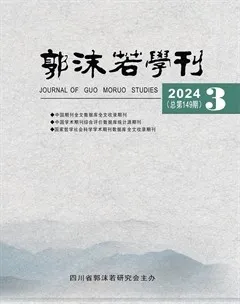“协力耕种这一块小小的园地”
摘 要:1926年创刊于上海的《白露》半月刊,由进社文艺研究会编辑,泰东图书局出版发行,是民国时期的一份重要文学刊物。该刊刊载了大量的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对于民国时期的上海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其中映射出进社文艺研究会的社团情况,是研究民国时期上海社团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此外,《白露》作为泰东图书局出版持续时间最长的刊物,对《白露》及其伴生的进社文艺研究会的研究亦有助于全面呈现泰东图书局立体的历史面相。
关键词:进社文艺研究会;《白露》;泰东图书局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25(2024)03-0017-09
一、进社文艺研究会概况
进社文艺研究会,又称白露社,是进社上海总社下属文艺研究会。1925年5月16日,“进社文艺研究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民国日报·觉悟》所刊登的《进社文艺研究会宣言》上。宣言宣称:这是一个由“爱好文艺的朋友”组成的社团,“感着文艺和人生关系的密切和重要,并且觉得我们目前的文艺上的贡献,委实太岑寂,太颓丧了,因此组织一个文艺研究会,来继续历史上伟大的使命与工作①。”主旨是“互相研究,注重修养,使得我们的思想与作品,能渐渐走上文艺的正轨,跨到人生的坦途②。”由此可见,进社文艺研究会在成立之初就秉持着积极向上的文艺创作态度,致力于营造相互交流、共同进步的创作环境,期盼着创作出具有一定质量和艺术高度的作品,并将文学作为促进个人成长,实现自我超越的途径。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和《中国现代社团辞典》等社团辞典均未收录“进社文艺研究会”的相关条目,仅有咸立强的《中国出版家·赵南公》一书对社团核心成员有所提及,并从“进社文艺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的相似性出发,对其发展历程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与概述。鉴于此,为了深入了解这个社团,我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向由其直接编辑的社刊《白露》,以此为线索,试图揭开这一文学社团的面纱。1926年11月1日,《白露》半月刊创刊号由泰东图书局出版发行,32开,每期50页左右。《白露》的实际编辑者共变更过五次,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八期的实际编辑者为汪宝瑄,第九、十期的实际编辑者为杨幼炯,第十一至十三期的实际编辑者为杨熙时。第二卷以后,蒯斯曛承担了《白露》的主要编辑任务,成为《白露》在任时间最长的实际编辑者。1928年11月16日,《白露》半月刊发行完第三卷第十二期。1929年1月,半月刊改为《白露月刊》继续出版,其中第一到三期仍由蒯斯曛负责编辑。直到第四期开始,毛圣翰接手《白露月刊》的编辑任务。此外,自《白露》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开始,编辑余话中陆续出现对“白露丛书”出版情况和出版计划的介绍。在第三卷第八期的《编完以后》中,蒯斯曛提到“白露丛书”的出版计划:梦茵翻译的《爱与死》已经付印,即日付印的还有席涤尘翻译的独幕剧集《情侣》,不久可编完的有汪宝瑄的短篇小说集《孤雁》和斯曛的短篇小说集《幻灭的春梦》……①可惜最终这些出版计划并未实现。目前明确的已出版的“白露丛书”共有5种:蒯斯曛的《凄咽》、翰哥(毛圣翰)的《两种力》、王任叔的《殉》、梦茵翻译的《爱与死》以及罗吟圃的《纤手》。至此,我们可以从主要编辑者和“白露丛书”出版者这两个方面确认“进社文艺研究会”的八位基本成员:汪宝瑄、杨幼炯、杨熙时、蒯斯曛、毛圣翰、王任叔、梦茵、罗吟圃。此外,汪宝瑄和蒯斯曛曾在《白露》半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碎话》中透露出白露社的社团组成情况:“本社现在几乎没有一点形式上的组织等等,所有社友均散迹四方,有许多是从来没有会面过的。我们觉得凡是爱护白露,投寄白露稿件的,都是我们的友人,都是白露的同人。”②据此我们可以得知,和“语丝社”性质相同,进社文艺研究会也是一个由刊物聚集起来的文学团体,没有明确的组织机构,成员即为社刊的实际编辑者、主要撰稿人和白露丛书的作者。《白露》半月刊和《白露月刊》共发行四卷、四十三期,若以十篇撰稿量作为衡量标准,能够确定进社文艺研究会的其他五位成员依次为:柳无忌、蒋山青、席涤尘、诗灵、陈汝梅。
二、进社文艺研究会的
文学主张与创作倾向
作为进社文艺研究会成员的主要活动阵地,《白露》自1926年11月1日发行创刊号始至1929年6月15日停刊,活跃时间约两年七个月,一度成为泰东图书局内存在最久的一份刊物。据笔者初步统计,在此期间《白露》共刊有作品358篇,其中诗歌138篇,约占总篇章的38.5%;小说101篇,约占总篇章的28.2%;散文32篇,戏剧8篇,批评18篇,译文53篇,理论介绍2篇,通信6篇。从这些作品能够看出,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小说创作占主导地位,超过了全部杂志内容的半壁江山。这种倾向不仅凸显出杂志鲜明的文学色彩,也映射出进社文艺研究会的核心文学主张与创作倾向。
(一)强调真挚的态度与自我表现
《白露》杂志自创刊以来,就将“以真挚的态度进行创作”视为其最为根本的文学主张和精神支柱。汪宝瑄在《白露》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馀话》中把“真挚的态度”作为《白露》引以为傲的成就:“……但是我们可引以自豪的就是我们真挚的态度;我们秉这点真挚的态度,永远不息地向文艺追求……”③,并寄希望于能够通过“真挚的态度”扫清文坛上充斥着的“以名流为贵”的虚妄之风:“我们最痛恨的是目前一班所谓名流,所谓文学大家;他们的作品既然更是未成熟,而他们的态度却完全是虚伪的,卑劣的,然而他们寡廉鲜耻,自称名流,自号为文学家,并且还霸占文艺的园地为己有,专横斥异,……”④在进社成员看来,文学创作的本质在于真诚地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思想,而不受外在功利目的的干扰。这意味着作家应当从灵魂深处汲取灵感,用文字忠实记录个人的感受、经历和思考,要求作家必须拥有直面自我的勇气,敢于剖析内心的复杂情感,勇于呈现那些脆弱或不完美的瞬间,以此来触动读者的心弦、引发共鸣。因此,《白露》上的文学作品大多直接抒发出青年所面临的思想困惑与人生问题。
婚姻与爱情问题是《白露》最常见的创作体裁。张春波的短篇小说《晨》,采用第一人称女性视角,细腻地勾勒出女主角从恋爱至婚姻阶段生活转变的轨迹。女主角曾陶醉于恋爱的甜蜜与幻想,彼时的伴侣用言语编织了一个个美丽的梦,然而,婚姻生活并未如她所愿般温馨与理想化,相反,她不得不面对婆婆的刁难、苛责和丈夫渐行渐远的感情,这一切犹如寒冬之冰,冷却了她心中的热情与期待。她深刻地感受到了恋爱与婚姻之间的巨大鸿沟,意识到婚姻并非只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庭的融合,其中包含着诸多未知与挑战。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开始怀念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那时的她对未来充满了无限憧憬,未曾经历过生活的磨砺。而今,面对婚姻中的种种不如意,她只能默默承受,心中充满了对往昔的留恋与对未来的不确定。①《晨》是对婚姻中普遍存在的矛盾与挣扎的一次深刻反思。生存压力下理想与现实的差异问题同样也是《白露》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在战乱年代,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也同样面临就业困难、生活成本高昂的问题,生存成为一大挑战。?的《麻木》讲述了一位青年在大学毕业后遭受生活的重重打击,他的精神日渐萎靡,生存的唯一目标变成了果腹。为求一餐温饱,他不择手段,甚至计划抢劫。在一次次行骗失败后,他准备变卖掉自己的长衫,却意外撞到了一个拾捡烟蒂的乞丐——这竟然是他离家出走已久的亲哥哥。哥哥给了他一些钱,但这笔救命稻草却被他在短暂的放纵中挥霍殆尽。当他再一次面临饥饿的窘境时,他决定彻底放弃尊严与底线,成为和哥哥一样的乞丐。他已不再憧憬未来,唯一的愿望就是活下去,无论这条生存之路多么卑微。“要活,要活就管不得什么高低了”②这句话道出了无数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辛酸。小说主人公是民国时期无数青年的缩影,他们曾怀揣着理想主义情怀,渴望毕业后改变社会、服务国家,但在巨大的现实落差面前他们不得不向生活低头,放弃曾经高举的理想旗帜。这是个人命运的悲歌,揭示了在社会现实面前青年的个人理想如何被重塑乃至破灭的过程。
“以真挚的态度进行创作”不仅是《白露》自身文学品味和价值取向的彰显,更是提醒着创作者不要被商业利益和流行趋势扭曲了创作的初衷,呼吁创作者回归文学创作的初心。“以真挚的态度进行创作”成为《白露》区别于当时其他文学刊物的独特标志,见证了进社文艺研究会成员们在文学的道路上不断探索,追求心灵的共鸣与成长。
(二)提倡关注社会现实
尽管《白露》以“纯文艺”刊物标榜自身,但它并未深陷于纯粹美学的探讨,忽视当时的社会矛盾与政治变迁。相反,这份刊物巧妙地平衡了艺术追求与现实关怀,避免了将自身封闭于象牙塔之中。进社文艺研究会成员深知,文学不仅是个人情感与想象的抒发,更是反映时代精神、参与社会对话的重要途径。回溯至《新青年》杂志引领的“文学革命”,其核心主张之一便是文学应当承担起启蒙民众、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文学被视为一种有力的媒介,能够触及人心深处,激发对社会现状的思考与变革。同样,《白露》虽以“纯文艺”为旗号,但其内容却远非空洞的唯美主义,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土壤,勇于面对并剖析现实的复杂性,使得《白露》从整体上呈现出“为人生”的团体性格。
《白露》的实际编辑者之一杨熙时在第一卷第十一期《创造我们的新园地》中便向社团同人以及所有关注《白露》的读者发出呼号,展现出《白露》“关注社会现实”的创作倾向。杨熙时首先驳斥了“文学无用论”“文学者为反革命者”的观点,从文学的情感性和社会价值方面阐述了文学对于民众的激励作用。杨熙时认为,在帝国主义横行的中国,文学对时代的反映和对民众心的唤醒使得革命文学的产生成为必然现象。“文学有如此伟大的使命,那末,在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下的中国民众,在毒蛇猛兽般压迫下奄奄一息的中国民众,正热切地盼望文学来润泽来感染他们枯槁的情田,使他们得到强烈的刺激与兴奋,猛生出一种极大的反抗,努力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挣扎起来,求民族自由之实现!”③然而,杨熙时指出在当时的文坛上存在着众多以“革命文学”为噱头,实则为口号、标语式的短篇散文和无病呻吟的靡靡之音。目前文坛真正需要的是作者心灵深处发出的真实纯洁的情感所构成的文学作品,比如描写人生和社会的病态、以及借男女真实挚爱为点缀的作品,只有这种作品才可以滋润社会上被压迫的人们,使他们得以振奋起来向光明之路进取。因此,杨熙时号召关注《白露》的同人们多多创作此类的作品,一起创造开辟文艺的新园地。
1926年至1929年期间,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外来文化的影响、政治的动荡不安、战争的频仍,这一切都深深地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的面貌。在《白露》的作品中,不乏有锐意批判社会不公、揭示人性深处矛盾的作品。这些文章聚焦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它们不仅仅是对现状的揭露,更是在呼唤改革,倡导一种更加公正、理性与人道的社会秩序。蒋山青的短篇小说《送葬》聚焦于剖析社会的阶级差异带来的不平等。在这部作品里,一场送葬仪式无意间揭示了社会底层人民艰苦生存的现实。随着送葬队伍缓慢地行进,一幕令人心痛的画面赫然呈现:一位人力车夫的棺木仅由四块薄板拼接,简陋至极,在搬运工——当地人称“码头”的粗犷搬运下,这最后一丝尊严也顷刻间粉碎,仅仅因为他的遗属无力支付更多的搬运费用。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不仅呈现了人力车夫死后僵硬的肢体与失去生气的面容,更借旁人之言,道出了他生前贫寒的背景与坎坷的经历,以及他身后遗孀与幼女面临的绝望与无助。①小说以送葬这一场景为载体,反映了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即便是死亡也无法抹平的阶级差异——面对生命的终结,不同社会地位的个体仍遭受着截然不同的待遇。蒋山青的另一篇短篇力作《闵老太太》,同样描绘了一幅令人心酸的底层人民的生活画卷。故事围绕闵老先生与闵老太太展开,这对老年夫妇在丧子之后,又遭遇儿媳离家出走,只留下他们与年幼的孙子相依为命。为了维持生计,六十多岁高龄的闵老先生不得不每日早出晚归,在一所私立学校担任庶务员,他战战兢兢,生怕自己的衰老成为他人眼中的负担,因此加倍努力工作。与此同时,闵老太太则默默地扛起了家庭的重担,悉心照料着疲惫不堪的丈夫,忍受着他因外界挫折而倾泻的不满与抱怨。在一个冬夜,风雪交加,寒风刺骨。闵老太太怀抱孙子,思绪飘回往昔,她沉浸在对三四十年前青春岁月的幻想之中,梦寐以求的是一个充满爱与和谐的家庭,以及一段富足安宁的人生。然而,现实的残酷打断了她的梦境,在这个冰冷的夜晚,闵老先生并未如约归来。蒋山青以细致入微的笔触,刻画了闵老太太在漫长一天的等待中,内心的挣扎与煎熬。最终,留给读者的是一个凄凉的结局——闵老太太与她唯一的小孙子,面对着闵老先生不会再回来的事实和不确定的未来相拥痛哭。②柳无忌的短篇小说《圣诞夜》针对的是民国时期教育不公的问题,小说讲述了在圣诞夜来临之际,一所非基督教信仰的学校彻夜狂欢的故事。尽管师生们并非教徒,却热衷于庆祝这一西方节日,大肆享用山珍海味,耳边回荡着西方圣诞歌曲的旋律,沉浸在一场与信仰脱节的狂欢之中。③柳无忌通过这部作品揭示了学生群体中出现的思想麻木现象,在国家正遭受帝国主义压迫,民众处于困苦之际,校园却成为了西洋音乐与电影的天堂,柳无忌借一群沉溺于奢侈生活方式的学生之口,道出了当时存在的严重教育问题:学习的目的已被功利化,学习不再是为了知识的追求或理想的实现,而是为了将来能在商业领域获得一席之地;学校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熔炉,但锻造的不是高尚的品格与真才实学,而是逐利的技能;书籍上的内容不再是智慧的结晶,而是点石成金的法术。这一切的背后,是贫困阶层获取教育机会的日益渺茫,彰显出教育的不平等与教育本质的偏离。
总而言之,《白露》的存在与实践,强有力地证明了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密关联——文学不仅仅是情感与审美的抒发,更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的桥梁。通过文学的视角,《白露》在文艺的土壤中深耕社会议题,将社会的脉搏与个体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并以文字为媒介,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风貌,批判了社会的弊病,将文学的内在价值与社会的外在需求紧密结合,展现了文学作为社会公共话语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及文学在推动社会正向发展方面的独特价值。
(三)号召无名作家建立联合战线
在《白露》的创刊号版权页上,醒目地刊载了一则题为《本刊启事》的声明,其内容透露出《白露》的编辑方针:“本刊系纯文艺性质,竭诚欢迎国内外青年无名作家投稿。但所谓名流杰作,恕不接受。”④这一声明清晰地表明了进社文艺研究会在对待当时国内文坛名流时所持有的坚决立场,其中蕴含着明显的对抗色彩。《白露》第一卷第三期刊登了一则《无名作家联合战线》启事:“偶像们霸占了文艺之宫,于是天才永被埋没,无名的作家永被抹煞。我们不能再懦弱了,我们要似怒狮般跃了起来,将我们的血和泪一齐洒到纸上。无名的作家,还不走向这儿来?!这儿有您们心花怒放的园地,这儿是我们联合的战线!我们向伪文学家下总攻击,我们愿做文艺的忠臣。无名的作家呵,白露在欢迎您们!进社文艺研究会启。”①以“无名作家”自称,这种态度体现了《白露》及其背后的进社文艺研究会对于文学创作和出版理念的见解。他们强调文学的纯粹性,重视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而非作者的名气,希望通过提供一个公平的平台,让才华横溢但尚未为人所知的作家有机会展示自己的作品。此举旨在打破当时文学界、出版界既有的权力结构,挑战由名流主导的文学生态,为文学新生力量开辟道路。
《白露》誓在打破“文坛偶像”的想法切实反映在了“文艺批评”的创作之上。《白露》不仅鼓励社内外同人进行批评创作,还积极刊载了一系列敢于揭露文坛弊病、勇于质疑偶像地位的文章。王皎我所著的《中国近时的文艺批评十篇之二》是对当时文艺批评领域症结的一次精准剖析。王皎我指出,文艺批评正面临四大核心问题:一是批评的态度,当前文艺批评存在着戴着有色眼镜的、以营业为目的的、“两面人”式的批评态度;二是误把“骂”当做批评,单纯以己之好恶发出骂语,这种情绪化的骂语是无效率、无价值的;三是批评失去了目标,偏离了文学批评的本质追求,无法触及作品的核心价值;四是不识建设批评的紧要,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应该重视批评的破坏,更重视批评的建设与改造,这是当前所缺失的。②王皎我的论述真诚且中肯,其观点直击要害,是对当时文艺批评界现状的可贵反思。汪宝瑄的《添上去》犀利地批评了郑振铎试图通过反复校订和增补《泰戈尔》译本,以增加印刷次数达到敛财目的的做法。同时,汪宝瑄对陶晶孙作品中的语言风格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文字组织过于西化,脱离了中文传统的审美习惯。此外,他还讽刺了当时批评界对李金发诗歌晦涩难懂之处的盲目追捧,这种现象暴露了批评界在评判标准上的偏差和对真正艺术价值的认知缺失。③王任叔的《新诗漫谈》是一篇诗歌批评,王任叔在文章中指出了目前诗坛上所出现的问题,一是抒情诗歌学腔过重,丧失了个性与真情实感的表达;二是议论诗过分侧重于阐述观点,忽略了诗歌应有的艺术性和表现手法,一味议论难以为诗;三是以朱湘的《草莽集》为代表的叙事诗,过于讲求诗歌格律,有“生吞活剥”的拼凑之嫌,缺乏自然流畅之美。王任叔认为现在的新诗大有复古的趋势,每一个作家都特别强调格律和韵脚,“把新诗的灵魂——诗意——撇在一边”。④此外,王任叔肯定了以李金发、胡也频为代表的“神秘诗”自由的表现方法,但也提醒创作者,倘若作品过于晦涩,致使读者难以理解,那么这种艺术创作就会失去其根基与意义。在文章结尾,王任叔热切呼吁,新诗应当追求形式与精神上的自由与灵动,鼓励诗人突破传统束缚,创作出既能触动人心又能传达深刻内涵的佳作。王任叔的这篇批评文章,不仅对新诗创作的现状提出了批评与反思,也为新诗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
《白露》号召无名作家建立联合战线的举措不仅彰显了其对文学独立性和多元化的追求,更是对文学界整体生态健康发展的积极推动。在那个由名流主导出版界的时代,《白露》勇于打破常规,为无名作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使他们得以在文学的舞台上发光发热,与早已名声在外的作家们同台竞技,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繁荣与多样性。
三、《白露》的停刊与
进社文艺研究会的解散
进社文艺研究会作为一个由青年学子构成的团体,其核心成员大多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且多数并非文学专业出身。在《白露》的实际编辑工作中,尽管五位主要编辑者专业背景各异,却共同怀揣着对文学的炽热之情,齐心协力耕耘着这份刊物,使其成为泰东图书局旗下存续时间最久的杂志。这份由青年主导的刊物自然有着其独特的优势,然而,伴随优势而来的挑战也不容忽视。
首要的难题在于稿源的不稳定性。由于进社文艺研究会松散的组织结构,加之战乱时期成员们分散各地,导致稿件来源极其不稳定。虽然《白露》一直秉持开放态度接纳无名作家的投稿,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稿源的质量和数量的可控性,给刊物的稳定输出带来了挑战。自创刊之初,《白露》便意识到稿件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即诗歌、小说的投稿量远超其他体裁,而文艺批评与理论文章则寥寥无几。编辑部多次呼吁社内外的文艺爱好者增加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介绍的投稿,以期丰富杂志内容、提升其学术价值和吸引力,遗憾的是,这一愿景未能得到实现。据统计,在《白露》刊载的358篇作品中,批评文章仅有18篇,文艺理论介绍更是仅有2篇,远远低于预期。在第三卷第八期的《编完以后》中,编辑部提及了读者反馈,读者普遍希望增加批评文章,并开设杂感专栏,同时要求《白露》更加透明地表达立场,定期分享杂志的最新动态。面对此类建议,编辑蒯斯曛的回应透露出编辑者的无奈与现实考量:“我们并非没有这一类的稿子,但无庸隐讲,我们读书有限,所写的批评文,大半不能应用。我们觉得与其登载无聊的批评以应景,还不如不登的好。一到有比较可读的批评文时,自然就要登出来的。”①可以看出,稿件质量的参差不齐,尤其是文学批评与理论文章的稀缺,成为了制约《白露》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瓶颈,这不仅影响了杂志的学术定位和内容多样性,也影响了其在读者心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其次,不够成熟的运营机制。在短短的两年间,《白露》从撰稿到发行并未也难以建立起一套系统而严谨的规章制度,《白露》的编辑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要编辑者的辛勤付出,这不仅消耗了巨大的个人时间和精力,也增加了运营的不确定性。编辑工作不仅要求极高的个人投入,还伴随着时间与精力的巨大消耗,对个人生活与创作空间造成了不小的挤压。作为《白露》最长时间的编辑者,蒯斯曛在编辑后话中多次袒露编辑工作的艰辛与挑战。在《白露》第三卷的最后一期中,蒯斯曛撰写了一篇名为《本刊底过去与未来》的文章,其中流露出深深的疲惫与无奈,他写道:“一则因为我办事缺乏能力,再则自从我负起这个编集稿子的责任以来虽已有一年,但成绩毫无,所以在发觉没有人肯来继续我办下去的事实以后,我想只有让白露暂时的停刊了。自己是想多读一点书,多写一点文章。虽然并不是怎样忙乱的事,但单是写回信与看稿子,也要化去不少时间,而编辑一期大概至少也要我五六小时的光阴?这种于己于人都无裨益的时间底浪费,我很吝惜。”②这段文字真实流露出蒯斯曛作为主要编辑者所面临的压力和感受到的力不从心,也反映出杂志运营过程中面临的实际困难与挑战。
最后,导致《白露》走向停刊的最关键因素,莫过于社团成员的流动性。大学生涯如同生命旅程中的一段短暂停留,学子们终究会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汪宝瑄、蒯斯曛等非文学专业出身的编辑者,他们虽在《白露》的编辑中倾注了自身心血,但并未将文学创作视作毕生的职业追求。相反,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生涯轨迹,有的步入官场,有的投身军旅,这直接引发了《白露》在人员更迭上的重大挑战。《白露》的编辑团队在创办期间历经五次更迭,其间甚至一度陷入停刊危机。在第二卷第一期的《关于编辑的话》中,编者披露:“因为交通关系,宝瑄到不来上海,同人们都散迹四方,白露终于无人负责,到了停刊的地步。”③蒯斯曛在执掌第二、三卷编辑工作时,亦多次提及寻求接班人的艰难:“白露编辑一职,正在觅社友继续。”④然而直至第四卷第三期,编辑工作依旧由蒯斯曛独自承担,显然,接班人选始终未能落实。直到第四卷第四期,毛圣翰作为《白露》的最后一位编辑者出现,陪伴《白露》走完了最后的路程。《白露》的最后一期刊于1929年6月15日,至于确切的停刊原因,至今仍笼罩在一层迷雾之中。然而,从1930年10月12日《读书月刊》上的一则《国内文坛消息》中,我们或许可以窥见一斑。该报道写道:“毛翰哥为上海白露社中坚之一,与汪宝瑄,蒯斯曛等出版白露半月刊,白露月刊,对于文学极为努力,毛君于去年赴日,研习日文,方于春间回国,即任东海中学教员。暑假时寓居上海,不料于九月卅日突患猩红热逝世,赴医院医治无效,当日即逝世,闻自患病至死,仅十九小时,可谓快矣。毛君曾主编白露月刊,创作集《两种力》,翻译有《文学的战术论》,今年二十四岁。”⑤依据上述讣告提供的线索,我们可以推测,毛圣翰的赴日留学可能是《白露》停刊的直接诱因。在缺乏稳定编辑团队的情况下,刊物的持续出版变得异常艰难,最终迫使《白露》走到了尽头。《白露》的消逝,不仅标志着一个文学平台的落幕,也象征着进社文艺研究会这一集体文化生命的终结。在社团成员流动性所带来的挑战面前,《白露》及其背后的进社文艺研究会,终究未能抵挡住时间的洪流,留下了一段充满遗憾与怀念的文学记忆。
尽管《白露》承载着一群热血青年的文学梦想,但在人员流动、运营机制、稿源管理等方面存在着种种不足,最终成为制约其长远发展的因素。这份由青春激情点燃的文学火焰,虽在有限的时间里绽放了耀眼的光芒,却也因现实的重重阻碍而难以持久燃烧,但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终究不失为一次可贵的尝试。
附录:
进社文艺研究会主要成员概况
1.汪宝瑄(1900-1991年),字抱玄。笔名鲍玄,鲍弦。江苏省连云港市人。早年就读于江苏省立第八师范,毕业后跻身政界并加入国民党,崇拜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北伐期间,他奉国民党之命以特派员的身份前往灌云县,进行该县的国民党组建工作。因受当时灌云县县长窦瑞生的排挤,遂愤然离去,后考入复旦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深造。1932年获得学士学位后,赴法国巴黎大学勤工俭学,1935年学成归国。同年5月15日,汪宝瑄接任无锡县县长。任职一年不到,又调任国民党民政厅。抗日战争爆发后,汪宝瑄离开政界,在上海租界潜居,并执教于复旦大学政治系,以教授的身份,掩护国民党在上海秘密开展的地下抗日联络工作。后因珍珠港事件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在租界搜捕国民党潜伏下来的军政人员。迫于形势,逃亡大后方重庆。抗战胜利后,汪宝瑄出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后当选为立法委员。大陆解放后,曾在香港自筹创办一所中学,自认校长。数年后前往台北郊区定居。曾先后任国民党立法院外教委员会负责人,中非友协负责人。①
在《白露》半月刊和《白露月刊》上发表的作品:《白露》半月刊:第1卷第1期《献词》《吴淞江上月》,第2期《爱之春(译)》《薛丽(译)》,第3期《薛丽(续)(译)》,第4期《文学与反革命》,第5期《失恋者的薤露歌(译)》;第2卷第1期《枕头》、《关于编辑的话》,第3期《闲愁万种(之一)》,第4期《闲愁万种(二)》,第5期《闲愁万种》。
2.杨幼炯(1901-1973年),字熙清,号复斋。湖南常德清江人。1923年从日本归国,入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系完成学业。后历任《神州日报》《中央通讯社》总编辑,民智书局编辑所长,国立中央大学、上海法政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教授,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部主任、中央政治会议专门委员、司法院法官训练所教授、建国法商学院院长、《中华日报》总主笔等职。②
在《白露》半月刊和《白露月刊》上发表的作品:《白露》半月刊:第1卷第10期《给读者》。
3.杨熙时(?-?),193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会理事,1955年起任武汉市农工民主党秘书长。著作有《最近的国际问题》《现代外交学》等。③
在《白露》半月刊和《白露月刊》上发表的作品:《白露》半月刊:第1卷第11期《创造我们的新园地》《编辑余话》,第12期《新都游痕》《通讯》,第13期《嘹唳》。
4.蒯斯曛(1906-1987年),原名蒯世勋,江苏省吴江县人。1924年秋考入上海复旦大学。1927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悼亡集》。1932年,参加柳亚子主持的《上海通志》编纂,编写《上海公共租界史稿》。1927年至1930年,编辑《白露》半月刊和《白露月刊》。1938年,参加《鲁迅全集》编辑工作。1940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1941年接编《译文丛刊》,出版《战争与文学》特辑。1942年,赴苏中抗日根据地,任《滨海报》《苏中报》编辑。次年,调入部队,先后担任华中军区司令部秘书、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秘书处主任、华东军区司令部外文学校政委。1944年10月至1949年年底,任粟裕秘书。1954年6月,转业到上海做文学出版工作,历任上海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等职。1978年参加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领导工作。1987年去世。④
在《白露》半月刊和《白露月刊》上发表的作品:《白露》半月刊:第1卷第2期《abnormal》,第3期《燕子去后的秋光》,第4期《酒后》,第5期《酒后(续)》;第2卷第1期《除夜》《关于编辑的话》,第2期《可汗和他的儿子(译)》《通信及其他》,第3期《总董老爷》,第5期《这一期》,第9期《平凡的故事》,第11期《游戏》;第3卷第3期《一个医生底访问(译)》,第7期《“道连格雷画像”底译本》,第11、12期《关于“道连格雷画像”底译本之商榷》、《本刊底过去与未来》;《白露月刊》:第1卷第1期《一生》,第2期《一生》,第3期《被握住了的那颗心》,第4期《强者之力》,第6期《纳租》。
5.毛圣翰(1907-1930年),笔名含戈、翰哥。浙江奉化人。上海白露社中坚之一,与汪宝瑄、蒯斯曛等人出版《白露》半月刊、《白露月刊》,致力于文学的发展。著作有《两种力》小说集,《文学的战术论》翻译作品。1929年赴日研习日文,1930年3月左右回国,任东海中学教员。暑假期间寄居上海,9月30日染猩红热逝世。①
在《白露》半月刊和《白露月刊》上发表的作品:《白露》半月刊:第1卷第2期《我们的诗人》,第4期《秋风下的哀歌》,第5期《海鸥》,第7期《哦!这原来就是你》;第2卷第1期《两种力》,第2期《两种力(续完)》,第3期《两种力重抄后附记》,第4期《心的重葬》,第5期《别了,你们》;《白露月刊》:第1卷第3期《追求(译)》,第4期《爬蟲》,第5期《战士》《兼职》《扫墓》《编后》《再来一条尾巴》。
6.席涤尘(?-?),江苏吴县人。南社成员,译有《武器与武士》、《约会》等。②
在《白露》半月刊和《白露月刊》上发表的作品:《白露》半月刊:第2卷第1期《归来(译)》,第2期《戏剧箴言(译)》,第3期《史蒂文生文艺杂话选译》,第5期《除夜的忏悔(译)》,第8期《Epilogue(译)》,第9期《〈爱西亚〉小序》《夜底尽头》,第12期《爱神》;第3卷第4期《在阴影里》,第6期《聚散》,第7期《深夜幽情曲》;《白露月刊》:第1卷第1期《the lagoon(译)》《幸福的幽谷(译)》,第2期《约会(译)》《幸福的幽谷(译)》,第3期《梨莎(译)》《幸福的幽谷(完)》,第4期《梨莎(译)》。
7.柳无忌(1907-2002年),原名锡礽,笔名啸霞。江苏吴江人。柳亚子之子。幼时柳亚子为其延师,在家读书,后进镇上第四高等小学。年仅12岁便加入南社。1923年10月14日,新南社在上海正式成立,又加入新南社。1920年去上海就读圣约翰中学、大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赴北京清华学校为插班生。1927年毕业后,赴美国留学4年,攻读英国文学,在劳伦斯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28年),在耶鲁大学得博士学位(1931年)。翌年返国,任天津南开大学英文系教授兼主任五载(1932-1937年)。七七事变后,去南岳文学院任教,复随学校赴昆明。1941年,应重庆中央大学之聘,兼任文学院外文系与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并代理系主任一年。抗战胜利后,自渝去沪,于1946年春携眷赴美讲学,历任耶鲁大学(1951-1953)、匹兹堡大学(1960-1961)、印第安纳大学(1961-1976)教授。在印大时创办东亚语言文学系,任主任五年,为沟通中西文化、培养人才作出重要贡献。退休后为荣誉教授。1978年移家加州,1989年在美国成立国际南社学会,任会长。1990年11月13日,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任名誉会长,积极筹备《南社丛书》的出版,促进海内外文化交流与“南学”的建立,在推动南社研究方面,贡献甚巨。平生主要从事学术研究与翻译,著述颇丰,主要有《印度文学》《英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概论》《柳亚子年谱》《柳无忌散文选》《抛砖集》(新诗集)、《苏曼殊传》。编著主要有《苏曼殊全集》(与柳亚子合编)。主要译著有《葵晔集:三千年中国诗歌》《凯撒大将》(莎士比亚戏剧之一)。③
在《白露》半月刊和《白露月刊》上发表的作品:《白露》半月刊:第1卷第5期《十八世纪英国小说概况》,第7期《圣诞夜》,第8期《英国情感派小说创造者理查孙》,第9、10期《一公,你从死国带福音来》,第11期《写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之后》;第2卷第8期《忏悔》《阿宝的剪发》,第9期《狂人之歌》,第10期《赠美女歌》,第11期《小黑猫》,第12期《人影(译)》;第3卷第1期《观剧》,第2期《乞箭》,第3期《有赠》,第4期《亲爱的别爱我》,第5期《怀诗人济慈》《题维纳斯像》,第6期《译莎士比亚诗歌》,第7期《赠球丽丝钏(译)》,第10期《月女》《黑夜的宠孩》;
《白露月刊》:第1卷第1期《赠所欢及其他(译)》,第3期《黎明的一刻》。
8.蒋山青(1906-1960年),原名蒋明祺,号山青。江苏淮阴县人。教授,会计审计学家,审计实务专家。国民政府重庆市审计处处长。④
在《白露》半月刊和《白露月刊》上发表的作品:《白露》半月刊:第1卷第1期《送葬》,第2期《车辚辚》,第4期《闵老太太》,第6期《拟赠》,第7期《月上柳梢头》,第8期《醒来后》;第2卷第1期《泣冢》,第2期《惆怅》,第3期《想》,第4期《今朝有酒》,第5期《红睡》,第12期《双死》;第3卷第6期《我们和我们底朋友》,第7期《我们和我们底朋友(二)》,第8期《我们和我们底朋友(三)》,第9期《我们和我们底朋友(四)》,第10期《我们和我们底朋友(十一)》,第11、12期《我们和我们底朋友(十二)》;《白露月刊》:第1卷第1期《访问》。
9.罗吟圃(1910-2000年),又名吟圃。广东梅州丰顺县人。1926年罗吟圃留学归国不久,受新文学运动的浪潮影响创作新诗,之后投笔从戎。1932年任国民党一五六旅政治部主任,在此期间由翁照垣口述,罗吟圃执笔撰写《淞沪血战回忆录》。1937年上海沦陷后前往香港,任《星报》经理和主笔。1955年出以“南木”为笔名,翻译了美国作家艾温·威蒂尔的散文《春满北国》。后移居美国。①
在《白露》半月刊和《白露月刊》上发表的作品:《白露》半月刊:第1卷第3期《赠我这莹莹的白蠋一枝》,第5期《前尘》、《活着我无多奢求》;第2卷第1期《吟此一杯,送别那美好的青春》,第2期《我们俩管领着这深的静夜》,第3期《我如今眼角已褪尽了泪痕》,第4期《江干聚拢了雾白的夜色》,第5期《繁华的夏梦已过》《残烛还吐着青黄的微光》《如今只好离开这广漠的荒原》,第6期《瓶里的白菊昨天已是憔悴》《“纤手”编后题记》,第7期《红窻中不见你黑发蓬蓬》,第8期《译道生》,第9期《姑娘,你给我划一根火柴》,第11期《你请把头儿埋在我的怀间》;第3卷第4期《自从那回走入了迷阵》。
10.诗灵(1904-2004年),原名顾泽培。上海崇明县人。1920年考入苏州第一师范学校。1925年毕业,1926年受邀前往上海大学旁听。1927年于崇明县立师范教学,经匡亚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受党指派参加崇明西沙秋收暴动,失败后离开上海,辗转来到贵州,失掉党组织关系。1938年春,在贵阳经生活书店经理邵公文介绍重新入党,受指派到湄潭中学任教,协助湄中校长乔光鉴(中共党员)开展学生运动,组建民族解放先锋队和飞鹰步行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后湄潭形势恶化,被迫离湄。建国后,长期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2004年10月2日逝世。②
在《白露》半月刊和《白露月刊》上发表的作品:《白露》半月刊:第2卷第5期《奠情曲》,第9期《把残賸的爱情给你》;第3卷第3期《这样的献给你了》,第4期《握手曲》《我愿把快乐给你》,第5期《把我的灵魂葬了》,第6期《姑娘请莫忘我》,第7期《昨夜梦见你了》,第8期《我并不怨你》、《洋囝囝的自杀》,第9期《你已不是我的了》《文艺该是做梦(通信)》,第10期《我是一个被弃的土瓶》《祭台之前记和后记》; 《白露月刊》:第1卷第1期《老龚》,第2期《死的赞曲》,第3期《落日曲》。
11.陈汝梅(?-?),又名汝梅。
在《白露》半月刊和《白露月刊》上发表的作品:《白露》半月刊:第1卷第5期《新霁后我踏着斜阳》,第6期《病情者》,第8期《月华》;第2卷第8期《病起》;第3卷第9期《败舟》,第10期《蝶躞》《请葬我在此潮头》,第11、12期《南高峯晚归》《重别西湖》《沙滩上》。
12.王任叔(1901-1972年),现代作家、文艺理论家。又名于虞,号愚庵,笔名巴人、屈轶等,奉化人。1920年从宁波第四师范毕业后在宁波等地任小学教师,接触新文学。1922年加入文学研究会,次年出版国内第一本散文诗集《情诗》。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与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抗战爆发后,积极从事抗日文化宣传活动,参加并主持《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1941年至南洋从事抗日活动和支持印尼独立的民主运动。1948年4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第二处副处长。建国后,为首任驻印尼大使。1953年后,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中联部东南亚研究所编辑室主任,“文革”期间曾受到迫害,在奉化病逝,著有《莽秀才造反记》《文学论稿》《论鲁迅的杂文》等。③
在《白露》半月刊和《白露月刊》上发表的作品:《白露》半月刊:第1卷第1期《骷髅底活剧》,第5期《新诗漫谈》,第10期《无意之歌》,第12期《鸤鸠》;第3卷第1期《给梦蕙》,第7期《苏格拉底》;《白露月刊》:第1卷第4期《虚伪的情感》、《辟克涅克(译)》,第6期《夜之幻象》。
(责任编辑:陈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