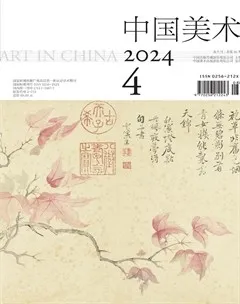“淀园”风雪
[摘要] 《寒林冬山图》是戴熙为“子衡”所作山水画,绘制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即戴熙陷入仕途危机称病辞官的前一年。画中人物形象与文献中陶渊明的形象相近,戴熙借此应为表达归隐山水之意。这些边跋除为追忆戴熙外,还记录了晚清官员述及太守与诸生游“淀园”(按:即圆明园)旧事。本文通过分析《寒林冬山图》的绘制与递藏经过,钩沉相关历史细节,探讨晚清官员的收藏趣味,以期帮助读者更加立体地认识“庚申之变”。
[关键词] 戴熙 晚清官员 绘画收藏 圆明园 “同光中兴”

《寒林冬山图》是戴熙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所作水墨山水,自题款识“寒林尚未苏,冬山已先笑。犯晓过溪来,独往搜众妙。何处早梅华,夜闻孤鹤叫。营丘华原之间。子衡大兄法家鉴政。戊申仲冬醇士戴熙作于池南旧庐”,后钤“醇士”朱文方印、“与江南徐河阳郭同名”白文方印。画中另有晚清官员戴兆春、谢维藩、秦毓麒、严玉森和孙万春所书五段边跋,并钤有“介眉审定真迹”“孙氏家藏”“忍俊不禁”三方鉴藏印。目前,学界关于戴熙的研究多集中于其绘画风格和画论,[1]关于其作品鉴藏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通过考析《寒林冬山图》的创作过程和晚清官员观看此画时的历史场景,分析不同历史语境下画面所生成的图像含义,尝试对“同光中兴”时期晚清官员的绘画收藏趣味展开探讨。
一、归隐山水:作品的绘制缘由
《寒林冬山图》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系》[2]一书中被定名为“寒林东山图”。不过,该作品原名应取自画上戴熙题诗“寒林尚未苏,冬山已先笑”每句前两字,笔者以此为据,认为该作名称应为《寒林冬山图》。书中将画名定为“寒林东山图”,“东山”一词的使用是否有合理性?若为“东山”,画面含义与陶渊明诗中的归隐之意是否有关联?想要厘清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寒林冬山图》的内容及绘制缘由进行分析。
“寒林”与“冬山”是清代画家王翚笔下常见的母题。戴熙《寒林冬山图》在风格上虽师法王翚,但二人笔法有所不同。王翚所绘山石树木用笔清晰,戴熙画中山石则往往只见墨色而不见线条,轮廓边缘线因干笔皴擦而较为模糊。《寒林冬山图》与戴熙同时期作品的用笔一致。比如,故宫博物院藏《忆松图》卷与《寒林冬山图》的创作年份相同,是戴熙47岁时为军机大臣祁寯藻所作,代表了其山水画成熟期的风格。其画山石善用擦笔,用墨干湿结合,画风细密精致。这类“四王”风格的山水画符合晚清官员对正统山水画审美的理解。黄小峰研究晚清文物市场官员的收藏问题时,认为最受欢迎的书画是乾嘉年间名家翰墨和清初“四王、吴、恽”绘画。[3]《寒林冬山图》的收藏与鉴赏者身份皆为晚清官员可以佐证这一观点。
《寒林冬山图》中绘有一个头戴葛巾、手持黎杖、身着宽袍的男性,身旁随一侍童,二人正在渡桥。此男性人物形象与史书中记录的陶渊明形象相吻合。《隐逸传·陶潜传》中云:“郡将候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4]除此之外,有关陶渊明的绘画作品也与《寒林冬山图》中的人物造型有共同特征,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李公麟《归去来辞图》、吉林省博物院藏何澄《归庄图》、故宫博物院藏王仲玉《陶渊明像》等,都呈现出相对定型化的表达方式,葛巾、黎杖、宽袍、侍童等元素都出现在画面之中。

戴熙为什么要在这一年绘制一幅与“渊明归隐”题材相关的作品?这可能与他所经历的两次仕途危机有关。第一次仕途危机发生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科场舞弊案。有关科场舞弊案的经过见载于《清实录》:“昨因黄恩彤违例妄请赏给年老武生职衔,饰词渎奏,市恩邀誉。当降旨交部严加议处,并谕兵部查明定例。”[5]戴熙在此次事件中因“任内失察年老武生入场”[6]而遭到革职留任的处罚。
第二次仕途危机发生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其以直言粤事忤帝,此后便以病乞休回乡。事件的具体经过在《清稗类钞》中有所记载:“宣宗末年,为枢相穆彰阿雍蔽,略不省事,时盗已萌芽,督抚承穆风旨,莫敢奏闻。戴文节公熙为广东学政,期满还朝,召见,问汝一路由江西、安徽、江苏来,民情如何?文节遽对曰:‘盗贼蠭起,民不聊生。’宣宗大骇曰:‘如汝言,尚复成何事体。’怒询穆,穆免冠谢曰:‘戴某见皇上春秋高,欲以此撼皇上,沽直名,非实也。’宣宗遂恶文节。旧例,年终赐南书房翰林福字,文节不与焉,乃遂以病告归。”[7]创作《寒林冬山图》的时间正是戴熙陷入仕途危机、准备称病辞官返回杭州的前一年。再结合画面人物形象和“子衡大兄法家鉴政”的款识,我们可知此图的受画人为“子衡”。关于此人的文献记载极少,笔者仅从《习苦斋画絮》中找到两条戴熙为友人“沈子衡”作画的记录,分别为“大痴浅绛,若春夏初,甘霖新霁,柴翠万状,在褭窕冲融间。此殆西庐所谓神乎当于象外求之。大幅为沈子衡”[8]“秋山万叠。子衡二兄年大人来索画扇,因对使者和墨赋色,俄顷而成。一时兴到,要非应酬率笔。贻沈子衡”[9]。不过,也不能据此便认定《寒林冬山图》的受画人为沈子衡,只能推测“子衡”应为戴熙的同辈友人。戴熙陷入政治困境后作《寒林冬山图》赠予“子衡”,这可能也是戴熙将官场的艰辛和人生体悟对友人诉说的一种方式。
二、以人论画:晚清官员的收藏趣味
要厘清《寒林冬山图》的具体递藏经过,我们需要先对画中的五段边跋进行分析。谢维藩、戴兆春和严玉森三人的跋文都是写给秦中“子衡太守”的,此人即为《寒林冬山图》的收藏者。从《续修陕西通志稿》可知,跋文中所谓“子衡太守”为光绪十年(1884)任佛坪厅同知的官员秦毓麒。秦毓麒,字子衡。[10]此处需要注意,《寒林冬山图》的收藏者“子衡太守”与戴熙款识中的“子衡大兄”并非同一人,因为《寒林冬山图》完成时秦毓麒年仅一岁,并非戴熙笔下的同辈友人“子衡”。光绪十四年(1888)前后,秦毓麒邀请官员谢维藩、戴兆春、严玉森观画并题跋。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此画归官员孙万春所有。

《寒林冬山图》右侧首段边跋为戴熙之孙戴兆春所题。《戴氏迁杭族谱》中记载了戴熙家族成员的具体情况,其中对戴兆春的为官经过记载道:“同治庚午科副贡生,癸酉科举人,光绪丁丑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壬午顺天乡试同考官,戊子陕西乡试正考官,壬辰甲午戊戌会试同考官,国史馆纂修功臣馆总纂,乙未科教习庶吉士。京察一等,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授陕西陕安兵备道,赏戴花翎,覃恩加一级,清授文林郎,封中议大夫。”[11]戴兆春在《寒林冬山图》中的跋文为“光绪戊子典试秦中榜发后,晤子衡太守,敬观所藏”。由此可知,戴兆春的官职为陕西乡试正考官。为官期间,其与秦毓麒相见并观秦毓麒所藏先祖戴熙之作。跋文还写道:“先祖文节公戊申年遗墨,时值承平,南斋多暇,太守方以诸生从游淀园,日侍挥毫,所得为不少矣,并述此幅装池后。先祖见而喜曰:‘居然古画,诚得意笔也。’今已四十余年矣,缅怀祖德,不胜宰木空山之感。睹手泽之如新,赖知交之藏弆。是画当永垂不朽,惜轺车匆促,不获与世交旧好常相聚处,徒怅于怀。然燕山渭水,天涯比邻,此游不仅与太守结一重翰墨缘也。谨识数语于后,仍敬归太守藏之。十月四日兆春并志。”对戴兆春而言,此作还有“缅怀祖德”的特殊意义。
其他几段跋文更多是在强调戴熙气节高尚。实际上,咸丰十年(1860)发生的政治事件对晚清官员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广州府志》记载了戴熙殉难的经过:“庚申发,逆破杭州,投园池死。”[12]因此,当光绪十四年(1888)秦毓麒邀请友人观赏此画时,画作中不仅体现了戴熙的归隐之意,还带有特殊的历史记忆。谢维藩跋曰:“鹿床早退身犹健,琴隐闲居鬓已鬖。天遣湖山壮忠节,二公遗墨满东南。”秦毓麒跋:“传闻公子与公孙,宝持手迹慰忠魂。”孙万春跋曰:“殉赭寇之难矣。都人士遂重其画。后南皮张子清相国倩人到处搜罗,而片羽吉光,遂等于洛阳之纸,世间不恒见矣。此幅为其中年得意笔,予与黄孝子万里寻亲图定为收藏压卷。一取其忠,一取其孝,而翰墨之工拙不与焉。”这些内容反映了晚清官员收藏戴熙作品的目的。此外,《中国绘画总合图录》中收录的戴熙山水册页后可见吴大澂跋文:“公与金陵汤贞愍为江浙老名士,皆以气节重,好事者专以汤画佩公,称曰汤、戴名迹与四王、恽、吴并重。”[13]这亦可佐证在晚清内忧外患的历史语境下,对“忠义”和“气节”的强调成为官员收藏汤贻汾[14]、戴熙作品的重要原因。
三、从“寒林冬山”到“淀园风雪”:历史记忆的转向
《寒林冬山图》题跋中反复提及的“淀园”值得我们关注。戴兆春跋文中的“太守方以诸生从游淀园”和严玉森跋文中的“丈示以戴文节公山水真迹,又屡称淀园往日”都提到了“淀园”。那么,《寒林冬山图》与“淀园”到底有何关联?其实,这与作者戴熙的殉难时间有关。前文提及,戴熙殉难于咸丰十年(1860)。同年,英法联军攻占并烧毁了圆明园。作品题跋中之所以反复提及“淀园”“赭寇之难”,一方面在于秦毓麒与戴兆春等官员曾在圆明园交游,有共同的个人记忆,另一方面在于观者看到画作时会不约而同地将戴熙殉难与“庚申之变”相联系。

对晚清官员而言,未烧毁前的圆明园与官员个人仕途、社会声望紧密相关。圆明园最初为“世宗宪皇帝藩邸赐园,康熙四十八年所建”[15],在雍正朝以后逐渐成为清廷的另一政治统治中心,具有接见官员、宴请朝臣和举行科举殿试等重要政治功能。乾隆时期《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之“正大光明”与“勤政亲贤”表现的就是这些场景。圆明园在官员心中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然而,在“庚申之变”发生后,一把大火将清廷的威严和官员的荣耀全部烧毁,圆明园只剩一片废墟。此后,“淀园”成为文人笔下无法抚平的伤痛。笔者通过梳理,发现咸丰十年(1860)后提及“淀园”的诗文和描绘“淀园”的画作已与“庚申之变”这一政治事件相关联,如“离黍悲淀园,将营两宫养。终鉴阿房焚,贤王伏青蒲”[16]一诗和有些作品中出现的“淀园风雪”题材。[17]
“淀园风雪”题材并非单纯的艺术主题,其展现的还是当时的历史事件。目前,学界已有研究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圆明园被焚毁与咸丰十年(1860)10月初京津一带气温骤降的气候条件有关。[18]由于英法联军物资补给系统存在隐患,无法支撑其长期作战,他们需要赶在当年11月初河流冰封之前结束战争,这才制造了火烧圆明园事件,迫使清政府屈辱投降并签订了《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晚清官员便是这场“淀园风雪”的亲历者。另外,《寒林冬山图》中的多数题跋者很可能还经历了同治年间圆明园的两次重修风波。这两次重修风波分别发生在同治八年(1869)和同治十二年(1873),最终在奕?等十位重臣联衔上疏的请求下停止重修,此事才告一段落。《寒林冬山图》的题跋者谢维藩曾两次上疏言:“淀园当罢茸,大婚繁费请节用以振饥民,语多激切。”[19]由此可见,“同光中兴”时期出现的重修圆明园风波也对官员产生了较大影响。以上因素导致《寒林冬山图》中谢维藩、秦毓麒等官员的跋文内容已不再与归隐有关,而是开始将“庚申之变”与图像相关联,为作品赋予了“淀园风雪”题材的意涵。
观者在观看图像时会受到当下环境的影响,主动将自身所处环境与画面相联系,对画面进行重构与再造,以符合其身份及情感偏好。因而,《寒林冬山图》受到晚清官员重视的原因在于戴熙殉难和火烧圆明园的惨痛历史记忆对“同光中兴”时期官员的警示作用。戴兆春、严玉森等官员试图在《寒林冬山图》中寻找到“淀园风雪”的记忆,学习戴熙的忠孝品质。这正是身处“帝国黄昏”阴影下的文人官员们所迫切需要的。
四、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戴熙《寒林冬山图》的绘制与递藏过程,探究此作画意从“寒林冬山”到“淀园风雪”的转变过程。最初,戴熙绘制此图是想要向友人表达归隐之意,画作的笔墨风格符合晚清官员对正统山水画的审美观念。此画在光绪年间先后经秦毓麒和孙万春收藏,晚清官员戴兆春、谢维藩和严玉森也先后在画上题跋。不过,这些官员在题跋时已不再关注画中的隐逸之情,而是开始将“淀园”意象加入其中,原因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与戴熙殉难发生于同一年,这两个事件对官员和文人产生了强烈的内心冲击,致使他们再观《寒林冬山图》时便将“淀园风雪”与画作联系了起来。总而言之,探究戴熙的《寒林冬山图》有助于我们了解晚清官员的绘画收藏趣味,帮助我们更加立体地认识“庚申之变”。
注释
[1]周永良.浅析戴熙绘画艺术的嬗变——兼及〈习苦斋画絮〉纪年抄本的发现[J].故宫博物院院刊,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4):51-59+93;梅雨恬.戴熙绘画风格研究[D].中国美术学院,2017.
[2]范迪安,编.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系(中国古代书画卷)[M].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324-325.
[3]黄小峰.晚清北京古书画市场中清初“四王”绘画之境遇[D].中央美术学院,2005.
[4]沈约.宋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323.
[5]广东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办公室,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编.清实录广东史料(四)[M].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395-396.
[6]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四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28:50.
[7]徐珂.清稗类钞(第11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16:46.
[8]参见戴熙撰《习苦斋画絮》(卷四大幅类),清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第242页。
[9]同注[8],429页。
[10]参见宋伯鲁、吴廷锡撰1934年版《续修陕西通志稿》。清光绪本《定远厅志》还记载了秦毓麒为官期间的诸多政绩,如筹措常平仓储粮、修筑道路等。
[11]参见上海图书馆藏《戴氏迁杭族谱》1917年刻本第69—70页。
[12]参见《广州府志》,清光绪五年(1879)刊本,第2540页。
[13]铃木敬,编.中国绘画总合图录(第2册)[M].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158.
[14]汤贻汾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时投水而死,谥号贞愍。
[15]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八十)[M].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1321.
[16]邓辅纶,陈锐.白香亭诗集抱碧斋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2:61.
[17]董文涣.砚樵山房诗稿[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445.
[18]裴广强.再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圆明园被焚毁之因——基于宏观视角的考察[J].北京社会科学,2015(8):96-104.
[19]参见《湖南通志》,清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第14817—14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