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剑华学派”的新创获
[摘要] 《中国印论辑要》是在当前古籍文献整理质量低下的背景下,所产生的一部“学术当随时代”的成果。由于“俞剑华学派”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篆刻研究的内生逻辑,决定了编者采用类书型编纂方式,以此深耕于俞氏未曾涉及的印学领域,来扩大“俞剑华学派”的学术内涵。同时,《中国印论辑要》对篆刻技法予以了必要关注,并将印论的时间上限推到先秦、两汉时期,还辑录了不少史学文献,充分发挥“互著”“别裁”之法,建构了独特的中国印论分类体系,体现了敢与名家论短长的学术魄力。此外,《中国印论辑要》还有着“有述有作”的文献学特点,注释部分承袭了俞剑华文献整理的特色,“导读”部分则凭借其优异的思辨能力和丰富的创作实践言他人之所未言,不啻为“俞剑华学派”的新收获。
[关键词] 篆刻 《中国印论辑要》 俞剑华 “俞剑华学派” 朱琪

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在当前学术界和出版界业已呈现磅礴之势。具体来说,不仅从事古籍整理的青年学者日益增多,而且从21世纪以来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来看,一方面,整理方式从曾经一度非常流行的白话文翻译转向标点、简化、注释、翻译并存的多元化方式,另一方面,出版数量明显增长。近年来,大部头影印乃至数字化这一“述而不作”的整理方式得到了业界青睐,然而遗憾的是这一繁荣景象的背后却是整理质量的日益低下。
关于大型文献的整理,无外乎两条路径:一是编年式(按:专科文献可名为“丛书式”),二是分类式(按:专科文献可名为“类书式”)。编年式辑录靠的是考证功夫,分类式辑录则依赖思辨功力。学术演进过程中有“汉宋之争”,自现代学术分化以来,两条路径亦多交替进行。葛兆光的《想起四十多年前那股学术的力量》一文中有这样的论述:
四十多年前与现在,学术环境与取向显然不同。我总觉得,现在的学术界,崇尚的是高深理论、繁复论说、前沿时尚,有些像乘飞机在云端翱翔,但那个时代,学术界刚走出机械和刻板的论述,特别反感“以论代史”,追求的却是文献实证,以便重回可以安心脚踏的实地。被提得最多的,一方面是重视文献考据的清代乾嘉诸贤,一方面是五四时代胡适所谓“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 1 ]
这段话隐含着对40年前学术环境的回味。实际上,学术发展,自然有其外在背景和内在规律。笔者曾梳理清代考据学巨擘翁方纲的相关材料,其凭借取向好恶,对明人学问一味鞭挞,甚至有“明人不知考订,触手即误”[2]的断言,几无半分首肯。当时,笔者对此殊感无谓。当然,无论是取实证还是取思辨,都不能过于极端:好放大言而缺乏文献支持自然是空中楼阁,可如果真要践行证据为王的宗旨,对一些合理的学理推论闭口不谈,学术亦无法进步。前人尝谓“笔墨当随时代”,学术何独不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琪的《中国印论辑要》(按:在其博士论文《清代篆刻创作理论研究与批评》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清代篆刻理论研究”过程中形成的文献整理成果,以下简称《辑要》)有述有作,显得特别突出。之所以说《辑要》“显得特别突出”,除了其本身具备时代性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这是一部“俞剑华学派”的新创获。
一、继承“俞剑华学派”的类书式整理而有所突破

作为中国古代画论专科文献整理的集大成者,俞剑华对画论的整理依循了两种方法。一是丛书式,即依文献类别收载原书,属画论汇编,如《中国历代画论大观》。二是类书式,即按性质采摭,随类相编排,“区分胪列,靡所不载”,属画论辑成,如《中国画论类编》。[3]丛书式整理一般按时代编排,在编纂形式上很难有所突破,不过这种方式有一个优点,即无论是节选抑或收录全本,都不存在“别裁”和“互著”的问题。读者手持一编,多省翻检之劳。类书式整理是编者对某一专科文献进行全面阅读后,根据宏观认识,形成一张严密的网,从而分门别类,将文献纳入这张网中。这一方法所录多为节选,完全打破了原文的时代、体例,根据自己“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命名类目,从而对既有文献进行自我改造。由此来看,丛书式整理的文本属于一次文献,而类书式整理的文本在依从原文的基础上带有强烈的编者个人学术色彩,介于一次文献到二次文献之间。严格来讲,无论是何种整理方法,其事实上并无高下之分。至于各自的缺点,也是比较明显。正如俞氏《中国历代画论大观》凡例云:“唯中国书籍,不能严格分类,兹不过取其大略以便排列而已。”[4]《中国画论类编》卷首语亦曰:“中国古籍,一时难加以科学之分类,兹仅略为区分,彼此混同之处尚多。”[5]“取其大略”“彼此混同”正点破了各自难以避免的问题,非经甘苦,无由道之,诚为智者良言。
从学术的承续来看,《辑要》并未采用俞剑华《中国历代画论大观》按时序收载原始文献的丛书型编纂方式,而采用了《中国画论类编》裁割文献而据类编排的类书型编纂方式。同时,《辑要》亦未踯躅于俞氏画学领域,而深耕于俞氏未曾涉及的印学领域,扩大了“俞剑华学派”的学术内涵。对此,笔者认为应是受到了两个因素的推动。
一是“俞剑华学派”潜移默化的影响。朱琪在《辑要》的“前言”部分写道:
我于2015年进入南京艺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跟随徐利明教授从事书法篆刻创作与理论研究。南艺素有搜集整理书画理论文献的学术传统。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开风气之先,后有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季伏昆《中国书论辑要》,皆为相关艺术门类理论著作的扛鼎之作。俞剑华先生是先师王一羽好友,二人时有诗题往还。周、季二先生则是导师徐利明的同事。今拙编《中国印论辑要》能够步武前修,使书、画、印三门姊妹传统艺术的理论工具书合为全璧,于我而言既是荣幸,也是一份不可推卸的职责。故在本书编纂过程中,对几位前辈的著作多有留心学习。[ 6 ]
这段话对俞剑华有着“开风气之先”之评。笔者认为,俞剑华的地位其实不止于此:尽管俞氏重点耕耘画学,堪为当代画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领域的“广大教化主”,但因其嫡嗣众多,流风所及之处,余脉于传统书画、篆刻领域文献皆有涉猎,影响力当不止于南京艺术学院(以下简称“南艺”)。其对当代整个艺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来说都是奠基式、标杆式人物,故而窃以为不是“开风气”一语所能道尽的。准确来说,以南艺为中心,学界对艺术文献的整理,尤其是类书式整理之风,皆可纳入“俞剑华学派”的范畴下予以考察。《辑要》自然亦作如是观。
二是篆刻研究内生逻辑的结果。40年来,以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为始,郁重今的《历代印谱序跋汇编》、黄惇的《中国印论类编》、黄尝铭的《篆刻语录》相继问世,篆刻文献的整理一直为印学家素所致力。就这里列举的几部著作而言,编者皆在“前言”部分对优、劣进行了精准的评价,兹不赘引。笔者想谈的是,凡古近文艺大势,每以创作发轫,评述继之,而以文献整理助推高潮。在各文艺类文献中,书画篆刻和文学有所不同,文学主要是文本文献,书画篆刻则有文本文献与图本文献之分。[7]这两种文献同时出现大型整理工作的时代,往往是书画、篆刻大盛的时代。聊而表之,如书法史上,两宋的文本文献《墨池编》《书苑菁华》和图本文献《淳化阁帖》《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几处同步状态。清代的文本文献《佩文斋书画谱》《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及图本文献《三希堂法帖》《金石萃编》亦处同步状态。上述两类文献并盛之际,亦是两朝书法昌炽的学术基础。篆刻一门亦然。明中期以后,作为图本文献的顾氏《集古印谱》和木刻《印薮》相继问世,文本文献则有甘旸的《印章集说》和徐上达的《印法参同》两部印论整理作为呼应。清代中期,浙、皖并帜,印谱呈现前所未有的勃发之势。文本文献的整理有鞠履厚的《印文考略》和桂馥的《续三十五举》乃至《四库全书》之庋罗与蜂拥般的印谱互为依衬。清末民初,印人灿若群星,审美边缘被拉到极致。随着金石学的流行和印刷革命的兴起,《十钟山房印举》《丁丑劫余印存》《明清名人刻印汇存》等图本文献的发展达到顶峰,文本文献也随着叶铭、吴隐之作和《美术丛书》的排印工作而愈加盛行,蔚为大观。近40年来,篆刻复兴,各大博物馆所藏玺印和私人印谱难以计数。文本文献之整理,如前文所述,亦相应地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局面。朱琪此前以《真水无香:蒋仁与清代浙派篆刻研究》《新出明代文人印章辑存与研究》《蓬莱松风:黄易与乾嘉金石学(附武林访碑录)》享誉学界,被韩天衡称为“年轻一代中理论与创作兼善的翘楚”。其以深厚的印学功底与精微的思辨能力,对历代篆刻的文本文献进行了深耕式整理,这符合艺术创作与文献整理同盛的内生性历史逻辑。
二、体现编者敢与历代名家论短长的学术魄力
在学术研究中,尤其在学理构建中,很多学者往往会陷入一种“需要主义”,即无论是否具备某类材料,亦无论此种材料占据何种分量,还是会强行无中生有或取重就轻,以配合理论的“美观”和“合理”。这是一种典型的教条行为,缺乏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就《辑要》而言,其分上、下两编,计27类。上编分“印道”“史制”“功能”“理法”“流派”“风格”“审美”“品评”“宗尚”“流变”“创新”“宜忌”“借鉴”“修养”14类,下编分“字法”“篆法”“笔意”“章法”“刀法”“修饰”“印内”“印外”“印人”“印谱”“器用”“钤拓”“艺文”13类。由前述引文可知,“有一分材料就说一分话”的余波尚在,窃以为可再加一条,即“有八分材料,经过学理思辨,也可适当地说九分话”。从《辑要》的分类情况来看,编者不仅秉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强行偶合对称之数,而且凭借敏锐的学术意识,在编排顺序和文献取舍方面匠心独运,真正达到了“说九分话”的效果,体现了引领印学体系建构的雄心壮志。
其在《前言》中曾自述曰:
古代印论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篆刻技法的总结,讲的是印章的形质塑造。另一方面是针对篆刻原理的阐释,主要对印章神采的品评,涉及审美内涵的部分。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关联密切。此外,由于篆刻从古代实用玺印发展而来,古玺印作为制度之器包含丰富的政治历史及器物学的信息,在篆刻艺术中多有保留与延续,尚不能割裂于印论之外。

从篆刻的研究情况来看,学界对这三个方面中的“篆刻原理”“印章神采”“审美内涵”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致力尤多,取得了较为丰赡的成果。然而,遗憾的是对第一方面和第三方面关注较少,存在诸多缺失。其一,篆刻技法属于“形而下”的范畴,具有强烈的匠人色彩,虽操刀者素所重视,但往往为治学者所摒弃。其二,历代印论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政治历史及器物学的信息”具有强烈的朴学色彩,往往为历史学家所关注,而艺术界则多有忽视。基于第一方面的现状,《辑要》将“钤拓”“器用”这些“远离学术”的材料各汇为类,意识是非常敏锐的。例如,笔者近来常关注“钤工”问题。在书法界,对书家之外的刻工、拓工的研究已非常深入,而篆刻界则往往只关注印人,对印章背后的其他参与者着墨甚少。实际上,善治印者虽多善钤拓,但未必尽然如此,历史上就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线索,如傅栻跋《西泠六家印谱》云:
是谱经始于辛巳春,竣事于甲申冬,各印半为亡妹隽儒(寯)、采儒(寀)手钤。两妹幼承庭训,性俱慧,知书史,嗜金石。长妹尤精摹拓款识,细密不爽毫发,予与次妹皆不逮焉。长妹适冯文卿大令(彬蔚),次妹适徐伟卿茂才(藜青),三年中均罹产难,谱成而两妹不及见矣。附缀数言,益深手足之痛。[ 8 ]
傅跋不仅高许了二位亡妹,尤其长妹“细密不爽毫法”般的“手钤”技艺,而且手足悲恸之心亦昭然于肺腑,读之不禁令人神伤。实际上,结合笔者搜集的材料来看,除了印人自身之外,篆刻的钤工、拓工还往往假手幕僚和朋友,而以印人的女性至亲居多,这可能与其心思天然细腻、缜密有关。尽管因篇幅所限,这些材料并未被《辑要》尽录,但相信读者自能在这样的分类基础上举一反三,获得进益。同时,基于第三方面的现状,《辑要》不仅辑录了不少先秦、两汉时期的著述,而且辑录了不少枯燥乏味的史学文献,这一点非常大胆。如果说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中国任何一门文艺门类都必然会追溯到的文献,“印道”类中的《吕氏春秋》《淮南子》、“史制”类中的《东观汉记》《后汉书注》、“功能”类中的《周礼》《汉官仪》则属于印学所独有。至于史学文献,则取用了不少诸如许慎的《说文解字》、陈寿的《三国志》、王鸣盛的《蛾术编》等古籍。这些文献通常是不会引起一般篆刻学习者注意的,不过篆刻本身自带朴学色彩,这注定在构建篆刻理论体系时,对此不得不着墨。《东观汉记》力倡的“符印所以为信也,所宜齐同”原则即为一例:
上以援为伏波将军。援上言:“臣所假‘伏波将军印’,书‘伏’字‘犬’外向,‘成皋令印’,‘皋’字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一县长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为信也,所宜齐同。”荐晓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国印章。奏可。
编者将中国印论的时间上限推到先秦、两汉时期,同时辑录了不少史学文献,是在文献学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上充分发挥其敢于破冰的学术魄力,否则很难从事此类追本溯源的工作。
俞剑华的《中国画论类编》汇编了我国历代画学文献,并将其分为“泛论”“品评”“人物”“山水”“花鸟畜兽梅兰竹菊”“鉴藏、装裱、工具和设色”六大类。尽管此书辑录了不少罕见的文献,但从分类情况来看,主要是根据文献内容列为大类,缺少系统而精到的学理思辨。相比之下,朱琪的《辑要》从印道、史制到借鉴、修养,又从字法、篆法到器用、钤拓,对历史所遗数百万言的印论取精用宏,充分发挥“互著”“别裁”之法,挥斤运斧,横批纵斫,建构了其独到的中国印论分类体系,体现了敢与名家论短长的学术魄力,不啻为“俞剑华学派”的后出转精之作。
三、彰显“有述有作”的文献学特点
“述而不作”是孔子重要的文献学思想,即整理古文献时只应转陈,不宜对其进行自我解读,要相信并尊重古文献遗产。如果严格按照这一原则进行文献整理,可能当前最好的方式是以丛书式编纂影印原始文献,连标点、简化、注译的工作都不可用。而为节约成本计,数字化甚至是践行这一原则的最佳方式(按:这也是这一方式在当前文献学界得以盛行的主要原因)。不过按此推论,古籍整理似乎是一件可以不用学人亲自参与的事情。事实当然不是如此。一方面,于学者而言,有着利用文献、发覆己见的需求。另一方面,于读者而言,亦有着“鼎尝一脔”(按:此为《辑要》“前言”部分编者语)、迅速获得所需文献的需求。因此,采用“俞剑华学派”的类书式编纂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
从对文本的整理情况来看,《辑要》的“述”最能体现编者的文献功底。因为体例原因,为便于阅读,《辑要》只是在每一则后方注明作者和文献来源,而将版本情况统一纳入书后的“参考文献”,这是一种为读者考虑的做法。从“参考文献”来看,编者尽最大可能找到了原始文献近五百种,在这数百万言的古籍中披沙拣金,洋洋洒洒,从容归类,不失方寸。因为笔者近来修订旧稿时需要复核大量文献,《辑要》又是第一时间得置案头,因此算是最早使用该书的人之一。于是笔者将修订时用到的一次文献同这一准“二次文献”复核近百条,竟未发现有明显的讹、脱、衍、倒之病。其依循原文不径改的“述”的功夫的确值得称赞。
《辑要》的“作”则是继承俞剑华整理方法的重要表现,也是笔者认为最精彩的部分。一方面,《辑要》遵循要言不烦的原则,对原文涩难之语和版本情况等进行了注释。如注人名者,并不一一详注,也不以人名生平之繁简作为注释标准,而是根据正文中的情况予以酌情处理——在正文中一带而过的人名为简注,有重要表述的人名为详注。日常熟知的人名为简注,非熟知的人名为详注。如注罗振玉《传朴堂藏印菁华序》“有晋之世,嵇叔夜始自为锻工,戴安道博综群艺,手镌《郑玄碑》”一句中的“嵇叔夜”和“戴安道”即有区分。具体来说,注“嵇叔夜”为“指嵇康”,注“戴安道”为“戴奎,东晋谯郡铚县人,字安道。少博学能文,善鼓琴,工书画。因不乐当世,故屡召不仕”。如此作注,真正做到了有的放矢。同样,对罗振玉此序的版本问题,编者又注曰:“罗振玉序作于1917年,《传朴堂藏印菁华》刊行于1925年,后1944年葛昌楹、胡淦合辑《明清名人刻印汇存》,亦移用此序。”如果注释“嵇叔夜”和“戴安道”的目的是被普通人所接受,对罗序版本的注释则是为专业研究者所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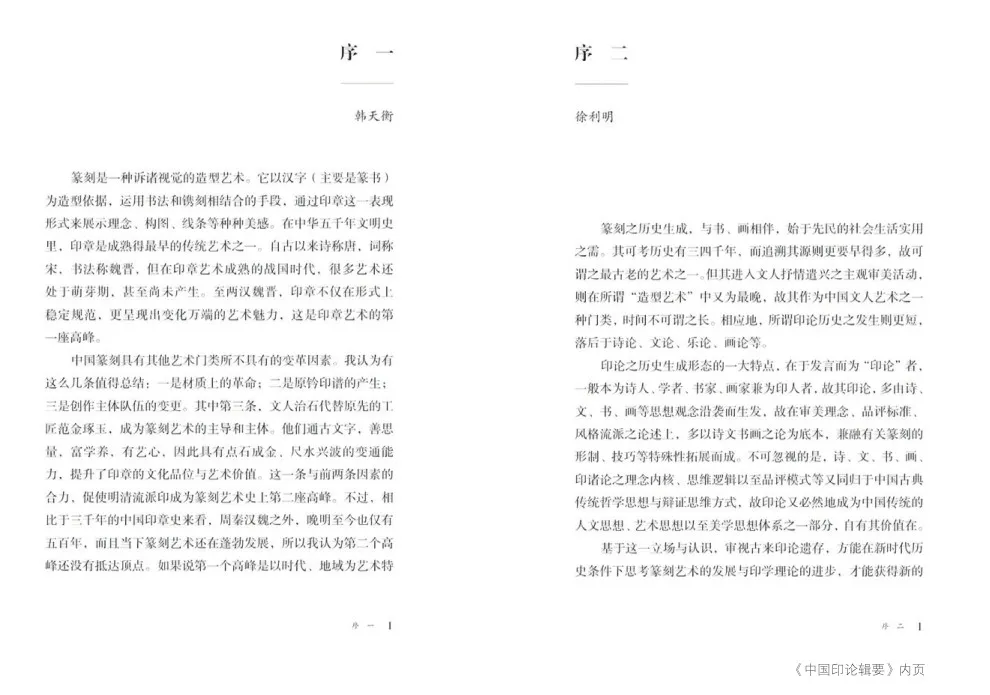
另一方面,《辑要》在27类的每一类之前都有一篇简短的导读性文字,旁征博引,点石成金,最能体现出编者的学术气质。《辑要》虽自陈上、下两编为“总论”和“分论”,但窃以为并无总、分之别——上编总体偏“道”,下编总体偏“器”,上编14类的“导读”需要强有力的思辨能力,下编13类的“导读”依赖丰富的篆刻实践经验。如上编“印道”导读有言:“中国艺术的哲学核心是道,篆刻亦莫能外,是故艺即是道,印即是道。道体现着中国印章的独特本质,也是篆刻艺术审美的内在依据。”“理法”导读有言:“道通则理通,理通则法通,法通则技通。”“宗尚”导读有言:“‘印宗秦汉’的思想酝酿于唐宋‘复古’思潮,肇始自宋代‘金石学’风尚,这一观念至少在北宋已然确立。”这些论点都是围绕篆刻本质进行的终极思考,非博览群籍、玩味摩挲是很难达到此般境界的。正如前文所述,篆刻因为有着天然的朴学色彩,使得印学研究在考证方面一直居于主力地位,而对篆刻的哲学质性问题鲜有人深入探究。《辑要》27类之首得名“印道”。以此领衔,正是编者过人之处。另如,下编“刀法”导读有言:“‘印从刀出’应当建立在作者具有丰富篆刻创作经验的基础之上,方能游刃有余,驱刀如笔,创造出与常规不同的篆刻之美。”“修饰”导读有言:“应当看到,篆刻审美的多元性决定了修饰与做印法存在的特殊价值,不应断然否定。”“印外”导读有言:“作诗与作印具有相近或共同的创作规律,都需要运意、言志、造境、移情,产生艺术魅力,最终激起欣赏者的共鸣。”非于刀、石之间长期浸淫,不足语此。朱琪作为篆刻家,既能做缜密不苟之学术考证,又能做胆大可佩之艺术创作。睹其《文字的魅惑:朱琪篆刻作品选》,笔者不觉精神为之一振,取法之博与约、构思之巧与拙、下刀之粗与细竟能一寓其间,始知天资不可强违,良有以也。无怪乎李刚田曾为其作品集作序云:“他的理论研究立基于创作,他的思考与研究最终又反哺了他的创作,这本作品集大概就是最好的反映。”[9]而《辑要》似乎也是朱琪的“双向反哺”在理论方面“最好的反映”。
文献整理和学术论著有所不同。前者以“述”为核心,一般以忠实文本为第一要义,为学界提供一批或文字稀见、或版本权威的文献是一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工作。后者以“作”为宗旨,一般以发覆己见为第一追求,努力做到言前人之所未言,从而推动学术的进步。而《辑要》“有述有作”,“述”是基本功,“作”是其最亮眼的地方。其中,注释部分承袭了“俞剑华学派”的特色,“导读”部分则凭借其优异的思辨能力和丰富的创作实践言他人之所未言,诚为“俞剑华学派”的新创获。一言以蔽之,《辑要》融述、作于一炉,充分发挥并突破了“俞剑华学派”的类书式整理方法,是40年来印学文献整理领域的重要成果。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辑要》采用了“俞剑华学派”特有的类书式整理方法,同一文献可能因具有不同的理论价值却只能编排于某一类目之下,使用起来需要留意,以免遗珠。与此同时,韩天衡在《辑要》序中提出了一个希望:“将来如有机会,朱琪可在此基础上再做精简,出版一本更为简明的《中国印论精要》,相信对于印人乃至普通篆刻爱好者而言更是一件幸事。”韩天衡自然是从大手笔作小文章的角度欲启广大愚蒙,而笔者作为一位普通研究者和文献使用者,反而希望“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朱琪能继续弘扬“俞剑华学派”的精神,以丛书式的编纂方式领衔新时代《中国印论集成》的编纂工作,让一般的印学研究者能自由于鼎中尝脔,挑肥拣瘦皆能一索即得。当然,这些都不是《辑要》本身的问题,而是文献整理方法抉择的必然得失。由此来看,古籍整理依然是摆在当前艺术学界乃至整个文献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不过,《辑要》的面世对印学文献整理风气的引领是可以预见的。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清代法书目录整理与研究”、2022年度四川省“天府峨眉计划”青年人才项目“中国书法文献学历史与理论研究”、2023年度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翁方纲书法文献学”阶段性成果。)
注释
[1]葛兆光.想起四十多年前那股学术的力量[N].文汇报,2023-5-23(10).
[2]翁方纲.《致李宗瀚》第三札[M]//沈津.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21.
[3]祝童.从《颐园论画》批跋论俞剑华早期中国画学[J].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23(1):33-38.
[4]俞剑华.中国历代画论大观·第7编[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2.
[5]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3.
[6]朱琪.中国印论辑要[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3.
[7]祝童.“法书”“法书目录”与“法书目录学”诠解[J].书法研究,2022(4):106-134.
[8]参见傅栻《再跋〈西泠六家印谱〉》,光绪十一年(1885)钤刻本。
[9]李刚田.观念·形式·个体——《文字的魅惑:朱琪篆刻作品选》代序[M]//朱琪,文字的魅惑:朱琪篆刻作品选.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