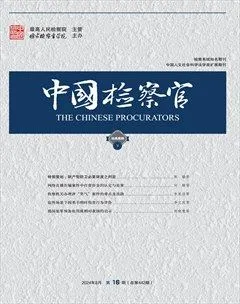杀人后临时取财行为的性质判断和占有认定
摘 要:命案发生后,部分行为人存在临时起意获取被害人财物的情况。张某杀害刘某后临时窃取其电子产品等行为即是其中一例。如何判断此类行为性质,则涉及到对抢劫、侵占合盗窃三种行为模式的理解。由于行为人实施暴力行为时尚无获取财物的主观意图,该行为不符合抢劫罪构成要件。杀害被害人后,行为人并不自然获取被害人生前财产的占有,故不成立侵占罪。虽然不能认为被害人死后的占有归属其继承人,但应当认为被害人的生前占有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有限延续而构成盗窃罪。
关键词:占有 杀人 临时取财 行为性质
一、基本案情
2021年1月,行为人张某与被害人刘某通过聊天工具结识后,约定在刘某住宿的杭州某快捷酒店见面。根据行为人称,二人系商谈嫖资金额未果而发生口角,张某离开时认为遭到被害人鄙视而心生怨恨,遂在饮酒并准备刀具等凶器后再次回到刘某房间并发生激烈争执。期间,张某双手紧掐刘某脖子致其死亡。杀害刘某后,张某在整理被害人刘某的衣物时发现其行李箱里放置着一些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遂又临时起意,从其行李箱内窃取两部手机、一部平板电脑后潜逃至异地,对外销赃后得款人民币三千余元。
二、分歧意见
张某杀害刘某,当然构成故意杀人罪。但杀害被害人之后,又临时起意取得了死者财物应当如何定性?对于这一问题,虽然司法解释在先期有规定[1],但在理论和实务判断中,存在较大分歧。
第一类意见认为,张某构成抢劫罪。该意见的理由是,张某虽系临时起意,但事前已使用暴力,取财时亦对其事前的暴力行为有所明知及利用(即取财行为与杀害被害人之间的暴力具有刑法上的因果联系)。故而,张某的行为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
第二类意见认为,张某构成侵占罪。本案中,刘某的死亡即导致其丧失对手机、平板电脑等物品的占有。此时,张某已经取得了对财产的占有权。由于张某将非法占有转化为非法所有,因此应以侵占罪定性为妥。当然,也有极少数的人认为,由于死者遗留的财物难以认定为遗忘物,故主张临时起意取财的行为应当无罪化。[2]
第三类意见认为,张某构成盗窃罪。侵害对象的认定也存在三种不同认识:第一种观点认为刘某被害后丧失占有,但财产已经转移至其继承人所占有,故张某侵害的是死者刘某继承人的观念占有。第二种观点也认为被害人死后丧失占有,但此时刘某财产占有已自然转移至其临时住所的控制人,故行为人侵害的是刘某临时住宿的快捷酒店占有。第三种观点认为,需要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承认死者生前的占有,故张某侵害的仍然是刘某本身的占有。
三、法理评析
犯罪是违法和责任相统一,结合人们对刑法中“占有”的一般认知,我们同意第三类意见中的第三种观点,即认为:行为人张某的事后取财行为构成盗窃罪,其所侵害的仍然是占有。这种占有并非死者继承人的占有,也排除评价为酒店的占有,而是死者本人生前的整体占有,理由如下:
(一)抢劫故意的排除
得出抢劫罪定性的基础,是将抢劫看作暴力行为和取财行为的前后统一过程,认为张某使用了导致被害人无法反抗的暴力行为(即杀害被害人),取财行为系利用了该事前暴力,二者之间具有可归责的因果联系。同时在主观上,张某取财时对自身的暴力行为亦有明知。于是,顺理成章的就得出如下结论:如果行为人杀害被害人后,又“利用这种压制状态而夺取财物要成立抢劫罪”。[3]
不过,认定行为人构成某种犯罪,必须就行为人的主观意志和客观行为得出一致性的结论。就对行为人是否构成抢劫罪的判断而言,其暴力行为与事后的取财结果之间,应当具有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必然联系,即:行为人先前的杀人行为是其获取被害人财产这一目的的手段。易言之,行为人构成抢劫罪的前提是,其暴力行为系受到自身图谋钱财的主观意志所支配,并因该暴力而导致被害人死亡(即达到抢劫罪中不能反抗的后果)。
在本案中,行为人掐死被害人的理由与其箱子里的财物无关。虽张某事后窃取财物利用了自身的暴力行为,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仅仅存在于暴力结果客观作用上,而非主观的手段和目的上。既然行为人暴力行为并不具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财产的主观故意,将其评价为抢劫罪就存在主客观不一致的问题。况且,行为人的杀人暴力已经被故意杀人罪所评价,而认定行为人构成抢劫罪,势必要再次将原有的暴力行为认定为抢劫罪构成要件中的内容,也实有重复评价之嫌。
(二)继承人占有说和场所控制者占有说
相对与抢劫罪,侵占罪和盗窃罪的观点分歧主要集中在被害人死亡后财物占有状况的认定结论存在差异。一般认为,如果行为人侵害了他人的占有,则应当盗窃罪定性。若未侵害他人的占有,仅仅是将占有变为非法所有,则可能构成侵占罪。[4]因此,只要存在他人占有的情况,无论是否是被害人自身所占有,行为人的行为都侵害了他人占有的基本权能,就应当评价为盗窃罪,否则即应认定为侵占罪。对于他人占有的情况,存在继承人占有、酒店占有和死者生前占有三种不同观点。对此,笔者将进行逐一分析,只有认为上述占有都不存在时,才能构成侵占罪。
继承人占有说。认为属于其继承人占有的观点认为,因杀人而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死者的财物应当由继承人占有,因为占有不仅是指实际占有,也包括观念占有,而继承人的占有即属于观念占有。[5]这是我国台湾地区司法实务和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近期在我国大陆也颇有学者认同这种理解。依照这种观点,本案合逻辑得出的结论是:因为张某窃取了死者的财产而导致了其继承人的观念占有受到侵害,因此也构成盗窃罪(有学者认为继承人的占有应当构成侵占罪,该观念不符合一般占有的理解,上文已经驳斥。[6]有反驳的意见认为,如果行为人没有继承人,是否就意味着无人占有。但持肯定论的意见可以辩解,称在无人继承的情况下,可以由国家承担相应的权能。不过,该观点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对刑、民两种法律关系中“占有”概念存在混淆。一般认为,民法上的占有,是一种类物权的概念,是以物的权属所有之下的一种应当保护的权能,其占有意思在各国并不相同,得出占有可以继承的结论主要还是依照各国涉及继承事务的法律规定而非占有事实。但占有意思和事实在却是刑法意义上的“占有”不可或缺的内容。[7]有论者称,虽然继承人不知道被害人死亡因而丧失占有,故死者遗留的财物可以视为继承人“遗忘”之物。[8]但是,即便是观念占有与物理占有存在差异,但仍强调在规范、社会的要素上存在一定的占有意思和事实。完全忽略占有意思和占有事实,不仅会严重限缩侵占罪的空间,而且在继承人不知晓财产甚至是抛弃财产的场合下,被害人的占有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比如,在杀害被害人后,行为人并未即时取财,过后多年,有人发现相关遗漏财产后进行占有的,也应该认定为盗窃罪,这明显与有违一般观念。因此,认为继承人占有的观点因为不符合刑法中的占有概念,并不能排除侵占罪的适用。
场所控制者占有说。认为属于酒店占有的观点认为,被害人刘某死后,其房间内部的全部物品权属均转移至占有权能即随之转移,归属于其场所的真正控制者。
就本案而言,由于被害人系对酒店的临时租住而非长期租住关系,因此其房间实系酒店所控制而非其刘某的实际住所。当刘某居住时,该场所归刘某所控制,但在居住者离开时,其物品归酒店占有。这种占有存在两个明显特征:第一,除了旅客外,通常酒店还具有另一套旅客房间的钥匙或出入卡片,当居住者遗忘或遗失卡片时,可以向酒店借取房卡进入房间,这也是酒店支配力和占有意思的一种体现。第二,当顾客离开酒店后,酒店的服务员要对房间查房和进行清扫工作,如果发现有行为人的遗忘物,则自动归酒店占有并进行发还,如果有人拿走亦构成盗窃罪而非侵占罪。行为人因此至刘某死亡的那一刻起,其物品就转移至酒店所占有——即在其临时居住的酒店所概括支配的场所之内,进而使得酒店经营者实际上取得了占有事实。由此可见,被害人死后,其财产至少能够认定为属酒店占有——而非无人占有。由此得出的必然结论是,行为人杀人后取财的行为应定性为盗窃而非侵占。
(三)生前占有的探讨
虽然属于酒店占有的观点排除了本案侵占罪的成立空间。但在理论上仍然存在分歧:如果认定为酒店占有,其前提必须是死者自身已经丧失了占有,否则行为人侵害的便是死者的占有而直接认定为盗窃。在一些荒郊野外杀人后取财的案件中,这样的理论分歧就会影响行为人的最终处理。
认为人死后会丧失其对生前物品占有的意见,是日本刑法学界相当有力的观点,相似理论在国内也有部分知名学者认可。[9]仅仅从逻辑上说,死者本身已经无法解释为刑法中的“人”,因此认定死者丧失占有的观点的确最可自圆其说。但是,这样的结论与当前社会公众的认知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特别是在类似本案——行为人自己杀害他人又临时起意取得其财物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其先前的杀人行为而将改变行为性质,似乎精巧的逻辑推理并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因此,仍有许多学者基于社会的一般观念,在一定的场合下承认死者的占有。比如认为被害人在家中被杀害这一特殊场合,因为“家中的财物都属于在家人特殊控制下的财物”而认定为盗窃。[10]也有观点则笼统的认为,“死者自身也可以成为占有的主体。”[11]上述简单的将占有归结于死者的观点与刑法上的占有理论存在矛盾,实际是将“占有”的概念空洞化——无论是在理论根据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无法自洽,还容易招致不符合罪刑法定需求的批判。
既要达到理论上的自洽,更需要在现实中得出合理结论,只有将物品的“占有”归结到死者的生前,即:在行为人杀害被害人后当场获得财物的有限场合,将被害人的占有(系其生前占有而非死者占有)评价至其死后的有限时间。这种观点的逻辑性理由主要包括:第一,被害人的死亡是一个从占有到丧失占有的动态过程,需要从规范的立场加以评价,从大多数命案形成的证据看,死者被致死暴力袭击后,常常有一个抢救的过程,导致其死亡证明时间通常要明显晚于行为人的杀害行为时间,因此从行为人的致死暴力与死者完全丧失占有之间,存在规范上可滞留的余地。当然,这种规范中可滞留的空间与行为人的杀害被害人的工具、地点、手段等密切相关,需要个案判断。因此,部分学者批判的所谓把“杀害被害人86小时后取走财物的认定为盗窃罪,而把杀害被害人9小时取走财物认定为侵占罪的判决”[12]并非一定无理。第二,被害人的死亡(即其所谓的“丧失占有”)结局,与行为人的暴力之间存在客观上的紧密因果关系。尽管行为人在实施暴力行为时主观上没有要使得被害人丧失占有的意志,但行为与丧失占有的因果关系并不因此而断裂。第三,从罪刑均衡的角度出发,行为人对被害人采取致死暴力后又临时起意事后取财行为在刑法上的否定评价,至少不应低于没有使用致死暴力(即被害人因没有死亡而不丧失占有)后再行取财的行为。如果行为人杀人取财后所承担的后果要低于一般盗窃行为,其形成的结论不符合公众的基本认知。
从上述逻辑分析看,得出死者生前整体占有的结论须遵循两个前提:第一,死者的死亡结果系行为人自身暴力所导致,如第三人杀死被害人后,行为人再窃取财物的,不能将死者生前的占有整体评价。第二,行为人的杀人行为与其获取财物的行为之间具有时空上的紧密性,即在空间上需要与其杀害行为具有强烈的关联性,时间上具有必要的承继性。在本案中,张某本人杀害刘某后即在整理其衣物时发现并窃取死者生前的财产,符合上述两个将死者生前占有整体评价的基本要求,可整体评价为侵犯了死者刘某本人生前的占有。由于占有中的支配地位具有排他它性。因此,行为人张某可以侵犯刘某本身生前占有而排除了酒店占有而构成盗窃罪。
综上,笔者认为,行为人张某除了构成故意杀人罪外,还构成盗窃罪。本案起诉至法院后,一审法院支持了上述观点。被告人不服判决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并经最高法核准,目前行为人已经被执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