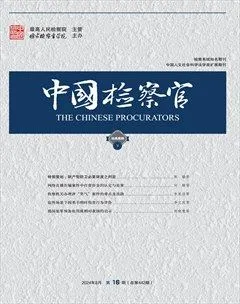网络直播诈骗案件中打赏价金的认定与处置
摘 要:行为人谎称进行不法交易而骗取打赏价金的,被害人虽不具有返还请求权,但并不影响财产损失的成立,应坚持“违法判断多元性”理论,认定为诈骗犯罪。在计算犯罪数额与处置非法所得时,需根据打赏价金性质准确区分,将不法原因给付之物、联结阶段自愿打赏和直播平台抽成全部计入犯罪数额,并对不法原因给付之物予以没收,同时从是否尽到注意义务角度审查直播平台善意与否,平衡第三人与被害人利益,促进营商环境优化。
关键词:直播打赏诈骗 财产损失 犯罪成本 不法给付
一、网络直播诈骗案件中打赏价金的认定争议
[基本案情]被告人王某、邓某某、张某(另案处理)预谋成立直播公司,由主播在直播过程中以暧昧语言、性暗示等方式引诱并许诺直播间观众打赏礼物后可添加主播微信好友,后续由运营人员接替主播通过微信聊天,虚构打赏礼物即可获得女主播的性陪侍,骗取他人财物。邓某某先后成立两家传媒公司,并陆续招募运营与主播多人开展诈骗,所得的非法收入由抖音平台抽成50%后,公司内部按比例分成。被告人通过上述手段骗取被害人翟某、付某等93人共计人民币390424.4元。案发后相关涉案人员向10名被害人退赃14万余元并取得谅解。
辩护人认为,一是本案被害人刷礼物的目的是为与主播发生性关系,是因不法目的而遭受的损失,具有一定过错,不应过多保护其权益;二是以运营人员接替主播添加微信聊天,虚构打赏礼物即可获得性陪侍为界,前期被害人自愿打赏的目的是加微信,而刷完礼物后也确实加到了微信,这一阶段并不构成诈骗,相关打赏数额不应计入犯罪数额;三是公诉机关认定的诈骗数额中,包含被抖音平台的抽成数额,该抽成部分被告人并未实际获得,不应计入诈骗数额。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某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被告人邓某某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其余被告人略)。对被告人的犯罪所得(扣除已自愿返还被害人的部分)予以追缴,上缴国库。[1]
网络直播诱导打赏行为具有一般民事赠与行为或服务对价行为的外观,实践中对于打赏行为与打赏价金的认定具有较大争议,民法与刑法的规制界限不清。本案存在争议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不法原因的打赏价金的性质及财物处置问题;二是虚构打赏礼物可获得女主播的性陪侍前,被害人自愿打赏部分是否应当在犯罪数额中扣减;三是打赏价金中被直播平台抽成部分是否计入犯罪数额,以及抽成部分如何处理。
二、基于违法判断多元性理论界定骗取不法给付行为的性质
不法原因给付之物的取得者无法获得该财物的所有权,《民法典》亦未对不法给付主体是否具备返还请求权作出明确规定,在谎称进行性交易而骗取打赏的案件中,基于不法原因而给付的行为如何认定,这部分财物有无刑法保护的必要及后续如何处理尚有争议。
(一)骗取不法原因给付行为入罪分析
违法判断多元性理论认为,民法上的权利关系对于刑法上财产犯罪的认定并不重要,对于民法不予保护的利益,刑法也可以根据自主目的予以保护。[2]本案中被告人谎称进行性交易而骗取财物的行为构成诈骗罪。首先,在骗取打赏的场合,正是由于主播一方在先的欺骗行为,被害人一方才处分财物,如果不是受骗,被害人便不会进行打赏。其次,即便打赏是基于嫖娼等不法原因,但在打赏之前被害人合法占有相应财物,其打赏的价金在因受骗而给付之前并不具有违法性,值得刑法进行保护。最后,虽然被害人因不法目的而打赏,但这一原因并不能降低犯罪者的不法程度。“相反,利用非法的关系进行诈骗,其手段甚至比一般的诈骗在恶性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刑法不将其认定为犯罪是难以让人接受的。”[3]如果对于那些通过违法的内容来欺骗被害人并使之交付财物的行为不以诈骗罪处罚,无异于给罪犯指明了逃避刑事制裁的方向与手段。因此,在虚构不法交易骗取打赏的案件中,打赏者的利益应当受到刑法保护,行为人通过欺骗行为侵害了打赏者的财产,构成诈骗罪。
(二)不法原因给付物处置的实践检视
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处置“谎称进行不法交易而骗取的财物”分歧明显。本案中法院是以“是否自愿返还被害人”为区分条件,仅将未返还部分予以追缴。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诈骗罪”和“提供性服务”为关键词检索2021年至2024年7月的裁判案件,并从中随机抽取30份裁判文书,经过统计发现:判决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的有14件;判决被告人退赔未退赃款,发还被害人的有9件;被告人在侦查或者审查起诉阶段主动退赔的有7件,其中5件获得被害人谅解,2件未明确说明。
笔者认为本案做法的合理性有待商榷。对于被骗款项的认定,并不能改变给付物的性质。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嫖娼行为在行政法上被禁止,嫖资属于应当予以追缴、没收的违法所得。在刑法上,患严重性病而嫖娼的构成传播性病罪;在公安机关查处嫖娼活动时,为违法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构成窝藏、包庇罪,无不体现了刑法对于嫖娼行为的否定性评价。本案中的被害人以获得性陪侍为目的打赏相关价金,其主观目的是嫖娼,不能因为“打赏礼物可获性陪侍系主播虚构”这一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从而认定其给付行为的合法性,即被害人被欺骗的事实并不影响打赏价金是嫖资的非法性。若在认定被告人构成诈骗罪的同时,将嫖资认定为被骗取的合法财产,被告人对嫖客负有退赔义务,司法机关也对扣押的嫖资负有返还义务,甚至被告人为了从轻处罚还要取得嫖客的谅解,这既违背民众的常情、常理、常识,又会导致对违法犯罪行为打击不力等消极后果。因此,被害人基于不法目的向被告人给付财物的行为,如果违反了行政法规,为法律所禁止,那么对于该部分财物应当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三、依据固定化犯罪模式认定联结阶段打赏价金的性质
本案的诈骗模式可以类型化为“直播筛选特定诈骗对象——实施诈骗行为——卷款跑路”三个阶段。在直播筛选特定诈骗对象的联结阶段[4],被告人并未实行诈骗行为,此时,对于被害人的打赏能否认定为赠与行为或者服务对价行为,该部分财物是否应当从犯罪数额中核减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被害人出于自愿打赏主播,并在打赏后如愿添加了主播微信,打赏目的已然实现,其本质是附条件的赠与行为,并不存在财产损失,该部分打赏金额应当扣减。另一种观点认为,联结阶段直播的目的在于筛选诈骗对象,直接为犯罪服务,此阶段所获收益也是犯罪所得,不应进行扣减。笔者认为,联结阶段自愿打赏系犯罪预备行为影响下的财产处分,应计入诈骗犯罪数额。
(一)联结阶段自愿打赏系犯罪预备行为影响下的财产处分
表面上看联结阶段自愿打赏是被害人出于添加主播微信而进行的赠与,属于合法的民事行为,但理解其本质必须从这一行为在整个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本案中被告人前期的直播活动是为了从平台的用户群体中筛选出特定的诈骗对象,其犯罪模式为引诱被害人打赏大额礼物添加微信好友,后续进一步实施具体的诈骗行为,即“首次大额打赏+后续多次打赏”,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因此,被告人联结阶段的直播活动直接为犯罪服务,其本质是为犯罪的实行创造便利条件的预备行为,而非合法民事行为。鉴于此,被害人无论基于何种目的打赏,其都处于被告人预先设定的骗局中,联结阶段自愿打赏系犯罪预备行为影响下的财产处分,应计入诈骗犯罪数额。
(二)任何人不因不法行为获利
法谚有云:“任何人不得从其违法行为中获利。”利益的取得要通过合法方式,违法行为不能获利。如前所述,被告人自直播伊始就预谋犯罪,其在联结阶段的直播行为直接为诈骗犯罪服务,是犯罪模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此外,单就直播行为本身而言,以性暗示方式引诱平台用户本就已经违背《网络主播行为规范》和《抖音用户服务协议》,是网信办部署“清朗”行动集中整治的行为。如果人们可以从自己的不法行为中获利,会形成反向激励,诱使民众通过非法行为来追求利益,这无论如何都是法律所不能容许的。因此,对于这部分的财产收益,不应得到司法的保护和支持。
四、以基础法律关系厘清直播平台抽成性质
在直播打赏中,直播平台会收取打赏价金的50%作为手续费,被告人实际所得与被害人损失差距较大,因而直播平台抽成是否计入诈骗犯罪数额对于罪行轻重具有较大影响。一种观点认为,在直播打赏中,被害人和被告人均明知直播平台会抽成作为手续费,对于这部分费用被害人既不存在财产损失,被告人也无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因而应当在犯罪数额中扣除。另一种观点认为,平台抽成的手续费属于被告人使用直播平台的费用,是其违法犯罪活动所支出的直接成本,不应从诈骗数额中扣除。笔者同意后者观点,直播平台抽成的手续费不应从诈骗数额中扣除。
(一)直播平台抽成的手续费属于犯罪成本
本案中王某及邓某某招聘主播入驻抖音平台,实际上与抖音平台形成了网络服务合同关系,由平台为主播提供直播媒介,主播使用平台的技术服务及用户资源,通过平台提供的引流推荐、充值打赏、互动交流等多项功能来获取经济利益。在打赏价金的分配上,用户将在平台充值购买的虚拟礼物赠送给主播后,平台会按照事先约定的比例与主播进行结算。直播抽成实质上属于主播入驻并使用平台的费用,于犯罪而言,是行为人将平台作为诈骗工具所应当支付的工具费用,属于犯罪成本,应一并计入犯罪数额。虽然第三方支付平台及银行转账也能实现类似功能,但通过直播平台打赏更利于实现诈骗目的。一是直播平台打赏可以取得被害人的信任,深化其有偿性陪侍的谎言,如若在取得财物环节要求被害人使用其他支付方式转账,易引起被害人警觉;二是在当前严厉打击“两卡”犯罪的高压态势下,短期内频繁私下转账易引起监管部门警觉,而用户打赏后通过平台结算获取财物能为犯罪行为披上合法民事行为外衣,便于逃脱罪责,躲避监管。正是基于以上便利,即使王某等人明知直播平台抽成比例高达50%,还是选择直播平台作为结算工具。尽管犯罪成本的多少会影响行为人实际获取的经济利益,但不能因为有犯罪成本就掩盖其真实的犯罪目的,行为人的行为就是围绕其目的实施的。此外,对于本案中平台抽成这种直接犯罪成本计入犯罪数额也有明确的法条依据可循。如最高法《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第3款明确规定:“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广告费、中介费、手续费、回扣,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不予扣除。”最高检印发的《检察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指引》在谈到诈骗数额认定时也指出:“犯罪嫌疑人为实施犯罪购买作案工具、伪装道具、租用场地、交通工具甚至雇佣他人等诈骗成本不能从诈骗数额中扣除。”
(二)善意取得原则在诈骗追赃中的适用
以犯罪成本认定直播平台抽成的性质必然涉及该部分财物的处置问题。近年来电信网络犯罪频发,由于侦查取证难,涉案财产权属、来源无法查清等问题,追赃挽损工作存在不少困难。电信网络诈骗赃款流入网络直播平台的现象较为普遍,一些办案机关根据赃款流向,以直播平台体量大、资金充裕而易追赃为由,直接查封扣押网络直播平台账户,并将资金用于弥补被害人财产损失的现象客观存在。[5]然而这种追赃模式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两高”《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已经明确“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对于本案中直播平台的抽成是否追缴,关键看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善意取得诈骗赃款,即需要关注直播平台是否“善意”及“支付合理对价”。对于前者,在根据举证责任对直播平台进行善意推定的前提下,需审视直播平台是否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本案中用户的充值打赏呈现长期、多次的显著特征,并无金额畸高情形,平台通过审核准入资质、完成信息备案、落实实名制规定、进行消费提醒等操作,已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另外,网络直播平台流量大、充值打赏多,要求其逐个核实并不具有现实可能性。对于后者,纵观整个直播活动,直播平台不仅承担技术研发、平台搭建、营销推广等前期成本,在每场直播中还要提供网络技术服务和运营维护,于打赏金额而言应属于“合理对价”,不能因为用户长期、多次打赏的总金额较高就认为打赏行为超出了“合理价格”。
网络直播作为借助互联网和移动终端技术而生的新兴行业,是娱乐业态下的新趋势,不仅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互联网经济火热的背后是十不存一的惨烈竞争,从2016年“千播大战”席卷大江南北到2018年仅剩下几十家直播平台还在正常运营[6],倒闭的不乏熊猫TV这种头部平台。数据显示,斗鱼和虎牙两个平台的直播收入占全年营业收入的比例一度超过90%[7],如果不加以区分,一味要求平台承担责任,将不利于该行业发展。因此,诈骗案件中办案机关在维护被害人利益追赃时,应当审慎衡量判断网络直播平台是否规范经营,是否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从而妥善保护网络直播平台的合法收入,维护交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社会的变迁及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导致基于血缘和地缘的情感获取缺失,网络直播的出现填补了这一空缺,成为网民情感寄托的理想平台。但不法分子利用网络交往的数字化、虚拟性、匿名性,虚构情境诱骗消费者,并逐渐发展成为新型诈骗手段,肆虐横行;又因其隐匿于直播打赏等合法民事行为外观之下,给公众财产安全带来威胁。因此,实践中对网络直播诈骗打赏价金的处理必须抽丝剥茧、准确定性,既做到严惩电信网络犯罪,又平等保护被告人、被害人、直播平台三方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