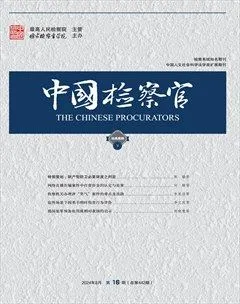罪刑法定原则下非列管麻精药品犯罪的认定方法
摘 要:行为人实施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等行为作用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其他物质在案发时未列入有关机关发布的管制目录,但只要行为人认识到该麻精药品具备毒品的麻醉、兴奋、致幻、成瘾等功能,即使案发时该麻精药品未列管,无论行为人是否明知其未列管,也不影响毒品犯罪故意的成立。该行为由于具备毒品犯罪不能犯未遂的成立条件而构成毒品犯罪的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益片面追求打击效果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采取类推解释将非列管麻精药品解释为毒品,从而将该行为认定为毒品犯罪既遂。
关键词:毒品 麻精药品 管制目录 罪刑法定原则 未遂犯
一、基本案情
2022年9月的一天,被告人彭某某向被告人乐某某,以3万元购买100克的“K粉”。被告人彭某某与被告人周某某(彭某某之妻)以每克800至90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吸毒人员杨某某等人。2022年10月10日,因吸毒人员向彭某某反映,在彭某某处购买的“K粉”质量差“不上头”,彭某某遂前往成都找乐某某换货。2022年10月24日9时许,彭某某联系乐某某以4.5万元购买150克“K粉”,周某某驾车前往成都找乐某某拿到“K粉”后驾车返回绵阳,途中被公安民警挡获,民警从周某某驾驶的汽车内查获疑似“K粉”3袋共计147.71克。之后民警从彭某某与周某某的住所内查获疑似毒品“K粉”40袋共计37.84克。经检验,案发时公安机关从扣押的疑似毒品“K粉”中未检出氯胺酮、氟胺酮,检出乙基氟胺酮(未列入国家管制毒品)。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乐某某、彭某某、周某某明知是毒品予以贩卖,其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被告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系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故判决被告人乐某某、彭某某、周某某犯贩卖毒品罪。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乐某某、彭某某、周某某不服,以没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客观上贩卖的不是毒品,其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罪为由向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乐某某、彭某某、周某某将乙基氟胺酮当作毒品氯胺酮(俗称“K粉”)贩卖,因乙基氟胺酮未被国家列管,属对象的不能犯。但乙基氟胺酮具有与氟胺酮相似的效应,将乙基氟胺酮当作氯胺酮贩卖,同样对法益造成了具体的危害,乐某某、彭某某、周某某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但属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参照氯胺酮的量刑数量标准,乐某某、彭某某、周某某贩卖毒品的数量较大,依法应予惩处。首先,乐某某、彭某某、周某某贩卖的乙基氟胺酮属未被国家列为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品或精神品,但乙基氟胺酮与氟胺酮(氯胺酮)不仅外形相似,且效用相仿,吸食后均具有使人兴奋、头昏、意识麻木等症状,对公民健康足以造成现实的危害。其次,案涉乙基氟胺酮属新型化学合成类物质,案发时虽尚未列管,但乐某某在与彭某某交易时,是将乙基氟胺酮当做氯胺酮贩卖,彭某某从乐某某处购得乙基氟胺酮后,又以“K粉”名义向吸毒人员销售。根据乐某某、彭某某在实施贩毒行为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如将乙基氟胺酮称为“K粉”向吸毒人员贩卖,吸毒人员吸食后提出效果不好要求换货,乐某某与彭某某、彭某某与吸毒人员在交易时,均采取不合常理的隐蔽交易方式,足以认定乐某某、彭某某主观上将乙基氟胺酮当作毒品氯胺酮售卖。最后,如上所述,乙基氟胺酮虽未列管,但乐某某、彭某某、周某某在行为时已认识到其贩卖的物品具有毒品类似功效,贩卖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已造成现实的危害,对乐某某、彭某某、周某某贩卖乙基氟胺酮的行为应评价为贩卖毒品罪的未遂,故判决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乐某某、彭某某、周某某犯贩卖毒品罪。[1]
二、分歧意见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涉毒犯罪由于具备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历来是我国刑法惩治的重点,但上述罪名成立的前提是,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所作用的行为客体必须是毒品。根据《刑法》第357条第1款,“毒品”被界定为“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对于何为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3条第1、2款和《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第3条第1款,系指列入《麻醉药品目录》 《精神药品目录》《非药品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其他物质,上述目录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就最新的情况而言,2024年6月16日,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决定将溴啡等4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迄今为止,我国已列管多种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整类芬太尼类物质、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以下简称“麻精药品”)
在国家对麻精药品严格管控的同时,司法实践中新型麻精药品犯罪越发频繁地发生,即行为人对未列入管制目录,但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其他物质(以下简称“非列管麻精药品”)实施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等行为。此类行为能否被认定为相关毒品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极大的争议,如何认定其性质成为关键。该争议通常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毒品的界定,二是故意的成立与否。
毒品的界定具体是指非列管麻精药品能否被解释为毒品。具体到本案,未列管的乙基氟胺酮能否被解释为已列管的氟胺酮存在争议。第一种意见认为,可通过运用扩大解释的方法,将乙基氟胺酮解释为氟胺酮。理由在于,乙基氟胺酮与氟氨酮不仅在化学结构和名称上类似,还具备相同的麻醉、致幻、成瘾功能,另外还可以防止行为人通过规避氟胺酮的已列管性,制造类似毒品而逃避刑法打击。第二种意见认为,将乙基氟胺酮解释为氟胺酮属于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理由在于,既然《刑法》第357条第1款明文规定了“国家规定管制”一词,将某种麻神药品解释为毒品时则无法忽视有关机关制定的管制目录。既然乙基氟胺酮未被该目录列管,即使其与氟胺酮具备名称、成分和功能上的类似性,也无法被解释为后者,否则将成为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从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上述争议的影响在于:如果采取第一种意见,行为人的行为将构成毒品犯罪既遂,但如果采取第二种意见,行为人的行为则无法构成毒品犯罪既遂,是否构成毒品犯罪既遂取决于故意的成立与否。
故意的成立与否具体是指行为人是否具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毒品犯罪的故意。具体到本案,对于乐某某等贩卖乙基氟胺酮的行为可否被认定为贩卖毒品罪未遂,第一种意见认为,尽管乙基氟氨酮未列管,但乐某某等认识到了该物品对公民健康的危害性,具备贩卖毒品罪的故意,该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的不能犯未遂。第二种意见认为,由于乙基氟氨酮未列管,乐某某等明知该物品不是毒品,不具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该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罪未遂。上述争议的影响在于:如果采取第一种意见,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毒品犯罪未遂,但如果采取第二种意见,行为人的行为无罪。
由此可知,上述争议涉及毒品犯罪既遂、毒品犯罪未遂、无罪三种定性结论,对行为人在定罪、量刑上影响较大,有必要通过深入的探讨提出相应的犯罪认定方法。
三、评析意见
笔者认为,乐某某等人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未遂)。判断乐某某等贩卖非列管麻精药品行为能否被认定为贩卖毒品罪,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一)对以非列管麻精药品为行为客体实施的相关行为,在认定犯罪时应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不能以扩大解释之名行类推解释之实
不同于1979年《刑法》,1997年《刑法》取消了类推制度[2],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属于罪刑擅断主义的反面,在刑事司法领域旨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作为刑法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之一,对罪与非罪的判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审判实践中必须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包含排斥习惯法、明确性、排斥绝对不定期刑、禁止有罪类推、禁止重法溯及既往等具体要求。[3]其中禁止有罪类推是指,凡是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都应当禁止,但有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可以采取。
对于乙基氟胺酮能否被解释毒品,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能将乙基氟胺酮解释为毒品。第二种意见认为,不能将乙基氟胺酮解释为毒品。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认为不能将乙基氟胺酮解释为毒品。理由在于,将乙基氟胺酮解释为氟胺酮并非认定犯罪时可以采取的扩大解释,而是禁止采取的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这涉及到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别,该区别是解释刑法时罪刑法定原则是否真正受到遵守的试金石。类推解释是指超越了日常用语可能范围的解释[4],或者一般国民无法预测到的解释[5]。就日常用语可能的范围而言,由于乙基氟胺酮和氟胺酮的语词仅在“氟胺酮”上类似,而前者有“乙基”的前缀,无法硬性地认为乙基氟胺酮在氟胺酮可能的口语范围以内;就国民预测可能性而言,尽管对化工领域的专业人员来讲,在功能上将乙基氟胺酮理解为氟胺酮可能并非难以预测,但对我国一般公民而言,由于二者在用语上存在明显差异,化学式上也存在不同,作此解释明显超越了其预测可能性,使国民无法预测自己的行为在刑法上的意义和后果。因此,将乙基氟胺酮解释为氟胺酮属于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类推解释而不可取。尽管第一种意见以乙基氟胺酮与氟胺酮在成分和功能上类似等理由推导出对氟氨酮作扩大解释的必要性,但无论其理由如何充分,这种所谓的“扩大解释”在本质上都属于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而罪刑法定原则所禁止的类推解释,就其制定初衷和客观效果而言并不在于入罪上的扩大而是限制。
(二)应灵活、实质地解释非列管麻精药品犯罪的故意认识内容
对于乐某某等贩卖乙基氟胺酮的行为可否被认定为贩卖毒品罪未遂,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由于乙基氟氨酮未列管,乐某某等明知该物品不是毒品,不具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该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罪未遂。第二种意见认为,尽管乙基氟氨酮未列管,但乐某某等认识到了该物品对公民健康的危害性,具备贩卖毒品罪的故意,该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的不能犯未遂。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理由在于,在认定行为人是否具备毒品犯罪的故意时,不能机械、呆板的运用传统故意理论,认为只有行为人认识到其实施的行为所作用的麻精药品是已列管的毒品,才具备毒品犯罪的故意。这里首先涉及不能犯未遂的成立要件。尽管日本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严格区分不能犯与未遂犯,认为前者不构成犯罪[6],但我国和德国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认为不能犯未遂和能犯未遂均属于未遂犯的下位概念,由此构成犯罪未遂而可罚。[7]未遂犯的成立要件包括主观和客观要件,主观要件是故意[8],客观要件包括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行为、犯罪未得逞、犯罪未得逞是基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9]由于不能犯未遂与能犯未遂的成立要件在故意这一主观要件上完全一致[10],而能犯未遂与犯罪既遂的成立要件也在该主观要件上完全一致[11],因此,认定乐某某等贩卖乙基氟胺酮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的不能犯未遂,需要认定乐某某等具备贩卖毒品罪的故意。《刑法》第14条第1款将故意界定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这并不意味着故意的认识内容仅包括实行行为、结果和因果关系。相反,故意的认识内容较为复杂和多样,远不止于上述要素。第14条对故意的内容描述得较为简略是由法律条文所必需的简明性决定的,因而将故意的认识内容限制性地理解为实行行为、结果和因果关系属于对法律条文的误解。面对复杂的司法实践,须运用完整的故意内容判断行为人是否具备故意。关于故意的理论存在一定的争议,有容忍说、故意危险说、盖然性说等。[12]容忍说作为传统理论属于刑法通说,认为故意由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构成。故意危险说和盖然性说作为前沿理论,均认为故意仅由认识因素构成而无需意志因素,前者认为故意的成立需要行为人认识到客观构成要件实现的可能性,但后者认为故意的成立需要这种可能性达到极大的程度。根据刑法通说,故意的内容包括,行为人对某种犯罪所有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行为主体,实行行为,行为客体,结果,因果关系,时间、地点等行为情状)具备认识(此即认识内容),并对实行行为、结果和因果关系具备意欲(此即意志内容)。[13]而贩卖毒品罪中的毒品属于行为客体这一客观构成要件要素,该罪故意的成立则需要行为人认识到其贩卖的物品是毒品。诚然,某种麻精药品成为毒品的前提是其已列管,但这并非理所当然地意味着行为人必须认识到该麻精药品是已列管的毒品才具备贩卖毒品罪的故意。在此必须灵活、实质地解释贩卖毒品罪的故意认识内容。
尽管非列管麻精药品在成分和名称上与列管麻精药品可能存在一定的区别,但二者在功能(麻醉、兴奋、致幻、成瘾)、对公民生命和身体健康的危害性、诱发其他相关犯罪(抢劫罪、暴力犯罪、危险驾驶罪等)的可能性这些更为实质、深刻的对公民人身的影响和社会连带效应方面没有任何区别。此外,有关部门对麻精药品进行动态列管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而某些具备化工知识、技能和设备的行为人出于逃避打击的目的,利用列管目录的漏洞,通过修改已列管麻精药品基团、改变其化学式结构,不断“推陈出新”地制造新型非列管麻精药品,继而实施走私、运输、贩卖等犯罪行为。如果机械、形式地将毒品犯罪的故意认识内容解释为行为人认识到其行为作用的是已列管的毒品,将导致行为人对非列管麻精药品实施的贩卖等行为因欠缺故意而不构成毒品犯罪,最终将导致对非列管麻精药品实施的犯罪行为在社会上横行泛滥,不仅将侵害毒品犯罪的法益、违反刑法设立毒品犯罪罪名的初衷,还对我国公民的生命和身体、毒品管理秩序乃至社会大局稳定造成危害,甚至无意中姑息纵容行为人有意规避已列管性,将罪刑法定原则变成危害社会的工具。此即非列管麻精药品犯罪的处罚必要性。因此,应突破已列管性的局限、填补其在毒品犯罪可罚性上形成的严重漏洞和不当出罪的效果,将非列管麻精药品犯罪的故意认识内容灵活、实质地解释为行为人认识到非列管麻精药品具备毒品功能。只要行为人认识到其行为作用的麻精药品具备毒品的麻醉、兴奋、致幻、成瘾等功能,即使案发时该麻精药品未列管,无论行为人是否明知其未列管,也不影响毒品犯罪故意的成立。换言之,在行为人明知该麻精药品不是已列管的毒品(未发生认识错误)以及误认为该麻精药品是已列管的毒品(发生认识错误)这两种情形下,其都具备毒品犯罪的故意。上述论断的实质在于,毒品的内涵可分为麻精药品和已列管性两个部分,在非列管麻精药品的场合解释毒品犯罪的故意认识内容时,保留麻精药品部分而以毒品功能替代已列管性部分,将毒品的内涵变更为麻精药品和毒品功能,毒品犯罪的故意认识内容由此变更为行为人认识到麻精药品具备毒品功能。这是一种以本质替代形式的实质做法,也是由非列管麻精药品犯罪的处罚必要性决定的必然选择,对规制日新月异、千变万化的新型毒品犯罪具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效果。但必须强调的是,毒品内涵的变更仅在审查毒品犯罪的故意是否存在时适用,在审查毒品犯罪的行为客体是否存在时,必须回到毒品的原本内涵即麻精药品和已列管性,以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由此可知,对行为人实施的非列管麻精药品犯罪进行认定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第一,依据国家毒品管制目录。应当严格根据案发时最新的国家毒品管制目录对毒品的范围进行界定,不能随意超出目录的范围认定毒品。第二,遵守含罪刑法定原则在内的刑法规定和理论,并且灵活、实质、正确地运用未遂犯(含不能犯未遂)、故意、解释方法等刑法基本理论,认定犯罪时不宜过于机械、保守,但也不可过于激进而违反刑法规定及基础原理。第三,高度重视毒品的社会危害性。应当将毒品的社会危害性,包括其麻醉、兴奋、致幻、成瘾功能,对公民生命和身体健康的危害性,诱发其他相关犯罪的可能性,作为灵活、实质地认定毒品犯罪的根据。只有同时考虑上述因素,对非列管麻精药品犯罪的认定才能合法、合理。
本案中,由于乐某某等认识到其贩卖的乙基氟胺酮具备毒品功能,因而具备贩卖毒品罪的故意,同时已着手实施贩卖行为,由于乙基氟胺酮未列管而自始至终不可能既遂,具备不能犯未遂的所有成立要件[14],其行为据此构成贩卖毒品罪的未遂犯,可以比照该罪的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如果行为人对非列管麻精药品实施走私、运输、制造等行为,应当将该行为认定为相应毒品犯罪的未遂犯。
面对当前我国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层出不穷的严峻形势,将行为人针对非列管麻精药品实施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等行为认定为毒品犯罪的未遂犯具备以下合理性:既未通过将该麻精药品类推解释为毒品从而认定为毒品犯罪既遂以致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还可以及时、有效地惩治我国社会中不断发生的非列管麻精药品犯罪行为,防止行为人利用列管目录的滞后性逃避刑事处罚,填补刑法在新型毒品犯罪规制上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