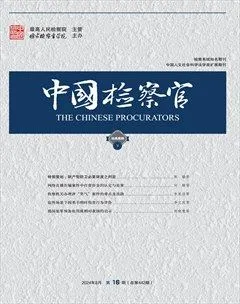论防卫过当中手段过限与结果归责的判断
摘 要:在防卫过当中,“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判断阶层;其中,关于“行为过当”的认定是判断“结果过当”的前提和基础。关于防卫行为是否符合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判断标准在于,防卫行为是否属于为有效制止不法侵害所必不可少的手段。在确定防卫手段过限的情况下,还需要进一步考察,重大损害结果是否可归责于过当的防卫行为。此处有必要引入结果避免可能性(或曰“合义务替代行为”)的原理。只有当事后证明,合乎限度的防卫手段确实能够避免重大损害发生时,才能从规范上将该结果归责于过限的防卫手段。
关键词:防卫过当 必要限度 结果归责 合义务替代行为
一、防卫过当判断的双层次结构
按照《刑法》第20条第2款的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属于防卫过当。如何理解“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即所谓“行为过当”与“结果过当”之间的关系,学界存在一体说和分离说之争。[1]笔者支持分离说,即主张“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是防卫限度中相互独立的两个判断阶层;其中,关于“行为过当”的认定是判断“结果过当”的前提和基础。理由在于:
第一,在关于防卫限度的判断中,将防卫行为从损害结果中独立出来,并使之居于优先地位,这是由正当防卫的本质所决定的。
根据紧急权的基本原理,行为所造成之结果的严重性具有一票否决紧急行为合法性的权能,这是以行为人对紧急状态所带来的危险负有一定忍受义务为前提的。例如,在攻击性紧急避险的场合,一旦避险行为造成的损害大于其所避免的损害,避险行为即属违法。这也就意味着,在此情况下行为人丧失了紧急避险权,他只能选择忍受危险。本来,根据法治国当中的自由平等原则,自我决定的权利与自担风险的义务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任何公民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危险都只能独自面对和承担,而不得“祸水东引”至其他无辜公民。只是,法律基于社会团结的思想,通过例外性地规定紧急避险赋予了遇险公民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取得社会其他成员照顾和帮扶的权利,从而容许其将一定程度的危险转嫁给第三人。因此,一旦法益均衡要件未获满足,那么要求遇险公民自行忍受损害,这不过是使其丧失某种超常的优待、回复至自担风险的平常状态之中而已,于情于理皆无任何不妥。
然而,正当防卫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如果说对于攻击性紧急避险来说,要求忍受危险是原则,允许行使紧急权是例外;那么就正当防卫而言,允许行使紧急权是原则,要求忍受危险是例外。因为,既然按照平等原则,任何人在行使权利和自由时均不得侵害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那么任何公民对自己所遭遇的非法侵害也就自始没有退缩和忍受的义务。从防卫人的角度来说,由于侵害人已率先违背了对自己所负有的不得侵害的义务,那么对等地,自己也就不再负有不得损害侵害人利益的义务;从侵害人的角度来说,他不仅在本可以避免的情况下制造了法益冲突,从而使自己陷入可能遭受损害的险境之中,而且也违反了不得侵害他人法益的义务,故其法益的值得保护程度较之于遭受侵害的法益来说,就出现了大幅“贬值”。总而言之,所谓“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实质上就是指权利人无需向对其权利地位发起挑战者让步。假如结果的严重性能够像在紧急避险当中那样,单独地发挥否定防卫行为合法性的作用,那便意味着,“在行为人只有通过采取具有造成严重结果之风险的手段才可能制止不法侵害的场合,他将在事实上丧失正当防卫权”[2]。遭遇侵害者也由此背负了吞下侵害所生之苦果的义务。这与正当防卫的本质是完全相悖的。
第二,既然正当防卫必然伴随着对暴力的使用,而且该暴力并非花拳绣腿般的“银样镴枪头”,而是始终担负着有效压制和排除不法侵害的使命,那么防卫行为就天然地或多或少包含着造成侵害人死伤的危险,就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确保侵害人的人身安全毫发无损,也不可能总是恰到好处地将结果控制在与侵害完全均衡的尺度内。所以,一旦法律准许公民实施某种防卫行为,它就必须连带地对该行为所包含的风险也一并予以容许,否则就无异于是对公民防卫权本身的否定。[3]
第三,2020年8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也基本采取了这一判断思维。其第11和13条分别规定:“认定防卫过当应当同时具备‘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两个条件,缺一不可。”“防卫行为虽然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的,不应认定为防卫过当。” 指导意见起草小组所撰写的《〈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的理解与适用》更是明确指出: “比较而言,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作为两个要件把握更为妥当,更符合为正当防卫适当‘松绑’的立法精神。”[4]
结合本案来看,虽然谢某等人已经骑上康某的摩托车并驶入公路,属于盗窃既遂,但康某此时仍可通过即时追击、拦截夺回摩托车,故应当认定不法侵害仍在进行、尚未结束。所以康某针对谢某所实施的击打行为,具有防卫的属性。现在的问题是:康某的行为是否符合正当防卫的限度要件?根据上述双层次结构说,防卫限度的判断应当分为两个步骤来加以分析。
二、防卫手段明显过限的判断标准
基于“行为优位”的防卫限度判断思路,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只要确定防卫行为适当,正当化的效果即可自动延伸覆盖该行为所引起的结果。即,“防卫的合法性原则上只取决于一点,即防卫行为处在必要性的界限之内,只要肯定了这一点,那么即便防卫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超越了为防卫所需要者,不论防卫人对此已经有所预见还是仅有预见的可能,该行为均属正当防卫。”[5]于是,防卫行为是否具有必要性,就成为防卫限度判断的枢纽所在。
笔者认为,关于防卫行为是否符合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判断标准在于,防卫行为是否属于为有效制止不法侵害所必不可少的手段。具体来说,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作为一名与防卫人具有相同能力、条件的公民,他在当时情形下还有没有比现实案件中的行为更为理想的其他防卫方案?如果行为人完全可以选择强度更小的反击措施,而且这样做既能达到同样的防卫效果,又不至于使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那他的防卫行为就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反之,若防卫人在现实防卫行为的基础上已退无可退,一旦减弱防卫的强度,要么无法保证能及时有效地阻止不法侵害,要么会增大防卫人本人面临的危险,则该行为造成的损害就属于侵害人必须承担的风险。[6]
结合本案来看,笔者认为,康某所采取的防卫手段超出了为制止侵害所必要的限度,理由在于:
第一,康某击打谢某头部的行为,并非为有效拦截谢某所必不可少的手段。在谢某已经骑上被盗的摩托车试图驶离现场的情况下,要及时、有效地夺回摩托车,就必须采取拦截措施,关键是要当即剥夺其继续行驶的能力。因此,撞击驾驶者或者摩托车迫使其停下,自然是行为人不可避免需要使用的手段,舍此之外并无其他更佳的选择。这时,既可以考虑使用棍棒等器械进行截击,也可以考虑驾驶其他交通工具进行撞击。在摩托车行进的过程中,突然对驾驶者或者车辆进行撞击,本身就极有可能导致驾驶者失去平衡而摔落,故这种手段必然包含了致其死伤的危险。在司法实践中,曾经出现这样的案件:行为人为夺回被抢的手袋,驾驶车辆将抢劫者乘坐的摩托车撞翻,导致一名抢劫者死亡,法院认定该行为成立正当防卫。[7]
结合本案来看,当康某手持木方对谢某进行猛力击打时,不论是击打肩、背、手臂等非要害部位,还是击打头部等要害部位,都足以使其丧失继续驾驶的能力,即从防卫效果上来看并无明显的区别。但击打针对人体不同的部位,导致侵害人死伤的风险却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具体来说:如果击打的是非要害部位,那么基本上只存在其跌落地面而死伤这一种风险;但如果击打的是要害部位,则产生了双重风险,即除了跌落地面的风险之外,还存在着因要害部位受到强力打击而死伤的风险。由此可见,在防卫效果相同的情况下,康某并没有选择危险性相对较低的手段,所以难以认为其防卫措施处在必要的限度范围之内。
第二,康某在当时条件下具有选择打击部位的可能。按照《指导意见》第2和12条的规定,防卫限度的判断要坚持事前判断标准。即,司法者应当采取“情境式”的判断方法,充分考虑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防止在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评判防卫人。的确,在有的案件中,防卫人面临着侵害人的暴力袭击,在千钧一发之际难以冷静、精准地选择打击的部位和强度,所以不能要求其只能打击侵害人的非致命部位。然而,本案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尽管从康某发现摩托车被盗到实施拦截行为时间仅有半分钟,但是谢某毕竟只是消极地逃离现场,他并未对康某实施新的侵害,在此情况下,康某完全具有选择非要害部位实施击打的条件和余地,要求他这样做并没有强人所难。
三、重大损害可归责性的判断标准
按照《刑法》第20条第2款的规定,防卫过当的成立还要求重大损害是过限的防卫手段所“造成”的。这就表明,在确定防卫手段过限的情况下,还需要进一步考察,重大损害结果是否可归责于过当的防卫行为。以往刑法理论界对该问题关注不多。既然这里的“重大损害”是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之一,而一个手段过限的防卫行为既有获得法律容许的内容(即针对不法侵害进行反击),又包含了受到法律禁止的因素(即反击措施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那么仅仅肯定防卫行为引起了重大损害这一点是不够的。只有进一步认定,是防卫行为中不被容许的那个要素,即“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这一属性引起了重大损害,才能以该结果为依据向行为人发出谴责,也才能从规范上将损害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有必要引入结果避免可能性(或曰“合义务替代行为”)的原理。
在过失犯中,任何一项注意义务都不可能保证避免一切损害结果的发生,否则就无异于完全剥夺公民的行动自由,使社会生活完全归于停滞;注意义务的结果避免能力必然是有限的,凡是超出注意义务力所能及范围的风险,都只能被视为被容许的风险。因此,虽然已经确定行为人违反了注意义务,而且行为和结果之间也具有条件关系,但是如果发现即便行为人遵守了注意义务,结果也无法得到避免,那就说明最终引起结果发生的危险并不在注意规范力所能及的防护范围之内,或者说最终导致结果发生的其实是被容许的风险,故无法将结果归责于过失行为。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合义务替代行为的结果避免可能性究竟要达到多高的程度,才能使注意义务违反性与法益侵害结果建立起必要的关联呢?对此,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的立场:(1)确定能够避免说。该说认为,只有当合义务替代行为确定地能防止结果发生,即在行为符合注意义务的条件下绝对不可能再出现该法益侵害结果时,才能成立客观归责。因此,只要无法排除“合法行为也同样会引起结果”的可能,不论该可能性有多小,也应一律根据罪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否定归责。(2)危险升高理论。该说提出,只要能够认定行为人对注意义务的违反与被容许的危险相比升高了法益侵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就足以肯定义务违反与结果之间的关联。换言之,只要根据事后查明的所有客观事实能够认定合义务替代行为具有防止结果发生的可能,不论该可能性有多低,即可成立归责;只有当合法行为确定地完全无法避免结果时,才能否定归责。其中,确定能够避免说是相对多数学者赞同的观点。[8]
我们可以将该原理借用到防卫过当的判断之中。在正当防卫中,法律对防卫人课以了一定的义务,即:当存在防卫效果相同的多种反击手段可供选择的情况下,要求防卫人只能采取给侵害人造成损害最小的那种手段。如果防卫人违反了这一义务,按照上述确定能够避免说,只有当事后证明,合乎限度的防卫手段(即合义务的替代行为)确定能够避免重大损害发生时,才能从规范上将该结果归责于过限的防卫手段(即违反了义务的行为)。如上所述,当康某选择击打谢某头部时,他实际上创造了双重风险,其中仅有要害部位受击的风险才受到法律的禁止,所以只有当该风险在结果中得到实现时,才能认为行为造成了过当的结果。反之,如果发现,最终得到实现的仅仅是摔落地面的风险,由于即便是击打非要害部位的防卫行为本身也包含该风险,它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所以不能将其作为认定结果过当的理由。
本案的鉴定意见指出,谢某在驾驶摩托车高速行驶过程中,头部被击打后车辆失控,后从高速行驶的摩托车抛出,头部撞击路边石头造成严重颅脑损伤,打击行为是形成车祸的主要原因。该意见只能证明,造成谢某颅脑损伤的直接原因是头部撞击路边石头,但是无法说明木方击中头部的行为本身是否对颅脑损伤的形成产生了实质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认定仅有摔落地面的风险在重伤结果中得到了实现。由于无法确定正当的防卫手段能够避免该重伤结果的发生(即,即便康某选择击打谢某的肩部、背部或者双臂,也同样可能导致其摔出并且头部触碰石块),因此不能将其归责于康某。
综上所述,尽管康某所采取的防卫手段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但由于不能确定其造成了重大损害,所以不宜认定其构成《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的防卫过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