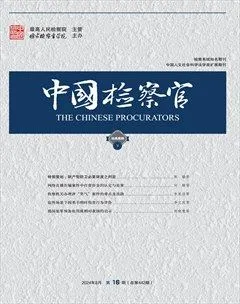轮奸共犯关系脱离的认定及情节适用
摘 要:“二人以上轮奸”部分共犯人中途离开,应当判断离开者是否脱离出共犯关系,因轮奸规定法定刑过重且带有情绪立法的因素,具体判断时应趋向宽缓,判断标准采缓和的因果关系遮断说更为妥当。轮奸规定性质上属于加重构成,存在未完成形态。轮奸既遂标准宜采“二人以上奸入说”,仅一人以下奸入的全体构成轮奸未遂,奸入者构成强奸既遂与轮奸未遂的想象竞合;二人以上奸入的,全体构成轮奸既遂。
关键词:轮奸 共犯关系脱离 加重构成 既遂
一、强奸案件中轮奸情节适用的争议问题
[基本案情]2019年1月13日晚,张某、李某、卞某某与被害人陆某某在酒吧喝酒,结束后李某、卞某某离去。张某将醉酒的陆某某带至酒吧北面河边,趁被害人醉酒之机实施奸淫行为并得逞。后张某将被害人带至酒店房间,李某、卞某某知悉后到达酒店,在张某安抚好被害人情绪并脱光被害人衣服后,轮流进入房间对被害人实施抠摸、性器官接触等奸淫行为,因被害人反抗及醉酒呕吐二人均未得逞。卞某某告知张某、李某后离开酒店,张某、李某继续留在酒店房间内,李某再次实施奸淫行为并得逞。被害人在酒店的整个期间内,张某未再次实施奸淫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张某、李某、卞某某犯强奸罪且有轮奸情节,系犯罪未遂,分别判处有期徒刑7年、8年、4年6个月。检察机关认为,轮奸作为情节加重犯,犯罪形态应根据基本犯形态确定,根据共同犯罪“一人既遂全部既遂”的原则,张某、李某、卞某某构成轮奸既遂,且张某有单独强奸行为,在犯罪中发挥主要作用系主犯。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张某、李某、卞某某构成强奸罪且系轮奸适用法律正确,但认定构成轮奸未遂属适用法律错误,对三人的量刑畸轻,因而抗诉。二审法院认为,张某、李某、卞某某犯强奸罪且有轮奸情节,卞某某系犯罪未遂,判决维持张某、李某定罪部分以及卞某某定罪量刑,撤销对张某、李某量刑部分,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2年,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
本案中行为人实施的值得刑法评价的行为,按事件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A阶段张某在河边实施的奸淫行为;B阶段卞某某、李某在酒店房间内实施的奸淫未遂行为;C阶段卞某某离开后李某实施的奸淫行为。从因果共犯论的立场看,本案中B、C阶段卞某某、李某与张某A阶段的不法事实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将A阶段不法事实归属于卞某某、李某;李某参与B、C阶段的奸淫行为,应当对B、C阶段不法事实承担罪责;因张某奸淫既遂后将醉酒的被害人带至酒店,安抚被害人情绪并脱光其衣服,与B、C阶段不法事实存在物理的、心理的因果关系,B、C阶段的不法事实应当归属于张某。但围绕上述行为事实,尚存在如下争议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一是共犯人承担罪责的范围问题,重点是卞某某在B阶段离开后是否应当对C阶段不法事实承担罪责;二是轮奸情节的适用问题,包括轮奸规定的性质、轮奸的既未遂问题。
二、关于罪责范围问题
本案中,卞某某告知其余共犯后离开酒店,其是否应当对后续C阶段李某奸淫得逞的不法事实承担责任,这在理论上即为共犯关系的脱离问题。认为B、C两阶段系两个独立行为的观点非常有力——为表述方便将该观点称为“二行为说”,下文在讨论卞某某是否脱离共犯关系时首先对该观点予以回应。
(一)对“二行为说”的回应
“二行为”说认为C阶段的奸淫行为相对于B阶段行为,是基于新的共谋实施的独立行为。言外之意,即C阶段李某、张某“形成了不同于当初共谋的新共谋或者犯意,并基于新共谋或者犯意实施了行为,因而当初的共谋不及于该行为与结果,不能将最终结果归责于未参与新的共谋或者犯意者”[2]。但该两阶段行为侵害的法益、对象、发生的空间具有同一性,动机、目的具有共同性,时间具有接续性,理应回答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才可以说是新的犯罪决意”。然而二行为说回避了这一问题,直接认定属于另起犯意的行为,论证上并不充分。
那么如何判断是否为基于“新的共谋”支配下形成新的共犯关系实施的行为,这正是共犯关系脱离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退出者一旦被认定为脱离了共犯关系,从脱离者的角度而言属于脱离共犯关系,从剩余共犯的角度而言则属于形成新的共犯关系。”[3]换言之,认定共犯是否脱离出共犯关系,与认定剩余共犯行为是否是基于新的犯意支配下新的共犯关系的再生,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或者“倒不如说后者(共犯消解)是前者(共犯脱离)的效果”[4]。就本案而言,如果认定卞某某脱离出共犯关系,则卞某某对李某C阶段奸淫得逞的行为不承担罪责。反之,卞某某应当承当奸淫既遂的责任。
(二)卞某某脱离共犯关系的认定
基于因果共犯论的立场,卞某某告知剩余共犯人从酒店离开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脱离出共犯关系,不对C阶段的不法事实承担罪责。
其一,卞某某离开的行为切断了与C阶段不法事实的物理因果力。卞某某对于被害人置于危险境地并未显著贡献物理因果力,应当认为自卞某某离开酒店的时间点开始,其对于后续奸淫既遂结果切断了物理的因果力。
其二,卞某某告知其余共犯人并离开的行为,可以规范地评价为切断了心理的因果力。B阶段各共犯人以自身的行为默示达成了轮奸共谋,对共犯结果产生了心理的因果力。缓和的因果关系遮断说认为,对于因果性(包括心理的)遮断的判断,并非意味着因果性为零[5],而是要进行“规范的评价,判断脱离者的脱离行为对于剩余共犯心理的因果性影响,是否减弱到了不必对结果归责的程度”[6]。这就将事实判断转化为规范判断,将存在与否的判断转换为程度判断,核心问题是判断“脱离者从自身立场出发,是否实施了可期待的通常足以消除所造成危险的措施”[7]。本案中各共犯人之间以默示形式所形成的轮奸共谋本就“脆弱”,当卞某某告知剩余共犯人离开的意思并实施离开的行为,虽无法测明因果力是否切断,但因立法确立对轮奸加重处罚的客观依据不足而伦理色彩和情绪立法的意味浓厚[8],对轮奸情节应当限缩认定,既然无法客观测明切断与否,“根据‘存疑有利被告原则’,不能强调心理性因果关系残存可能性,而应该肯定因果关系的切断”[9]。
综上,卞某某应当对其实施的B阶段的不法事实承担罪责,对于C阶段的不法事实,因其脱离出共犯关系对此不负罪责。
三、关于轮奸情节的适用
B、C两阶段“被害法益、行为样态、行为对象、事件发生的空间具有同一性、时间上具有接近性”,应当作为一体的行为进行评价。[10]因卞某某、李某二人轮奸仅一人奸入,对二者行为定性分析时,必然面临如下争议问题:一是轮奸规定是否适用,本质上即轮奸规定的性质问题;二是轮奸的既遂标准问题。
(一)轮奸规定的性质
关于轮奸情节的性质,理论上主要存在传统说、量刑情节说与区分说三种观点。传统说基本将法定刑升格条件与加重构成同等使用,认为结果加重、数额加重、情节加重及其他加重情节均为“加重构成”,学理上存在未完成形态[11];量刑情节说则认为加重情节属于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它决定着法定刑幅度的选择,仅具有具备与否问题,不涉及犯罪的停止形态问题,犯罪的既未遂取决于基本犯的既未遂;“区分说”认为法定刑升格条件可以区分为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其中因行为类型发生变化而增加违法性,导致法定刑加重的情节为加重构成,其余单纯因数额、次数等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情节为量刑规则,加重构成存在既未遂状态,量刑规则只有具备与否的问题。[12]不难看出,区分说带有折衷的表象,以表明行为类型变化的因素作为分类标准,“进行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的二元区分,具有分类上的合理性”[13]。
对于本案所涉轮奸规定的性质,有观点认为轮奸情节属于量刑情节(规则),主张轮奸没有独立罪名,不具有未完成形态,应当根据基本犯的停止形态确定犯罪形态,根据轮奸情节具备与否选择法定刑。[14]该观点在司法实务中不乏适用。[15]区分说虽然认为轮奸情节的性质存在争议,但主张轮奸情节并非单纯的量刑规则而是加重构成。就此而言,区分说与加重构成说具有结论上的一致性。从处罚的角度而言,一定条件下主张轮奸规定性质上属于量刑情节(规则),构成强奸未遂适用轮奸情节法定刑,与上述主张轮奸属于加重构成的处罚后果,在实质法律后果上难言区别。但在轮奸情节适用、轮奸既遂标准、轮奸共同犯罪等问题上,二者存在明显差异,加重构成说更具有合理性。
首先,轮奸行为具备构成要件的本质特征。轮奸是二人以上轮流实施奸淫行为,相对于强奸基本犯由于奸淫行为类型发生变化,导致违法性的升高因而属于加重的犯罪构成。事实上,持轮奸量刑规则说的学者也不否认轮奸情节实质上规定了加重构成,但由于轮奸并非独立罪名,不具有独立犯罪构成而只能视为量刑规则。[16]这一观点与我国刑法学界长期以来以罪名作为讨论平台的现象有关,但以罪名作为讨论平台存在内在缺陷,刑法出于精简的需要大量采用一类犯罪构成分配一个罪名的方法,因而研习刑法问题的基本单位应当是“一个犯罪构成”而非“一个罪名”。[17]强奸罪条款将基本构成要件与派生的构成要件规定于一个条文中,共用一个罪名。当行为既符合基本的构成要件,又具有加重因素而符合派生的构成要件时,属于法规竞合,只能按照特殊的构成要件处罚行为人。[18]
其次,主张轮奸属于加重构成是在构成要件范围内讨论未完成形态问题,能够贯彻责任主义的要求,齐备了轮奸构成要件的构成既遂,反之则为未完成形态。主张轮奸属于量刑规则,则是在构成要件之外,将加重因素视为客观加重处罚的条件。[19]
再次,轮奸量刑情节说难以合理解决共犯问题。轮奸必然涉及共同犯罪,轮奸量刑情节说将加重因素与基本犯置于并列地位,意味着在轮奸案件中,轮奸情节具备与否仅决定法定刑升格条件,共同犯罪问题完全取决于强奸基本犯的共犯原则。这一处理方式,无视轮奸行为的特殊性,可能造成诸如二人轮奸一人奸入的情形,只能根据强奸基本犯的共犯规则,对于未奸入者也认定轮奸既遂等问题。
总之,“二人以上轮奸”法定刑升格条件的性质应当是加重构成,存在未完成形态。本案中卞某某、李某二人轮奸仅一人奸入,属于轮奸的未完成形态问题,应当适用轮奸规定。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二人行为的犯罪停止形态如何认定,这本质上为轮奸的既遂标准问题。
(二)轮奸的既遂标准
对于C阶段李某奸入的行为构成轮奸既遂还是轮奸未遂颇具争议,本案虽然介入了共犯关系的脱离,根本上仍属于“二人以上轮奸部分未奸入”情形下轮奸停止形态的争议问题。对此,关于轮奸既遂的标准,在轮奸加重构成说内部存在几种不同主张。
第一种主张为“二人以上奸入标准说”,该主张认为轮奸属于共同正犯类型,以二人以上奸入为标准,只要有二人以上奸入则其余未奸入的参与者也为轮奸既遂;仅一人奸入或均未奸入时,所有参与者构成轮奸未遂。[20]第二种主张为“一人以上奸入标准说”,认为二人以上共谋轮奸,只要有一人奸入,其余未奸入者也应当认定为轮奸既遂。[21]第三种主张为“二人以上亲手奸入说”,认为强奸是亲手犯,必须由行为人直接对被害人实施,当二人以上奸入时构成轮奸既遂,未奸入者构成轮奸未遂,仅一人以下奸入时由于未出现轮奸结果而不构成轮奸。[22]第四种主张为“一人以上亲手奸入说”,该说肯定强奸是亲手犯、轮奸是强奸的共同正犯,认为轮奸的停止形态应个别判断,奸入者成立轮奸既遂,未奸入者成立轮奸未遂。[23]
以上四种主张均认为轮奸是共同正犯类型,该观点根源于1979年刑法关于轮奸的规定[24],但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仍然将轮奸限定为共同正犯类型的强奸缺乏文理依据[25],且事实上存在轮奸的教唆犯、帮助犯却不能认定轮奸共犯,明显不妥当。应当认为轮奸加重构成是以共同正犯参与类型为典型模式,并不排斥共犯的成立。刑法分则关于轮奸加重构成的规定是关于对轮奸最低限度的要求或言典型模式的规定,应从轮奸至少要求有两名行为人基于合意实施了奸淫行为这一角度来理解[26],而并非意味着轮奸加重构成这一规定排斥共犯的成立。“一人以上既遂标准说”形式上贯彻了共同正犯“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但没有认识到刑法分则的轮奸规定与强奸基本犯构成要件不同,继而既遂标准存在差异。以强奸基本犯的既遂为中心再根据共犯理论认定轮奸既遂,实质上仍然是以强奸基本犯为既遂标准,根源上混淆了强奸基本犯既遂标准与轮奸既遂标准。轮奸规定如单独犯规定一样,本身即以既遂为模式,因而该说难言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且未发生轮流奸淫客观事实,就不能构成轮奸既遂,否则明显罪刑失衡。
第三、第四种主张基本是在第二种主张的基础之上,引入亲手犯理论意图限缩正犯范围,以限制、调节轮奸加重法定刑的适用。但亲手犯理论自身存在重大争议,又叠加第二种观点自身存在的问题,无异于“试图在共犯理论这一‘黑暗之章’的荒芜地带开辟新道路,要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恐怕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27]。其一,学界虽然多数观点承认亲手犯的存在,但也强调亲手犯极为有限,甚至明确否定强奸是亲手犯。[28]其二,即便引入亲手犯理论作为共同正犯“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例外,至多只能限制未奸入者不成立共同正犯,难以得出轮奸既遂与未遂并存的结论。由于共同正犯是犯罪人之间相互协作实施,各行为人对结果的发生均具有因果性,当行为人的正犯性被否定而因果性未切断时,仍有成立狭义共犯的可能。[29]即未奸入者正犯性被否定,但仍至少对轮奸结果有心理的或物理的因果力,具有成立轮奸狭义共犯的可能。
笔者认为,第一种主张具有合理性。首先,“二人以上奸入标准说”是刑法文义的当然解释。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构成以既遂为模式,“二人以上轮奸”的条文规定同样以既遂为模式。“二人以上”限定了该行为模式必须由二人以上实施;“轮”本身包含“不同主体”的意味;“奸”则是“奸淫”,通说以“插入说”为既遂标准。“二人以上轮奸”明确了其既遂标准为“至少两名不同主体先后实现了插入”。其次,“二人以上奸入标准说”符合罪刑法定要求。一般而言刑法分则规定单独正犯,总则必须规定共同正犯,但并非意味着分则不能例外的规定共同正犯。关于“二人以上轮奸”的规定,属于刑法分则对刑法总则的例外规定,其特殊性体现在轮奸规定的是以二人共同正犯为最低限度的既遂模式。“轮奸”始终是争议较大的论题,其深层次原因是轮奸法益侵害不明。在判断某项裁判是否“正当”时,首先可能诉诸的认识根据就是法感[30],对于一个无法在教义学上作出圆满合理解释的法益,诉诸法感以求得裁判的妥当不失为一个合理路径。显然,以“二人以上奸入”作为轮奸既遂的标准,更符合社会一般人朴素的正义情感。
基于以上论证,A阶段不法事实应当仅归责于张某。B阶段张某、卞某某、李某构成轮奸共犯共同对不法事实负责。C阶段卞某某脱离出共犯关系,张某、李某构成共同犯罪对该阶段不法事实负责。B、C阶段具有主体、对象、动机、法益等的同一性、时间的接续性,相对张某、李某而言属于“一连的行为”或“一体的行为”,应当作为一体行为评价。本案中卞某某仅对B阶段事实负责,卞某某、李某均未奸入构成强奸(轮奸)未遂;李某C阶段行为与B阶段行为属于“一体的行为”,整体而言B、C两阶段二人实施轮奸仅张某一人在C阶段奸入,应当构成轮奸未遂,属于轮奸未遂与强奸既遂的竞合;张某A阶段实施奸淫行为并既遂,B、C阶段继续帮助他人实施轮奸行为,在C阶段张某奸淫既遂,相对张某而言有二人奸入,张某应当对二人以上轮流奸淫既遂的不法事实负责,构成强奸(轮奸)既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