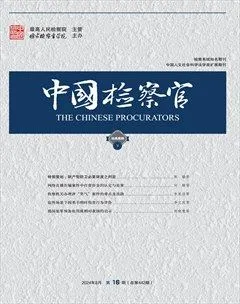检察监督视角下瑕疵增资的效力认定及法效果
摘 要:股东会作出增资的决议,应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且应以公司净资产为基础计算增资后的持股比例,如未经决议或以低于净资产价值的价格增发资本,会稀释原有股东的持股比例,尤其是在原有股东为国有企业时,更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此时对该增资行为及据此取得的股东资格应予否定,相应股权应予返还或涂销,公司原有或继受股东等有权就此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
关键词:瑕疵增资效力 股东资格确认 股权返还 当事人适格
一、基本案情
A公司系由B公司及C公司分别出资人民币90万元(以下币种同)、10万元于2001年6月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共计100万元),两股东的持股比例分别为90%及10%,邵某某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B公司系全资国有企业,C公司系B公司持股25.50%的国有资本参股企业。
D公司系于2003年6月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亦为邵某某。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为某嘉公司及某茂公司。
2003年7月,时任A公司董事长的邵某某在A公司净资产未经评估的情况下,由D公司增资70万元,取得A公司41.18%的股权,其他股东B公司、C公司的持股比例因此分别下降至52.94%、5.88%。之后,通过案外人的增资、股权受让及利润转增注册资本等,至2007年12月,A公司的注册资金增加至1000万元,登记股东分别为B公司、C公司、D公司等。2011年5月,因B公司对E公司负有债务,经法院强制执行,E公司继受了B公司持有的A公司22%的股权。
2013年1月,邵某某因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刑事判决认定,2003年7月至10月期间,邵某某在A公司担任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将该公司股权低价转让给由其本人实际控制的D公司,造成国有资产损失123万余元。刑事案件审理期间,邵某某授意D公司两名股东某嘉公司及某茂公司,分别以1元的价格将其所持有的D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案外某国有企业。后法院判决邵某某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
2017年3月,E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D公司通过增资方式取得的A公司的股东资格无效。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D公司通过增资方式取得A公司股权时,虽然未对股权价格进行评估,但B公司及C公司等其他股东未持异议。此外,由于另案刑事判决认定,邵某某的行为构成贪污罪,邵某某为了积极配合检察机关提出的退赃要求,已授意D公司的股东将各自持有的D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国有企业。由此可见,D公司的股东已变更为国有企业,现D公司持有A公司股权并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故不损害国家利益,遂判决对E公司的诉请,不予支持。
E公司不服生效判决,经向某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后,向某检察分院申请监督。
二、分歧意见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D公司通过增资入股方式取得A公司股权的效力认定问题;二是D公司将其自身股权结构调整为国有能否改变其对A公司的持股状态;三是E公司是否有权就D公司的股东资格提起确认之诉。对于上述问题,存在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D公司以增资方式取得A公司股权的行为虽造成了国有资产的重大流失,但在邵某某贪污罪一案审理中,邵某某为积极退赃,已授意D公司的股东将全部股权转让给案外某国有企业,现D公司持有A公司股权并不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不损害国家利益,且E公司于2011年才成为A公司股东,故非适格原告,应对其诉请不予支持。
第二种意见认为,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应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决议通过,且应以公司净资产为基础计算持股比例。D公司以增资入股方式取得A公司股权时,A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净资产远超100万元,然仍按注册资本(100万元)确定D公司持股比例,即70÷(100+70)= 41.18%,其本质是以不合理低价取得A公司股权,稀释了A公司其他国有股东的持股比例,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且该增资行为未经股东会有效决议,应属无效。虽然D公司的股东在嗣后的刑事追赃中变更为国有企业,但该行为仅是D公司自身股权结构的调整,并不能使其增资入股持有A公司股权的无效行为变为有效。又因D公司的瑕疵增资行为与E公司等其他股东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故E公司享有原告资格。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基于该意见,D公司以增资入股方式取得A公司股权的行为无效,E公司享有原告资格,有权提起确认D公司股东资格无效之诉。理由如下:
(一)D公司以增资入股方式取得A公司股东资格无效
公司增资活动具有较强的商业性,《公司法》第34条规定:“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的除外。”第43条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理论上讲,前述规定能够保护有限公司中小股东在公司增资时股权比例不被稀释。但在实践中,公司增资时可能会存在两种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一是控股股东利用其对股东会的控制,对特定对象增发资本;二是控股股东利用其对股东会的控制,以低于每股净资产价值的价格增发资本。[1]在前一种情形,只要是足价发行,股东的财产权益并未受到损害,只是持股比例被稀释。在后一种情形,因净资产属所有者权益,在增资时对公司净资产进行审价评估的基础上确定新增资本的价格,是为了实现新增资本对公司原有资本的补偿,从而在新增资本的股东和原先投入资本的股东之间维持公平。故以低于每股净资产价值的价格增发资本,会稀释原有股东的持股比例,侵害原有股东的财产权。因公司增资时,需依照《公司法》第43条第2款由股东会作出增资决议,再由投资者与公司订立增资协议,并依《公司法》第178条第1款规定缴纳出资。故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增资行为的效力采公司内部意思形成(股东会关于增资入股的决议)与对外意思表示(公司与新股东的增资入股协议)相区分原则判断。
1.A公司增资决议无效及法效果。依所述,D公司增资入股A公司的方案未以经审计评估的净资产进行,而是以A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100万元为基础,增资70万元后即获得41.18%的股权。且另案刑事判决查明,D公司增资入股A公司的行为实系邵某某在担任A公司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将A公司股权低价转让给其实际控制的D公司的违法犯罪行为,故应依《公司法》第22条第1款及《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认定增资决议无效。增资决议无效,依一般原理,新增股权自始未发生,故D公司未取得股权,其股权登记有误,应依不当得利等规定[2]涂销。[3]此时,就D公司出资相应部分股权,应限缩无效之溯及力,但不类推减资,而由D公司增资时A公司的原股东(或其继受者)按当时持股比例,以增资额承受D公司的股权。此种方式不会改变公司现有注册资本,也不改变现有股权结构(即后续新股东的股份并不增加),不影响后续增资入股股东的利益,较为可采。
2.D公司与A公司签订的增资协议无效及法效果。D公司与A公司订立增资协议,因D公司实际控制人邵某某明知增资决议无效事由,故决议无效可对抗D公司。[4]就该增资协议的效力问题,其本身也因违反国有资产管理法规而无效。此外,因D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邵某某,故增资协议也可能因双方恶意串通或准用禁止双方代理规则而无效。增资协议无效,则D公司无义务缴纳新增资本70万元,故其缴纳70万元构成非债清偿,可依不当得利规定请求A公司返还本息。至于D公司不当取得之股权登记地位,亦应依不当得利返还于A公司。
综上,增资决议和协议均属无效。而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不能发生当事人所追求的法律效果,故D公司通过前述增资方式不能取得A公司的股东资格。
(二)D公司自身股权结构调整为国有不能改变其无效持有A公司股权的现状
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当然、确定无效,该无效之法效果无法通过其他行为得以弥补。虽然D公司的股东在嗣后的刑事追赃中变更为国有企业,最终从B公司、C公司流失到D公司的国有资产因D公司自身变更为国有企业而被追回,但并不能使D公司增资持有A公司股权的无效行为变为有效。
且依前述,D公司增资入股行为被确定无效后,其不当取得之股东登记地位,应依不当得利返还,有过错的当事人还应当赔偿对方信赖利益损失。而纵观本案,D公司股东虽然变更为国有企业,但并未将其所持有的A公司股权返还。况且,C公司尚有部分股权系其他非国有企业持有,D公司自身股权结构无论再怎么调整,该部分股东利益均不会得到保护。
此外,刑事案件所涉邵某某的退赃行为也仅涉及到D公司自身股权结构的变动。而本案争议是针对D公司无效持有的A公司股权变动问题,与D公司自身股权结构调整并无关系。因此认定D公司增资取得股权行为无效并不会否定刑事案件对D公司股权结构调整系邵某某退赃行为的认定,与刑事判决并不矛盾。
(三)E公司有权就D公司无效持股现状提起确认股东资格无效之诉
关于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1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即,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仅系股东请求确认其或与其有股权争议的利害关系人是否系公司股东的诉讼,而非公司内部某一股东起诉确认其他股东资格之诉。但本案中,D公司低价增资入股A公司的行为,直接摊薄并稀释了A公司其他股东持股比例,侵害了其他股东财产权益,与其他股东存在直接利害关系。
依《民事诉讼法》第122条,原告是指“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权利主体。学理上认为,确认之诉中原告适格,即指其对确认之诉有“诉的利益”。[5]若原告权利或法律状态面临现实的不安定危险,而确认判决适于消除该危险(且不存在更经济的方法,如直接提起给付之诉),则原告有此种利益。[6]本案D公司所为增资行为无效,若不确认其未取得股权,则不仅稀释其他股东股权,而且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之虞,而要消除此种不利影响,必须确认D公司未取得股权。是故,虽然现行公司法及司法解释对股东要求确认其他股东资格并无授权性规定,但结合D公司增资取得A公司股东资格的行为无效,而在D公司承担责任的前提只能是确认其股东资格无效的情况下,本案案由确定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并肯定E公司等中小股东诉权并无不当。
至于D公司提出的E公司系2011年才成为A公司的股东,因而与本案系争事实不具有利害关系的主张。笔者认为,股权转让后,受让股东在取得股东资格的同时,依托于股东资格而存在的其他实体及程序上的权利随之转移,故E公司以股权折抵债权方式继受B公司持有的A公司股权后,理应享有作为股东相应的诉讼地位。[7]再则,无效合同违反了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由此决定了国家要对无效合同予以主动干预,这种干预主要表现在纠纷诉至法院后,法院不待当事人请求,便可以主动审查合同是否具有无效的因素。如果发现合同无效,应主动确认之。据此,若拒绝E公司的起诉,法院则缺乏审查系争协议效力的空间,无疑削弱了法院的司法职权。据以上分析,E公司有权提起本案诉讼。
(四)对无效持股状态下股东资格确认及股权返还规则的检察监督
本案涉及当事人适格、瑕疵增资行为的效力确认、涉股权贪污时的刑事退赃等多种法律关系,检察机关通过推理论证,剖析法理事理,并得出正确结论:一是D公司增资入股行为未经A公司股东会有效决议且稀释了A公司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并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应属无效;二是在刑事案件中,D公司为邵某某退赃的行为,并不改变邵某某先前的犯罪行为性质。同样,D公司为邵某某退赃而调整自身股权结构的行为,也不构成返还其无效取得的股权,无效行为造成的不当后果未获充分矫正;三是D公司的增资行为与A公司的其他股东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且股权转让后,受让股东在取得股东资格的同时,依托于股东资格而存在的实体及程序上的权利随之转移,E公司享有本案原告资格。基本理顺了无效股权确认及返还规则,很好地体现和发挥了检察机关在保护营商环境、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