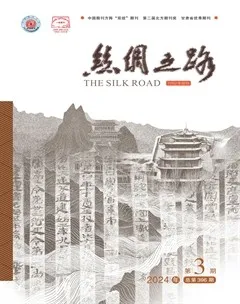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见妇女与商业债务问题探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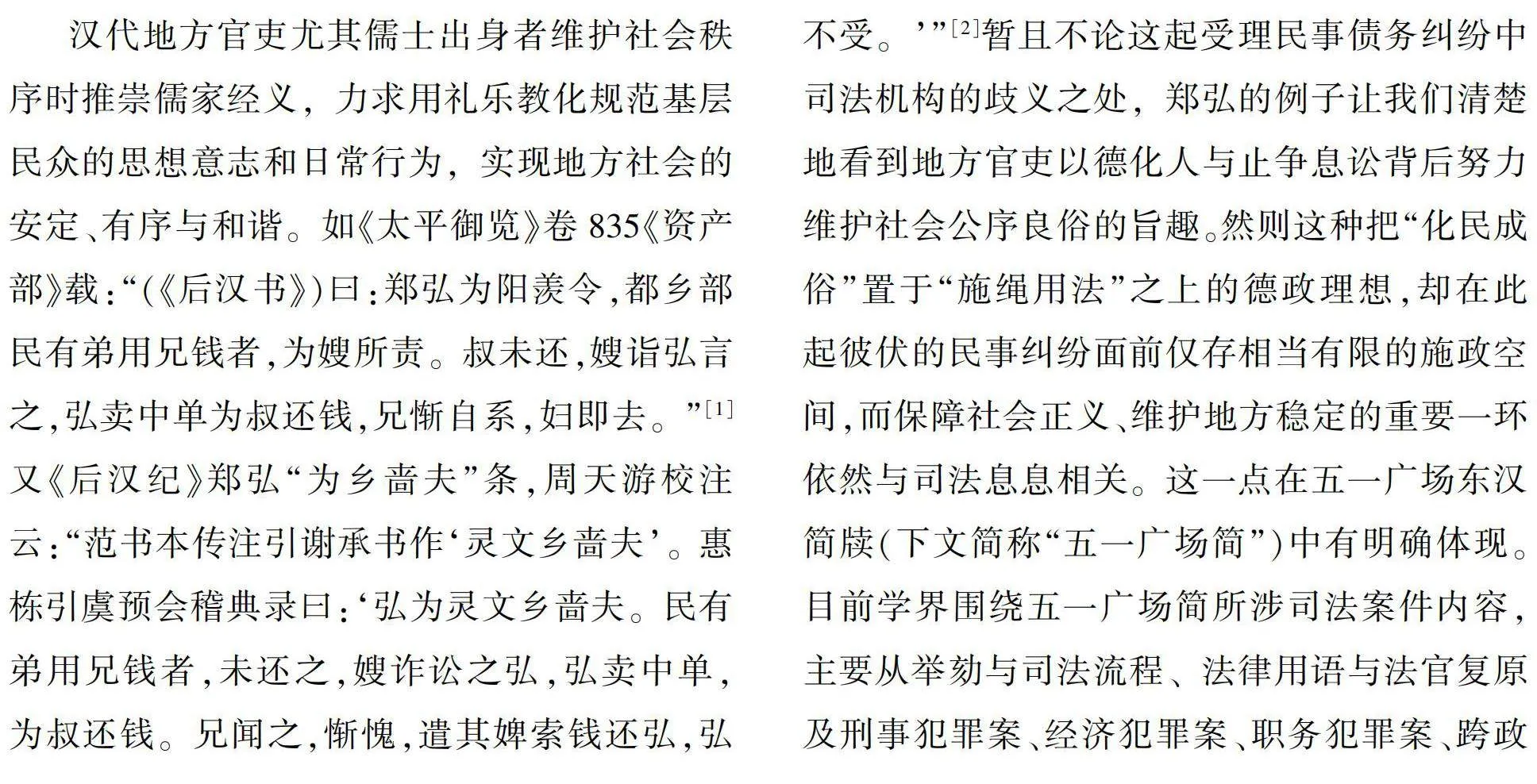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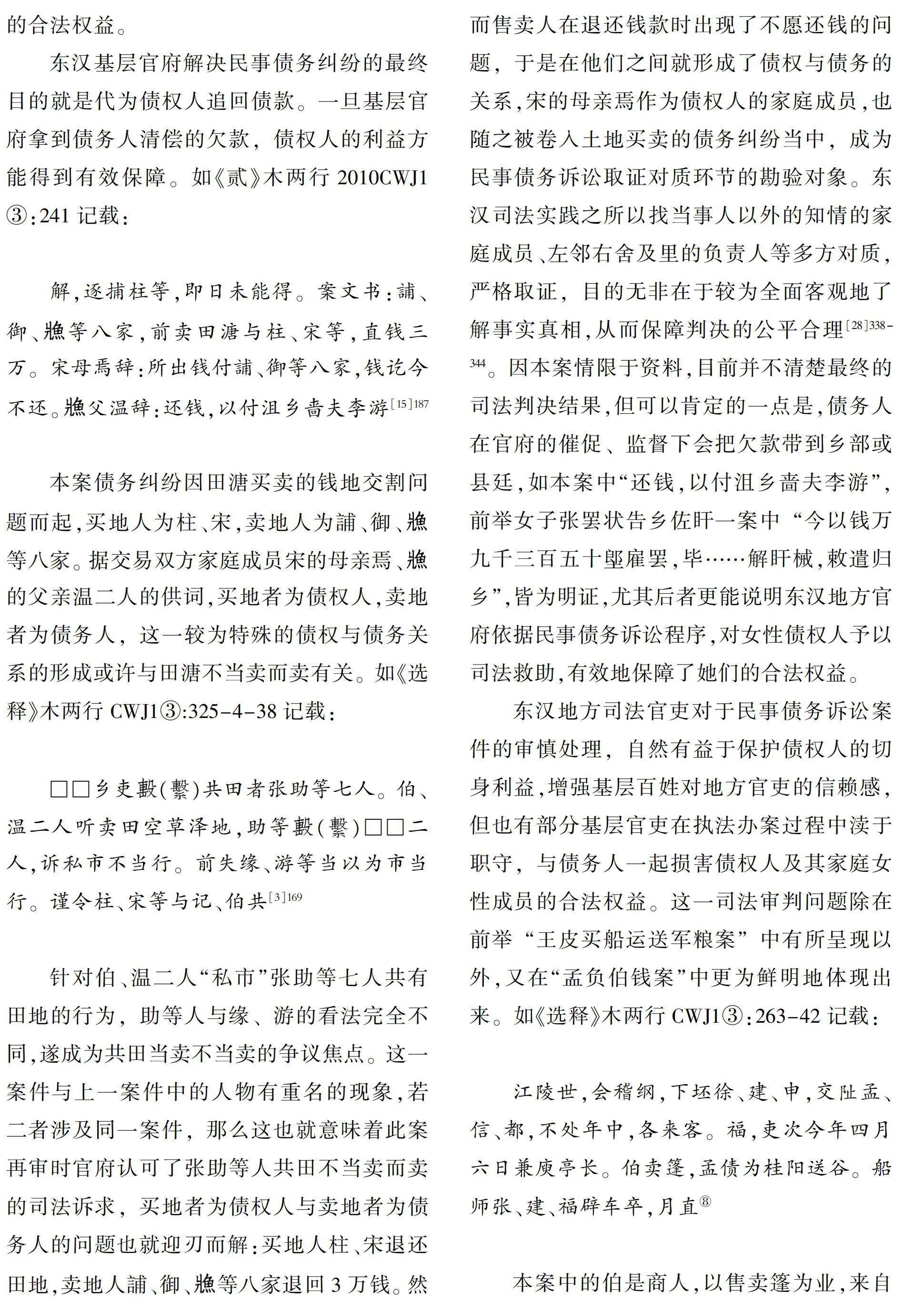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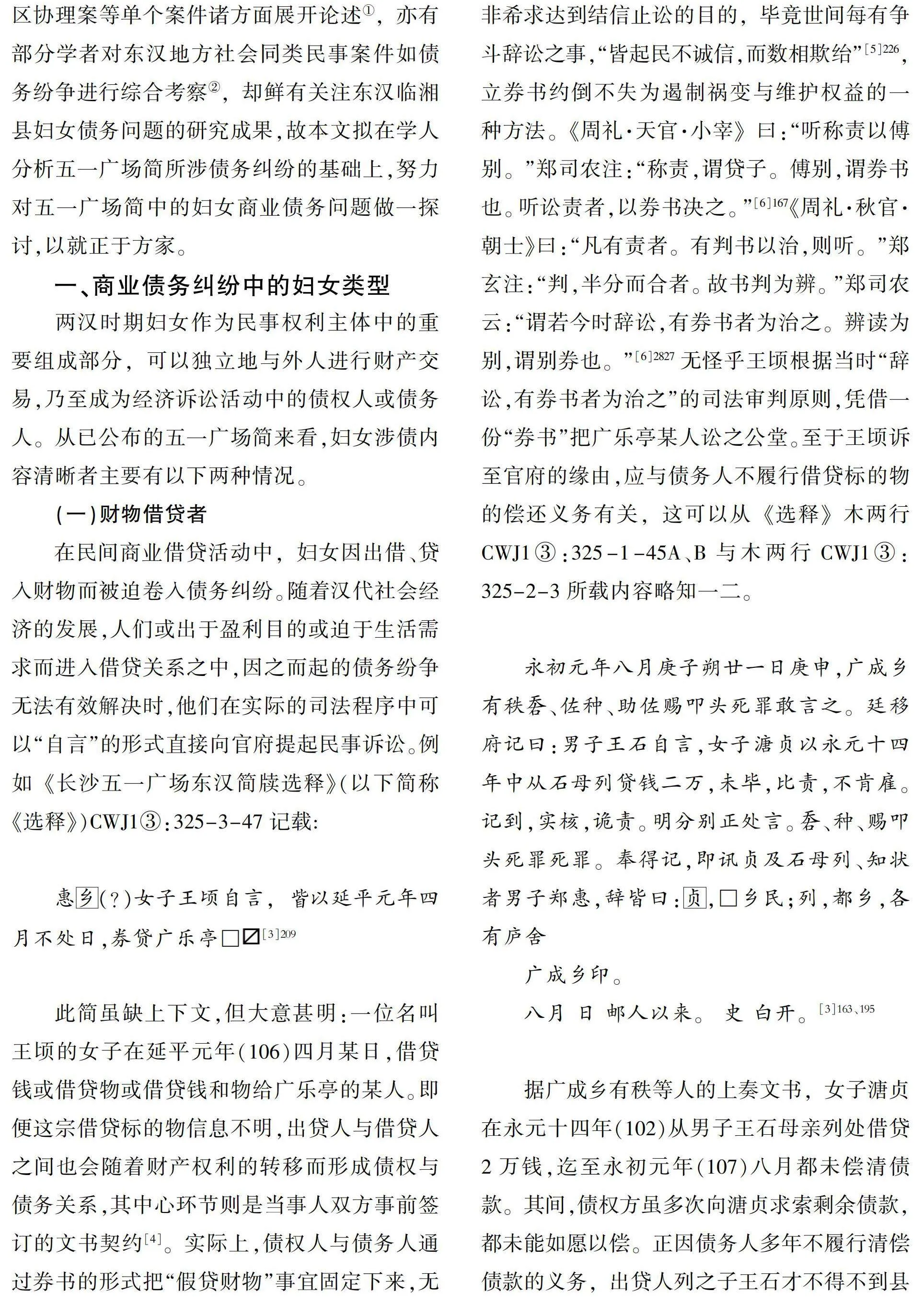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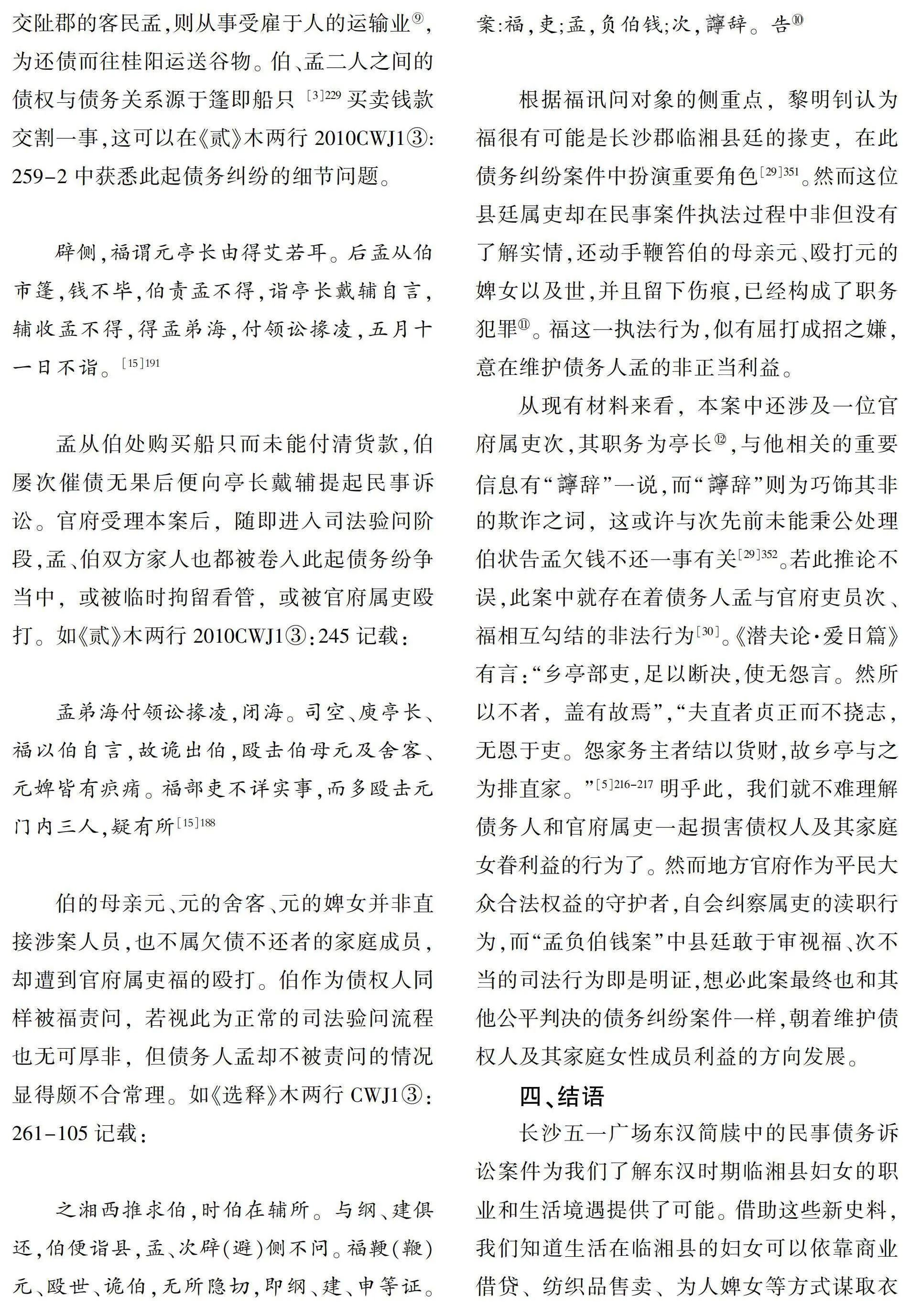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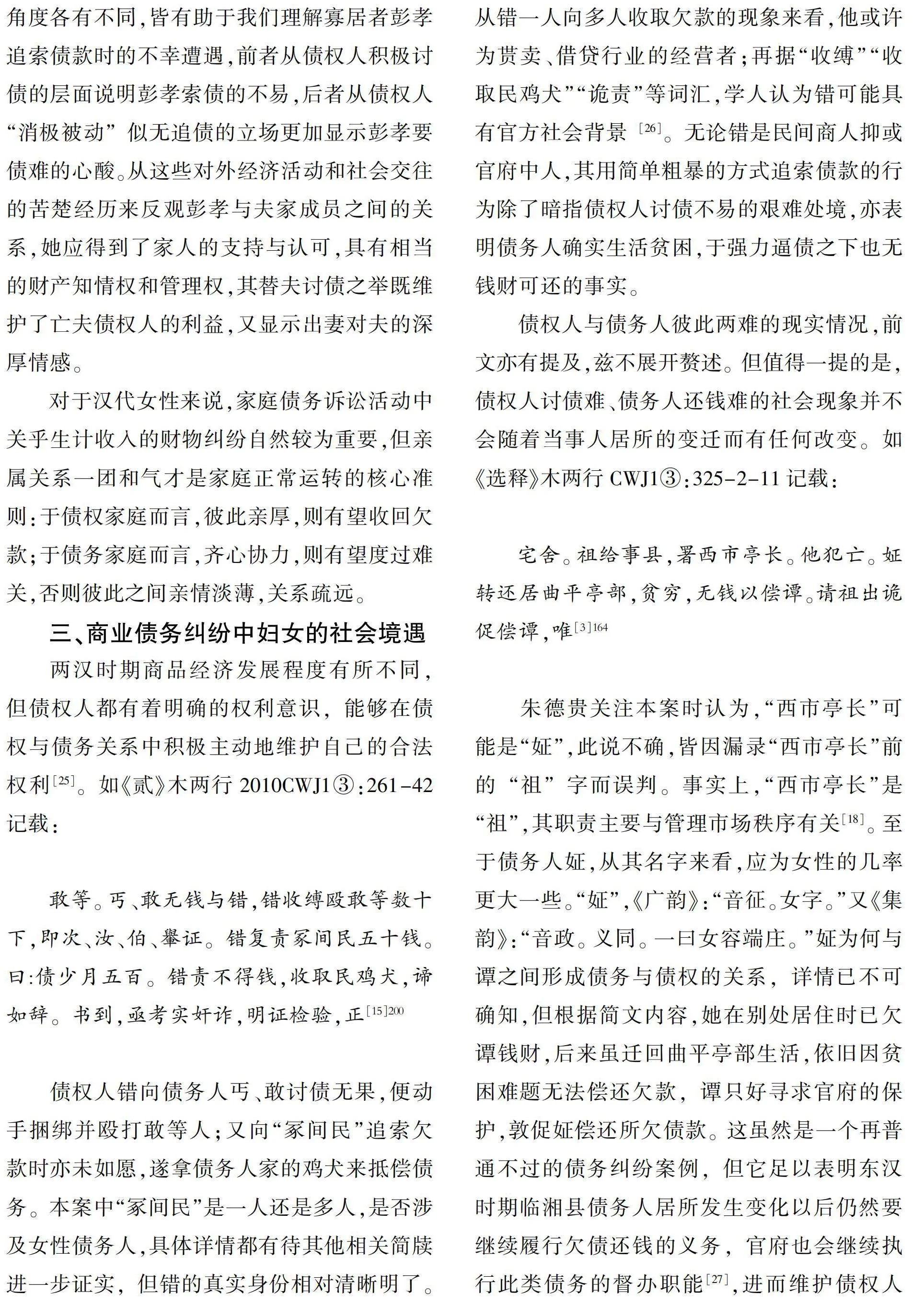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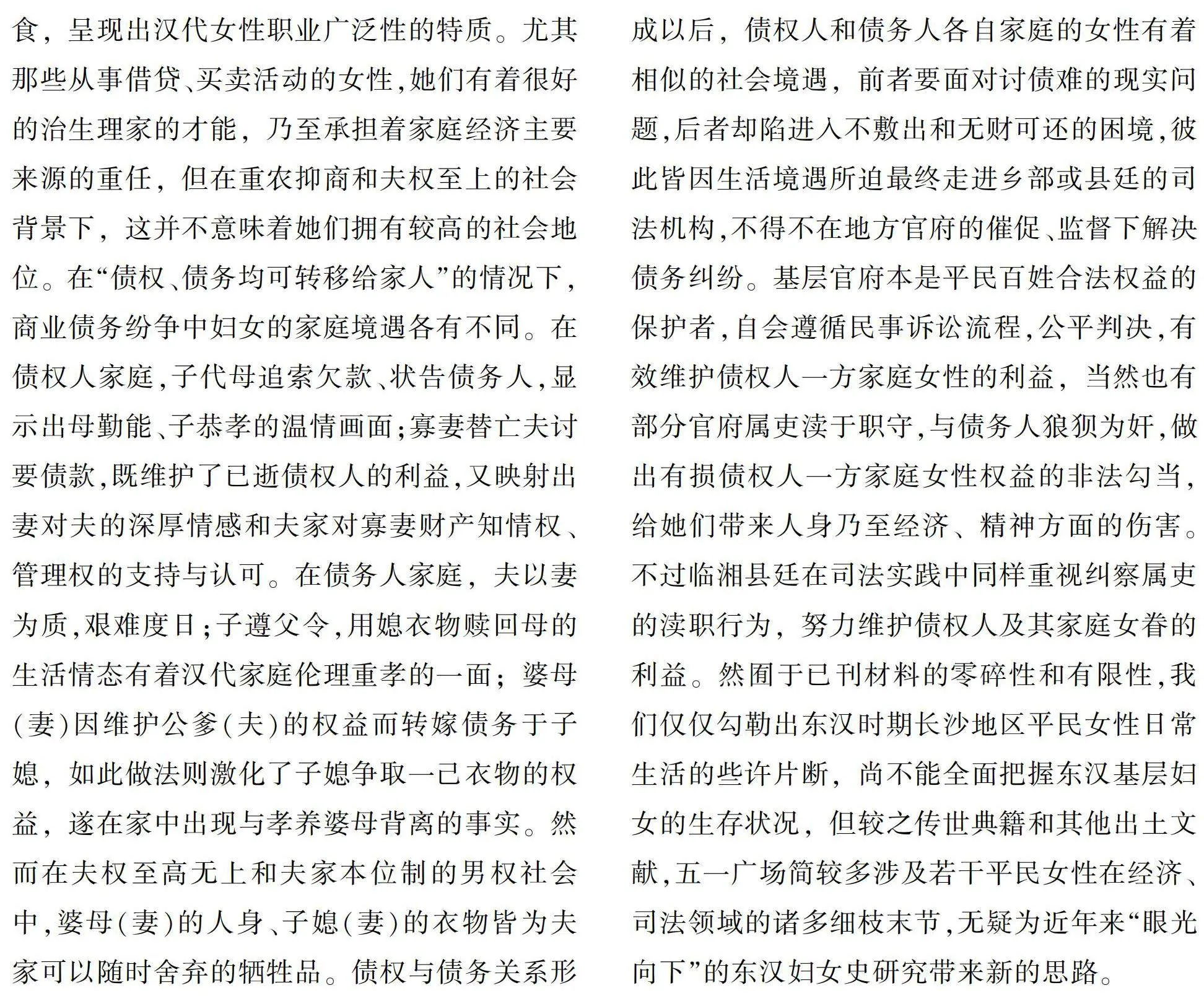
[摘要]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的民事债务诉讼案件涉及东汉临湘县妇女的职业和生活境遇。临湘县的妇女可以依靠商业借贷、纺织品售卖、为人婢女等方式谋取衣食,呈现出汉代女性职业广泛性的特质。在“债权、债务均可转移给家人”的社会习俗中,债权家庭既有彼此亲厚的一面,又有男尊女卑、夫主妇从的伦常情状。基层官府解决民事债务纠纷时,总体上能够做到公平判决,从而有效维护债权人及其家庭女性的利益。
[关键词] 五一广场简;东汉;妇女;商业;债务纠纷
[中图分类号] K87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3115(2024)03-0022-14
[作者简介] 罗操(1983-),男,汉族,河南许昌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基金项目] 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出土文献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方社会研究”(19YJC770030)。
汉代地方官吏尤其儒士出身者维护社会秩序时推崇儒家经义,力求用礼乐教化规范基层民众的思想意志和日常行为,实现地方社会的安定、有序与和谐。如《太平御览》卷835《资产部》载:“(《后汉书》)曰:郑弘为阳羡令,都乡部民有弟用兄钱者,为嫂所责。叔未还,嫂诣弘言之,弘卖中单为叔还钱,兄惭自系,妇即去。”[1]又《后汉纪》郑弘“为乡啬夫”条,周天游校注云:“范书本传注引谢承书作‘灵文乡啬夫’。惠栋引虞预会稽典录曰:‘弘为灵文乡啬夫。民有弟用兄钱者,未还之,嫂诈讼之弘,弘卖中单,为叔还钱。兄闻之,惭愧,遣其婢索钱还弘,弘不受。’”[2]暂且不论这起受理民事债务纠纷中司法机构的歧义之处,郑弘的例子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地方官吏以德化人与止争息讼背后努力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旨趣。然则这种把“化民成俗”置于“施绳用法”之上的德政理想,却在此起彼伏的民事纠纷面前仅存相当有限的施政空间,而保障社会正义、维护地方稳定的重要一环依然与司法息息相关。这一点在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下文简称“五一广场简”)中有明确体现。目前学界围绕五一广场简所涉司法案件内容,主要从举劾与司法流程、法律用语与法官复原及刑事犯罪案、经济犯罪案、职务犯罪案、跨政区协理案等单个案件诸方面展开论述①,亦有部分学者对东汉地方社会同类民事案件如债务纷争进行综合考察②,却鲜有关注东汉临湘县妇女债务问题的研究成果,故本文拟在学人分析五一广场简所涉债务纠纷的基础上,努力对五一广场简中的妇女商业债务问题做一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商业债务纠纷中的妇女类型
两汉时期妇女作为民事权利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独立地与外人进行财产交易,乃至成为经济诉讼活动中的债权人或债务人。从已公布的五一广场简来看,妇女涉债内容清晰者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财物借贷者
在民间商业借贷活动中,妇女因出借、贷入财物而被迫卷入债务纠纷。随着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或出于盈利目的或迫于生活需求而进入借贷关系之中,因之而起的债务纷争无法有效解决时,他们在实际的司法程序中可以“自言”的形式直接向官府提起民事诉讼。例如《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以下简称《选释》)CWJ1③:325-3-47记载:
惠乡(?)女子王顷自言, (此自)以延平元年四月不处日,券贷广乐亭□[3]209
此简虽缺上下文,但大意甚明:一位名叫王顷的女子在延平元年(106)四月某日,借贷钱或借贷物或借贷钱和物给广乐亭的某人。即便这宗借贷标的物信息不明,出贷人与借贷人之间也会随着财产权利的转移而形成债权与债务关系,其中心环节则是当事人双方事前签订的文书契约[4]。实际上,债权人与债务人通过券书的形式把“假贷财物”事宜固定下来,无非希求达到结信止讼的目的,毕竟世间每有争斗辞讼之事,“皆起民不诚信,而数相欺绐”[5]226,立券书约倒不失为遏制祸变与维护权益的一种方法。《周礼·天官·小宰》曰:“听称责以傅别。”郑司农注:“称责,谓贷子。傅别,谓券书也。听讼责者,以券书决之。”[6]167《周礼·秋官·朝士》曰:“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郑玄注:“判,半分而合者。故书判为辨。”郑司农云:“谓若今时辞讼,有券书者为治之。辨读为别,谓别券也。”[6]2827无怪乎王顷根据当时“辞讼,有券书者为治之”的司法审判原则,凭借一份“券书”把广乐亭某人讼之公堂。至于王顷诉至官府的缘由,应与债务人不履行借贷标的物的偿还义务有关,这可以从《选释》木两行CWJ1③:325-1-45A、B与木两行CWJ1③:325-2-3所载内容略知一二。
永初元年八月庚子朔廿一日庚申,广成乡有秩(天右)、佐种、助佐赐叩头死罪敢言之。廷移府记曰:男子王石自言,女子溏贞以永元十四年中从石母列贷钱二万,未毕,比责,不肯雇。记到,实核,诡责。明分别正处言。(天右)、种、赐叩头死罪死罪。奉得记,即讯贞及石母列、知状者男子郑惠,辞皆曰:贞,□乡民;列,都乡,各有庐舍
广成乡印。
八月 日 邮人以来。 史 白开。[3]163、195
据广成乡有秩等人的上奏文书,女子溏贞在永元十四年(102)从男子王石母亲列处借贷2万钱,迄至永初元年(107)八月都未偿清债款。其间,债权方虽多次向溏贞求索剩余债款,都未能如愿以偿。正因债务人多年不履行清偿债款的义务,出贷人列之子王石才不得不到县廷控诉溏贞欠债不还的行为,以便寻求官府的公力援助,进而更加顺利地追索债款。一般来说,汉代统治者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基层民众的合法权益,自然会关注民间借贷的风俗习惯,乃至用司法强力规制民间的借贷现象。如文帝四年(前176),河阳侯陈信“坐不偿人责过六月,夺侯,国除”[7]。又明帝“永平时,诸侯负责,辄有削绌之罚”[5]229。汉代朝廷针对诸侯负债于人而无限期拖延不还的行为,予以削减封地、贬降官爵的行政处罚,这些看似与民众相去较远的司法制裁,实则借助处理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颇高的债务人的案情,力戒民间借贷人信守债务约定,如期保量偿还债权人财物,进而实现维护黎民百姓财产利益的宗旨。就上举两起民间借贷标的物或暗或明的诉讼案件来说,基层民众固然明白汉王朝规制民间借贷习俗的初衷,但欠债长期不还仍是东汉时期临湘县相对严重的民事问题,当民间借贷演变为债务纠纷时,东汉县廷可以通过基层百姓的“自言”即口头诉讼获得地方社会民众之间利益相争的信息,进而及时介入民事债务纠纷,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由此我们也不难想见,东汉民间借贷钱或借贷物或借贷钱和物并非个别情况,而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就连以王顷、王石母列为代表的部分女性都从事着商业借贷活动,这种“外”的商业活计除了表征着汉代女性职业广泛性的特质以外,还意味着她们拥有较高的家庭地位,乃至承担着家庭经济主要来源的重任。不过在重农抑商的社会背景下,相较于那些众多固守家内纺绩、耕作的女性而言,王顷、王石母列等部分女性也不得不以牺牲尊严为代价,失去了崇“内”的身份标志[8]68。
(二)布匹售卖者
在商业买卖活动中,妇女因出售货物而深受债务纷争所累。东汉时期临湘县纺绩业发达,自然有不少妇女从事纺织品的生产、买卖活动,基层社会出现与之相关的司法案件也在所难免。如《选释》木牍CWJ1③:325-2-9记载:
君教诺。
辞曹助史襄白:女子张罢自言,桑乡佐盰负布钱万九千三百五十。械盰。曹下诡盰,今以钱万九千三百五十塱雇罢,毕。当处重罚,以钱毕,蒙阔略。丞优、兼掾畼议请解盰械,敕遣归乡。延平元年八月四日己酉白[3]156
在这份文书中,女子张罢到县廷申诉,桑乡乡佐盰欠其布钱19350,数目巨大,至今不还。乡佐为“乡部亲民之吏”,位尊职重。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乡部属吏除啬夫、游徼之外,“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9]。事实上,乡佐与“职听讼,收赋税”的啬夫一样,其主要职掌固然为征收赋税、徭役,但他也似乎参与行政、民事和兵事,其地位或许相当于郡、县之丞③,可谓是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一员。臧知非就乡佐隶属关系有不同看法,认为乡佐直属于县廷,直接对县令、丞负责,于国家财政收入方面方可“有效防止乡佐与基层长吏、地主大姓相互勾结,背公向私,有利于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10]。以上着眼于汉代地方政治运作模式的论述,都揭示出乡佐于公的行为直接关系到基层社会秩序稳定的问题。当然,乡佐囿于“乡部亲民之吏”的政治身份,其于私的行为如债务纠纷也可能会诱发官民之间的矛盾,乃至影响地方社会稳定。因此,汉王朝十分重视吏治问题。当临湘县廷获取桑乡乡佐盰负债的案情后,相关职能部门拘留盰,并对之施加刑具,尔后交由负责财物纠纷的辞曹处理④。最终,在辞曹官吏的严厉审理、诘问、责成下,乡佐盰偿还全部欠款,债务纠纷至此结束。依据汉律,本案中因“不雇直”即不支付应有钱款而构成的经济犯罪行为,亦按赃罪论处[11]。乡佐盰理应受到司法重罚,因其悉数归还所欠布钱,才得到县廷宽大处理,被释放归乡。
值得注意的是,张罢追索的欠款数额并非一般的小数目,极有可能是陈年旧账累积的结果。东汉中后期长沙地区布匹的价格较为适中,每匹300-600钱[12]406-408,据此布价折算,乡佐盰欠付张罢33-64匹布钱。照常理推之,以五口之家每人各用4匹布估算⑤,乡佐盰及其家人一年内不大可能在衣服、被褥方面有如此规模的开销,其欠付张罢的布钱可能因月积年累而成;以日织二尺五寸布的进度计算,一位熟练掌握纺织技术的家庭女性一年可织约合25匹布[8]29-30,两三年内才能织出本案中的布匹数量,这也预示着张罢与乡佐盰之间有着布匹交易活动上的长久往来。至于张罢是坐贾,还是行商,因限于资料,目前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张罢从事布匹买卖的商业活动可以给家庭带来相对丰厚的收入,这体现出她在家庭中不可小觑的营生本领。与此同时,张罢也面临着不可预知的债务风险和状告欠债人如乡佐盰的民事纠纷,这反映出她在对外交往中司法诉讼的应对能力,但这些能力并不足以说明类似于张罢的汉代女性拥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
(三)劳动生产或歌舞表演者
与上述妇女作为民事权利主体不同的是,那些为他人从事劳动生产、歌舞表演的婢女们通常被视为民事权利客体,即拥有者的财物,可以和田宅、牲畜、器物一样被赏赐、赠予与买卖。因此,在民间商品交易活动中,处于社会底层的婢女们被买卖双方钱款交割的问题所裹挟,成为债务纠纷中的标的物。如《选释》木两行CWJ1③:325-1-16记载:
左一人本钱。时任人男子王伯兴、张叔陵。明辞:家单无人,愿遣从弟殷平赍致书责叔阳、孟威本钱。实问里正杨成,辞:明前市婢愿、谛,当应得。遣平责[3]187
此案中的债权人为明,性别尚不清楚,债务方为叔阳、孟威二人,彼此争讼的焦点在于买受人叔阳、孟威没有付清售卖人明卖出两名婢女愿、谛的钱款。事实上,东汉民间买卖奴婢并非个别现象,不但奴婢交易合情合法,而且还明码标价。如《选释》木两行CWJ1③:325-4-25记载:“后何卖民,直钱九万五千。以其五万买大婢侍。”[3]167临湘县一名婢女5万钱,与汉初江陵地区1.6万钱、西北地区1.2万和2万钱的婢女价格相比,确实不算低价[12]398-399。由此价钱再来审视明与叔阳、孟威之间的债务纠纷,标的物——婢女确实是一笔价值不菲的财富,拥有的数量越多,则意味着财富越丰。以愿、谛为代表的婢女是两汉时期一个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因其“财物”属性,在私人家庭无论从事劳动生产还是歌舞表演,都摆脱不了被主人奴役、买卖的命运。
二、商业债务纠纷中妇女的家庭境遇
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生产与消费单位,其生计方式可以呈现出汉代成年男女的职业类型和劳动能力。他们无论凭借个人苦力还是一技之长,都会在谋取衣食的过程中面临着潜在的经济风险。一旦出现经济活动方面的不测,如欠下债款,即便债务人死亡或下落不明时,其家人都必须替他或她继续偿还债务[13],与此相应的自然是债权人出现类似于债务人的情况时,其家人同样可以代他或她继续追索债款。
检视五一广场简,我们发现临湘县基层百姓之间的债务关系虽经某一家庭成员而起,但其他家庭成员也同时被赋予了相应的权利或义务。如《选释》木两行CWJ1③:325-1-27记载:
敢用。后荆物故,阳责汝,汝以钱二千付阳。□四百,并处阳钱凡九万三千四百,皆名阳钱□[3]190
这件债务标的物清晰的债款纷争,当事人双方关系、性别不明,我们可做两种情况理解:其一,荆与阳为一家人。荆生前借钱给汝,而汝一直未偿清债款,荆殁亡后,其家人阳接续荆向债务人汝求索欠款。其二,荆与汝为一家人。荆生前向阳借钱,且不曾还清欠款,故阳于荆逝世后直接向荆的家人汝追取债款。以上两种推论是否接近本案的真相,都引导我们循此“债权、债务均可转移给家人”的思路去理解家庭债务中妇女的生存境遇。
“孝”在汉朝处于社会伦理的核心地位,儿女照顾父母的生活既是分内的责任,又是稳定家庭关系应尽的义务。如前举“男子王石代母列状告溏贞”一案,债权人是列,债务人是女子溏贞,双方因债务纠纷而对簿公堂,但申诉人不是出贷人列,却是列之子王石,这除了说明被侵权的当事人可以由其家人代为诉讼之外,债权也似乎可以转移到家人名下。在本案中,广成乡有秩(天右)、佐种、助佐赐等人奉临湘县廷命令调查债务实情,审讯了债权人列、债务人溏贞、知情人男子郑惠,这与我们前文所说“债权人出现类似于债务人死亡或下落不明时,其家人同样可以代他或她继续追索债款”的情况有所不同,本案中的债权人列依然健在,且能出现在司法机构接受乡部属吏的调查,这一现象既不能否定我们上述的判断,又再次确证和丰富了东汉基层社会百姓家庭对外经济活动的细枝末节。在王石家庭,石母列应是一位治生理家的能手,一笔2万钱的放贷数额已隐约之间透漏出列的经商形象和家庭地位,其对儿子王石的权威意义不容置疑;王石也应是非常重视孝道的人,其代母追索债款、状告溏贞实属替母分忧和恪尽孝养之责的部分生活写照。对于放贷人来说,收回欠款确是难事,有些债务人非但不偿还欠款,还外出躲债,如《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壹)》(以下简称《壹》)木两行2010CWJ1③:196中的福“辟则不见”[14]246,《选释》木牍CWJ1③:325-4-43B中的董少“七月廿八日举家辟(避)则(侧)”[3]159,致使债权人讨债无果,乃至承担着最终损失钱财的风险,更有甚者债权人还要遭致杀身之祸。如《壹》木两行2010CWJ1②:121记载:
后傅数数责守,守曰:“但知,勿忧!”到今年三月九日,傅复之守舍责守,守曰:“今无见,方假贷,暮来取之。”傅归舍,其日暮傅之守舍,守念无钱与傅,意欲杀之,即佁谓傅曰:“若且留。”[14]220
又《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贰)》(以下简称《贰》)木两行2010CWJ1③:263-9记载:
月廿日叔责且钱,且不与,争言,斗,且以业刀刺叔右手,创一所,发觉,亡命,还归江陵,会今年正月乙巳赦令出,五月不处日,与素所知南阳宛男子王伯俱来,行道,伯从且贷钱六千,其月廿二日到临湘。[15]215
债务人且、守恶意欠债不还,并心生歹意,前者刀伤索债人,后者欲杀债权人,以至临湘县廷在审理漻阳乡乡佐王副欠债不还一案时发出“贷钱,有贷名,无偿心”的慨叹⑥。在如此凶险的讨债环境中,债权人可能基于人身安全的考量,让血亲男性前往讨债的案例也为数不少。如《选释》木牍CWJ1③:325-5-21中性别不明的惠曾派遣姐姐的两个儿子毐、小向贷款者易追索债款[3]157,《选释》木两行CWJ1③:325-1-16中性别不清的明以“家单无人”的理由派遣从弟殷平向叔阳、孟威索要本钱,无一不指向债权人处境维艰的事实。若惠、明皆为女性债权人,那么她们与王石母列一样,在讨债难的不良社会风气中不得不派遣血亲男性前去索要欠款,都在于借用男性的力量话语权而达到索债成功的目的。由此再来审视王石帮助母亲讨债的举止,更加可见王氏家庭母亲勤能、子男恭孝的温情画面。
王氏母子彼此亲睦而无怨嫌的生活片断,完全符合汉代统治者整饬家庭伦理和社会风俗的政治导向,而有些家庭的局部生活情态既有汉代主流社会家庭伦理重孝的一面,又有与孝养婆母背离的既成事实。如《选释》木两行CWJ1③:325-5-9A、CWJ1③:325-2-32、CWJ1③:325-5-11记载:
永初二年闰月乙未朔廿八日壬戌,领讼掾充、史淩叩头死罪敢言之。女子王刘自言,永元十七年四月不处日,刘夫盛父诸令盛赎母基持刘所有衣,凡十一种,从[3]173
钱赎衣。到二年七月,诸船载布重。绥闻诸得油钱,即令户下大奴主呼基,谓曰:今诸船以载得油钱,当赎衣不?基曰:已告刘,刘无钱,平卖衣以自偿,中间相去积八月。绥卖[3]166-167
附祉议解左。晓遣刘。充、淩惶恐叩头死罪死罪敢言之。桼月。基非刘亲母,又非基衣,□□也。[3]174
此案中的债务人起初是诸,即盛的父亲,因家庭置买或贷款一事遂把妻子基——盛的母亲抵押给债权人绥,诸于永元十七年(105)四月某日又命令儿子盛用儿媳王刘的11种衣服赎回基,至永初二年(108)七月债权人绥通知基清偿欠款,赎回王刘的衣服。不过从基回复绥“已告刘,刘无钱,平卖衣以自偿”的言辞来看,她已认定儿媳王刘才是置买或贷款的债务人。即便基极力撇清丈夫诸的债务人身份,也无法否认他们欠债的不争事实,无论由诸还是由王刘赎回衣服,他们履行欠债还钱的义务都说明“家”是对外承担债务责任的一个经济单位[16]。正是在这一经济合作彼此互利的亲密家庭关系中,我们看到的是夫权至高无上的威严性和夫家本位制的男权社会。“礼”是“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的社会准则[17]6,而汉代民众家庭内部呈现出的以父子关系为主轴、以夫妻关系为纲要的人际网络,同样是建立在“礼”的基本标准之上,即所谓的父慈、子孝、夫义、妇听。具体到本案中,诸因置买或借贷的缘由,把妻子抵押出去,后又命令儿子拿儿媳的衣服赎回基,一来显示夫对妻人身的支配权、财物的处理权,二来展现父对子的指挥权、公爹对儿媳财物的处理权,三来表明妻对夫、子对父、儿媳对公爹的服从义务。如此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性都说明,在父子关系中,则是上令下行,在夫妻关系中,则是夫主妇从,二者纵横交织,皆在于维护男尊女卑的夫权,乃至牺牲家庭女性的权益也在所不惜。
本案中的基,作为诸的妻子和盛的母亲,因夫家营生困难的缘故而被当作人质抵押在绥家。如果夫家一直无法清偿债款,那么基就要失去良人的社会身份,沦落为绥家的婢女。由此不难想见,基在家庭债务关系中的处境艰难且危险。对于基而言,她虽然在绵延子嗣方面功不可没,但也免不了以人身为质的苦楚经历,不论她是自愿为之抑或被动舍弃,某种程度上都表征着基的“外人”属性。然而基在儿媳王刘面前,又显示出强势的一面:在跟债权人绥交涉时,基声称王刘无钱赎回衣服,并让绥平价卖掉王刘的衣服,以此抵偿夫家债款。基这种忘却儿媳曾经救助自己的不义行为和不愿意用夫赚取的运输“缇油”之布的“僦直”[18]为儿媳赎回衣服的做法,可谓是把儿媳完全当作“外人”看待。这对婆媳虽有着“外人”的共性,但基的“外人”身份只是暂时的,毕竟“社会舆论和法律对夫系家庭的保护和对尊卑等级的维护,婆婆本人虽然没有男方系统的直接血缘,但却参与了繁衍男方家庭血脉的整个过程,她因此也就被赋予了男方家庭的象征”[8]168,故而基本着自己在夫家的地位,敢于无视王刘的个人权益。对于王刘来说,公爹命令儿子拿儿媳财物赎回婆母之事,呈现出王刘屈礼孝养舅姑的生活情状,完全符合男权社会对为人妇者家庭伦理价值的期许,“妇顺者,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以审守委积、盖藏”[17]1420。不过盛与王刘供事诸和基的温情一幕,却湮没在因家庭债务而引发的婆媳矛盾之中。从王刘到官府申诉的情况和司法官员“基非刘亲母,又非基衣”的言辞来看,王刘的不幸处境和个人权益应该得到了官府的怜悯和维护,基自身强势婆婆的属性也应在司法审判中受到了感情上的遏制。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基和王刘这对婆媳在家庭债务中都是悲情的角色,她们都要依靠夫家而生存、发展,其个人利益在夫家集体利益面前都得不到有效的保障,无论人身还是衣物皆为夫家可以随时舍弃的牺牲品。
在债权与债务关系中,像基一样努力维护夫权的女性也不乏其人,但与基撇清丈夫债务人身份不同的是,“王皮买船运送军粮案”中的彭孝维护的却是夫君债权人的利益。如《湖南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发掘简报》(以下简称《简报》)公布编号为J1③:325-1-140的木牍记载:
永元十五年闰月丙寅朔八日癸酉,武陵大守伏波营军守司马郢叩头死罪敢言之。前言船师王皮当偿彭孝夫文钱,皮船载官米,财遣孝家从皮受钱。郢叩头叩头死罪死罪。皮船载米四千五百斛,已重。孝不来。今月六日遣屯长王于将皮诣县与孝谊,诋未到。亭长姓薛不知名夺收捕皮,毄亭。案:军粮重事,皮受僦米六百卅斛,当保米致屯营。⑦
在这份下行文书当中涉案人员主要是船师王皮,他因欠债不还而被薛姓亭长拘捕,遂引发军粮运输滞留的严重问题。至于王皮与彭孝夫文之间债务与债权关系形成的缘由,我们可以在《选释》木两行CWJ1③:325-4-46中找到答案。
未敢擅付。又次妻孝自言,皮买船,直未毕。今郢言,恐皮为奸诈,不载。辞讼,当以时决皮。见左书到,亟实核奸诈,明正处言,会月十七日。熹、福、元叩头死罪死罪。[3]170
王皮从文处购买船只,却未曾付清钱款,致使债权人文的妻子彭孝卷入债务纷争。再检视与本案相关的另外两枚木两行CWJ1③:325-2-8、CWJ1③:325-1-33,售卖人文都没有出现在此起债务诉讼当中。据刘国忠观察,文“可能当时已经不在人世,因此由其妻出面向王皮索取所欠的钱款”[19]。此说可从。彭孝现为寡居,生活境遇跟我们前文所言“债权人出现类似于债务人死亡或下落不明时,其家人同样可以代他或她继续追索债款”的情况吻合,她到官府状告王皮与维护亡夫利益的举动也就不难理解了。然而本案中的一个难点就是彭孝的身份问题,她究竟是文的妻子,还是次的妻子,学界有不同看法。《选释》一书注解云:“次妻,次之妻。一说,次为序词,次妻即第二位妻子。”[3]170刘国忠依据《魏书》卢元明“凡三娶,次妻郑氏”的材料来理解本案中“次妻”的含义,认为“次妻孝”实为文的第二任妻子彭孝[20]252。杨小亮从语法学、五一简中人之取名习惯两个角度出发,更倾向于“次妻”为男子“次”的妻子,并进一步推导出彭孝寡后再嫁的身份[21]。汉代寡妻再嫁乃为婚姻常态,但往往也牵涉家财分割的重要问题。按《二年律令·置后律》,汉王朝准许寡妇在夫家继产承户,其代户顺序次于子、父、母,位列第四位[22]60,也有望成为夫家的一户之主。一旦寡妇为户后,法令又进一步规定,“其出为人妻若死,令以次代户”[22]61,即寡妇为户后若出现再嫁或死亡的现象,夫家就要由顺位者接替她继产承户。这也就意味着曾为夫家户主的寡妇再嫁后要放弃对夫家传宗接代、继立门户、养老送终的义务,自然被法律剥夺其在夫家所享受的继产权利[23]。与之相应的是,非户主的寡妇再嫁后也会被夫家收回其享用财产的权益。总而言之,寡妇再嫁后与夫家财产已无任何关系。
具体到本案中,我们认为彭孝“次妻”的身份应更接近于“第二任妻子”的内涵。也就是这样一位寡居后的女性,出于家庭生计的考量,接替夫文继续向王皮索要债款,却遭遇外人的挤兑和欺凌,这主要体现在王皮的拖欠行为和军守司马郢为王皮(为己)开脱的说辞两个方面,而释文中的“孝不来”“诋未到”则是理解彭孝讨债艰难的关节点。刘乐贤依据《简报》中的图版和释文,把“孝不来”释为“孝不成”,“谊未到”释为“诋未到”,并梳理出王皮拖欠债款的不合作行为:当彭孝得知王皮的船只运送官米后,彭孝家人就追着王皮索要债款,因王皮身上乏钱且不能离开运送军粮的船只,致使彭孝讨债无果;郢乃至伏波营知道此事后便委派王于屯长带领王皮前去县廷与彭孝商议解决办法,又因王皮拒绝或抵赖而未能到达县廷,遂使调解以失败告终[24]。杨小亮重新厘定本案释文时分别吸收了《简报》“孝不来”、刘乐贤“诋未到”的见解,并概述了军守司马郢为王皮(为己)推卸责任的心理:王皮曾两次努力偿还欠款,但因承运军粮无法离开船只,县廷通知彭孝家人到王皮处收回债款,彭孝却没有来;闰正月六日王于屯长带领王皮前去县廷与彭孝协商处理债务纠纷,彭孝依然“诋未到”。郢遂把债务纷争无法解决的过错完全归咎于彭孝一人[21]。就常情而言,一位寡妇怎么可能在欠债人积极还债的情况下却不去收回欠款,这显然属于郢的不实之词。由此可见,上述两种分析立足角度各有不同,皆有助于我们理解寡居者彭孝追索债款时的不幸遭遇,前者从债权人积极讨债的层面说明彭孝索债的不易,后者从债权人“消极被动”似无追债的立场更加显示彭孝要债难的心酸。从这些对外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的苦楚经历来反观彭孝与夫家成员之间的关系,她应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与认可,具有相当的财产知情权和管理权,其替夫讨债之举既维护了亡夫债权人的利益,又显示出妻对夫的深厚情感。
对于汉代女性来说,家庭债务诉讼活动中关乎生计收入的财物纠纷自然较为重要,但亲属关系一团和气才是家庭正常运转的核心准则:于债权家庭而言,彼此亲厚,则有望收回欠款;于债务家庭而言,齐心协力,则有望度过难关,否则彼此之间亲情淡薄,关系疏远。
三、商业债务纠纷中妇女的社会境遇
两汉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程度有所不同,但债权人都有着明确的权利意识,能够在债权与债务关系中积极主动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25]。如《贰》木两行2010CWJ1③:261-42记载:
敢等。丐、敢无钱与错,错收缚殴敢等数十下,即次、汝、伯、轝证。错复责冢间民五十钱。曰:债少月五百。错责不得钱,收取民鸡犬,谛如辞。书到,亟考实奸诈,明证检验,正[15]200
债权人错向债务人丐、敢讨债无果,便动手捆绑并殴打敢等人;又向“冢间民”追索欠款时亦未如愿,遂拿债务人家的鸡犬来抵偿债务。本案中“冢间民”是一人还是多人,是否涉及女性债务人,具体详情都有待其他相关简牍进一步证实,但错的真实身份相对清晰明了。从错一人向多人收取欠款的现象来看,他或许为贳卖、借贷行业的经营者;再据“收缚”“收取民鸡犬”“诡责”等词汇,学人认为错可能具有官方社会背景[26]。无论错是民间商人抑或官府中人,其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追索债款的行为除了暗指债权人讨债不易的艰难处境,亦表明债务人确实生活贫困,于强力逼债之下也无钱财可还的事实。
债权人与债务人彼此两难的现实情况,前文亦有提及,兹不展开赘述。但值得一提的是,债权人讨债难、债务人还钱难的社会现象并不会随着当事人居所的变迁而有任何改变。如《选释》木两行CWJ1③:325-2-11记载:
宅舍。祖给事县,署西市亭长。他犯亡。姃转还居曲平亭部,贫穷,无钱以偿谭。请祖出诡促偿谭,唯[3]164
朱德贵关注本案时认为,“西市亭长”可能是“姃”,此说不确,皆因漏录“西市亭长”前的“祖”字而误判。事实上,“西市亭长”是“祖”,其职责主要与管理市场秩序有关[18]。至于债务人姃,从其名字来看,应为女性的几率更大一些。“姃”,《广韵》:“音征。女字。”又《集韵》:“音政。义同。一曰女容端庄。”姃为何与谭之间形成债务与债权的关系,详情已不可确知,但根据简文内容,她在别处居住时已欠谭钱财,后来虽迁回曲平亭部生活,依旧因贫困难题无法偿还欠款,谭只好寻求官府的保护,敦促姃偿还所欠债款。这虽然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债务纠纷案例,但它足以表明东汉时期临湘县债务人居所发生变化以后仍然要继续履行欠债还钱的义务,官府也会继续执行此类债务的督办职能[27],进而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东汉基层官府解决民事债务纠纷的最终目的就是代为债权人追回债款。一旦基层官府拿到债务人清偿的欠款,债权人的利益方能得到有效保障。如《贰》木两行2010CWJ1③:241记载:
解,逐捕柱等,即日未能得。案文书:誧、御、()等八家,前卖田溏与柱、宋等,直钱三万。宋母焉辞:所出钱付誧、御等八家,钱讫今不还。 父温辞:还钱,以付沮乡啬夫李游[15]187
本案债务纠纷因田溏买卖的钱地交割问题而起,买地人为柱、宋,卖地人为誧、御、 等八家。据交易双方家庭成员宋的母亲焉、 的父亲温二人的供词,买地者为债权人,卖地者为债务人,这一较为特殊的债权与债务关系的形成或许与田溏不当卖而卖有关。如《选释》木两行CWJ1③:325-4-38记载:
□□乡吏 ( )共田者张助等七人。伯、温二人听卖田空草泽地,助等 ( )□□二人,诉私市不当行。前失缘、游等当以为市当行。谨令柱、宋等与记、伯共[3]169
针对伯、温二人“私市”张助等七人共有田地的行为,助等人与缘、游的看法完全不同,遂成为共田当卖不当卖的争议焦点。这一案件与上一案件中的人物有重名的现象,若二者涉及同一案件,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此案再审时官府认可了张助等人共田不当卖而卖的司法诉求,买地者为债权人与卖地者为债务人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买地人柱、宋退还田地,卖地人誧、御、 等八家退回3万钱。然而售卖人在退还钱款时出现了不愿还钱的问题,于是在他们之间就形成了债权与债务的关系,宋的母亲焉作为债权人的家庭成员,也随之被卷入土地买卖的债务纠纷当中,成为民事债务诉讼取证对质环节的勘验对象。东汉司法实践之所以找当事人以外的知情的家庭成员、左邻右舍及里的负责人等多方对质,严格取证,目的无非在于较为全面客观地了解事实真相,从而保障判决的公平合理[28]338-344。因本案情限于资料,目前并不清楚最终的司法判决结果,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债务人在官府的催促、监督下会把欠款带到乡部或县廷,如本案中“还钱,以付沮乡啬夫李游”,前举女子张罢状告乡佐盰一案中“今以钱万九千三百五十 雇罢,毕……解盰械,敕遣归乡”,皆为明证,尤其后者更能说明东汉地方官府依据民事债务诉讼程序,对女性债权人予以司法救助,有效地保障了她们的合法权益。
东汉地方司法官吏对于民事债务诉讼案件的审慎处理,自然有益于保护债权人的切身利益,增强基层百姓对地方官吏的信赖感,但也有部分基层官吏在执法办案过程中渎于职守,与债务人一起损害债权人及其家庭女性成员的合法权益。这一司法审判问题除在前举“王皮买船运送军粮案”中有所呈现以外,又在“孟负伯钱案”中更为鲜明地体现出来。如《选释》木两行CWJ1③:263-42记载:
江陵世,会稽纲,下坯徐、建、申,交阯孟、信、都,不处年中,各来客。福,吏次今年四月六日兼庾亭长。伯卖篷,孟债为桂阳送谷。船师张、建、福辟车卒,月直⑧
本案中的伯是商人,以售卖篷为业,来自交阯郡的客民孟,则从事受雇于人的运输业⑨,为还债而往桂阳运送谷物。伯、孟二人之间的债权与债务关系源于篷即船只[3]229买卖钱款交割一事,这可以在《贰》木两行2010CWJ1③:259-2中获悉此起债务纠纷的细节问题。
辟侧,福谓元亭长由得艾若耳。后孟从伯市篷,钱不毕,伯责孟不得,诣亭长戴辅自言,辅收孟不得,得孟弟海,付领讼掾凌,五月十一日不诣。[15]191
孟从伯处购买船只而未能付清货款,伯屡次催债无果后便向亭长戴辅提起民事诉讼。官府受理本案后,随即进入司法验问阶段,孟、伯双方家人也都被卷入此起债务纷争当中,或被临时拘留看管,或被官府属吏殴打。如《贰》木两行2010CWJ1③:245记载:
孟弟海付领讼掾凌,闭海。司空、庾亭长、福以伯自言,故诡出伯,殴击伯母元及舍客、元婢皆有疻痏。福部吏不详实事,而多殴击元门内三人,疑有所[15]188
伯的母亲元、元的舍客、元的婢女并非直接涉案人员,也不属欠债不还者的家庭成员,却遭到官府属吏福的殴打。伯作为债权人同样被福责问,若视此为正常的司法验问流程也无可厚非,但债务人孟却不被责问的情况显得颇不合常理。如《选释》木两行CWJ1③:261-105记载:
之湘西推求伯,时伯在辅所。与纲、建俱还,伯便诣县,孟、次辟(避)侧不问。福鞕(鞭)元、殴世、诡伯,无所隐切,即纲、建、申等证。案:福,吏;孟,负伯钱;次, 辞。告⑩
根据福讯问对象的侧重点,黎明钊认为福很有可能是长沙郡临湘县廷的掾吏,在此债务纠纷案件中扮演重要角色[29]351。然而这位县廷属吏却在民事案件执法过程中非但没有了解实情,还动手鞭笞伯的母亲元、殴打元的婢女以及世,并且留下伤痕,已经构成了职务犯罪{11}。福这一执法行为,似有屈打成招之嫌,意在维护债务人孟的非正当利益。
从现有材料来看,本案中还涉及一位官府属吏次,其职务为亭长{12},与他相关的重要信息有“ 辞”一说,而“ 辞”则为巧饰其非的欺诈之词,这或许与次先前未能秉公处理伯状告孟欠钱不还一事有关[29]352。若此推论不误,此案中就存在着债务人孟与官府吏员次、福相互勾结的非法行为[30]。《潜夫论·爱日篇》有言:“乡亭部吏,足以断决,使无怨言。然所以不者,盖有故焉”,“夫直者贞正而不挠志,无恩于吏。怨家务主者结以货财,故乡亭与之为排直家。”[5]216-217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债务人和官府属吏一起损害债权人及其家庭女眷利益的行为了。然而地方官府作为平民大众合法权益的守护者,自会纠察属吏的渎职行为,而“孟负伯钱案”中县廷敢于审视福、次不当的司法行为即是明证,想必此案最终也和其他公平判决的债务纠纷案件一样,朝着维护债权人及其家庭女性成员利益的方向发展。
四、结语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的民事债务诉讼案件为我们了解东汉时期临湘县妇女的职业和生活境遇提供了可能。借助这些新史料,我们知道生活在临湘县的妇女可以依靠商业借贷、纺织品售卖、为人婢女等方式谋取衣食,呈现出汉代女性职业广泛性的特质。尤其那些从事借贷、买卖活动的女性,她们有着很好的治生理家的才能,乃至承担着家庭经济主要来源的重任,但在重农抑商和夫权至上的社会背景下,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债权、债务均可转移给家人”的情况下,商业债务纷争中妇女的家庭境遇各有不同。在债权人家庭,子代母追索欠款、状告债务人,显示出母勤能、子恭孝的温情画面;寡妻替亡夫讨要债款,既维护了已逝债权人的利益,又映射出妻对夫的深厚情感和夫家对寡妻财产知情权、管理权的支持与认可。在债务人家庭,夫以妻为质,艰难度日;子遵父令,用媳衣物赎回母的生活情态有着汉代家庭伦理重孝的一面;婆母(妻)因维护公爹(夫)的权益而转嫁债务于子媳,如此做法则激化了子媳争取一己衣物的权益,遂在家中出现与孝养婆母背离的事实。然而在夫权至高无上和夫家本位制的男权社会中,婆母(妻)的人身、子媳(妻)的衣物皆为夫家可以随时舍弃的牺牲品。债权与债务关系形成以后,债权人和债务人各自家庭的女性有着相似的社会境遇,前者要面对讨债难的现实问题,后者却陷进入不敷出和无财可还的困境,彼此皆因生活境遇所迫最终走进乡部或县廷的司法机构,不得不在地方官府的催促、监督下解决债务纠纷。基层官府本是平民百姓合法权益的保护者,自会遵循民事诉讼流程,公平判决,有效维护债权人一方家庭女性的利益,当然也有部分官府属吏渎于职守,与债务人狼狈为奸,做出有损债权人一方家庭女性权益的非法勾当,给她们带来人身乃至经济、精神方面的伤害。不过临湘县廷在司法实践中同样重视纠察属吏的渎职行为,努力维护债权人及其家庭女眷的利益。然囿于已刊材料的零碎性和有限性,我们仅仅勾勒出东汉时期长沙地区平民女性日常生活的些许片断,尚不能全面把握东汉基层妇女的生存状况,但较之传世典籍和其他出土文献,五一广场简较多涉及若干平民女性在经济、司法领域的诸多细枝末节,无疑为近年来“眼光向下”的东汉妇女史研究带来新的思路。
[注 释]
①参见吴方浪:《长沙五一广场出土东汉简牍研究综述》,载邬文玲、戴卫红主编:《简帛研究》2021(秋冬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66-369页;张炜轩、温玉冰:《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研究概述(2013-2021)》,载黎明钊、刘天朗编:《临湘社会的管治磐基: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探索》,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2年版,第377-381、387-388页。
②朱德贵、齐丹丹:《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见若干经济史料初探》,载杨振红、邬文玲主编:《简帛研究》2015(春夏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5-199页;朱德贵:《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见商业问题探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4期;张朝阳:《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见早期房屋租赁纠纷案例研究》,《史林》2019年第6期;段艳康:《东汉中期临湘地区民间债务关系初探——以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为中心》,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
③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9页;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下册,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200页。
④关于辞曹的职能,参见王朔:《东汉县廷行政运作的过程和模式——以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黎明钊:《长沙五一广场出土东汉简牍中的辞曹》,载周东平、朱腾主编:《法律史译评》第7卷,中西书局2019年版,第104-132页。
⑤许倬云在估算汉代农户的衣料支出时,五口之家或需10匹布(《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程农、张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70页)。乡佐为乡部属吏,其衣料支出可能比一般农户家庭要高,故本文按每人4匹用量估算。
⑥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编:《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贰)简491,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187页;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编:《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伍)简491+1709,中西书局2020年版,第123页。
⑦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6期。释文、标点见杨小亮:《关于“王皮木牍”的再讨论》,《出土文献》2020年第4期。
⑧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编:《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简155,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228页;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编:《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贰)简692,第221页。
⑨参见蒋丹丹:《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见流民及客——兼论东汉时期长沙地区流动人口管理》,载邬文玲主编:《简帛研究》2017(秋冬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5页;李周炫:《秦、汉官府的物资运输与人力利用》,载周东平、朱腾主编:《法律史译评》第9卷,中西书局2021年版,第68-69页。
⑩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编:《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简146,第222页;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编:《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贰)简619,第209页,释“鞕”为“鞭”,“()”为“谩”。
{11}李均明:《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见职务犯罪探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戴卫红:《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见亭长及其职务犯罪》,载王捷主编:《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第9辑,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364-366页。
{12}张朝阳:《东汉临湘县交阯来客案例详考——兼论早期南方贸易网络》,《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黎明钊:《试析几枚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载邬文玲、戴卫红主编:《简帛研究》2018(秋冬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50页。
[参考文献]
[1]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3729.
[2]周天游.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346.
[3]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编.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M].上海:中西书局,2015.
[4]连劭名.汉简中的债务文书及“贳卖名籍”[J].考古与文物,1987,(03):77-83+60.
[5]潜夫论笺校正[M].汪继培笺,彭铎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
[6]孙诒让.周礼正义[M].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1085.
[8]彭卫,杨振红.中国妇女通史:秦汉卷[M].杭州:杭州出版社,2010.
[9]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3624.
[10]臧知非.简牍所见汉代乡部的建制与职能[J].史学月刊,2006,(05):23-30.
[11]李均明.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见职务犯罪探究[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5):82-87+128.
[12]郭伟涛.简牍所见东汉中后期长沙地区物价初探[A].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20辑[C].上海:中西书局,2021:393-421.
[13]李均明.居延汉简债务文书述略[J].文物,1986,(11):35-41.
[14]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编.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壹[M].上海:中西书局,2018.
[15]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编.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贰[M].上海:中西书局,2018.
[16]谢全发.汉代债法研究:以简牍文书为中心的考察[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7:42.
[17]孙希旦.礼记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
[18]朱德贵.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见商业问题探讨[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04):8-25.
[19]刘国忠.长沙东汉简所见王皮案件发微[J].齐鲁学刊,2013,(04):41-43.
[20]刘国忠.五一广场东汉简王皮运送军粮案续论[A].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7辑[C].上海:中西书局,2015:250-253.
[21]杨小亮.关于“王皮木牍”的再讨论[J].出土文献,2020,(04):13-19+154-155.
[22]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23]尹在硕.秦汉妇女的继产承户[J].史学月刊,2009,(12):115-125.
[24]刘乐贤.长沙五一广场出土东汉王皮木牍考述[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3):52-61.
[25]李一鸣.试论汉代的民间借贷习俗与官方秩序:兼论汉代民间借贷中的“契约精神”[J].民俗研究,2018,(01):78-86+154-155.
[26]符奎.环境与社会的互动:从新出简牍看东汉基层社会聚落[J].社会科学,2023,(03):57-74.
[27]张燕蕊.简牍所见秦汉时期债务偿还问题刍议[J].史学月刊,2018,(06):128-132.
[28]李均明.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掺验”解[A].邬文玲,戴卫红主编.简帛研究:2018(秋冬卷)[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338-344.
[29]黎明钊.试析几枚五一广场东汉简牍[A].邬文玲,戴卫红主编.简帛研究:2018(秋冬卷)[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345-357.
[30]刘子钧.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孟负伯钱”案再探[EB/OL].http://www.bsm.org.cn/?hanjian/8238.html.202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