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媒介转向、“异质”解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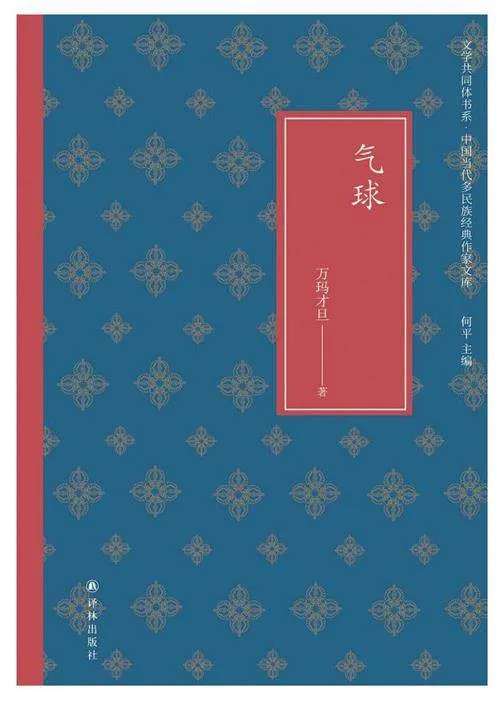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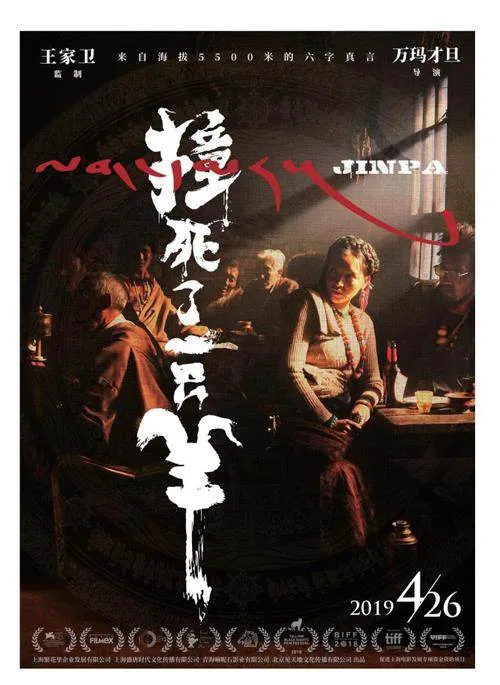
摘 要:藏族导演万玛才旦以其作者性的本色式写作游走于小说与电影这两种媒介之间。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爬梳其媒介转向进程中的文化认同与“异质”解构,万玛才旦携带的天然跨域性身份与丰盈的影像文本群落,不断对藏汉文化的互动交融进行内视角建构以及媒介的合力书写。以全球化语境再度审视藏地影像,借由藏地文化世俗演绎的有效续接、媒介转向中藏地空间的影像化延展,万玛才旦试图间接实现在地性与全球性的关系平衡,进一步强化民族间的国家认同与身份自觉,筑牢多民族国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万玛才旦;中华民族共同体;跨媒介改编;媒介转向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开封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调研课题“万玛才旦小说的跨媒介改编研究”(ZXSKGH-2023-3019)研究成果。
跨媒介改编是当下文学与电影之间发生关联最直接的方式,其实质是电影对于文学的一种影像化的解读和再现。中国电影自诞生初期便与文学缔结了亲缘关系,从1916年电影初创时期改编自清末谴责小说家吴趼人的《黑籍冤魂》开始,电影对文学的改编实践表明,一方面,电影在不同程度上以文学原著为选材基础,从题材内容、主题内涵、艺术形象、谋篇布局等方面对文学作品进行艺术的选取与重塑,以“重读”的方式阐释并传播文学的魅力;另一方面,新时期以来随着电影作为大众媒介在群众中地位与影响力的逐步提高,以文学作品为底本改编的电影创作也因其媒介属性更为广泛地进入了受众的视野。
万玛才旦作为当今少有的能够穿行于文学与电影,游弋于汉藏两地间的艺术家,其小说创作与电影创作很大程度上引领了藏地文学艺术在当下的发展潮流,他的电影作品多是自己编剧,其间也不乏有直接将自己的小说改编为电影的尝试,《塔洛》(2015)是他第一部以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此后的《撞死了一只羊》(2018)《气球》(2019)更是小说跨媒介改编的优秀作品。
通过小说中原生、本质的现实描写与对文化境遇的描绘,万玛才旦实现了自身生活的藏族地区厚重的文化认同,从叙事形式、叙事主题、叙事策略三个方面着手建构一个去“他者化”、本真的藏地形象,通过影像构筑藏区民众长久未变的文化心理结构。在媒介转向的过程中,他将小说语言所传达的信息进行解码,并重新分解、组织,以适应影像媒介特质与受众期待的方式重新编码,以长镜头、镜像构图、黑白摄影等电影特有的表现形式实现文学语言向电影语言的转译,从而将小说文本中的作者特性放大、延展,不同媒介间的特性在过程中相互区分并不断融合。与此同时,他也精准地捕捉到了现代化进程中藏族生活面临的忧思,在藏地文化世俗化演绎的过程中,实现了精神空间的开拓。处在推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万玛才旦以新时代的“少数民族电影”展示了藏族地区独有的民族风貌,为全球化语境内的国族电影提供了中国视角。
一、文化认同:返原生的叙事建构
文化认同是一个地区的人民对本区域内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是建立在对自然认知的超越与升华之上的一种情感共鸣。这些被认同的文化可能基于地缘要素、国族空间或民族特质生成,深深根植于这片土地的血脉之中。在广义层面上,文化认同在精神层面对“自我”与“他者”做出了区分,并对群体关系的凝结与聚合提供了依托。正如本雅明所言:“个人的反应从一开始就以他置身其中的群体反应为前提。”[1]文化认同在当下的呈现形式更接近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对特定文化的认同通常是一种自然、社会与历史的深层积淀。通常文化认同与集体性的仪式、交流与生存环境相关联,但在文化传播方式与形态日益改观的当下,更多种身份、更加多元复杂的文化开始成为“地球村”中可供拣选的对象,而那些既有的文化身份与认同模式逐渐被替代,艺术手段成为固牢共同体内部情感纽带与文化认同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作为通过艺术手段传播当代少数民族文化的先导者,万玛才旦的艺术创作体现出厚重的文化认同。在其小说的跨媒介改编过程中,原先作品中投射的“自我”意识与藏地文化的认同观念在电影中得到了强化。从叙事层面来看,万玛才旦在对自己的小说作品做影像化改编的过程中,分别从叙事形式、叙事主题及叙事策略三个层面或改动、或合力实现了对于藏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和推介。他一改历史上少数民族电影存在的“他者”视角,以原乡人、“我族”的身份切入自身的文化语境中,通过对“原生”状态的描画,旨在将文化内在最为真实的、生活化的潜流呈现给更广泛的受众,进而实现民族认同、国族认同及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微妙平衡。
(一)叙事形式:复调编排与符号寓言
谈及万玛才旦小说跨媒介改编中叙事形式的更新,自然需要关注小说与电影两种艺术内在表达形式的区别。作为以文字描写建构整个文学世界的小说写作,叙事形式在其中不仅承担着讲故事的功用,同样需要结构阅读体验、提供叙事视点。考察万玛才旦的小说创作,可以用“质朴”来概括其形式上的特征:小说多是采用第一人称的主观视点,进行严格依照时间行进的线性叙事,鲜见人称转换或者复杂的结构安排。他笔下的文字一如藏区的草场般辽远开阔,又如清泉般汩汩流淌,即便没有过多技巧性、书面化的表达,却恰切、有力地通过叙事捕捉到了那些最为本真的情感肌理。
但在电影叙事的处理中,万玛才旦有意识地对媒介变更引发的不同观感进行了处理,小说中那些单一、线性的叙事开始被更为复杂的结构取代。电影《撞死了一只羊》改编自导演本人的同名小说以及次仁罗布的小说《杀手》。常规的线性叙事被插入的事件打乱,司机金巴与杀手金巴两条线索相互交织、互为表里,小说文本原有的戏剧性被最大程度地保留,在确保故事完整性的同时,强化了叙事的视听属性:酒馆和仇人家中的两场戏,司机与杀手身处同一场景内的同一位置,通过交叉剪辑的方式,以黑白摄影代替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件,两条本应并行不悖的生命线产生了奇妙的交织。而在另一个层面,小说原有的第一人称叙事被第三人称的全知视点所取代,摄影机如同游荡在山间的野风,冷静而客观地注视着即将发生的一切,叙事者不断在司机金巴、老板娘、杀父仇人之间转换,人物无法长久地占据叙事的中心,且同时又在进行着争夺叙事权的游戏。即便如此,叙述视点却依旧长久地保持静止,影像不断地闪回和重复赋予了电影文本以“众声喧哗”之感,加之主观视角的时而显现,影像内部的时间与空间则被无限的拉伸、延展,在同一个时间段内被平等地展现给观众,它们之间不是断裂的,而是同时被释放出来,巴赫金所言“复调”的叙事向观众敞开。
除去叙事精密的复调编排,一些符码式的文化景观也时常出现在万玛才旦的电影中。在《撞死了一只羊》《塔洛》等短篇小说当中,万玛才旦只描述事件而不做价值判断,甚至缺少修辞学意义上的文体研判,如同民间说书艺人在故事结束时的留白,阐释的空间往往全部向读者敞开。同深植于湘西边城的沈从文、生长于南洋幽暗密林中的张贵兴相比,万玛才旦的写作也带着极强的文化认同感,他用最质朴的方式呈现藏地本真的文化风貌,在小说中他多用平铺直叙的方式对事件直接陈述,而在电影叙事的处理中,民族元素则与视听元素大量融合,产生了许多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码。
万玛才旦敏锐地捕捉到了藏族艺术与宗教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宗教占据了藏民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重要位置,作为藏文化的表现形式,经院、喇嘛、佛像、转经筒、煨桑台、牦牛、嘛呢石、酥油灯等象征物从视觉上建构了文化内部的物理空间,它们无时无刻不关联着藏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而导演本人正是试图以这些符号化、形式化的东西来隐晦地强调其文化认同内在的独特性。正如他本人在访谈中所言:“藏族文学可能不太注重现实主义的东西,反而更强调或者突出象征的、寓言性的东西。”[2]因而在跨媒介改编的过程中,那些“符号性”“隐喻性”的要素被不断放大。早在拍摄《静静的嘛呢石》(2005)《老狗》(2011)等作品时,藏戏《智美更登》、手卷烟(旱烟)、羊与摩托车、辽阔的草场等要素已然构成了一套严密的作者表意系统。万玛才旦正是面对着东方主义和国族共同体的双重想象,找回了失落的能指,拒绝他者式的编码与悬浮[3],以完全在地的、我族的方式不带奇观性地呈现小说中所描写的生活本身,通过隐喻和寓言的形式诉说藏区文化中那些久已深入人心,但依旧生猛、粗粝的原生文化形态。
(二)叙事主题:民族景观的合力书写
“主题,是一部优秀小说和电影最重要的要素。主题引领素材编制结构,所有的情节、人物等元素都应为主题服务。”[4]对传统藏族文化的书写是万玛才旦在小说和电影中一以贯之的聚焦主题。通过阅读万玛才旦近年来发表的小说作品,能够归纳出一条清晰的脉络——他有意识地融合个体的生活经验,坚定地从藏民族的内在视点出发,讲述一个个充满生活质感与灵动生命体验的藏区故事。随着近年他的创作重心转向电影领域,不同媒介的加持极大丰富了其作品序列的深刻意涵,正是通过电影艺术与文学的共同合力,书写藏民族的文化、地缘与人文景观。
小说和电影都是叙事的艺术,如何推进叙事,如何让人物更加丰满,在不断联结电影与文学的过程中,万玛才旦始终在不断前进。《塔洛》相较底本小说而言,花费了大量笔墨对藏区地理空间进行描绘。在主人公塔洛放羊及其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几乎所有外景段落都采用低对比度色彩、大全景的摄影景别。在大景别下人物通常处在画面中极边缘的位置上,在广阔的高原土地上如蝼蚁般踽踽独行,而低对比的色彩呈现使得原本高远辽阔的牧区草场变得生冷而静默,通过对外部环境的描写契合主人公的心境。一方面小说的核心故事情节得到保留,确保了电影改编之后的主题不变,另一方面更多人物形象、性格的刻画与塑造,极大程度地丰富了小说文本的视觉表现,使其能够在不改换原意的情境下深化表达。
在藏区现代化的过程中,万玛才旦一以贯之地通过兼具诗意与作者性的目光观照藏地故乡的日常生活以及发生在这个场域之内宗教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以独特的影像风格与叙事方式呈现主人公们面临的传统信仰与现实冲突的困境,以及个体的生存境况等。自第一部小说改编作品《塔洛》开始,万玛才旦的改编道路一直都在重复并不断深化同一个主题:文化交融下对于现代性的忧思。以塔洛为代表的传统牧人相信,世界无非就是黑白两种颜色,好坏也时常随当下的情况不断转换。因此当杨秀措饰演的理发店老板娘代表的“现代思维”进入他们的生活之时,已形成的价值观念将会遭受强烈的冲击。
与《老狗》中那只藏獒犬所意指的内容相似,塔洛的羊代表着藏区传统的生存模式,也是保有期待的“前现代”居民们始终坚守的信仰观念,而随着羊群被变卖,作为提喻的小辫子被剪掉,摩托车取代马匹成为交通工具,现代性对文化认同带来的演变和“威胁”便被放置在前景。现代之所以成为奇观,是因为“直接作用于感官”的银幕形象与传统所描绘的藏民形象大相径庭[5]。万玛才旦对于藏区地缘特质及当下真实情境的描绘,并不仅仅停留在“物质现实的复原”层面,主题上对民族景观的客观再现,仅仅是小说中所具备的内容,而电影通过对当代藏地生活更为深入、考究的观察,发掘了其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文化与私人情感的多样性,文化认同更多意在强调对现代性与民族传统之间此消彼长的复杂关系的重新思考,这也是其小说经由跨媒介改编之后呈现的复杂内蕴之一。
(三)叙事策略:奇观祛魅与精神复归
在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中,“少数民族电影”作为一个专事描写汉民族以外的民族景观、文化风貌与历史事件的特殊电影类型,长久存在于区域电影研究的视野当中,虽然在全球化意识日益普及的当下,这一概念逐渐被“民族志电影”或“母语电影”的称谓所取代,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少数民族电影”所代表的仅仅是一种国族化、景观化的叙事策略[6]。
“十七年”时期国营制片厂创作了《五朵金花》(1959)《农奴》(1963)《阿诗玛》(1964)等一批描绘少数民族生活的影片,这些作品全部由非少数民族导演执导,甚至在演职人员中也鲜有少数民族的参与。一方面它们承担着佐证宏大叙事模式中“家国叙事”的重要任务,充当缓和民族矛盾的重要策略,而另一方面这些由官方授意拍摄的影片又视少数民族为待拯救的、未开化的对象,其间暗藏着对少数民族一种“他者化”的认知。通过意识形态机器的询唤,“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7]而自德国探险家威廉·费尔希纳(Wilhelm Filchner)于1903-1905年间在西藏地区拍摄的《西藏东部探寻》[8]至今,对于西藏等少数民族区域长期存在奇观式、景观化的呈现,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描述的那样:“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浪漫情调、异国风味、美丽风景、难忘记忆和已逝往昔。”[9]欧洲中心主义者对待亚洲的看法,似乎正与西藏地区自身的处境不谋而合。
特殊时期对于少数民族电影的国族化处理,很快随着80-90年代市场化的席卷与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被重新“赋魅”,西藏成为杂志报刊、口耳相传中未经世俗沾染的“圣地”,被认为是涤荡心灵、洗尽铅华的世外桃源。高耸入云的雪山、地广人稀的草场、澄澈见底的湖泊等景观式的自然景象,与虔诚的朝圣之旅及摄人的宗教秘仪等刻奇的人文景观,似乎从不同方面构成了短暂而超脱于现实秩序与世俗生活的“异质”空间,成为一种致力于制造以假乱真的视觉幻象的“伪现实主义”。万玛才旦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通过叙事策略的扭转,在其小说的改编过程中实现对藏地形象的祛魅以及原生民族精神的复归。
在影像内部的表达中,万玛才旦褪去了一切藏地空间被赋予的文化、经济与想象的符码,打破了期待视野中的异域奇观,试图原封不动地呈现一个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日常性的,甚至对于外界而言略带危险的西藏,并且精准地捕捉到了藏地所身处的“中间位置”(in-between)。《塔洛》以大量传统藏区与现代城镇的空间对比呈现社会转型期的变化,寂静的草场上成群结队的羊仔伴随着牧人的呼叫声缓缓走过,与吵闹的市集及摩托车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形成鲜明的对照;而理发女杨措这一人物的设定,充分探讨了在努力追逐梦想或面对金钱诱惑等情境下人性的复杂难解,超越了常规少数民族电影中单一的人物性格设定。《撞死了一只羊》中司机金巴所穿越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更是漫天风沙、天寒地冻,直观而不加修饰地注视康巴藏民生存环境的劳苦与艰辛,从花重金超度一只撞死的羊这种看似荒诞的行为,透视宗教轮回观念浸淫下普通民众对于生死的真实态度。
处于媒介改换之下的小说改编,努力去实现关乎民族文化认同的身份探索。小说中那个超脱、神圣而质朴的西藏仍旧保留在影像中:磕长头去拉萨的朝圣者,对藏传佛教视如神明般虔诚;耕作、畜牧等传统藏区既有的生活方式,依旧被部分藏族百姓所坚守;作为宗教文化传播的实践者,对出家之人的敬畏同对精神世界的需求一样,被广大群众所接受……万玛才旦主动去发掘和探索那些久未被关注的日常性仪式,借摄影机擦除蒙蔽其间的灰尘,将目光投注在以宗教文化为核心的藏地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塑造之上,试图重新复归在“主体”认知主导下的民族精神。
二、媒介转向:作者风格的承继与延伸
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电影改编小说文本在现代社会中被广泛关注。当一种媒介形式渗入其他媒介时,它会引发内在的相互作用,并在新的媒介载体中发挥其优势。跨媒介改编的核心概念是将原始媒介中的故事、主题和叙述理念等要素从独立的文学文本中提炼出来,从而形成各种文本之间的互动和共生关系。媒介本身作为叙事的传播工具,依赖于其独特的媒介属性。在早期,小说文本通过印刷品进入读者的视野,而电影改编则以更广泛的受众基础为出发点,通过影像深化和重建故事,并将影像属性作为其媒介特点。电影以多种表现形式和形态在不同媒介之间流动,以其独特的方式表达叙事内容,并不断创新,与其他媒介形式区分开来。观众可以在这个跨媒介的环境中自由的流动或停顿,这种形式为叙事构建了一个开放的世界,允许受众以各种方式进入并参与其中。由小说向电影的媒介转换,万玛才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保有小说语言的特质,与此同时,作者性的一面得到了承继与延伸,凭借文学、影视双栖的身份把握媒介间的语言转向,并努力将其独有的作者风格放大并展示给更多的观众。
(一)电影语言对文学语言的转译
作为媒介信息传播、表意最为重要的形式,语言是媒介表达最为重要的因素。广义上讲,任何用来传播信息的符号都属于媒介语言。但不同媒介通常经由不同的媒介语言的呈现,凸显其内在的媒介属性。语言通过艺术创作者的加工、编码,以一定的媒介形式进行传输,接受者根据自身的教育背景、认知能力与艺术鉴赏能力等进行解码并获取所要传递的信息,可以说媒介传递信息的过程,必须经过特定的语言处理,进而实现艺术创作的交流与交往。小说语言作为文学语言的一种类型,主要以字、词、句段的方式组成叙事肌理。在阅读的过程中,文学语言内部存在一定的修辞,文字、语句进入读者的视野,符号转化为头脑中既有的图像经验,进而在意识中重新组合。相较之下,电影语言则体现在视觉和听觉之上,镜头的角度、色彩、滤镜以及内部的场面调度拓宽了文学语言中单一的视觉接受。小说的跨媒介改编,正是将小说语言所传达的信息进行解码,并重新分解、组织,以适应影像媒介特质与受众期待的方式重新编码,重新进入文本接受的前景。
长镜头的使用是万玛才旦“作者性”的标识性特征之一,与小说中客观而不加修饰的白描构成互文,日常生活的流程在镜头长时间的注视下默默展开,电影《塔洛》全片只有84个镜头,塔洛在警察局背诵“老三篇”之一《为人民服务》的场景、在照相馆等待照片采集的场景、在情感与金钱双双被骗时怅然若失的场景等,全部采用固定机位的长镜头,真实的叙事空间不断在影像中延展,文字缺失的环境描写与细节描写被全部涵盖其中,甚至增添了影像中未能涉及的部分。在色彩的运用上,《撞死了一只羊》以彩色指代现实的情境,而使用黑白呈现闪回的部分,在处理黑白影像时,万玛才旦使用了特殊的旋焦镜头,将单个镜头内部的焦点控制在画面的特定区域,而焦点之外的画面则呈现光斑散射的效果,人物仿佛身处与现实世界平行的世界,同时部分超现实的插入镜头超越了小说内部纯粹而客观的现实主义描写,进而放大了人物复杂且细微的情绪变动,精准地以影像的方式窥见回忆的泥淖。
分析其镜头表现时能够发现,万玛才旦鲜少在场面调度上进行铺陈,更注重对画面的镜框、景别与构图设计:在早期的“故乡三部曲”(《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中,万玛才旦就多次将画面内部的要素和景观统合排列成几何状的布局,如寺庙等宗教场地的再现就多用全景镜头、对称构图,其间建筑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空间,与身处内部人物的渺小身影形成鲜明对照,突出一种神圣而庄严之感。此后几部根据自身文学改编的电影作品,更是实现了这一作者风格的完善与发展,除严整、和谐的构图之外,万玛才旦大量使用镜像构图、反射构图及框架构图,来实现增强现实隐喻或强化主题内核的功用。如《撞死了一只羊》开场不久司机金巴和杀手金巴在车内的对话戏,摄影机被放置在车辆挡风玻璃的正中央,两人分别位于画左及画右,并且面部有一半区域都处在画外,同前景中一面是活佛一面是女儿的照片挂件构成互文,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作为藏地百姓生活的一体两面,以这样极具形式感和表现力的方式传递给观众。万玛才旦巧妙运用道具或自然物像增强文学语言向电影语言转化时单个镜头的表现力,引导观众的视线聚焦在表意符号的中心,同时以更具象征意味的视听语言暗示将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现实的境遇视觉化,从而达到“意在言外”但“意在象中”的境界。
通常情况下,电影的画面直接投射于视网膜,观众只能被动接受导演输出的价值观念,而在影像媒介的单向输出之外实现电影语言对文学语言的拓展,完成个人风格在不同媒介之间的承继与延伸,是跨媒介改编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万玛才旦于2022年出版了汉语小说集《故事只讲了一半》,其中多部短篇小说都采用了“只讲一半”的叙事方法,往往在故事高潮或结局之处戛然而止,留下意蕴充分延宕的空间。其中《尸说新语:枪》一篇更是套用藏地民间故事的回环结构,主人公不断在“如意宝尸”的诱惑下追问故事的结局,叙事者借“尸”之口讲述一个个时而绮靡诡谲,时而谜团丛生的寓言故事。在语言转译的实践中,万玛才旦的电影作品并非是完全阻隔于观众,不带任何阐释空间的私人影像,恰恰相反,电影语言的视听属性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文学语言的留白,一种“言已尽而意无穷”的处理手法恰恰将不同媒介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关联了起来,不断从对文学语言的解码、重新编码中探索自身媒介属性的独特价值,为受众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想象空间。
(二)媒介转型下藏地文化的当代传播
作为当代藏地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万玛才旦于1991年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且能够同时用藏语和汉语写作。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作品的接受存在一定的准入门槛,以藏语书写的小说不但非藏区的读者无法阅读,藏区内部分义务教育程度较低的偏远地区,小说的表现形式也难以被更为广泛的群众所接受。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娱乐化、商品化及通俗化等媒介特性决定了其天生就具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正是经由社会发展过程中科技变革带来的媒介转型,电视、报刊、广播等既有共同点又存在互补性的不同媒介,在内容、宣传、形式等方面进行整合,创建资源通融、内容兼融、宣传互融、利益共融的新型媒体[10]。与藏戏相比被认定为“精英文化”的小说更具有生命力,也更为当下的形式与影视等新兴媒介构成合力,而其中包孕的内在肌理,则是万玛才旦对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深刻体察。
在万玛才旦的电影作品序列中,除《喇叭裤飘荡在一九八三》(2008)之外,全部长片、短片均采用藏语对白、以藏族演员出演。民族语言作为一项重要的符号,它不仅承载了藏族地区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百姓的身份认同,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观看一部藏语电影,对于少数民族观影者更是一次身份认同的镜化演绎[11]。然而仅仅凭借语言这一个要素,就将万玛才旦的电影划归为传统意义上“少数民族电影”显然过于肤浅。从微观的视角切入,万玛才旦正是以他独有的、对民族文化“在地性”的理解,通过视听媒介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建构提供有效且合理的视角,基于由文学艺术到影像艺术的媒介改换,以更易为观众接受的方式推进藏文化的传播;而从宏观层面来看,万玛才旦艺术创作的影响力也不只局限于藏地一隅,近年来他的作品于海内外知名电影节上频频获奖,也证实了藏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支脉所发挥的重要力量,对于这些差异性的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文化的认可和传播,有助于建构一种更容易得到认同的、多元开放的国家形象、国家身份,印证了藏地文化在发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民族性、全国性与世界性之间产生的关联。
三、“异质”解构:藏地文化的世俗演绎
万玛才旦以雄鹰之姿闯入文学与电影之中,生动质朴的本色式写作在影像的赋能下不断扩展其丰富的想象力,影像作品序列中始终流淌的藏地民族风情的叙事主题,亦不断指向以藏地神话与民间传统故事为主体的地理空间与文化场域。其作品中身份自觉的影像内核表达使其成为民族间交流的中介与桥梁,对过去与未来进行双向的触摸与反拨。更重要的是,以全球化语境再度审视藏地影像,借由藏地文化世俗演绎的有效续接、小说到电影的转向中藏地空间的影像化延展,都在间接实现在地性与全球性的关系平衡。
(一)民族肌理的内视角洞悉
哲学界巨匠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以世俗化研究闻名于世,“世俗性是关于理解之整体语境的问题”[12],其研究核心表明,世俗化不能被简单的定义为宗教功能的弱化,而是应该被解释为解读宗教的语境整体性迁移。万玛才旦的作品序列始终处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境中,在这一整体性的语境之下阐释其民族文化,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都有着非常鲜明的故事基调与个人风格的内视角探询,充斥着对于宗教文化的世俗化表达。
万玛才旦以其独特的知识分子视角建构起根植于藏地空间的、面向藏地人民的人文观照,试图以其独特的作者化写作手法柔软温和地给出兼顾信仰价值与现实力量的世俗答案。以影片《气球》为例,主线讲述主人公达杰一家因为避孕套的“不当出现”而陷入一系列尴尬事件,气球与避孕套的重叠意象在勾连嵌合之下,构成了从家庭个体单元到社会整体结构,从宗教到文明的寓言拼图。支线中卓嘎与尼姑妹妹、尼姑与德本加这两条支线又同时与主线紧密连结,虚实相生并行发展,从而使电影获得了复调结构里的民族宗教质感,多线互动的故事结构亦给世俗化表达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万玛才旦以藏地经验与藏族文化为底,将民族影像的魅力无尽放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语境之下,在更广阔的中华大地上不断绵延编织与内在建构,在藏语、汉语之间灵活互动,以一种更接近于叙事的、纪实性的拍摄手法展现城镇化进程中藏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交融并生,在本色写作的质朴美学上使宗教文化的世俗化表达落地。
“嵌入”与“脱嵌”亦是理解查尔斯·泰勒世俗化理论的重要概念。嵌入既是身份的问题——对自我想象的语境限制——也是社会想象的问题:我们可以对整个社会进行思考和想象的方式[13]。在小说与电影合力书写的过程中,万玛才旦从未局限于藏地语境,而是一以贯之的从国家、社会与时代的整体性出发,在媒介转向的过程中,他借由“死亡”“轮回”“生育”“爱情”等普适性议题将藏族文化中的“异质性”稀释剥离,抽丝剥茧般巧妙提炼并使用普通意象进行二次编织,实现带有作者性风格的藏地文化的世俗演绎。他的作品几乎都在处理和平衡民族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这不仅仅是藏区问题,更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气球》中小儿子在梦境中拿掉了哥哥身上的黑痣,三人在沙漠里追逐嬉闹,俨然是一种纯粹的、回归自由的原始状态。痣的脱落似乎意味着思想禁锢的解除,孩子不再作为奶奶的转世,而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此类超现实主义梦境表达亦是万玛才旦解构宗教文化,使其完成世俗化演绎的重要手法之一。
(二)世俗化的精神空间探询
传统藏区游牧式的生活形态,造就了其独特的分散型草原居住模式。建国以后,乡镇机构的完善打破了原有的民族部落制度,传统的牧区生存空间开始动态变化,藏地游牧民族经历了有组织的社会变迁以及“再社会化”的过程,藏民定居的步伐亦开始不断迈进。万玛才旦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转型期,观照其作品序列中诸多藏地传统居民建筑与宗教遗产建筑,都能洞悉在文化过渡与融合的转型期地域性特征,呈现出该时期的艺术审美与民族文化。千禧年以来,城市化进程推进了藏地空间与地缘文化的交互与流动,现代性的住房建筑、基础设施、学校等逐一深入藏地,他在观照藏地地理空间的同时,亦在心理上触及了藏地人民的精神空间。
与原著相比,电影《塔洛》对藏地空间环境进行了影像化补充,通过呈现传统牧民的藏区住房与现代化城镇建筑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藏区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双向拆解建构,续借其对藏地、时代与人民的深思与自省。电影多次使用框式分割意象来凸显塔洛作为一个传统的牧民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的落寞与疏离。主角“小辫子”塔洛以辩经式背诵语录的形象出现,在反黄金比例的影像构图中,万玛才旦反复将其置于画面的边缘地带,又或者被门、窗、墙、镜子、烟囱等物象隔开,这也恰好呼应其中空的边缘人身份位置。塔洛所代表的是以游牧文明为基点,以藏族传统文化为信仰的质朴式“原始人”,办理身份证的进程亦是一个“人”向“民”转变的过程,理发店女老板则指向了以商品经济为出发点,将开放、自由作为生活准则的“现代人”。在进入城市后,塔洛的个人世界与主体活动被强行挤压与置换,短暂经历了幻想式的爱情后又独自返回原乡,骑着摩托车的塔洛疾驰在高原的公路上,仿佛孤勇的堂吉诃德。来自藏地主体的影像自述在某种程度上亦完成了全球影像的更新与嬗变,巧妙而细腻地展现了踟蹰于传统原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边缘人”的怅然与窘迫。
然而,塔洛这一人物形象又绝非仅是常规意义上的边缘人物,而是同贾樟柯镜头下的“小武”、梁鸿笔下那些梁庄村民们所属同一序列,共同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与文化的流动。万玛才旦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的嬗变与文本符号之外的物质文明高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剧暗合勾连,相互阐明、相互解释,审视同一个主题,进行同一种探询,重构新世纪以来藏地民族想象与文化寓言。叙事内核在光影流动之间指向藏地空间与藏族人民的信仰危机与精神症结。这不仅仅是塔洛作为独立个体的身份迷失与精神孤寂,更是整个藏区面对现代文化侵入之后有关自我身份的焦虑与迷茫。
四、结语
万玛才旦在其短篇小说集《乌金的牙齿》中,开篇写道:“我渴望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乡的故事……一个更真实的被风刮过的故乡。”将小说进行跨媒介改编之后,万玛才旦借由电影这一艺术形式在传播民族文化的广度和深度上持续发力,他携带着独一无二的藏地生命经验、不断完善的自我观念、对藏地文化的世俗演绎、开始走向一个全新的、未知的领域。其媒介转向看似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之上审视宗教与信仰的冲突,但其内涵早已超越了地域的限制,其真正的魅力在于,创生出一种饱含东方式电影的生命性的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电影。在保持原著小说浪漫温柔与克制隐忍的前提下,借由电影的艺术媒介实现了饱含作者性的世俗化表达,其开放式的结局更是留给了观者无尽的想象空间。
“一旦不同民族之间形成了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各民族建立起了相互依赖、相互渗入的社会关联,就能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持续的稳定的社会性基础。”[14]万玛才旦从小说到电影的转向中,坚持以人民为创作主体讲述中国故事,不自觉地形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合力,为藏汉之间的民族互动不断注力赋能。各民族之间的交融发展,必然是以民族之间的差异作为前提基础的,而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认同。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其小说与电影合力书写人民故事与民族景观,其过程亦是藏汉文化的流动与互嵌,本质上更是民族文化的借鉴与互动,对民族关系的整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强化民族间的国家认同与身份自觉,筑牢多民族国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呈现出鲜明的时代价值、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M].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36.
[2]万玛才旦,杜庆春,于清.也许这才是讨论世界的方式——与万玛才旦导演谈《撞死了一只羊》[J].当代电影,2019(5):18-23,177-178.
[3]谢建华,万玛才旦,陈佑松,等.万玛才旦:作者电影、作家电影与民族电影的多维实践者[J].艺术广角,2020(1):4-13.
[4]徐兆寿,刘京祥.中国现当代文学电影改编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206.
[5]肖月,谢建华.行在迷途:万玛才旦电影的现代性危机[J].艺术广角,2021(3):35-42.
[6]向宇.国族化、景观化、民族化——国产西藏电影叙事的身份想象[J].电影新作,2016(5):81-88.
[7]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
[8]霍金斯.影视人类学原理[M].王筑生,等编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4.
[9]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
[10]尚策.融媒体的构建原则与模式分析[J].出版广角,2015(14):26-29.
[11]刘静.2000年以来少数民族电影的身份问题研究[D].徐州:中国矿业大学,2015.
[12]泰勒.世俗时代[M].张容南,盛韵,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6.
[13]Taylor C.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2003:62.
[14]郝亚明.民族互嵌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逻辑[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8-12.
作者简介:
谢庆威,河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电影文化研究、电影节展研究。
赵瑞宇,河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影视批评与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