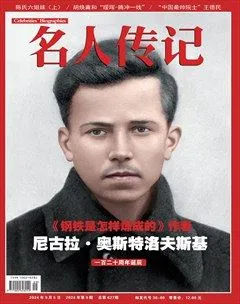我和《名人传记》的三十年文缘
在我的成长与写作历程中,《名人传记》这本杂志和编辑部的几位编辑老师,可以说是我文学道路上的加油站和充电桩。算起来,我和《名人传记》的交往有三十多年了。
1991年,我偶然读到《名人传记》,觉得我的文字适合,便从当时正在写作的《许继慎将军传》中挑选部分内容,写成《将星,陨落在大别山上》一文寄到编辑部。不久,就接到编辑部寄来的校对稿,还有一封编辑王亚东(肖兵)的信,这便让我和《名人传记》建立了联系。
那个阶段,有了王亚东老师的指点,我在《名人传记》相继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应该是《沈炳麟先生的赤子情》一文。这篇文章写了香港爱国同胞沈炳麟捐资助学的事,结果是我和编辑部都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都是说要联系沈先生到他们的家乡捐资助学的。另一篇是《蒋光慈与宋若瑜的生死恋》,发表后被不少杂志转载。
2006年,王亚东老师退休后,接着联系的是一位陈女士,当时她还是一位青涩干练的女青年,现在已成为杂志社的当家人了。
陈女士一直要求杂志能挖掘新鲜的选题,找到一手的资料和故事呈现给读者,于是要求编辑努力、大胆地去挖掘有潜力的作者。从她的编前编后及在公众号推荐的一些文章看,她对杂志的发展壮大是有一整套规划的。之后与我联系的又是两位年轻编辑,这两位科班出身的青年人对审稿子也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前几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我正在写作有关红二十五军长征史及开国大将徐海东的传记。徐海东家族为革命牺牲了七十余位亲人,但有很多烈士情况不明。为此,我四下徐海东家乡,在当地政协及文史部门支持下,总算把纷繁复杂的情况摸清楚,于是便写了《“光荣流血”——记徐海东家族为革命牺牲的七十余位亲属》一文交编辑部,作为《名人传记》2022年开年头篇发表。这篇文章影响不小,后被不少杂志转发,并被喜马拉雅电台选播,甚至还被一个“作者”全文照抄发表在了某一知名刊物上。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另一件往事。1981年,我还在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那时写小说,满天下投稿。其中一次,河南人民出版社主办的纯文学杂志《奔流》的编辑涂白玉老师,就我的一篇小说稿写了几页纸的修改意见,还就另一篇小说稿多次与我通信交流,让我受益匪浅。1982年毕业参加工作后,一段时间我停止了纯文学的创作,但始终没有忘记涂白玉老师的教诲。我现在仍在写作的道路上耕耘,仍有他作为推手的力量。这样一些经历,都让我觉得河南人厚重、靠谱,有人文气质,值得永久相处。
我写这篇文章,也是感慨作者和编辑之间这种彼此扶持的关系。这次,贵刊一位年轻的编辑约我写这篇文章,想听我谈谈和《名人传记》的故事,我想,也是贵刊接地气、充盈自身的有益举措。三十年来,《名人传记》可以说是我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所沟通合作过的编辑们确是我的良师益友。虽是君子之交,淡淡如水,但却情谊牢固。
《名人传记》于20世纪80年代诞生于中州大地,一路走来,已成为同类杂志的佼佼者。从一期期杂志和通联工作上,不难看出其不断探索的脚步、认真经营的态度和洋溢其间的向上发展的蓬勃气势。现在网络发达,传统纸质刊物受到巨大冲击,难免面临巨大挑战,但《名人传记》有积淀深厚的中原文化作沃土,有奔流不息的黄河洛水作血脉,有巍峨高耸的嵩山太行作依靠,有催人奋进的红色文化作旗帜,有朝一日,一定会再次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