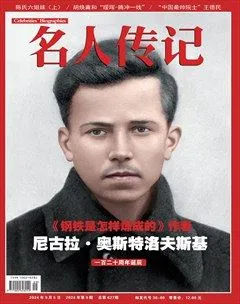“沙漠旅者”雷石榆




1986年4月1日清晨,由北京飞往日本东京的航班上,坐着一位年逾七旬的老者,虽头发斑白,但清瘦矍铄,尤其是一身考究的西装,显示出与旁人相当不同的气质。这位老者便是河北大学中文系教授雷石榆。机舱中,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东京啊,现在你变成什么样了呢?我将借此机会,进行文化交流,访问旧友,追悼故人,面晤新交……”的确,这次出行并非普通的出国访问,而是一次跨越了整整五十年的沧桑巨变的回忆之旅……
以日语唱响“沙漠之歌”,壮大东亚左翼力量
雷石榆,1911年出生于广东著名的侨乡台山。他幼年丧母,被祖母抚养长大,自幼聪慧过人。依靠父亲下南洋到爪哇的首府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经商所赚取的侨汇,雷石榆得以入读私塾,之后又借着新文化的风尚及现代教育制度的普及,相继在新学制高小和西式化的县立中学继续学业。中学时期,雷石榆已经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毕业后便开始在国内报刊上发表相关评论文章,并因此被解职。1933年樱花开放时节,雷石榆终于得以前往东京留学。时值日本左翼政治运动被当局镇压、衰退时期,然红色火种犹存,进步青年被迫转向文化运动,雷石榆也直接参与到当时许多反映现实、坚持斗争的文艺社团与活动当中。
在当时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被封锁,而在日本却有着得天独厚的开拓新局之条件。初到日本,雷石榆的日语尚且稚拙,但语言无法压抑身处变局时代中诗人满溢的诗兴,他奇迹般写出大量富有个性的日语诗篇。在郭沫若等人的指引下,1934年春,雷石榆与同乡兼好友林为梁(即后来的烈士林基路),以及魏晋、林焕平、陈紫秋、黄新波、陈子谷等留日爱国青年一道,加入中国左翼文艺联盟东京分盟,并相继创办《东流》《诗歌》等机关刊物。
1934年秋,雷石榆加入日本左翼诗人团体的刊物《诗精神》,成为该杂志唯一的中国同人,与创办人新井彻及后藤郁子夫妇,诗论家远地辉武、讽刺诗人小熊秀雄、剧作家秋田雨雀、童话家槙本楠郎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也给《文化集团》《诗导标》《诗人时代》《文学案内》等日本左翼刊物写作日文诗、文坛报道及诗评。
1935年,在新井彻等人的帮助下,雷石榆用日文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沙漠之歌》,并在东京新宿“白十字”召开《沙漠之歌》出版纪念会。“沙漠”的意象来源于鲁迅1932年在《〈自选集〉自序》中的一段自况:“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而雷石榆的诗作与鲁迅或有共同的心境,更回到对集体主义的追索,其诗使得“沙漠”意象更加具象化,成为一代人处境的象喻:
印在沙漠上的无数足迹——/野兽之群发现了我的形影吗?/在暴风雨中/交错着轻微磨牙锉爪的声音/旋风卷起沙柱/往我头上压来/我却无所畏惧地/牢牢地踏着大地前进/不久,啊不久/通过这短程的沙漠/就会到处遇到无数/有力的赤裸裸的“手”/来把我的手紧握起来。
孤独的个体在恶劣而迷茫的旷野之中,逐渐团结起一股强大的前行之力,生成在艰苦的旅程中努力走到绿洲的坚强意志,自此,“沙漠”成为东京一大批左翼诗人群体所共通的典故。
正如雷石榆的好友、留日中国台湾诗人吴坤煌1935年末创作的《漂流旷野的人们》一诗,就与《沙漠之歌》有明显的呼应与唱和:
在悠久的时空里,/我现在仍然在漂流旷野的人们之中/像沙漠的旅人/只有一颗星光/导引我们的方向。……/就像在沙漠中旅行的阿拉伯人/究竟要往何处——/我却毫无所知/只有在仰望星空的瞬间/大家手挽手唱起歌来/似乎此时大家都不再恐惧与战栗。
当时,台湾还在日本殖民者的铁蹄之下,两岸明明同文同种、同根同源,却被生硬地长期隔绝。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台湾成为日本攫取原材料、培养苦力的“落后”之地,受着极其残忍的不公平待遇。因此,两岸人民的处境,以及谋求反抗的心理实际是相通的。吴坤煌与雷石榆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34年10月在日本进步诗人远地辉武的出版纪念会上相识。
雷、吴的熟识,打破隔绝,开眼前沿,使得彼此都成为当时祖国文艺运动中的青年人。雷石榆曾在台湾文艺联盟的机关刊物《台湾文艺》上多次发表诗歌、评论、散文,甚至还作为唯一的祖国大陆同人,参加了台湾文艺联盟东京支部的茶会。在这次茶会上,雷石榆为台湾文艺的继续发展提供了相当恳切的意见,并指出台湾文坛与大陆文坛携手合作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吴坤煌也在左联东京支部的《诗歌》杂志上连续供稿,为大陆的左翼文学青年介绍台湾诗坛的现状。并且,通过从雷石榆及左联东京分盟获取的报刊、书籍,吴坤煌又得以向日本左翼文坛介绍祖国的文艺动向。例如,他将左联诗人林林的诗作《盐》翻译并发表在《诗精神》上,附注点明其中的革命隐喻。
雷石榆等人的努力有目共睹,日语反成为东亚噤声者争取发言权的利器。而日本诗人们普遍认为雷石榆的《沙漠之歌》出版纪念会对他们的启发很大,因为中国诗人说出了日本文学者没有说的话。雷石榆以文艺的方式撬动现实,团结起帝国主义之外的进步日本群众,共同组成了走出“沙漠”的国际纵队。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变本加厉的集权统治,日本国内的气氛也越发肃杀凝重,尤其外来的留学生更是被严密监视。1935年秋,雷石榆两次被日本警视厅东亚系传讯,对其发出严厉的质问和警告。是年冬天,终于将其逮捕拘禁、严加审问:“你是一个中国人,为什么参加日本人的诗杂志《诗精神》?你为什么用日语写东西……”在这之后,雷石榆被驱逐出境。寒风萧瑟的冬日,雷石榆被便衣日警押送至横滨码头,日本的新井彻、后藤郁子、小熊秀雄,左联东京分盟的蒲风(烈士,1942年8月积劳成疾,死于淮南抗日根据地)、魏晋、林林、戴何勿,中国台湾的吴坤煌等一众诗友赶来问询送别。此时的他们已经为营救雷石榆而奔走多日,却屡遭拒绝,得见雷石榆能活着回国,非常高兴,用日语再三高呼:“雷君万岁!”这“冬寒”时代伟大的众口一声,至今余音绕梁,荣光犹存。
从前线到后方,以文艺坚持抗战
归国后的雷石榆曾寓居上海,卖文为生,与白曙、柳倩、田间等左联作家都有交往,还曾捐出全部稿费救助病重的叶紫。此时的雷石榆仍不愿放弃东京的学业、运动以及与日本读者本多菊枝新建立起的爱情,于是在第二年春天以化名再度冒险赴日。但日本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雷石榆只好彻底死心回国。
在好友蒲风的邀请下,雷石榆前往福州一中学任教,同时兼任《福建民报》的编辑,并在全国各地乃至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上发表救亡文章。此时的雷石榆已蜕变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前辈诗人了,并开始与地方文化教育界及文艺青年交往。他和蒲风发扬并壮大了左翼诗歌朗诵运动,向青年们提倡“歌唱就是力量”的新诗歌运动。过去,诗歌以文字为载体、以视觉的方式呈现,在当时基础教育缺失的中国,文字诗注定只能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文艺活动。而诗歌朗诵运动则是一种公共性的诗歌表演活动,主要运用朗诵、合唱、诗剧等听觉形式,将诗歌搬演到街头巷尾。这一变化并非将无声的字句诵读出来那么简单,而是对作者本身提出了转变的要求。这样的朗诵诗承载着左翼诗人群体与人民群众交互融合的理想,尤其在那样的危急存亡之秋,更显出其极高的宣传鼓动能力。正如雷石榆自陈:“但被魔鬼放逐回到上海以后,我就感到用故国的言语,爆发出愤怒的火花的必要了。”不难发现,随着局势的愈发紧张,雷石榆的创作实践,都尽可能地改换过去个人痛苦心声的抒写,而愈发朝着一种写实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发展了。
1937年夏天,雷石榆回到故乡台山,旋而卢沟桥事变爆发,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雷石榆参与当地知识分子组织的抗日后援演剧活动,不久,即与好友蒲风、黄宁婴等人在广州兴办《中国诗坛》杂志,使其成为保持着左联色彩、具有一定自发性的地方抗战文化阵地。实际上,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上海一直是中国文化出版的中心,但随着战局的变化,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文化版图被迫重制。大批文人南下,辗转汉口、广州、香港等地。由此,广州成为抗战初期后方的重要文化中心。在此背景下,雷石榆等广东本地的知识分子被陆续团结至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中国诗坛》也得以有条件开展长期的串联活动。随着文化中心的南移,一时间,夏衍、郭沫若、茅盾等文化巨擘皆云集广州,坐镇后方的文化宣传工作,雷石榆也由此参与到由夏、郭二人组织复刊的《救亡日报》的撰稿工作中。
这样的“笔战”生活持续一年,诗人得到了从戎抗敌、前往晋南第二战区担任日语翻译的机会:
别了,广州!/前线需要我/我要在北国的尘埃中/在沙场的血泊里/冒着敌人的炮火/飞驰我们的战马/战斗,战斗!/我要把俘虏变成我们的斗士/我要把敌兵变成我们的战友/把新世界的土台筑起/把法西斯的尸首深埋!
于是,雷石榆一行人一路北上。直到晚年,他仍能以平实而潜藏激动的语言,清晰回忆起在舟车劳顿中初见母亲河的场景:
我们乘火车直上郑州转往渑池,搭乘大卡车盘着起伏不平的山间土道爬行到黄河岸边,再乘木船横渡到对岸。第一次看到浑浊的黄色波浪,只见沙滩中的洼坑浮现清水,我们用手掌勺着喝,黄土地带的暑气特别蒸人。
终于,雷石榆到达太行山脚下的垣曲,之后又随军转往平陆、洛阳,在卫立煌的领导下承担编译日文资料、与俘虏沟通等工作,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行旅途中,雷石榆仍然坚持写诗,比起过去的宣传朗诵诗,此时他的诗歌具有更充分的叙事色彩。诗歌内容多涉及前线战场九死一生的切身体验、战斗英雄的光辉事迹、日军俘虏的个体故事、与战地作家访问团的交游等。这一时期,诗人对诗艺的理解在实际的斗争工作中得到升华,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战地直接经验。
出于种种原因,1939年秋天,雷石榆离职,从艰苦的前线转向沉郁的后方,到昆明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的会务工作长达四年,并主编会刊《西南文艺》,协助罗铁鹰编印《战歌》杂志,得到郭沫若、老舍、巴金、穆木天、楚图南、谢六逸等多人的支持,也和左联时期的许多作家朋友持续交往合作。之后又创办《文学评论》一刊,得到李广田、王佐良等一众西南联大师生的大力支持。
在大后方发展文艺的经历,与抗战初期的广州,或者北方行旅时期皆不相同,对雷石榆来说也是一大挑战:
在大后方发展抗战文学是比较复杂艰巨的,有经济生活的动荡、出版检查的关卡、政治气候的反常、读者层的不同心理状态等原因,就不可能像在抗敌前线那样,随心所欲地放怀歌唱、果敢地呐喊;反之,在大后方的环境下,多数读者能接受或起痛感作用的,是感同身受的情绪,是有助于理解客观的某些真实或引起的联想与反思。
或许正是有了在大后方从事文艺抗战活动的经历,使得雷石榆的文艺关系网辐射全国各地,从而使他成为一个更加坚定、成熟的文艺工作者,也对他之后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缔结台湾悲喜情缘
从1944年初春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雷石榆一直在中国东南部漂泊,相继在桂林、信丰、龙南等地办刊、任教,最后落脚在福建长汀。雷石榆的诗歌总是热情洋溢且相当高产,但抗战胜利当晚所写下的诗篇,却意外有一股沉郁之气于其中:
我记起在多年的征逐里/写过不少预期胜利的诗篇/在这时,我握起笔/好久,好久,不知怎样写/“胜利”两个字。
按照他自己的总结,当时的心情是“百感交集”。的确,日本的侵略使得他与恋人被迫分离,使得老师、姐姐、姐夫饿死,使得供养自己的父亲死于印尼战火,不见尸首……八年间走南闯北,参与全国各区域抗战,甚至还深入军中,又多与战俘接触,那股天生的激情反而被延宕了,这一次,诗人雷石榆意外地比时代情绪“慢”了半拍。
抗战胜利后,雷石榆到厦门任《闽南新报》副刊主编。到了厦门,他很快意识到:“厦门是敌伪盘踞较久的著名海岛城市,日本一宣告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各派系大小人物,立即争先恐后来发‘胜利’财,挑肥拣瘦‘接收’一通后,又滥发‘金圆券’……市面呈现虚假的繁荣……但盛景不长,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渐渐变得萧条、杂乱。”
抗战胜利后大陆曾出现赴台高潮,厦门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有志于到台湾加入文化重建,而雷石榆在东京时就曾与吴坤煌、赖明弘等人交往甚密,在台湾文坛上也算小有名气。于是,当他所在的报刊因资金问题停办,雷石榆就同熟人一道也前往台湾。就这样,雷石榆开始在高雄的《国声报》担任主笔兼编副刊,之后又趁报社内讧辞职北上,到台北的台湾交响乐团担任编审。正是在交响乐团的工作中,雷石榆认识了著名台湾舞蹈家蔡瑞月。
蔡瑞月出生于台南,自幼喜欢跳舞,自台南第二女高毕业后得以赴日学舞,战后回台传播现代舞,开设了台湾省第一个舞蹈研究社——“蔡瑞月舞俑艺术研究社”。1946年冬,蔡瑞月在雷石榆竭尽全力的协助下顺利在台北中山堂公演,场场爆满,轰动一时,二人的感情也迅速升温。这次表演后,雷石榆离开乐团,到台湾大学法学院担任副教授。
雷石榆虽有过几段感情经历,但均因时代原因被迫分离,以至年过而立仍孑然一身。初次与蔡瑞月约会时,他写下这样的句子:“这么轻柔的声音,发自这么丰富的身体。我在心里赞叹她艺术上的专门和锻炼,我也不由自主地,不由自主地,被她吸引,被她焕发着东方与西方美感的身体,和眼神,和灵魂吸引。”而对于蔡瑞月来说,即将独自带团前往台中的她,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雷石榆。于是,在分别的前一晚,雷石榆送蔡瑞月回家时,摘下手腕上的旧表向她求婚。
1947年5月20日,二二八起义刚爆发不到三个月,台湾仍处在风声鹤唳之中。但这无法阻挡一对恋人步上红毯的热情。二人婚后有过相当安稳快乐的一段时光,雷石榆曾为妻子写下《假如我是一只海燕》:
我发狂地飞旋歌唱/用低音唱出爱情的小调/用高音开始进行曲的前奏/哦!假如我是一只海燕/永远不会害怕/也不会忧愁。
蔡瑞月以此诗编舞,夫妇二人可谓琴瑟和鸣。1948年3月,儿子雷大鹏出生了。
然而,局势的恶化并不以个人的幸福为转移,凛冬悄然而至。先是1948年夏天,雷石榆等人被台大解聘,但他并不愿远离现实,坚持继续文艺斗争,尤其是当年他又投入《新生报》的《桥》副刊上那场著名的关于“新现实主义”的论战中,一连发表五篇文章。雷石榆的这一系列提倡,可以说是首次将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化地引入台湾。在台期间,除却与留日旧友来往亲近,雷石榆与大陆赴台的许寿裳(鲁迅挚友,1948年被暗杀于台大宿舍)、李何林、李霁野、陶晶孙,台湾的覃子豪、杨逵、陈文彬、宋斐如(烈士,在二二八起义中被杀害)、吕赫若(台湾共产党人,烈士,1951年牺牲在台湾山区)也都有交往。可以想见,持有这样的立场观点,有着这样交际圈的文化人,在当时的台湾会受到国民党当局怎样的注目。
果不其然,1949年6月1日傍晚,刚筹款买好全家赴香港船票的雷石榆,在家门口被几名陌生男子逮捕,押送至特务机关所在的西本愿寺。牢狱中的生活环境极其恶劣,雷石榆也被多次严加审讯。1949年9月1日,雷石榆被告知判处“驱逐”,这对于当时的外省人来说是相对较好的结局。拘留所允许通知亲人来见面,时隔三个月,雷石榆终于得见妻子和儿子。
经过交涉,蔡瑞月本以为可以与雷石榆一同出境,便携子随夫赶赴基隆港。当时没有雷石榆出发的确切消息,蔡瑞月只能先把行李送到码头寄存,每天抱着儿子探监。然而上天似乎刻意安排好了剧本,一天,儿子大鹏突发高烧,蔡瑞月便留下儿子在家休息,不料船却在这一天起锚。蔡瑞月后来回忆道:“我很想跟着先生走,可是大鹏不在身边,我不能走。”仓皇之下,蔡瑞月丢了两只皮箱给丈夫,并叮嘱道:“要珍重身体,只要健康活着,总有一天会见面的。”这样一幅画面,和青年时代在日本被驱逐出境时的情境神似,似乎冥冥之中又一轮回,令雷石榆终生难忘,抛妇别雏,血泪余生……
重温旧梦
轮船驶离台湾,最终停在了香港。雷石榆一面在南方学院兼课,一面在《大公报》《文汇报》《星岛日报》等刊物上继续笔战,也始终不忘向华文世界的读者介绍台湾风情。他与蔡瑞月一度保持通信,本约好在香港团聚,不料妻子却受自己牵连,以“思想动摇”的罪名,在没有任何定罪文件的情况下被关进绿岛两年,出狱后也被严加监视。不久,因雷石榆转托友人带奶粉与夹克给幼子,甚至牵连妻兄受到严刑拷打。
同时,雷石榆身在香港也常有被迫害的不安全感。几经思量,他终于决定接受李何林的推荐,回到内地,在天津津沽大学(河北大学前身)任教。雷石榆肩挑中国现代文学、世界文学、文学概论、写作等多门课程,后半生一直致力于科研、教学与写作,过着相对安定的生活,却只能长久地与妻子分离。
骨肉分离是雷石榆毕生的痛楚,他尝试以文学的方式排解愁苦,每当有不知情者问起儿子,他都难以回答。1974年12月,雷石榆忽然收到台山老家的来信,原来当时在澳大利亚的独子雷大鹏,通过中国驻澳大使馆请求寻父。时隔二十余年,父子二人终于取得联系,雷石榆激动难眠,当晚连写七绝三首《喜闻吾儿寻父有感》。此后,受国际局势及政治形势的影响,父子俩时断时续地保持了多年联系,直到1988年才得以相见。
阔别四十余年的雷石榆和蔡瑞月,直到1990年才重聚。只是,白发苍苍,相逢不识,一切都隔着漫长的年代,隔着难以言说的历史以及无法跨越的鸿沟。雷石榆在五十岁那年已与张丽敏女士(雷石榆逝世后,张丽敏几乎将余生所有心血灌注到对雷石榆作品的整理、编译与研究当中)再婚,而蔡瑞月母子二人始终对雷石榆离开香港存有怨气,大家不能完全理解但尽量包容彼此。雷、蔡二人年岁已高,这是第一次重聚,但也是最后一次。
此外,雷石榆晚年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件大事,则是时隔五十年后再度访日,与诗友重聚。事情则要从20世纪30年代雷石榆与小熊秀雄往复唱和的明信片诗歌说起。
小熊秀雄在1940年英年早逝,但他的夫人小熊常子却怀揣着深沉的爱,在战火动荡中完好珍藏丈夫的诗稿长达近四十年,直到1976年才将这批“往复明信片”原稿交出整理,发表在《文艺》特大号上,在当时的日本文坛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此因缘际会下,雷石榆得以于1986年赴日。当年参与《诗精神》的同人,仅剩下新井彻的夫人后藤郁子一人,所谓“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不过如此。雷石榆拜祭了小熊夫妇之墓,他庄重地进行了扫墓祭礼,又展开《谒拜小熊秀雄夫妇墓》七绝诗稿,大声朗诵:“相依墓穴夫妻骨,知否重来战友声。”随后依照中国习俗,雷石榆将悼诗原稿点燃焚化,以期到达友人之灵。烟火缭绕升腾,在场的人们无不动容。
数天之后,雷石榆在日本东方学会组织的会议上,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自己所亲身经历的中日文化交流往事,在报告的结尾,和木岛始(他扮演小熊秀雄)合作朗读了《中日往复明信片诗集》开头部分:
两人在东京/成了厨师/把挤满行囊的/这个岛和/大陆的土产 /用世界的/大锅来烹调吧!
30年代的梦之旅,30年代的诗魂,多少往事又一一浮现在雷石榆的眼前。斗转星移,一切都变了,一切又都没变,而诗人还是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