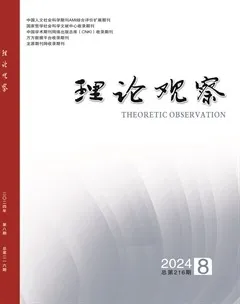数字资本逻辑下大学生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困境与出路
摘 要: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数字深刻塑造着人类社会。资本与数字技术共谋所产生的数字媒体平台,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演绎着数字资本逻辑。作为数字媒体上的活跃用户群体,部分大学生在数字资本逻辑影响下精神生活出现了失范现象。主要体现为主体性地位式微,精神生产、精神需求和精神交往发生异化。因此,实现数字资本逻辑下大学生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项重要议题。在阐述数字资本逻辑对大学生精神生活影响路径的基础上,本文从加强大学生丰富精神生活的意识自觉、改进新时代高校精神建设工作的宏观思路,以及推动数字媒体平台传播机制与内容创新等方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个体自由全面发展可以从增强大学生丰富精神生活的意识自觉、多元改进新时代高校精神建设工作的宏观思路、推动数字平台传播机制与内容创新等思路进行破解。
关键词:数字资本;大学生;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8 — 0152 — 05
当代大学生作为“Z世代”青年,是与互联网大数据和算法共同成长的群体,又称“数字土著”,其精神世界和行为模式深受数字技术的形塑。随着资本与数字技术的结合,产生了数字媒体平台。数字媒体平台为数字资本逻辑的演绎提供了绝佳的场景,而使用数字媒体平台的大学生用户群体则成为资本的目标之一。在数字资本搭建的“美好”精神图景下,三观仍在形成期的大学生难逃数字资本逻辑的精神布控。当代大学生虽普遍积极乐观、道德观念明确、理想信念坚定,但受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多元复杂社会思潮的浸染,表现出精神生活异化的现象。对此,应在剖析数字媒体平台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推导数字资本逻辑对大学生精神生活的深层影响,对大学生精神生活加以干涉和引导,使其扬弃资本逻辑,走向人本逻辑,推动全体大学生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一、数字资本逻辑下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异化
21世纪初,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逐渐密切,随着数字技术在世界范围和各行业的全面渗透,人类社会进入“大数据”时代,数字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资本与数字结合也催生出一种新型资本样态——数字资本。“数字资本”最早由美国学者丹·希勒于2001年提出,日本学者森健和日户浩之将“受数字化影响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定义”为“数字资本主义”,国内一些学者认为,“数字资本”即掌握数据的公司进行数据和流量生产的资本形式。笔者认为,数字资本是资本借助平台把大规模的私人数据占为己有,将数据作为“生产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剩余价值的创造和剥削的形式。
随着数字资本的介入,诸如快手、抖音、火山、哔哩哔哩等数字媒体平台迅速勃兴,资本借助大数据和算法重新塑造着整个人类社会,高度数字化成为年轻人生活的全新样态。据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10-29岁网民占比为28.4%[1]。青年网民中大部分为大学生,这一群体为了娱乐放松每天花费大量时间上网,出现了短视频成瘾现象。
相较于中小学生,大学生则是各大数字平台的主要受众,他们可自由支配时间,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渠道更多样,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数字技术探索世界。
数字带来的自由并非意味着现代大学生的精神生活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与解放,相反,是资本通过数字进行的新一轮精神殖民。数字资本逻辑下呈现的客观物质世界,对正处于育苗拔穗期的大学生产生着深刻影响,部分大学生精神生产、精神需要、精神交往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范现象,面临着严峻的精神异化危机。为此,需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地看待数字资本逻辑下个体的精神世界,破除精神危机的重重迷雾,使大学生的精神生活走向真正的自由与解放,实现大学生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一)数字资本逻辑下物质生产的异化
唯物史观指导我们在分析精神生活中人的异化时应先分析物质生产中人的异化。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创造财富,但财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使工人受其支配。数字时代,大学生使用各种数字媒体平台看似消磨时光,实则在为背后的资本进行数据生产,只是资本凭借数字技术将这种物质生产活动包装得更为隐秘了。此外,数据生产活动打破了从前固定的劳动时间限制,无形中加深了对人们的剥削。从诸如抖音短视频、微博、哔哩哔哩等企业新媒体平台的盈利模式分析,平台以半强制形式搜集用户的个人隐私、地理位置和使用偏好数据,并打包销售给广告商,从而赚取大量广告费。平台的这种盈利模式,从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视角分析,是“通过数字生产资料的采集占有、数字商品的生产流通,将数字资本积累的增殖链条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体系”[2]。除此之外,用户观看视频时点赞、评论、转发,以及付出的时间与精力实质上是无偿的数字劳动。异化劳动理论指出:“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3]也就是说,大学生用户使用平台的时长越长,付出的数字劳动就越多,产生异己的力量和为资本创造的财富就越大。因此,资本驱动的数字化看似打破了时空阻隔,为人类描绘了自由、民主的光明图景,但实质上它在与资本共同谋求现实的人的异化。
(二)精神生产的异化
数字资本逻辑下的物质生产异化导致大学生精神生产异化。马克思曾明确“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属于精神生产,且精神生产受物质生产的制约。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看,数字资本使人在物质生产中逐渐异化,那么,也不可避免地会使人的精神生产被异化。在自由与剥削合二为一的同时,资本主义也在对主体精神进行邀约,试图在人们的精神生产活动展开空前的布控。第一,目前,大学生热衷复刻内容空洞的爆款短视频。以大学生常用软件抖音为例,《2020抖音大学生数据报告》显示,抖音平台上的在校大学生用户超过2600万,占全国在校大学生总数的近80%,其发布视频播放量累计超过311万亿次[4]。其中不乏对搞笑类、颜值类大V短视频的模仿。从观看内容贫乏的精神产品到自我进行精神生产,再到影响身边同龄大学生,平台热度推送机制所导致的蝴蝶效应,会使大学生群体精神产出的异己力量越来越大。这也会间接导致部分大学生逐渐丧失思考辨别能力,纯粹跟风模仿流行视频内容,失去精神生产的创新与创造能力,成为单向度的人。第二,平台为使信息投放效率最大化,创设了开屏播放功能,用户打开软件便是正在播放的短视频,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个体在信息筛选上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大数据和算法程序会代替大学生作主观价值判断,使推送的信息内容逐渐同质化,把人们禁锢在牢固的信息茧房之中。数字资本正从多维度异化着大学生的精神生产活动。
(三)精神需要的异化
数字资本带来的西方社会思潮使大学生精神需要异化。人类社会历史被马克思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人的依赖关系”,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缺乏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5];第二阶段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的依赖关系”,人会形成多样的物质需要,进行普遍的物质交换,建立全面的关系;第三阶段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阶段,摆脱了“人”与“物”的束缚,个人的才能得到全面发挥。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更为丰富的物质生活也使精神生活更为自由,填补精神世界的选择也更自由与多样。但现如今,部分数字媒体平台充当了西方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思潮的扬声器,一些短视频与直播通过剧情设计、明星带货和销售话术传递消费信号,赋予商品符号价值,销蚀大学生的价值认同。部分大学生在数字媒体平台上受这些思潮的影响,获得物品的使用价值不再是其消费的终极目的,获得符号价值以彰显身份品位,获得精神上自我实现的满足才是其目的。大学生的精神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对立面,即客体,而这种客体又会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凌驾于主体之上,使某些大学生不惜借贷消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认为,虚假需求是消费异化的本质。在这里,数字资本所营造的假象导致人们精神需求异化,大学生为自我确证所追求的符号价值并不能满足真正的精神需求,满足的只是其虚荣、炫耀的心理需求。当商品符号价值主宰着大学生自我价值的满足程度时,那就意味着大学生的精神需要被物质所奴役,对物的依赖性逐渐加深,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服务于虚假的精神需要,主体为产生的对立面而劳动并走向异化的深处。
(四)精神交往的异化
数字资本搭建的社交平台会使大学生精神交往异化。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提出,人们“必定要在必然条件下来同他的同胞为伍”[6]。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精神交往与物质交往并存于交往行为之中。人类精神交往不只是信息的传递,更是思想的对话、情感的激荡。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体现在精神交往上,应为主体找寻到自我价值精神上的极大充盈与自由。在现代信息社会中,数字技术使大学生精神交往的形式更加丰富、交往场域更加广阔、交往对象间的互动更为频繁,但数字资本主义实质上赋予了大学生“假自由性”。第一,平台会通过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制造信息垄断,以用户偏好为指向,凭借信息的精准投放,满足主体的个性化精神交往诉求,以期达到增强用户黏性,收获“回报”的资本增值目的。第二,网络上拥有庞大粉丝群体的意见领袖,可能受背后资本利益链条的影响,通过发表某些言论刻意炒作话题,引起社交平台上的围观与争议,以期制造热度获得流量。大学生稍有不慎便会在资本主义制造的交往乱象下遭受蛊惑,失去交往理性。第三,大学生沉沦在数字媒体带来的数字化信息之中,对现实世界实践中的精神交往缺乏理性认识与参与。这会强化大学生群体在精神交往上的工具理性,而削弱其价值理性。在这种场景下,大学生的精神交往很难是自由的、解放的,他们受不良社会思潮审视,受所谓“意见领袖”所引导,最后,主体产生为自身的对立面,对自身精神交往产生怀疑。
二、数字资本介入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解读与实践价值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应从个体、社会、国家三个层面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论进行透视,理清数字资本介入的算法机制,为大学生摆脱数字资本逻辑提供现实思路。
(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来源
精神生活水平是衡量社会和个人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以往哲学家密切关注的话题。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最高实体,费尔巴哈把“精神”作为感性对象的附属。但费尔巴哈只看到了抽象的自然人,而马克思看到了人的社会属性。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强调了意识活动的重要性,对“精神生活”的理解进行了革命性变革。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征。”[7]人本质上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存在,即有精神生活的存在。所以,相较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丰富和解放对人的自由和解放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他所建构的精神生活是人在扬弃私有财产的基础之上,能够在与自然、他人的交互中实现自我确证,摆脱对物的片面占有和享受,主动追求自由、自觉的精神生活状态。马克思的精神生活思想为新时代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论和实践路径指明了方向。中国自古以来的仁人志士对人民的精神生活给予了极大关照,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中便蕴含着极高的精神修养,如周初构建的“敬德”“明德”的观念世界、传统义利观中的“以义为上”“以义取利”“义利相兼”的思想,无不是对资本逻辑中“利益至上”的超越。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8]“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9]唯物史观告诉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人的物质需要被逐渐满足后,需要的结构就会从单纯的物质需要变为全面需要,从作为动物的“即他们的本性”过渡到真正的人的需要。我国目前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在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目标的征程中,在丰富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论指导下,人民精神生活水平也亟须提高。
(二)数字资本介入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透视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个体、社会、国家层面呈现着不同的样态与要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在个体精神富足基础上全体人民精神世界的丰盈,它不是少数先富阶层和文化精英的特权,而是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多维层次的丰富。在个体层面,它体现为高水平的文化素养、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社会层面上,它体现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多样;在国家层面上,它体现为精神生活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全新人类文明形态的紧密结合。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在共同富裕理论基础上为回应时代需求而提出的宏大愿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表现,它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精神生活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相关理论研究。
而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要落实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要求,首先要厘清数字资本赖以生存的算法机制。一,在数字平台算法机制中的马太效应会导致优质内容的流失。算法会把转评赞数量高的内容推送给更多受众,这会间接抑制小众优质内容的推送,由此算法推送并不能满足所有大学生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实质上就是对大学生主体性的消解。如果数字平台的算法机制不加以改进,大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就会逐渐丧失。此外,被推送内容是否优质未经科学评判,是否能够提高用户精神生活水平更有待商榷。二,算法机制形成的信息茧房会使受众视野固化。传统媒体的传播机制会综合考量社会效益、价值观等因素,但现代算法机制为占据用户更多时间,会充分迎合受众喜好,使大学生用户群体接收的内容同质化趋势严重。长此以往,处在信息茧房中的用户间缺乏信息交流,形成认知差异的鸿沟,以及大学生创作内容的同质化。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肯定了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的作用,但在其他著作中也表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必然导致技术的异化,而技术异化必然会引起劳动的异化,最终会导致人的异化。由此,面对数字资本下算法机制的难题,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求大学生应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度的文化自觉,发挥主体性逃脱数字资本平台精心构筑的“算法牢笼”。
(三)大学生精神生活超越数字资本逻辑的现实需求
大学生群体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精神生活水平会对其家庭、社会产生辐射连带作用。对此,重视这一群体的精神生活质量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之路的必然要求,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从微观角度看,实现大学生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旨归在于实现大学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通过数字技术,把中华优秀文化和西方优秀文化等人类精神文明成果,以多样的形式展现出来,潜移默化地提高大学生精神生活水平,丰富大学生群体精神生活。从宏观角度看,实现大学生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助于构建中华民族集体的精神家园,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10]只有极大程度上丰富了精神财富,才会筑起精神的长城,帮助大学生抵御西方错误思潮的腐蚀和渗透,才能使中华民族朝着伟大复兴的目标进发。
三、数字资本逻辑下实现全体大学生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思路
数字时代背景下的资本触角无孔不入,大学生的三观仍处于塑造期,好奇心和求知欲也较为旺盛,应从大学生主体、高校,以及社会层面加以干涉和引导,使大学生扬弃资本逻辑,走向人本逻辑,推动全体大学生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一)增强大学生丰富精神生活的意识自觉
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从根本上要依靠个体的内生动力。因此,大学生在思想层面上要认识到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通过自我警醒、自主学习,在避免无批判意识的生产中不断提高个人精神生活水平。
第一,要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其精神需要。引导人们对隐藏于数字技术之后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高度警惕,提升辨别是非曲直的能力,使自身跳出符号化商品的泥淖。精神生活富裕程度非商品价值决定,而与认知水平、自由程度、创造力高低相关。要矫正大学生对自我价值实现方式的错误认知,厘清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帮助大学生形成对高质量精神生活的正确认知。
第二,引导大学生进行创造性精神生产。恩格斯认为,人的“正常状态是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而且是要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11]。当代年轻群体思维活跃、认知面广,极具创新、创造活力,其精神生产不应受资本所裹挟,而应依托优秀精神文化产品进行自觉主动创造,并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追求更丰富的精神成果,实现对精神世界的丰富与超越。
第三,促进构建多样的精神交往活动。面对越来越圈层化、垂直化、小众化的社交渠道,以及平台上主导风向的“意见领袖”,应引导大学生跳出精神交往固化的泥潭,把注意力投入到类型多样的精神活动中,发展多种爱好,提升个人综合能力与素养;坚定理想信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取向,博学慎思、明辨笃行,促进大学生进行健康积极的精神交往,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改进新时代高校精神建设工作的宏观思路
高校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是帮助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要阵地,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要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用好数字媒介,抢占数字高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青年学生的头脑,使大学生在面对错误思潮冲击时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
第一,推进构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论体系。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高校工作者应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现实需要对话与沟通能力。为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贴近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高校工作者应构建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论体系,将其融入思政课教学大纲,搭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论思想数据库,帮助大学生把握思想诉求,解决思想困境。
第二,提升精神建设权威队伍的媒介素养。要培养官方媒体工作者的政治敏锐性和宣传表达力,了解新媒体运营机制,掌握新媒体的使用技巧和发声规律,打造权威媒体新形态。为引导大学生正向精神交往,官方媒体要着力培育“意见领袖”,鼓励高校教师、专家学者在新媒体平台上撰文,让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网络舆情。让精神建设对大学生“实现从‘高势位’灌输到‘嵌入性’渗透的转变”[12]。
第三,树立大数据意识和算法思维。“数字化时代,大数据不只是技术工具,还可以作为价值观和方法论”[13]。为高效开展精神建设工作,需有效评估人们的思想动态,从大数据中筛选整合有价值的信息,以可视化方式呈现给高校工作者。不能停留于算法开发“数据模型”,更要从价值维度、认知维度、思想维度量化大学生的精神生活水平,并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策略。“数据模型”应严格保护大学生隐私,以促进全体大学生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终极目的。
(三)推动数字平台传播机制与内容创新
数字平台作为各种思潮汇集交锋与社会舆论产生的主要场域,是大学生获取社会新闻热点,接受各种舆论信息的首要渠道。应发挥数字传播的特点和规律,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传播场域。
第一,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数字平台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助新媒体话语体系,增强其对舆论的引领力。在数字平台为大学生开设专题板块,遴选优质内容丰富大学生精神生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剖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与西方错误思潮、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进行不懈斗争,使主流意识形态凭借生动易懂的网络话语,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认同产生正向引导,为推进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奠基。
第二,调节新媒体平台运营机制。面对开展播放功能对大学生选择权的剥夺,和灌输式推送机制对人的主体性的削弱,新媒体平台应明确权责边界,做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通过合理运用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既满足大学生对外部世界的探求欲,又能够提升大学生思想境界和精神生活水平,创造收益的同时造福人类社会精神建设。
第三,多元化精神文化产品。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生的精神需求指向更加丰富,优秀精神文化产品也应满足人们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激发人们的创新精神,解放思想,新媒体平台作为数字化精神文化产品产生的主要阵地,应结合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优秀精神成果,守正创新。应鼓励大学生投稿优质内容、生产优秀文化产品,合理引导其表达欲和表现欲,发挥新媒体传播样态与人们现实需求高度契合的优势,弘扬主旋律,增强优秀精神文化作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丰富大学生的精神生活。
〔参 考 文 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北京:CNNIC,2024:32.
[2]徐景一.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视角下的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批判[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11):133-14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91.
[4]2020抖音大学生数据报告[EB/OL].[2023-12-2].https://baike.baidu.com/item/2020抖音大学生数据报告/5594006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108.
[6]洛克.人类理解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26.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96.
[8]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2.
[9]习近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N].人民日报,2021-08-18(1).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23.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36.
[12]米华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204.
[13]董寰.寻找通往未来的钥匙[N].人民日报,2013-02-01(23).
〔责任编辑:丁 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