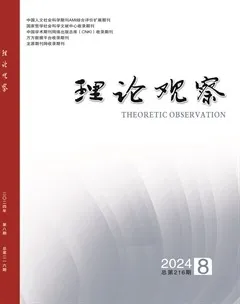法律实证主义与清末民初法制改革
摘 要:法律实证主义为十九世纪西方法律思潮产物。它为现代法律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科学实证的方法论,为现代法律构建了科学自洽的逻辑体系。自此,现代西方法律体系得以科学性。清末民初法制改革缘起于取消“领事裁判权”。因之,移植西方法律创制法典成为这一时期主要政治目标。改革期间,改革者竭力打破宗法等级制度之枷锁,为法律“祛魅”而引发“礼法之争”。立法者以“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为旨,全面开展民事习惯法调查。最终,他们形塑了科学自洽的法律逻辑体系。就此,清末民初法制改革得以科学性之关照,为中国法律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法律实证主义;科学性;祛魅;习惯调查;自洽性
中图分类号:D90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8 — 0131 — 08
清末民初法制改革主要通过法律移植的方式实现国家法制现代化,在此期间并未形成系统的实证主义思想。因此,学界鲜有以实证主义的立场分析研究清末民初法制改革之现代性特征。其实不然,实证主义是一种哲学立场,更是一种方法。它为现代法律发展提供了一套现实的、精确的、实用的法律体制。它动摇了旧有专制主义根基,通过对法律现象的科学归纳与推演,重构国家法律体制,打破了中国数千年的法制体系。
一、历史背景
(一)欧风美雨之催化
西方率先完成国家制度现代化改造,以殖民掠夺方式将其推行至东方。与此同时,清廷固步自封,对国家制度传统盲目自信。鸦片战争后,司法主权的丧失未警醒之。相反,清廷醉心于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器物文明,以求实现“同光中兴”。1865年,英人为达其自身在华商业利益提出了“借法兴利除弊”,清廷未以重视。中日甲午一战彻底击碎了这一幻想,清廷转而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是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过程,也是对西方先进文明冲击的回应。就统治者而言,西方先进文明或许是其拯救飘摇政权的救命稻草。在国人看来,西方因其先进文明而强盛,全盘西化后的日本复兴,无疑为中国人提供了“破局”现成方案。法律能成为改革的重要方面,是因其与国之政治、经济息息相关,是整个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同时,它也成为西方国家维护在华利益的重要途径。为达此目的,1902年中英条约英人抛出放弃治外法权之诱饵,实为以资本主义法律的方式为其殖民掠夺提供合法路径。
(二)社会内部矛盾
满清统治者将法律作为维系等级特权的工具,满汉民族矛盾加剧。统治阶级不断扩大政治、经济、司法的特权,主要表现如下:政治方面,少数民族统治者把持了军政要职,弱化汉族的政治权力。据统计,雍正至乾隆年间,首席大学士委任人选满人占四分之三,委任领衔军机大臣人选汉人只占三人。[1]官缺制度中明确分级,对中央级别的满蒙官职有缺,专有满蒙补足,“凡京堂而上,得用满洲缺,蒙古亦如之,内务府包衣亦如之。汉军司官而上,得用汉缺,京堂而上,兼得用满洲缺。满洲、蒙古无微员。宗室无外任”[2]。在经济上,士绅徭役优免,同时税负分类减免。在司法上,旗人犯罪专由宗人府、内务府慎刑司、理事厅等审理。在刑罚上,旗人犯“军、流、徒免发遣,分别枷号”[3]等等。
国贫民弱,任人宰割。从农业方面看,清末农耕地“只留下30%的耕地在余下的4亿人中分配。人口总数中60%到90%的人完全没有土地”,“无地农民必须将产出的50%用于支付地租,由于地租须转换成货币支付,又要多刮走地租的30%”[4],到了1851年人均耕地面积1.75亩[5],而在直隶望都县“每亩所获,岁约六斗,以人民之食料而论,每人所需日约一升,非有六亩之田,不足以一人之用”,使得有的农民迁移到别的地方开垦土地。道光二年,“浙江宁波、台州二府联界之南……无业游民借采扑为名,潜在私垦。现在十有八岙,计垦户二千四百有零,已垦田一万六千七百余亩”;有的将家庭手工业作为副业,英国对华贸易输入的调查结果发现“各农家的一切工作人,小的老的都去梳理棉花、纺织、织布;这种家庭制造的、重笨而结实的土布……中国人就用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把剩余的土布拿到近城去卖”[6]等。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侵入,加剧农民固有土地流失。同时,破坏了旧有农业生产模式,打击城市的工商业发展。“英国人,用武力夺得了五大商港中的自由贸易权,千百只英国和美国的运输船开到了中国区,而在很快的时期内,中国市场上就被充满了英国和美国的便宜的机器制造品。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竞争不过机器工业,于是稳固的中国就遇到了社会危机。赋税不复渊源而来,国家濒于破产于破产,大批居民落得一贫如洗,这些居民起而闹事”[7]。农民阶层遭受的压迫来自三方:统治阶级、帝国主义、地主阶级。
从商业方面看,秦汉以降,形成了重农抑商的政治传统和贱工轻商的社会心态。[8]这一传统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行业具有封闭性与地域性特征。清末,鸦片战争后,民族资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为自身之权益奔走呼告。郑观应认为“商”为“四民之殷”,主张“士有商则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有商则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则售其所作,而作益勤。商足以富国……”[9]。西方列强催生了中国资本主义之萌芽,1911年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总额较1895年增加了三倍。[10]随着中外贸易激增,民族资产阶级意欲挣脱于传统之束缚,积极投身于国家制度改革之中,寻求新时代的立身之本,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力军。
(三)中西法律冲突
资产阶级革命后,西方民商事法律发展已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即最大程度地实现个体权利为旨。它们所构建的民事商事法律体系也成为各国法律改革的范本。清末,中国国家法依旧以“出礼入刑”为原则,坚持德主刑辅的国家治理模式。国家立法中有关民商事法律几乎空白,习惯成为调整民商事关系的主要社会规范。随着英国新兴资产阶级打破以东印度中介的贸易传统,私商取代了国家垄断的贸易形式,华洋贸易量激增,华洋之间民商事纠纷数量激增,古代的民事习惯法之弊端显现。战争之前,华洋纠纷通过公行制度来缓解,即由政府通过外交的手段解决。战后,对于华洋商事纠纷则由会审制度主理。如,上海的华洋纠纷诉讼案,“占全国的十分之七、八”,当中由会审公廨管辖的案件又占十之八九。[11]1868年6月,上海英人魏金盛洋行诉华商单可一案,中西双方在买卖合同交易惯例不同,其中卖方对已卖出货物质量的责任承担问题。西方交易惯例是卖者必须对所售货物提供质量保证,而华商习惯是买卖双方无特殊协议,则卖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另外,中西双方对商事主体债务承担的方式不同。如,在中国,债务人有一个或者多个儿子,其子需承担清偿责任。其子辈清偿不能时,债务人的分家兄弟须承担清偿责任。西方,如若洋商发生倒欠而出现支付不能时,领事法庭则依据西方破产制度,承担有限责任,将财产按比例公摊给债权人。合同成立的条件不同,1900年10月,上海怡和洋行诉华商吴胜中案。[12]
中华法系已无法乘上现代巨轮,清末修律开启中国法律史的新篇章——法律现代化。清末修律意义深远,构建现代法律体系雏形为民初得以完善。时至今日,百年法治探索无不以此为鉴。它为中国法律现代化埋下了科学法律观的种子,贯穿始终的便是法律实证主义所开启的科学实证精神。
二、法律实证主义之推演
实证主义为人熟知的“社会进化论”促进了国家制度改革,以此作为诸多改革的理论支撑。从康有为到严复,再到孙中山都以此作为打破固守千年制度体系的理论基础。然而,“进步论”只能作为实证主义之理论之一,其核心是以科学实证方法寻找“秩序与进步”的社会规律,为此建立精确、实效的体系。法律实证主义对于法律现发展的意义:首先,法律“祛魅”,破除专制主义对国家法制主导,将实在法作为法律的渊源。其次,回归个体价值所需,通过对人类已形成的法律现象加以考证、整理、归纳及推演出适合个体存在的一般性规则,制度构建于此取材;最后,以科学方法构建逻辑自洽的法律体系,实现法律体系内部的自我证成。
(一)法律“祛魅”
韦伯曾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谜魅加以祛除的时代”[13]。何为祛魅?启蒙运动,人的理性被冠以世界主宰的光环。法律应受人之理性关照,受其掌控。那么,旧有法律所尊崇的传统习俗、宗教神灵、等级特权等理应得以消解。因此,“祛魅”是法律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自古法律集政治性与伦理性于一体,一方面它作为国家政治统治的工具,实现专制阶级的集权统治;另一方面,它作为维系社会伦理的强制力保障,以“礼法合一”作为法制构建基本逻辑。由此可见,传统法律之中是忽略了个体价值的存在。直至清末,随着法律政治化愈演愈烈,法律成为阶级利益的工具。在欧风美雨催化下,重塑法律价值势必成为国家改革的重心。
法制改革期间,法理派与礼教派就诉讼法和新刑律关乎纲常伦理之法条存留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史称“礼法之争”。双方争议的核心:新律是否坚持“礼法合一”。换言之,是否删除新刑律中的传统礼教法律条文,如“干名犯义”“犯罪存留养亲”“子孙违犯教令”等,以此打破古代以法律维系伦常秩序的传统。事实上,“礼法之争”是贯穿清末修律始终的,是有关法律指导思想的一场争论。法理派杨度基于国家主义之立场,反对以刑事法规的方式来维系家庭伦理。于邦华对杨度国家主义之说提出异议,指出“这个《新刑律》本是法律一种,这个法律替礼教的。礼教是主和平性质,全是以道德宗旨;法律不然,法律所讲的都是权利义务……要之刑法是刑法,礼教是礼教。”[14]而礼教派劳乃宣则认为“风俗者法律之母也,立法而不因其俗,其凿枘也必矣”[15]。
从清末修律成果来看,在《大清新刑律》刑律中不再单独制定破坏礼教伦理秩序的罪名,而将犯罪行为归入具体法益种类中。但在《暂行条例》中规定了对犯“第八十九条(危害乘舆、驾车者)、第一百零一条(内乱者)、第一百十条(外患者)、第一百十一条(外患罪)、第三百十二条(杀尊亲属者)、第三百十四条(伤害尊亲属者)”之罪,执行死刑的方式仍用斩刑;“第二百五十八条第一项、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二百六十一条至第二百六十三条之罪应处二等以上徒刑者,得因其情节仍处死刑”(即对亵渎祀及发掘坟墓罪);定无夫和奸罪;对尊亲属有犯不得适用正当防卫之例。新刑律中还删除原有刑律中对旗人的特殊规定,对旗人定罪与汉人“一体同科”。
辛亥革命后,经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争夺反清革命果实时期,军阀混战,动荡不安。他们将此社会变革等同于历史上的政权交替,为新“皇帝”头衔而前仆后继。民国初年,临时政府援用了《大清新刑律》,删除“侵犯皇室罪”12条,彻底祛除法律中的帝制色彩。同时,删除了《暂行章程》25条。北京政府将此定名为《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16]。这部刑律依旧保留了传统的伦常原则,比如,有关亲属相隐的观念被藏匿罪人及湮灭证据罪所吸收,以免除亲属刑事处罚为其特别规定;对尊亲属相犯的违法行为加重处罚。1914年,袁世凯为巩固其政权,制定了《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此条例是对旧有伦常、礼教秩序的回归,明确了三纲五常的等级制度。如,“行亲权之父或母,得因惩戒其子,请求法院施以六个月以下监禁处分”[17]与旧律“子孙违犯教令”无异。袁世凯为达其私利,提出了“礼教号召天下,重点胁服人心”。1914年“第一次刑法修正案”,袁世凯彻专设“侵犯大总统罪”,这是为其复辟帝制而备,彻底暴露其野心。但这部修正案随其复辟失败而胎死腹中。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废除了《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对当中的尊卑长幼亲属男女等级制度不予认同。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35年公布的《中华民国刑法》(以下简称《三五刑法》)中保留了民族传统的法律制度,是因根植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礼教传统无法即刻消除。但《三五刑法》中封建礼教内容得以进一步弱化,其主要表现如下:1.平等观念之推行,在法律适用上,实行男女平等。如,对于与人通奸之罪不再以“有夫之妇”为犯罪主体,而是以“有配偶者”为主体;2.不再专设“亲属相隐”及“尊亲属相反”的特殊罪名,而是通过加重、减轻或免除刑罚方式。《三五刑法》保留了中国重宗法等级和伦理亲情的传统,以期实现家庭伦理凝聚力的效果,回应本土现实之需。另一方面,纲常礼教不再作为国家刑法的主要核心价值,而是以罪刑等价原则、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对旧有以等级身份刑为主的刑罚体系进行变革。[18]
这一时期法制改革尝试剥离法律中的纲常伦理,这是其进步性。但人们对中国旧有法律传统的留恋,使法律又无法彻底摆脱礼教伦理秩序的桎梏。这种进步性与局限性的并存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这也说明,受现代性之引导,人们逐步意识法律“祛魅”的重要性,并通过科学实证方法对法律传统进行现代化调适,使其既符合本土国情又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
(二)对固有法律传统之实证考察
休谟将人的科学作为其他科学发展的“唯一牢固基础”,其必须建立在经验和观察之上的。[19]西方社会科学发展正是循此逻辑,从人类社会活动入手,以经验归纳与因果推论的方法,建立满足社会发展所需的逻辑体系。十九世纪,孔德集合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内涵,提出实证主义之学说,终结了经验科学与理性科学之争辩。他所提出的实证主义,注重个体发展的和谐性,促成其与群体的精神一致性。他认为实证主义应是精确的,要求其与“现象的性质相协调并符合我们真正所要求的精确度”并且是我们“智慧真正所能及的事物”,即真实存在的。那么,法律作为社会科学发展的一部分,同样被限定在现实存在的法律现象范围之内。对法律现象的整合与统一,是以实现人们对权利义务的认知与掌控为目的,从实现法律的价值。清末民初法制改革民间习惯调查,以实证之方式对本土社会规范的收集与归纳,据此制定的法律为人们所信服与遵守。沈家本、俞廉三认为:“人类通行之习惯,各因其它,苟反而行之,则必为人所摒斥而不相容。”[20]
中国自古并未有现代意义上的民商事规定,在国家律典中关于户婚、田土、钱债等规定,不再协调平等民商事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而是以维系伦理关系为前提的。民政部指出:“中国律例,民刑不分,而民法之称,见于尚书孔传。历代律文,户婚诸条,实近民法,然皆缺焉不完……”[21]清末新修民律以“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为编辑要旨。对此,清廷内部达成统一。张仁黼认为“凡民商法修订之始,皆当广为调查各省民情风俗所习为故常,而于法律不相违悖,且为法律所许者,即前条所谓不成文法,用为根据,加以制裁,而后能便民,此则编撰法典之要义也。”[22]张之洞认为“东西各国立法,可采者亦多。取其所长,补我所短,揆时度势,诚不可缓。然必须将中国民情风俗、法令源流,统筹熟计,然后量为变通,庶民官民惶惑,无所适从。外国法学家讲法律关系,亦必就政治、宗教、风俗、习惯、历史、地理,——考证,正为此也。”[23]
光绪三十三年,清廷批准在各省设立调查局,分为法制与统计两科,《各省调查局办事章程》规定由法制第一股负责调查“本省一切民情风俗并所属地方绅士办事与民事商事及诉讼事之各习惯、本省督抚权限内之各项单行法及行政规章、本省行政上之沿习及其利弊”[24],意义在于为宪政编查馆编订法律提供依据,“始免两相抵牾”。[25]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修订法律馆从宪政编查馆独立出来,十一月份,沈家本奏上的《修订法律馆办事章程》,规定馆中分设两科,各自负责民商律及诉讼律的调查起草工作。宣统二年(1910年),修订法律馆奏请朝廷派员分赴各地考察民事、商事习惯,并制定了《调查民事习惯章程十条》,拟定了《调查民事习惯问题》5编217条[26]。
清末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成果颇丰,内容详实。史料记载,清末民商事调查报告共计887册,其中民事共计823册,[27]当中大部分采取问答式。从现存调查报告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调查内容真实性可查。《广西民事习惯财产部报告书》中要求以习惯为主,“异同并录,美恶兼收”,“本编报告,不独土属区域,苗猺溪洞,调查不周,即各厅州县情形,亦详列互异,未敢虚饰,不免疏漏”[28]。修订法律馆对调查过程中所收集的婚书、合同、租券、借券、遗嘱等项,无论内容详细与否,都要求调查员各抄一份,汇寄本馆,以备观览[29]。第二,调查具有体系性,表现为两方面:其一,关于调查范围。其中民事习惯调查报告涉及全国除安徽以外的所有省区,商事报告涉及全国十一个重要商埠。[30]各个省在本区域范围之内又有细化,如广东省分为三级:村围为初级、都堡为二级、城镇为三级。逐级上报后汇总交至宪政编查馆。其二,关于调查内容。清末习惯调查中不仅就民商事关系而言,还包括各省行政、单行法规、诉讼等调查。如广东省规定对“诉讼事之习惯”“本省督抚权限内只各项单行法”“本省行政上之沿习”[31]等。对此类别再细化,如在民事习惯调查中,按照总则、物权、债权、亲属及继承分类,明确划分了财产权与身份权关系。如《湖南调查局调查民事习惯的各类问题》中划分了人事部十类,财产部十二类。[32]商事方面主要按照商主体与商业行为分类标准,进行系统的调查。
清末习惯法调查对国家立法的意义。《大清民律草案》第一条“民事本律所规定者,依习惯法;无习惯法者,依条理”。如,亲属法编纂理由:第一,欧美私法中采个人主义,中国则采家属主义。理由是“惟编纂一国法典者,须实际与理论兼顾,不得专以理论上之长短为长短”,而中国今日社会实际之情形为“一身以外,人人皆有家之观念存……现行于社会者既全然是家族制度,不是个人制度”。第二,中国与日本虽都采用家属制度,却又不同。“日本向来有家法无宗法,其宗即寓于家。寓宗于家者,凡继家之人即为继宗之人”。中国“宗法自宗法,家法自家法,嫡子未必尽为家长”,是故“中国继父母之家者,虽长子在,次子亦得与长子分继之。此中国宗自宗,家自家,承宗者须嫡长,继家者不以嫡长为限,宗祧与继家别无两事”。第三,亲属法采取中国家属制度,将亲属分为“宗亲、外亲及妻亲”,其中以“本律法所载丧服诸图一定亲属范围”。除此之外,确立家长权,即“家政统于家长”[33]。宗族内部的婚姻、立嗣或出嗣须经家长同意。当家族内部财产不分明时推定为家长财产。设立亲属会,其性质等同于旧时的宗族会议,只不过移植日本民法。“吾国习惯,家庭之内遇有重要事件则同族中及亲戚会议处以,但此不过为习惯上之事实,并非法律上之制裁。”[34]
民国七年,在全国设立了民商事习惯调查会,是因“审理民事及商事诉讼每苦无实体法规以为依据,恒用习惯为判案之帮助,有感于调查民商事习惯之关系重大,且足为修订民商法规之资料。”[35]。民初调查会由司法部主管,其主要设立在各省区的高级审判厅之内。同时,制定了会章、调查及编纂规则。[36]除此之外,民国政府推行司法试验区工作,是为推行新修司法制度。民国三十一年,国民政府分别在重庆璧山地方法院试行简化程序、设置司法助理员制度,主要包括:应依职权为公示送达;减少繁复之程序,以救济诉讼之拖累;增加当事人之便利等等。据此反馈,立法院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颁行了民刑诉讼法修正案[37]。这类试验意义在于以此推行新的司法理念与制度,考察民众对新的司法理念接受程度。这是新旧理念碰撞过程,以人们的真实体验来优化司法体制。
北洋政府时期,大理院以判例的形式对习惯法成立要件的确立,“酌采欧西法理,参照我国习惯,权衡折中”[38]。民国大理院第228号判例,对卑幼擅用财产条例作出解释:第一,卑幼私擅处分父兄之财产与处分他人财产相同,即不论相对人善意与否,为无效行为;第二,无论卑幼成年与否,母亲对其子所继承的财产有管理权。对于私擅处分者,其母有撤销权;第三,成年男子对其私有财产有处分权[39]。司法解释确立了成年男子对其私有财产的处分权。但卑幼对尊长财产和继承财产的处置权,均以尊长应允为前提,这与旧有习惯无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法制局认为“吾国旧制,累世同居,分子复杂,易启竞争之端,经济共同,尤长以来之性,弊害彰著,无待赘论”[40]。主张废除家制与宗祧制度。而有关亲属会的存废,立法院以“参考外国法制,斟酌吾国历来习惯及司法行政之现状”为原则提出保留。较之以往,这段时期的法律核心价值为“国家社会本位主义”。习惯法须以此为尺规,方可为立法所吸收,为司法所适用。
如前所述,清末民初以习惯法调查对法律全盘西化的修正,使其更为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需求。通过科学实证的方式,寻求适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法律发展路径。以此构建的法律体系是立足于中国现实的。期间,其必然是矛盾的过程,通过内部不断地调适来实现法律现代转型。
三、法律体系的逻辑重构
纵观各国法律发展,传统向现代之转型实为人治型向法治型转化。新的法律体系应更具科学性,否则它所维护的个体权利无法得到切实保障。个体权利的实现仅重视法律条文是不够的,还应将此理念贯穿于法律体系之中。于是,法律体系的自洽性成为法律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法律实证主义为此逻辑体系提供了科学方法论:一是,规范之间的纵向联结,对法律效力等级的规划。将法律限定在实在法范围之内,法之效力是源自其自身规范的等级创制,意及法律之所有产生效力是源于其自身所设定的规则体系;二是,规范之间的横向联结,旨在通过规划法律规范的类型,以求实现其精确、实用的规范效能。它们对规范进行分类,从法律所调整对象来划分部门法体系,以法律规定内容不同来区分实体法与程序法。实体法部分以确定权利义务为目标,实现法律精确性。程序法中则是以法律实效性为目标的,其可以是立法规则,或是行政规则,或是裁判规则等等。实证主义认为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是互动的关系,相互实现双方的价值。
(一)法律体系纵向逻辑
中国古代在固有的文化环境中孕育了中华法系,其主要特点是“礼法合一”,以“三纲五常”为逻辑构建从国家到家庭的伦理法规范体系。清末修律彻底打破了这种伦理法逻辑体系,法律自洽性自此得以重视。法律自洽性首先需要构建法律效力逻辑。较之以往,不同的是自洽性是以法律自身逻辑为其效力证成,不再渊源于神或者君主意志了。
法律体系的最高效力位阶——宪法。清末修律大臣认为宪制应“博采精取”,各国宪制分为“成于下者,始于君民之相争,而终于君民之相让”和“成于上者,必先制定国家统治之大权,而后赐予人们闻政之利益”两种模式,两者都以宪法与议院为关键。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为君民所共守,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当率循,不容踰越”。统治者最为青睐君主立宪制,是因其以“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主总揽统治权”为“最精致大义”[41]。1907年8月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宪纲中重申了君权至上的原则,君权之下的议会,官臣之权力皆不得与之相违。君主享有最高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拥有国家最高的统治权,如可设官员之制,由最高军制职权等等。宪纲将人民权利与义务首次纳入了国家根本法之中。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人民享有选举权,诉讼权、言论及出版自由权、集会及结社自由权、财产及住宅不受侵扰等权利,同时应承担纳税及服兵役、守法等义务。九月,资政院设立,其职责是决议国家预算、决算、税法及公债、新订法典及嗣后修改事件(不包含宪法)。第一场常年会议,议员们审查立法议案十个,其中包括《报律》《著作权律》、新刑律总则及分则部分等等。
宪法已成为法律体系的最高位阶,其他法律效力皆渊源于此。至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彻底告别历史舞台,其所维护的君主权力被法律加以限制,国家权力得以法律制衡。如,资政院的立法表决权;官制改革后中央各部门的行政规章,其中包括《民政部官制章程》《学部官制》《礼部职掌员缺》《陆军部官制》及《法部官制》等。
民初,从1912到1947年,正式颁布了两部宪法,其他都为宪法性文件,当中确立个体权利价值。但其不作为法律核心价值,直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法律的核心价值是“国家社会本位主义”,以及个人权利不得逾越国家社会之上。同时,宪法及宪法性文件中确立了立法权的独立。但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因时局动荡,政权交叠,立法权并未真正实现独立。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颁布《训政时期临时约法》中确立了宪法基本法,任何法律都不得与其抵触。此时,立法院的立法权才得以实行。1928至1947年间,国民政府在清末法制改革的基础上,完善了六法体系,完成中国法律近代化改造。
清末民初法制改革初步勾勒现代法律效力等级的雏形,但并未真正实现法律逻辑自证。究其内因,不外乎专制主义的残余作祟。期间,执政者意欲掌控立宪权实现政权永固。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宪法中确立立法权独立,但是又加以限制条件。如,《立法程序纲领》“立法院通过法律案,在国民政府未公布以前,中央政治会议认为有必要,得说明理由,法院复议,应依据修正,但同一议案之复议,以一次为限”[42]。事实上,清末民初,对于统治者而言,宪法仅仅作为实现政权统治的工具罢了,但并不影响后世实现法律逻辑自洽的决心。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便是以此为逻辑展开的。
(二)法律体系的横向逻辑
所谓横向逻辑,是以法律不同功能为逻辑来建构,以法律调整的对象所产生的功能为逻辑[43]。清末打破原有“诸法合体”的模式,法律部门分工更加细化,区分实体与程序、违法与犯罪、民事与商事等等。除此之外,各部门法内部按照各类法律行为的性质又作了明确的分工。以科学的方法构建实体法,使其更具实用性与精确性的现代法特征。
清末,首次以法律调整对象为分类修订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法、商法、诉讼法。1904年完成《钦定大清商律》,是法制改革过程中最早颁行的法律,随后聘请日本专家修订《大清商律草案》[44],民间商事团体自行订立《商法调查案》[45]。在官制改革后,1910年农工商部提出对《钦定大清商律》的修改,定名为《改订大清商律草案》[46]。1907年6月,民政部上奏请“速定民法”,称“查东西各国法律,有公法、私法之分。公法者,定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拟请伤下修律大臣斟酌中土人情政俗,参照各国政法,厘定民律,会同臣部奏准颁行,实为图治之要”[47]。十月始修订法律馆大量的翻译了国外的文献,聘请了日本专家松冈义正,调员江庸、王宠惠、丁士源、陈策、朱献文,派员调查各地民商事习惯[48],1911年奏呈《大清民律草案》[49]。
宣统二年(1910年)宪政编查馆认为“方今行政之病,由于职掌不清,以致权限不明,则整理之法,必先规定职掌,以明权限所在”。故此,以“各部现行职掌为经,以四级机关为纬,分别部居,列为简表”为体例制定《行政纲目》[50]。
清末,先后制定《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事诉讼草案》《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已具现代三大诉讼法体系的模式,分别调整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1906年9月,清廷制定《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对行政诉讼专门设置了裁判院,这部草案应是中国历史第一部行政诉讼法,其借鉴德、奥、日本之制,共21条。“掌裁判行政各官员办理违法致被控诉事件”即“民告官”,规定了受案范围(第9条)、回避制度、审判组织及审判程序等内容[51]。这部法律不是由专门的修律机关制定的,是附随官制改革而颁行的。
民初,进一步完善部门法体系。自1929至1931年先后颁布民法总则编、债权编、物权编、亲属编、继承编,合为民国时期的民法典。除此之外,颁行了单行的商事法规,《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船舶法》《保险法》等。自1928年至1935年颁行了《二八刑法》《三五刑法》两部刑法典。行政法发展分为:1928年至1931年,制定了《银行法》《农会法》《渔业法》等;1935年至1945年,制定了《行政执行法》《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公务员服务法》等。诉讼法,1928年颁行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1931年完成了第一部《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但是于1935年又拟定了新的民刑诉讼法[52]。
四、反思
实证主义开启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新篇章,它作为现代法制发展的基本方法论,为西方个人主义扫除障碍。为此,它构建了科学自洽的法律体系。本文以法律实证主义为视角分析清末民初法制改革的科学特征,以期回应当今学术研究的两个问题。
第一,近代法律改革是以科学方法实现中国法律传统的现代化转型。清末民初法制改革移植西方法律经验,形塑现代法律体系雏形。法律实证主义强调对现实的推演,通过科学的方法来构建适于社会发展的秩序体系。由此看来,清末民初法制改革并未真正脱离传统,相反,他们致力于现实完成法律之现代转变。
第二,法律实证主义之困境——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近代,西方道德遭受前所未有之危机。孔德认为道德就其主要部分“实际上都受到日益危险的侵害,以致于人的自然的公正与道德始终无法通过时间给予充分的修复”。道德失去了昔日的光环,它已沦为神权、君权、等级特权的工具。因此,法律实证主义科学方法是以实现法律与道德分离为目标。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将伦理道德为其立国之本,从家庭到国家都受此关照,国家法律体系更是以此展开逻辑建构。故而,这种根植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道德观在法律中是无法彻底根除的。
近代,个人主义兴起,人性得以解放。初期,法律道德的绝对分离,是人们对传统价值厌弃,以极端的方式与过去的告别。他们尝试用科学的方法实现法律的“价值无涉”。回归根本,人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是否真的能够做到价值无涉?答案是否定的。随着社会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科学僵化的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限制了权力,同时也限制了人的社会性发展。孔德认为“道德观点必然成为所有其他实证方面的科学纽带和逻辑调节器”,而实证主义在“今后所有及时化系统化的实际思辨会不断地尽可能促成道德的普遍优势”[53]。
〔参 考 文 献〕
[1]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6:289.
[2]钦定大清会典大清会典(卷七)[M].上海: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893.
[3]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91.
[4]徐中约.中国近代史[M].计秋风,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162.
[5]黄长义.人口压力与清中叶经济社会的病变[J].江汉论坛,2000(12):78.
[6]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M].上海:三联书店,1957:664、500.
[7]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恩格斯斯大林作译局.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43.
[8]马作武.清末法制变革思潮[M].甘肃: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91.
[9]郑观应.郑观应集(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593.
[10]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期(下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649.
[11]郝立舆.领事裁判权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46.
[12]蔡晓荣.晚清华洋商事纠纷之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5:125-126.
[13][德]马克斯.韦伯,钱永详,等,译.学术与政治[M].上海:三联出版社,2019:190.
[14]李启成,点校.资政院议场会议素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辩论实录[M].上海:三联出版社,2011:600.
[15]桐乡卢氏校刻.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M].台湾:文海出版社,1969:237.
[16]朱勇.中国法制通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498.
[17]郭卫,编.大理院判决例全书[M].吴宏耀,郭恒,点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398.
[18]朱勇.中国法制通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653.
[19][英]休谟.人性论(上册)[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7-8.
[20]李贵连.沈家本年谱长编[M].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313.
[21]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五)[M].张静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58:5682.
[22]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836.
[23]李贵连.沈家本年谱长编[M].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167.
[2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51.
[25]大清法规大全(卷六)[M].台北:考政出版社,1972:303.
[26]李贵连.沈家本年谱长编[M].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329.
[27]各省区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清册[J].司法公报.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926,(232):62.
[28]眭鸿明.清末民初民商事习惯调查之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52.
[29]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馆.大清新法令(第八卷)[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0:65.
[30]眭鸿明.清末民初民商事习惯调查之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5.
[31]眭鸿明.清末民初民商事习惯调查之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6-40.
[32]眭鸿明.清末民初民商事习惯调查之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75.
[33]杨立新,点校.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170.
[34]修订法律观编.法律草案汇编(上册)[M].北京:修订法律观司法公报出处,1926:68.
[35]转引眭鸿明.清末民初民商事习惯调查之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0.
[36]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编.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5.
[37]汪楫宝.民国司法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2-23.
[38]郭卫,编.大理院判决例全书[M].吴宏耀,郭恒,点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2.
[39]郭卫,编,吴宏耀,郭恒,点校.大理院判决例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398.
[40] 国民政府法制局.亲属编草案之说明[J].法律评论,1928(264):24-26.
[41]]怀效锋,主编.清末法制变革史料(下卷)[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89.
[42]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上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42.
[43]谢晖.论法律体系——一个文化视角[J].政法论丛,2004(03):6.
[44]怀效锋,主编.清末法制变革史料(下卷)[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337.
[45]任满军.晚清商事立法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7:134.
[46]怀效锋,主编.清末法制变革史料(下卷)[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150.
[47]朱寿朋,编,张静庐,点校.光绪朝东华录(五)[M].北京:中华书局,1958:5682-5683.
[48]张晋藩.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37.
[49]怀效锋,主编.清末法制变革史料(下卷)[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510.
[50]怀效锋,主编.清末法制变革史料(下卷)[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217.
[51]胡建淼,吴欢.中国行政诉讼法制百年变迁[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01):28.
[52]朱勇.中国法制通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612-617.
[53][法]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M].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0.
〔责任编辑:杨 赫〕